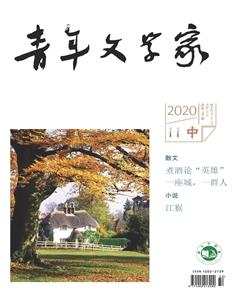试论叶芝《驶向拜占庭》中“拜占庭”符号的隐喻特征与象征意义
摘 要:著名的前期象征主义诗人叶芝在其《驶向拜占庭》一诗中,建构了“拜占庭”这一多义性的象征形象。在本诗中,拜占庭不仅是审美对象的复合象征、东方世界的奇幻想象,更连接了古典世界,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诗人在塑造拜占庭的形象时,对这一象征形象进行了唯美的处理,而历代文学批评家对于这一形象论说不一,都做出了自己独到的阐释。本文将试图阐释拜占庭这一符号的隐喻特征与多重象征意义,从而对诗歌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有整体的把握,并进一步管窥叶芝的生命哲学。
关键词:叶芝;象征;符号;拜占庭
作者简介:王尧(1999.7-),男,汉族,北京市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本科在读,专业:汉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2--02
一.引言
罗马帝国在灭亡五百年之后,它的文化遗产却并未湮灭,而是在东欧保留了下来。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古希腊与古罗马残存的遗产,在未来的数个世纪,成为了东欧重要的文化中心,起到了兴废继绝的作用,并独自点亮了黑暗的中古时代漫长的夜空。正如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中所引用的那首叙事诗所言:
你们的皇帝已经在许久之前抛弃了你,罗马,
你的荣耀和名号已经消失不见,去向了希腊……
如花绽放的拜占庭现在被认做是全新的罗马,
古老的罗马,道德衰颓,壁画脱落,是你的命运。[6]
如花绽放的拜占庭,因其深邃悠远的历史,梦幻灿烂的文明,自然也成为了爱尔兰诗人叶芝所中意的审美对象。对于欧洲文明的童年——古希腊的缅怀,是自18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母题。如《希腊古瓮颂》,《哀希腊》等。1927年6月,叶芝在都柏林图书馆阅读了天主教会所编撰的上古历史著作《历史之花朵》后,出于对逝去文明的缅怀,于次年即1928年创作了不朽的名篇《驶向拜占庭》,并于1930年创作了续诗《拜占庭》。而在《驶向拜占庭》这首诗中,对于拜占庭这一核心象征形象,叶芝对其进行了高度浓缩的加工,以其境界和情思的朦胧,内涵的多义性,给阅读受众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诚如叶芝本人所言,“诗歌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共情,只是因为它是象征主义的”。由此可见,象征主义,是叶芝衡量诗歌艺术水准高低的重要准绳。显然,象征主义诗歌力图规避外部描写的倾向,而是“向内转”。但是内心的情感与直观却需要外化才能获得丰满的具象。为了探寻“象征的森林”[3],将可感的物质与超验的内心相统一,叶芝一派诗人才广泛的运用暗示等手法,并且颇为强调诗歌的神秘性和音乐性。而象征符号的对象化,则是完成这一探寻过程的必要环节。正因如此,我们需要破解《驶向拜占庭》一诗中的核心象征符号,即“拜占庭”本身。而破解这一符号,需要通过对拜占庭这一象征形象本身加以阐释,并对其象征层进行剖析。
二.拜占庭的表层境界——光怪陆离的东方
1.异域风物的书写
叶芝在诗中,首先建构了奇幻绚烂的东方世界,并成为了拜占庭的第一重象征层。诗人运用怪诞华美的词汇,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异想天开、从未有过的意象。强烈的主观色彩常表现为意象复合的“通感”,往往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化平易为惊险、瑰丽,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瑰丽的异域风物,如圣火,镶嵌砖,金银器等,可谓奇崛险怪,风格独特。
对于东方异域文明的书写与想象,在浪漫主义勃兴的年代已然蔚然成风。如英国大诗人拜伦的《东方叙事诗》系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以及雪莱的《伊斯兰起义》、《麦布女王》等等。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而拜占庭,作为东欧与西亚文明的荟萃之地,自然也是异域文明叙事书写的不可多得的完美对象。拜占庭文明吸收了希臘、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多种文化内核,博采众长,文化多元。较之西欧人来说,是“他者”的哲学范畴,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情与神秘气息。在《驶向拜占庭》中,牧师们“立于神的圣火之中”,金鸟“在纯金的树枝上歌唱”[1]读来令人满口生香,使得审美主体不由得浸润在浓郁的异质神秘文化氛围之中。
2.审美主体的个人偏好
叶芝本人有着强烈的贵族情结,在他的认识中,只有贵族才有丰富的知识,与良好的教养,才能真正传承优秀的文化和艺术。然而,叶芝眼中的贵族并不是按照血统或物质财富来区别于平民的,而是精神上的贵族。正是这种贵族主义的倾向使得叶芝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以中世纪拜占庭王国为代表的贵族文明。在古罗马的奴隶制贵族制度崩溃,西欧进入军阀混战和封建割据的灰暗年代,拜占庭王国保存了古希腊文明的火种。
对于自己的祖国,叶芝具有着复杂的感情。在诗人看来,“道德败坏”是祖国的重要属性,而这种道德的丧失不仅由于英国人对爱尔兰社会长期的文化入侵,更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将爱尔兰人庸俗化,使得爱尔兰人失去了贵族精神。对于已是耄耋之年的诗人,古老的拜占庭与堕落的祖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占庭,象征着万世不朽的永恒力量。
正因如此,创作主体强烈的主观情感取向,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注入在这首诗歌之中。正如叶芝在其《诗与传统》一书中所言的那样:“祖国,我看清了你,所以新的象征物正在等待我的追寻”,“对于我来说,等待我的那个象征物,那就是拜占庭王国。[2]”
3.穿越时空的激情
自1453年拜占庭文明毁灭,至叶芝创作本诗的20世纪20年代,已是五百年有余。亡故的国家,到处可见的城迹,残留的石墙,不仅引起了诗人的怀古忧思。另一方面来说,爱尔兰孤悬北海,拜占庭则位于黑海之滨,可谓山川相阻,路途遥远,诗中的主人也只得“驶过汪洋和大海万顷”[1],方才得以一窥这座异域之都的风貌。时间与空间的双重距离,大大强化了诗歌风物的“他者”特征,也增强了诗歌整体的审美蕴藉。
诗人希冀抒发他的情感,然而在氤氲着这些情感的原型中提取素材,也就需要合成与其相切合的意象符号。正如卡西尔所言,“所有的文艺形式都是符号形式。[7]”诗人将历史现实的拜占庭抽象为意象符号,然而还需要加以还原成象征意义丰富的象征物,才能最终完成意象的建构与实现过程。因此,“拜占庭”所代表的同欧洲异质的东方世界镜像,只是这首象征意义浓郁的诗歌的表层意象。
三.拜占庭的深层境界——愿为金色的鸟儿
在表层意象之下流动着的,是叶芝所隐喻河暗示的深层次意象。
形象学理论家亨利·巴柔认为,“一切形象的生成,在于主客意识的分化,出现了‘本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本邦与‘异乡等等关系的对立之中[7]”。通过对拜占庭这一东方异国的书写,叶芝为自己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诗中建构的镜像世界中,年轻人“都迷恋于种种肉感的音乐,忽视了不朽的理性和杰作。”但“一个老年人不过是卑微的物品,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 [1]。灵与肉的对立,生与死的对立,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是西方文学史中永恒的主题。生命短暂如白驹过隙,青年时代沉溺于肉欲享乐,带来的却是老年后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空虚。面对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永恒归宿,诗人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解决方案。即是将灵与肉相分离,让灵魂脱离肉体的羁绊,在高贵的古典艺术品中追寻彼岸世界的永恒价值与精神自由。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金钱拜物教的统治一切,以及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的摧残,祖国爱尔兰的肮脏,天主教派别与新教派别的内斗,叶芝怅然中明白,在丑恶的现实社会“没有音乐院校诵吟古典的辉煌艺术品。[2]”于是,拜占庭,這一历史象征,被诗人化用作彼岸世界的寄托,那是一座永恒之都,有着金枝,金鸟,圣火,马赛克壁画的古典大城,是人类历代所有古典美的结晶。超脱于污浊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文化艺术所臻萃的伊甸园,只有崇高,典雅与圣洁。正如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所言:“艺术家表现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一旦艺术家掌握了操纵符号的本领,他所掌握的知识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个人经验的总和。[4]”这句话虽有所偏颇,但诗人叶芝在其创作中,正是以其对于人类普遍情感的真切把握,寄托于“拜占庭”这一唯美的符号,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人类至高美与至高纯洁的艺术画卷。
叶芝曾在《幻象》一诗中,对于历史的本质作出了独到的判断,即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而《驶向拜占庭》诗中的主人公,愿意“把我放在那金枝上作为一只金鸟歌吟,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是当今,唱给拜占庭的贵族和平民。[1]”流动的时间长河,在叶芝的笔下,围绕着拜占庭永恒循环,拜占庭代表着古典的世代,此岸的世代与彼岸的未来。而灵魂,只有融入拜占庭,才能不受生死的拘束,不惧时间的流动,永葆青春的容颜。正如叶芝在《老人临水自赏》中借老人之口写道:“凡美丽的终必漂走,如流水一般。”[1]写作《驶向拜占庭》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诗人,对着岁月的长河若有所思,希冀于自己的灵魂在拜占庭的不朽艺术中得到永生。
四.结语
符号学理论家卡西尔在《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一书中,对各种符号形式进行考察,并将它们放回到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而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的各种符号形式的形成,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成长的史诗。而在这些的形式中,语言能力和神话传说又是最为悠久的,它们是人类的思维能力与文明文化的滥觞,更是人同动物相区别的关键性标志。[5]”叶芝本人也曾在《温暖与安静的月光》中向我们倾诉,“我尽量使我的思维下沉到意识之下,从而与宇宙万物的精华融为一体,使其为我的创造力提供源泉,这种创造力来源于种族世世代代的文化烙印,而不在我个人;从这种暗流中,我们能够回溯到我们的先辈乃至始祖的那些动人的神话传说与民族史诗。[2]”
拜占庭,作为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国度,其所承载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原型,深深的潜藏在所有欧洲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而叶芝以其纯熟的象征主义手法,将这一文化原型赋予多重象征意义,解构了历史上那个真实存在的那个奴隶制东方王国,而是重构了富含隐喻特征的艺术天堂,使之成为人类最高灵魂的寄托之地,从而借诗中老人之口,将作者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思考与关怀予以表达。
在这首诗中,叶芝借灵魂的不朽以追求生命的永生,对年老肉体进行了决绝的摒弃,从而为富有浓郁人文主义色彩的生命哲学提供了坚实的内核。与同时代D.H.劳伦斯和T.S.艾略特等象征主义诗人对以死亡为中心的非个人化诗歌结构关注不同,叶芝为凡人“生命的完美”的实现,给出了自己肯定的回答。对于仍然无法解决生与死,灵与肉等矛盾的我们,同时又生活在后现代文明之中的我们,仍然具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袁可嘉(译).叶芝诗选[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2]王家新(译).叶芝文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查尔斯·查德维克.西方当代文艺批评译丛:象征主义[M].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4]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外文书局,1981.
[5]伊万·斯特伦斯基.二十世纪的四种神话理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6]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M].崇文书局,1991.
[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