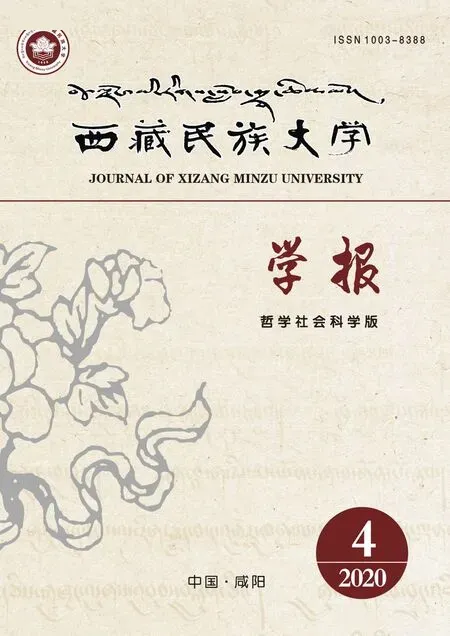“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的理路分析
——以西藏昌都地区“赔命金”为例
王亚妮,李志伟
(1.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 陕西咸阳712082;2.西藏昌都中级人民法院 西藏昌都854000)
“赔命金”产生于一个与世隔绝、无公权力存在或公权力薄弱、宗族势力强大的环境当中。“赔命金”并不是藏区所有藏民族普遍分享的习惯法,它只存在于偏远、公权力无力顾及的藏区部分地方,其中主要为西藏昌都及四川金沙江沿线藏族聚居区。①“赔命金”之所以系该地区藏民族的习惯法,在于它具有区别其他民族和地区民间人身损害赔偿法的主要特征。“赔命金”是民间自发通过赔偿财物来终结因杀人、伤害等暴力事件所引发的纷争的手段,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族势力之间无休止的复仇与械斗。
一、“赔命金”习惯法的缘起
“赔命金”习惯法产生具有独特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在西藏昌都,一提到“赔命金”,人们首先会想到昌都市贡觉县境内的三岩地区,②因为那里“赔命金”的风气历来最甚。《贡觉县志》对“赔命金”这一习惯法有详细的记载,它是指三岩地区“帕措”之间解决复仇和械斗的办法。“帕措”在藏语中,“帕”意为“父亲”,“措”有“团伙、部落”之意,“帕措”是指一个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群体[1](P940-948)。三岩为藏语音译,意为劣地或地势险恶,该地区山高岭峻、地势险恶、与世隔绝。历史上无论中央政府还是西藏地方政府都没有实现对三岩地区有效管理。因此,三岩地区的“帕措”势力特别强大。《武城县志》记载三岩“无酋长,以抢劫杀人为雄,历不属藏,亦未附汉”③。1917年,西藏地方政府控制昌都地区,恢复宗本制,贡觉、三岩分设两个宗。三岩宗驻地雄松乡(现昌都市贡觉县雄松乡)巴洛村,所派宗本也只是一年去一次,或派他人代行处理政务,收粮税,收完即离开,对百姓纠纷、困难不管不问[1](P286)。1954年,三岩宗解放委员会提到“自古以来到1910 年赵尔丰进军三岩止,三岩是几乎没有人管的地方,其名称为‘日格木黑龙巴’,藏语意思即是‘没有头人,没有王法’的地方,历史传下来的互相械斗、抢劫风气很严重。”[1](P931)
通过以上史料可知,历史上三岩地区是以“帕措”组织来维系的社会,在这个“无法无官”的地方,发生杀人、伤害等暴力事件,其主要解决途径有两种,一是无休止的复仇、械斗;二是通过赔偿财物以终结纷争。于是三岩地区民间在没有公权力的情况下自发选择通过“赔命金”方式终结双方的复仇、械斗纷争。一个“帕措”成员杀害或伤害另一个“帕措”成员,此“帕措”若想避免另一个“帕措”的复仇,此“帕措”全体成员就必须向另一个“帕措”支付一定数量的“赔命金”。《贡觉县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赔命金”的,而且“赔命金”是和“帕措”联系在一起的。昌都市其他县、区的地方志尚未发现有关“赔命金”的详细记载,由此可见,“赔命金”是三岩地区的独有习惯法。“与世隔绝”、“无法无官”、“帕措”宗族势力强大的地理、社会环境为“赔命金”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赔命金”产生之初并不是为了排斥公权力解决民间产生的杀人、伤害等暴力事件,而是在没有公权力或公权力非常薄弱的情况下,民间自发选择的一种解决纷争手段。这种解决纷争的手段经过民间的长期实践,久而久之,最终形成了普遍遵循的习惯法。
二、“赔命金”习惯法的地域解析
“赔命金”习惯法存在于藏民族民间社会当中,这一点毋庸置疑。“赔命金”是否属于青藏高原上所有藏民族共同认可的习惯法?已有的不少论著中想当然地认为“赔命金”是藏区所有地方的习惯法,或者至少会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实际上藏区广袤、地理环境多样复杂,这一习惯法并不是所有藏区普遍盛行。上文提到“赔命金”产生在一个“无法无官”的环境当中。由于昌都地理位置特殊,其地处偏远,境内山高谷深,与世隔绝。历史上,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西藏地方政府,他们的权力触角不可能延伸到偏远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造成人员重大伤亡的激烈纷争也是如此。1917 年,西藏噶厦政府控制昌都地区后,管理昌都28个宗,每个宗只有十几个地方政府官员。他们很难有效管理地域面积广阔的昌都地区,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去处理民间存在的大量纠纷,以至于“昌都总管时的司法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得不多。只知昌都总管无法庭,亦无专职法官”[2](P156)。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发生杀人、伤害等暴力事件,自发选择赔偿财物终结纷争就是必然选择。因此,“赔命金”在西藏昌都地区普遍存在,在西藏语境下,一提到“赔命金”,人们只会认为这是西藏昌都民间存在的习惯。
1995年4月13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发布的《关于坚决制止我区个别地区私自赔偿“赔命金”的通知》(以下简称《坚决制止“赔命金”通知》),[3](P519-521)该通知明确指出标题中的“个别地区”是西藏昌都地区和那曲地区个别县(两个地区接壤)。2002年7月26日,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关于严厉打击“赔命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定》(以下简称《严厉打击“赔命金”决定》),该决定历经2010年和2018年两次修订,其中都提到“我区少数偏远地方又相继出现了‘帕措’等封建宗族势力和少数僧尼操纵、参与‘赔命金’的违法犯罪活动”。而“帕措”这个群体主要分布在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芒康县及四川省白玉县、巴塘县等沿金沙江一带,历史上称为“三岩”的地区。以“帕措”这一词语描述宗族势力的基本上限于以上地方。通过国家机关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也可以印证,“赔命金”并不是藏区所有藏民族的习惯法。一个地区的习惯法肯定会以该地区为中心向外围扩散分布,扩散分布的边界相对较为模糊,也无法进行细致的考究。目前,有关研究“赔命金”的学术论文及论著实际上都是以历史上的“三岩”为背景的,即可认为“赔命金”主要地域范围与“帕措”群体分布区域一致。
三、“赔命金”习惯法的典型特征
一般而言,各个民族和地区在发生杀人、伤害等暴力事件后都会产生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也会以财物作为赔偿对象。昌都地区的“赔命金”与其他民族和地区民间人身损害赔偿法具有一定的区别。“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表现出来的。”[4](P29)根据相关刑事审判工作实践及其早期“赔命金”案例资料分析,昌都地区“赔命金”习惯法与其他民族和地区民间人身损害赔偿法相比较,表现出一些不同特征。
(一)“赔命金”是无须公权力介入的暴力纷争解决机制
“赔命金”是通过赔偿财物以终结双方的杀人、伤害等暴力纷争,而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任何一个人类文明能够从远古延续至今,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这个文明内部有终结无休止纷争的机制。“赔命金”就是西藏昌都地区民间自发产生的终结纷争的方式,西藏昌都部分民间发生杀人、伤害等暴力事件之所以通过“赔命金”来“私了”,它最初并不是为了排斥公权力的介入,而是根本没有公权力可依。一般而言,“帕措”之间发生争端时,可以依照习惯法向对方提出经济赔偿要求,如果对方同意,则事端平息。昌都法院曾经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前来法院为被告人求情,请求法院释放被告人,因为被告人家属已经赔偿了他不少财物,没有必要再判处被告人刑罚。这种现象反映了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也折射出“赔命金”在民间的思想观念里是可以终结双方纷争的。“赔命金”这一终结纷争的机制并不总是有效,也有被害方不愿意接受赔偿,或双方就赔偿达不成协议的情况,如此纷争就会长时间延续下去。如:《贡觉县志》记载,四川白玉县山岩乡“松果帕措”与“木勒帕措”从1939年一直打到1947年,双方损失惨重。
(二)“赔命金”存在的基础是复仇的强迫力量
习惯法并不会因为它是习惯就会得到民间自愿、自觉遵循,它具有强迫执行的力量。被害方家属获得赔命价之前,他们是以杀死加害方或其家属为要挟,强迫“赔命金”执行的力量是复仇观念。西藏昌都的复仇习俗甚浓,昌都相当一部分故意杀人刑事案件是报复行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2015 年共审理故意杀人案件共37 件,其中21 件就是报复杀人案件,足见昌都民间复仇观念的浓厚。1988年贡觉县敏都乡村民卓约赤某因经济纠纷将同乡村民次某伤害,被判刑。赤某出狱后于1990年将次某及其二个儿子并随同的两个同乡村民一同枪杀④。2011 年昌都市芒康县发生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两兄弟被同村另一个家族人员枪杀,对方支付被告人50多万元“赔命金”,被告人内心仍存不甘,一心想报复,最终履凶枪杀对方一人。2015 年,昌都市察雅县发生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件,被害方家族势力强大,不接受被告人家属的代为赔偿,经常公开扬言报复。被告人家属深恐对方报复,举家离开家乡,东躲西藏,离开时甚至没有来得及处理自己房内的财物和饲养的牲畜,直至现在也有家不敢回。一方因惧怕另一方报复,不得不离开家乡躲藏,在昌都并不是极个别现象。报复难以防范,则对加害方有长期的威慑。假如被害方宗族或家族势力强大,加害方承受的报复压力会更加巨大。为了换取被害方放弃复仇,赔偿被害方财物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可以说惧怕复仇是加害方“愿意”支付“赔命金”的重要原因。
(三)“赔命金”是原始的集体责任
一个“帕措”成员杀害或伤害另一个“帕措”成员,此“帕措”的全体成员就有共同的责任向另一个“帕措”支付一定数量的“赔命金”。“赔命金”一般不是由加害人独自一人负责赔偿,偿付比例中三分之一由肇事者承担,三分之二由“帕措”成员共同承担,也有依照经济状况承担的原则。接受赔偿也不是被害人个体,而是被害人所在的“帕措”集体,一般受偿比例的三分之二归受害人家属,三分之一由“帕措”成员平均分配。意即“赔命金”不是由被害人一人独占,而是在其所在的“帕措”中以一定的比例分配[2](P146)。被害人所在的“帕措”全体成员也有共同的责任保护本“帕措”成员的利益。在不存在“帕措”的地方,发生杀人、伤害案件,承担赔偿义务的是加害人所在的家庭,而不是加害人个人。因此,“赔命金”是集体责任而非现代法制的个体责任,在双方当事人的观念里是没有个体责任的。
四、“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考量
(一)西藏昌都地区“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现实关系
现代法制不允许被评价为刑事犯罪的案件当事人双方通过赔偿财物予以“私了”,这与当地“赔命金”习惯法产生了冲突。《坚决制止“赔命金”通知》和《严厉打击“赔命金”决定》两个规范性文件代表国家的立场对“赔命金”持严厉打击的态度,似乎“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会以激烈的方式在现实中呈现出来。事实上,2002年的《严厉打击“赔命金”决定》颁布施行后,2003-2013 年10年间贡觉县人民法院从未曾审理过一起打击“赔命金”的案件,这或许与两个规范性文件具体内容的规定本身有关系。首先,规范性文件对“赔命金”虽然持“严厉打击”的态度,但该规定实际上并不打击“赔命金”本身,而只是打击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要“赔命金”的行为,对于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没有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要“赔命金”的,两个规范性文件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其次,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通过贿买方式阻止作证或者帮助他人毁灭、伪造证据,亦或是帮助逃匿或做假证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既然没有规定对“赔命金”本身的具体处罚措施,执法机关也就没有什么法律依据严厉打击“赔命金”中的自愿提供帮助的行为。再次,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审判、检察、公安机关人员在受理刑事案件时,明确告知被害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被害方放弃民事赔偿权,索要“赔命金”的行为是违法的,一旦发生将依法制裁。但是,如果案件本身就没有进入诉讼程序,则附带民事赔偿也不可能实现,依法制裁的标准和程序也没有相关实施细则。最后,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对参与违法“赔命金”活动,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处罚。但实践中对于尚未出现治安管理处罚该种违法行为的状况。相关规范性文件固然对具体的事项作了规定,表达了对该种行为禁止的决定意义,但该种现象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规范的存在无法产生快速的效应。
事实上,支付“赔命金”是存在强制因素的。杀人、伤害等刑事案件发生后,由于复仇习俗的存在,加害方即时就能感到被害方复仇的压力,往往会“主动”想办法向对方支付“赔命金”,以换取对方放弃报复,而不需要对方采取明显的、表现在外的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要。既然“赔命金”是习惯法,那么当事人双方一般都会认同这一习惯法,加害方一般不会因为惧怕报复向国家机关报案,以逃避支付“赔命金”的责任。被害方一般也不会主动积极报案,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赔命金”案件的发现和证明就极其困难。加之执法力量有限,西藏一个县的辖区面积也很广阔,如昌都贡觉县,2003年县公安机关只有20多名公安人员,截至2019年,贡觉县公安机关在编人员和辅警达到400人左右,尽管工作人员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贡觉县的辖区面积达0.63万平方千米,这样一支执法力量几乎不可能及时发现、制止民间存在的“赔命金”案件。因此,现实中因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要“赔命金”而追究行为人敲诈勒索罪刑事责任的案件极其稀少。调查中仅在昌都地区普法办公室编印的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严厉打击“赔命金”决定》宣传册中记载一例,1998年,芒康县籍嘎某某、基某某因强行索要“赔命金”,被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刑罚。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下发《坚决制止“赔命金”通知》,1995-2000 年,昌都地区昌都县(现改为卡若区)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共184件[5](P377-380),没有一起是因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要“赔命金”而追究被告人敲诈勒索罪刑事责任的案件。2010-2015 年昌都地区11个基层法院共审理刑事案件917件,也没有一起是因采取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要“赔命金”而追究被告人敲诈勒索罪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说,“赔命金”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仅是停留在制度层面,在现实中的冲突并不是很激烈。
(二)“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关系的理性展望
“赔命金”习惯法不会因为国家对刑事案件处理权的垄断而在短时期内消失。昌都地区民间复仇观念还非常浓厚,由国家实施对加害人的刑罚,以实现正义,还不能得到具有浓重复仇观念的当地民间的完全认同。因此,发生杀人、伤害等刑事案件,加害方遭到被害方复仇的可能性仍是极大的。加害方为避免对方的报复,仍会依据习惯法支付对方“赔命金”。复仇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人们朴素的正义欲求无法通过公权力惩治犯罪而形成的。当公权力持续通过惩治犯罪来满足人们的正义诉求,人们就会慢慢放弃通过复仇这个代价大、风险高的实现正义手段。当复仇观念变淡,“赔命金”习惯法当中就少了强制的因素,“赔命金”就会演变为现代法制意义上的,以平等、自愿为基础的民事赔偿制度。
1、“赔命金”习惯法的现代化转型
西藏昌都解放以来,西藏地区的刑事法治得到一定的发展,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杀人、伤害等暴力刑事犯罪案件,已经很难遇到认为自己已经支付“赔命金”而不应被国家追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了。但是,这些被告人的亲属仍然会向对方支付“赔命金”,然后会要求法院大幅度的从宽判处,这与现代刑事法律、政策理念上基本一致的,即被告人积极赔偿或由其亲属代为赔偿被害方损失的,可从轻判处。现在刑事法律对人身损害赔偿数额是限制的,而对诉讼外的赔偿数额则不予干涉,而且诉讼外的赔偿情节也可以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依据,这与“赔命金”反而达成一定程序的契合。法院将被告人亲属支付“赔命金”的集体责任认定为“代为被告人赔偿”的个体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适度予以了承认。这样更为“赔命金”提供了一个宽容的环境,同时也为“赔命金”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共融找到契合,可以预见“赔命金”将会长期存在,但合理的方式是通过习惯法的转型来实现与现代刑事司法的共融。
2、“赔命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共生之路
“赔命金”经过民间长期实践,最终形成了普遍遵循的习惯法。习惯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会因为国家制定法的有力介入短时间消失。因此,在昌都地区的当下现实中对于杀人、伤害等暴力刑事犯罪案件,国家毫不妥协地追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行为人或其亲属双方仍会在诉讼外依据习惯法解决赔偿问题。国家对诉讼外解决“赔命金”的否定态度也仅仅是停留在制度屋面。受客观环境、执法力量等因素的限制,民间“赔命金”案件难以被发现,更由于当下刑事法律、政策的改变,诉讼外赔偿数额不受国家制定法的限制、赔偿损失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的依据。由此“赔命金”习惯法具有了存在的客观因素,司法实践中处理时可以结合本土资源及司法实践解决问题。尽可能的消减习惯法中弊端部分,吸收其理念中的合理成分。
首先,吸收“赔命价”习惯法程序并纳入官方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司法机关安排官方调解、确定赔偿,禁止任何形式的私了或者私下调解,与此同时,保障赔偿并不意味着不承担刑事责任,把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和民间追讨“命价”两个环节合并,即通过官方主导的方式,由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刑事谅解书,情节较轻的免于追究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适度减轻刑事责任。[6]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擅自追讨“命价”或者行为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的被害人补偿制度。“赔命金”习惯法能够存在的基础在于经济因素,即对受害者经济损失的补偿。经济损失中除用于被害者家庭成员的赡养辅助外,还有参与丧葬调和的亲友及其寺庙为死者念经超度亡灵之费用。藏民族普遍信仰佛教,为了使死者有一个好的来生,按照藏族的传统丧葬习俗,家庭丧事需要请活佛念经超度亡灵,做各项法事等,各种丧葬费用花费极高,“赔命金”很大部分用于丧葬费用。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这是现代刑事法治发展的需求,它能够发挥对被害人救助的功能,也是少数民族所谓“赔命金”习惯法的合理转化方式。
再次,树立和维护民族地区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主要是司法机关能够在实践中获得社会认同。“权威”既是规定性的,又是实践性的。规定性的权威是法律设定的,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专享,藏区司法机关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权来自于法律的授权,但权威认同的形成是实践性的。藏区司法机关权威认同有赖于自身服务能力、技术能力和理论能力的不断提高,以期使规定性的权威获得实践认可,实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成为藏区刑事法制中的唯一权威。[7]
[注 释]
①此处所指的藏族地区主要是指包括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地区、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这一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②历史上的三岩地区大致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贡觉县、芒康县,四川省白玉县、巴塘县等沿金沙江区域。
③《武城县志》根据刘赞廷家中藏稿复制,1960年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刘赞廷:河北河间人,清末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手下任职。武城县:1912年,赵尔丰攻克三岩后,在三岩设立“武城县”;1917年,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三岩,设立“三岩宗”,相当于现在县的建制。
④贡觉县的具体案件以及案例数据汇总资料主要来源于《贡觉县志》作者的实际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