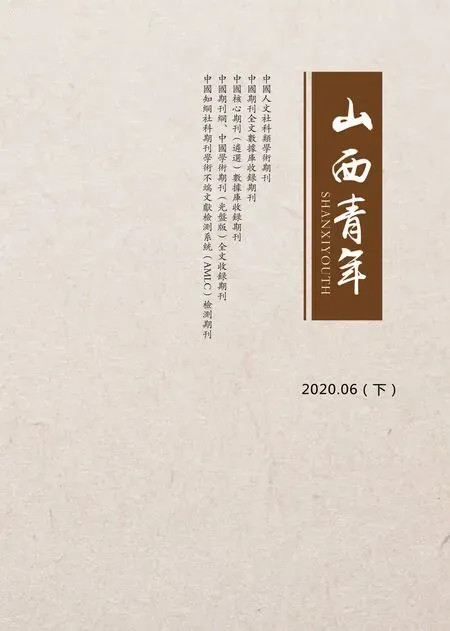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有感
王 霞
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41000
一、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自由的理解也会不同。
二、现代人的自由困境
(一)自由困境的内涵
弗洛姆将中世纪以前的人分为传统人。中世纪以前人们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稳定的生活和传统的文化,以及强烈的宗教信仰使得人与自然并未完全剥离开来。而自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人们萌生了个性和理性,开始慢慢成为独立的个体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弗洛姆认为现代人愈是割裂与自然、社会的联系愈是获得自由,就愈个体化。这种孤独感与恐惧感愈会使人放弃自由而选择被约束。因此我们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是逃避自由,放弃个性,使自己依附于集体或者一个外部的力量,沦为社会中可代替的复制品。要么就寻找一种积极的自由。既可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又可以与自然、社会建立自发性的联系,使我们克服孤独和对生命的怀疑,能够自由全面的发展。
(二)自由困境的成因分析
首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依附于土地,这种制度下使得人们的性格具有脆弱性。并且人们与外界交流甚少,在精神上很难解放思想。此外小农经济生产率低下,人们长期挣扎在贫困中,因此他们追求平稳,缺乏进取精神。在这种不安全感和无助下,人们会更容易逃避自由。
其次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局限性,无法带给人稳定感。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个人独自面对强大的上帝,不禁会有被击溃的感觉进而会彻底屈服以求得救。从心理角度讲,这种精神个人主义与经济个人主义并无太大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人完全形单影只,孤立面对强大的力量”。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人们容易丧失自主,随市场变化而随波逐流,个人的情感和行动都由市场决定,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
最后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虽然资本家与工人通过谈判得到了相对合理的工资,但这同样也使得剥削更加地隐秘和严重。飞速发展的科技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和相对稳定的生活使得人们消解了应有的独立性,没有了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人们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渐渐的归顺于资本家的统治中。其根源在于私有制决定了剥削的本质,不仅在物质上存在剥削,同样地,在精神上也存在剥削。资本主义制度实质上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去攥取更多的利益。他们用民主、自由、平等的外衣掩盖着社会分配的不公和物质财富占有严重的两级分化。弗洛姆的本意是人是核心、是根本、是最终的目标,而现在人却不断异化成为工具和手段。
三、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
(一)为现代人提供了追求自由的方法
弗洛姆提倡我们走向积极自由,即“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如何实现积极自由呢?弗洛姆的观点是在于自我实现、在于自发活动。自发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爱,一种是创造性的劳动。这种爱不仅仅是爱别人或者拥有别人的爱,而是在保留自我的基础上与他人、社会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爱。这种爱迸发出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活力。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仅要热爱自己的生活,做到人际关系的和谐,更要热爱整个社会,对事物保有好奇心和同理心。同时,创造性地去劳动——我们不是被利益驱动着工作,而是主动实现自己的价值。
(二)有利于塑造健全的人格,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
一个人的性格总是和他的成长经历离不开的。在家庭教育和学校环境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中,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家庭、学校、社会除了教导学生学习以外,更多的还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注重对他们的心理教育和心理疏导,这样才有利于个体健全的人格的形成,从而实现他们的自由发展,进而推动良好社会制度的构建。
(三)制度改革是个人追求自由的保障
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仅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个人的自由离不开国家及社会这个外部环境,也就是“母体”。因此,制度改革将是个人追求自由的保障。我们的政治制度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把人放在第一位,核心是人。经济上应更加注重生产资料和分配的社会化。文化上应该更加追求塑造健康的个性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这样人们将会更有能力承受外部的风雨,更加独立。
(四)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理论启示
除了制度、法律等外部约束力以外,也要加强对自我约束的追求。追求自由离不开心中的道德。越是自由的人,他的内心将会越有道德感。制度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但又反过来超出人自己的力量,支配着人。这种异化使得人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压制。而内心的道德约束力让我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从而使得人的尊严、责任和担当不会被破坏。心中的道德力量越强,那么对外界风险的抵御能力也越强,也就更能够成为独立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