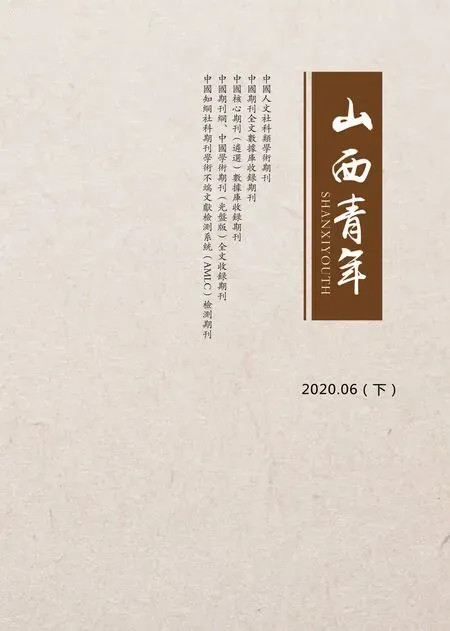对“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内涵”的思考
夏京超
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社会生活”与“实践”的概念
在西方哲学中,“社会生活”是相对于感性生活的理性生活的代名词。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通常将人与人的所有活动称为“社会生活”;在17、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发展的条件下产生了以形而上学为主的“生活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着重将“社会生活”描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动性,使得“社会生活”这个概念具有更为深刻的抽象性和高度的主观性,这也在认识论上使得这一概念进一步将自我意识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中各种物质生物的生产和再生活动”是马克思主义背景下“社会生活”的主要概念,从人的现实出发,将“社会生活”立足于现实根本来进行考察和分析,它涉及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维度,帮助我们深刻理解真实“社会生活”概念的现实意义和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理论基础,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了理性解释的基本立场。
关于“实践”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中“实践”被定义为“创生或改变人的社会关系”。古希腊智者学派认为社会关系的体系基础与社会制度是无真理性联系的,社会关系的创生在性质上也是相对主义的。基于相对创生主义,苏格拉底从研究人对社会价值的根基在哪里为入手点,得出理性是人对对象有一定认知的原因,在这里理性的发挥便是实践。但是马克思认为实践并不是发生在精神活动里,社会关系来自于生产运动,即革命。物质生产一方面生产物质的产品,另一方面产生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所以社会关系不是在宗教运动,也不是在科学运动中来的,而是在生产运动中即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
二、对当今“社会生活”和“实践”概念及内涵的思考
“社会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在旧的哲学语境中主要是以概念及逻辑化的方式存在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当中。“知识即美德”、“理性”等是古希腊时代人们对“社会生活”和“实践”概念的一般理解。在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社会生活”和“实践”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始终坚持实践与辩证的观点。就单单观念世界的改变并不能真正改造客观的物质世界,最终都要走向自我批判,所以“社会生活是自我批判的”。马克思哲学的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终方法是通过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实践”活动来改变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而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现制度变革,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
在高清海教授看来,人要回到社会生活的路径上就是要走出西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并且要确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从社会生活的实践出发,面向、深入、超越我们当今的社会现实生活。所以说,哲学在当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更应该以现代的眼光看待世界,更加关注“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此外,李文阁博士也在他的《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世界》中指出哲学与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分离是目前的哲学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庸俗主义、学术主义便是造成哲学与生活相脱节的最主要的两方面。
“实践”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内涵。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都是与人相关的问题,并且与人的实践相联系,所以都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已与传统哲学观点中的社会生活与实践的理解做了本质的区分,蕴含辩证法内涵的“实践观”是从抛弃抽象论证,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出发,引导人们根据认识—分析—反思—解决的步骤,辩证、理性的看待社会中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社会生活”的概念已经突破了旧哲学的思维,在哲学观以及认识论上实现了转向和变革。
三、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概念对我国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意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拥有人口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复杂交织的各种矛盾。在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中,如何解决这些会制约社会发展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观点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在我看来,“社会生活”及“实践”的观点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及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在“实践观”中所蕴含的自然、社会、人类自身和谐共存的三大理念,对我国“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的生态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进一步相融合提供了理论指导以及理论依据。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所有现实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去得到合理的解决。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社会生活”中以“实践”的方式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