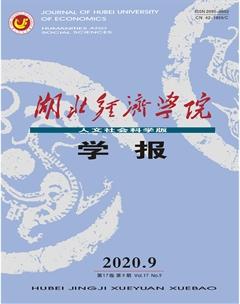安东妮亚:一位蕴含“双性同体”的新女性
苏博雅
摘要:“双性同体”是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突破了性别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达到女性主义的新境界。本文通过探讨双性同体在《我的安东妮亚》中的体现,从而说明双性同体有利于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僵化局面,促进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
关键词:双性同体;性别二元对立;和谐
一、简介
薇拉·凯瑟(1873-1947)是20世纪一位重要而又独具特色的女作家,她的题材清新隽永,文笔优美细腻。当代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妮亚·苏珊·拜厄特撰文认为“凯瑟和托妮·莫里森是第一流的美国女小说家,超过沃顿和斯陀夫人,凯瑟与诗人狄金森一样堪称一流,乃是因为她打造了一种艺术风格。”(拜特2001:151)她创作初期的“内布拉斯加系列”包括《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和《我的安东妮亚》(1918)三部小说,为她跻身优秀女作家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4岁时,安东妮亚随家人从波西米亚移民到内布拉斯加州。为了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一家人艰难地劳作,然而父亲因为思乡亲切和一系列挫折而选择了自杀。安东妮亚的哥哥(Ambrosch)能力有限,一人之力支撑不起全家,妹妹(Julka)年幼,弟弟(Marek)有智力障碍,从此,安东妮亚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变为家里的一根支柱。安东妮亚决定放弃学业,帮助哥哥分担责任。后经吉姆的祖母介绍,她到哈利家(Harlings)去做厨娘,后来为了捍卫自己跳舞的权利而辞职。安东妮亚在舞会上见到了一位列车员拉里·多诺万(Larry Donovan)并迅速坠入爱河,怀有其身孕的她最终被列车员抛弃。然而她并未就此而一蹶不振,而是更加坚强地努力生活。最后同一位同是波西米亚的异族男子结婚,他们生养了11个(文中说也可能10个)孩子,种植了果园,开垦了新地,过上了幸福而又愉快的生活。
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对《我的安东妮亚》的研究侧重于女性主义、女性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新批判主义、成长主题、文化回归、叙事学等角度,而很少有人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妮亚》。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妮亚》的硕士论文只有三篇,一般期刊一篇。虽然已有学者从“双性同体”的角度解读《我的安东妮亚》,但作者认为仍有从这个角度解读的空间,因此,本论文尝试从“双性同体”的角度来解读《我的安东妮亚》。
二、双性同体
双性同体(androgyny),也称雌雄同体,就词源来看,由希腊语andro(男性)和gyn(女性)组成。并非医学上表示雌雄同体的词“hermaphrodite”。1973年,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卡洛琳·郝贝兰(Carolyn Gold Heilbrun)出版了《朝向雙性同体的认识》(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一书,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双性同体。该书认为无论是在哲学、文学还是宗教中,双性同体应该是一种最完美的理想。其实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将人分为三类,即:女性、男性和双性同体,而双性同体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人。双性同体的理论在荣格的心理学说中早已有定论,他提到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阿尼玛是男性的女性特征,阿尼姆斯是女性的男性特征,每个人身上都有异性的某些特质。一个人保持平衡与和谐就“必须允许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因素在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中得到展现”。(冯川1987:53)弗吉尼亚·伍尔夫将这一思想引入女权批评,在她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一书中,她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性的头脑中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头脑中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是这两股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进行精神合作的时候。”(Woolf 1989:98)她引用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话“伟大的心灵都是双性同体的”,认为“艺术家应该是双性同体的”。在伍尔夫看来,莎士比亚、济慈、斯特恩、兰姆、柯勒律治等都是雌雄同体的。(Woolf1989:98)因此,伍尔夫指出:“任何人在写作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都是致命的,做一个纯粹的男性和女性也是致命的,只有大脑中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才能完成艺术创造。”(Woolf1989:103)同时伍尔夫意识到想要达到双性同体的难度以及双性同体的不确定性,因此说道:“要你们去找出来,去判断哪些值得保留”。(Woolf 1989:4)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托瑞·莫依(Toril Moi)运用法国批评家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的解构理论,认为她的双性同体说法其实是试图脱离早期狭隘的男女两性对立抗争的观点,反对二元对立的,“在强调两性相异性的同时,也强调两性的相通性。”(程锡麟2011:100)
作为女作家的凯瑟,内心矛盾重重,一方面羡慕莎士比亚、福楼拜等大师为代表的男性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她又感到社会对女性作家的不公,渴望追求并享有男女平等的权利。凯瑟的作品既不受男权文化的束缚,也不被绝对的女权意识所左右,她的作品《啊!拓荒者》、《云雀之歌》和《我的安东妮亚》中的女主人公都体现着“双性同体”的特征。《我的安东妮亚》一书以男性身份“吉姆”之口来讲述女主人公“安东妮亚”,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体现了凯瑟的“双性同体”愿望。本文认为双性同体有利于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僵化局面,促进两性之间的和谐相处。
三、“双性同体”特征在《我的安东妮亚》中的体现
(一)安东妮亚的男性特征
安东妮亚的父亲不忍思乡之苦与开垦新家园的种种挫折而饮弹自尽。安东妮亚伤心难过之余,深刻地意识到父亲死后自己肩上的重担,像男人一样干起了粗重的农活,她自豪地对吉姆说:“我现在能像男子汉那样干活了”(Cather 2005:85),尽管吉姆的祖母说她像个大男人,不秀气,但她说:“我就是喜欢像个男子汉”(cather 2005:94)。此时的安东妮亚已经不是刚来内布拉斯加州时的心境与行为了,安东妮亚此时的男性特质占了上风,并未被眼前艰难的处境所吓倒,而是尽全力担负起家里的重担,这是对男权社会男性担负养家职责的极端讽刺,表明她内心认同男性性别的价值取向。而祖母评价说她像大男人,不秀气也说明了当时社会上女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即使身为女性的祖母也被这样的男权社会所同化。后来,吉姆的祖母介绍安东妮亚到哈利家当厨娘,有一次安东妮亚到镇上跳舞,被哈林先生发现后下达了最后通牒:“你要么放弃跳舞,要么就另找下家,”(Cather 2005:140)。传统的父权制要求女性温顺恬静,贤良淑德,相夫教子,认为只有男性才可以追求自己的事业与兴趣爱好。被“消音”的女性根本没有发言权可言,男女地位极端不平等,而安东妮亚却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从未出现过“失声”的情况。面对自己的工作机会和跳舞的梦想,安东妮亚选择了后者,她并未表现出女性的唯唯诺诺,一味听从长辈的行为,而是说道:“那么,我走好了”(Cather 2005:141)这段话语不仅是女性对父权社会女性地位不公的反抗与控诉,也证明了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所体现出的男性特征,打破了传统性别二元对立的固定模式。传统婚姻观认为女性应该听从媒妁之言,然而安东妮亚竟然与一位拈花惹草的列车员拉里·多诺万(Larry Donovan)自由恋爱,并且在未婚先孕的情况下被对方抛弃,最后她只得回到家乡。波伏娃在她的书《第二性》中曾说过:“故事中总有一位单纯无知的女孩受到负心情人的欺骗,最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情节中必不可少地有家人和朋友的庇护,最后是堕胎,虽然可怕,但却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可行的办法”(波伏娃1972:470-471)。然而安东妮亚却非寻常女子,她选择回家生下孩子。当村里人得知她的事情后,闲言啐语不断,但是安东妮亚没有逃避抱怨,而是用她那瘦弱的肩膀辛勤地工作,勇敢地面对眼前的困难。“那年春天和夏天她都像个男帮工那样干活”“大家因为她勤快敬重她,都竭力像没出过什么事儿那样对待她。”(Cather 2005:214)她就像《红字》里的海斯特·白兰一样默默无闻毫无怨言地辛勤工作着,从而得到了大家的宽恕与谅解。“她谈论五谷和天气,好像她从来没有其它兴趣一样”(Cather2005:214)她俨然一位男性形象屹立在田野,完全不像只会操持家务的传统女性那样。她在田野干活一直到临产的当天,“她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就在那天她生下了那个孩子,她没有喊一个人,没有哼一声。”(Cather 2005:215)此时的安东妮亚身上的男性特征多于女性是因为她所面临的处境造成的,只有这样才能支撑她继续走下去。
正是她那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乐观精神吸引并鼓舞了她的丈夫安东·库扎克(Anton Cuzak),她的丈夫是个身材矮小的波西米亚族男子,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外形的男子是巧合吗?安东(Anton)是安东妮亚(Antonia)名字的一部分,作者以此来说明,男性并不总是强壮勇敢的代名词,男性也有脆弱无助的时候,安东对农事了解很少,而且经常打退堂鼓,安东妮亚对吉姆说:“如果不是因为我身强力壮的话,我们肯定捱不过去。”(Cather 2005:233)他们生了“恐怕有十个或十一个”孩子。(Cather 2005:224)面对柔弱胆怯的丈夫和生养密集的孩子,安东妮亚能做的就是拥有坚强的意志,像男性一样去田野劳作。传统的女性总是被描述成柔弱被动的形象,是男性保护和拯救的对象。这里的安东妮亚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垮,反而拯救了她的丈夫安东。小说中,安东这样一个男性人物也具备了女性气质,摒弃了男性霸权意识,转而拥有女性软弱,细腻的一面。
(二)安东妮亚的女性特征
然而,一个身强体壮、意志坚强的女性只拥有完全的男性意识,而忽略了女性温婉柔美的一面,那么世界上将只有男性(即使生理上是女性也是男性意识的女性),这是一种狭隘的女权主义思想,并不利于社会、人民的健康发展,这并不能构成健全的人格。凯瑟想要塑造的是一个不仅拥有男性特质还拥有女性特质的完美女性,因此凯瑟对安东妮亚的女性特征也进行了细腻的勾勒和渲染。安东妮亚的女性特质体现在她与自然的联系和适时地向男性示弱两方面。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自然与女性本身就有着隐喻意义。女性孕育子女的功能与自然生产万物的功能极为相似,因此常常有“大地母亲”之说。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特有的关心、爱护、体贴等特质对自然的修复与改善功能,反对男性中心论中男性对自然,女性的野蛮征服与占有。被列车员抛弃回到家乡后,安东妮亚没有放弃对贫瘠土地的开垦,而是将贫瘠的荒原变为了伊甸园般的果园。20多年后,吉姆再次回到内布拉斯加草原去看望安东妮亚时,他看到“整座果园就好像一只注满了阳光的酒杯,我们能闻到树上成熟的苹果。……挂满枝头,紫里透红,表面泛着一层薄薄的银光”。(Cather 2005:231)这是因为安东妮亚并不像父亲哥哥那样想要征服土地,而是怀着对土地深沉的爱细心呵护浇灌土地。安东妮亚懂得如何与自然为伴,与荒原融为一体和谐相处。她是草原女神,丰产女神,有着草原独特的庄严肃穆之美。《纽约时报》赞扬道:“凯瑟创作了一个新的神话,在这个神话里那种离开土地到城市打拼的传统美国英雄被一位对土地有深厚感情及崇敬土地上所有生命的丰产女神所替代。”(OBrein 1987:446)
安东妮亚在男性面前并不意味地强装坚强,她也有女性柔弱体贴的一面。安东妮亚的父亲自杀后,她伤心地一把抱住吉姆,吉姆深切地感到:“她紧靠着我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她的心在碎裂。”(Cather 2005:79)伤心不已的安东妮亚像个娇羞的小女孩一样借着吉姆的臂膀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内心的女性特质在吉姆面前展露出来。弗洛姆说:“我们必须永远记着,在每个人身上都混合着两类特征,只不过与‘他或‘她的性别相一致的性格特征更占多数而已。”(弗洛姆1988:259)父亲死后,安东妮亚经历一系列的挫折与磨难,男性特征始终占上风,支撑她坚强地生活下去,然而生下孩子后,她的女性特征展露无疑,母性的光芒熠熠闪光,她把婴儿的照片放在镀金的大镜框里挂在照相馆里展览。她未婚生下的孩子就好像她“结婚生的,从未为她感到丢脸。……安东妮亚是个天生的好妈妈”(Cather 2005:216)安东妮亚在后来和吉姆的交谈中说道:“自从我有了孩子,我就不想杀死任何东西。”(Cather 2005:233)面对软弱悲观的丈夫,她总是鼓励他,而且为丈夫一笑露出坚实的牙齿而自豪。除此之外,她还经常在外人面前夸奖自己的丈夫,“我男人以前在佛罗里达州的橘子园里干活,会嫁接果树。我们这一带没有哪一家的果园结得比我们好。”(cather 2005:231)在安东妮亚的心里,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是个能干的帮手,值得她骄傲并托付终身的好伴侣。西蒙·波伏娃认为,婚姻把两个独立的个体结合在一起,夫妻二人不应该被看成是脱离了外界社会的单独个体,丈夫和妻子都应该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两个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寻求自我的发展(波伏娃1972:470-471)安东喜欢喝酒,有时喝到半夜回家,可以说他是个“不安分的主儿”,但是安东妮亚尊重他的个人喜好,从不干涉,原本“寂寞得差点儿疯掉”(Cather 2005:249)的安东因为妻子体贴、善良、热情地把家收拾地妥妥帖帖而更加心系家庭。
(三)和谐的两性关系——安东妮亚的“双性同体”特征
孙绍先说:“女性既不应该继续作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型文化”。(孙绍先1987:130)文章首次介绍女主角是以安东妮亚(Antonia)的名字呈献给读者,随着吉姆与安东妮亚关系越来越熟络而唤其小名托尼(Tony)。安东妮亚是一个女性化的名字,而托尼却是一个男性化的名字,这两个名字附在一个人身上体现了此人的双性同体特征。
20多年后,当吉姆去看望安东妮亚时,她看到了安东妮亚经岁月洗礼后所具有的独特个人魅力。吉姆、安东和安东妮亚在田野散步时,吉姆发现“这两人相处得似乎很好,很愉快。显然,她是冲击力,他是矫正器。他们上坡的时候,他不断地斜着眼睛望她,看她是不是听懂了他的意思,或者她听到了有什么反应。”(cather 2005:243)两个人之所以能够相处的那么融洽,是因为彼此都能掌握好自己体内男性和女性特质的分量,女性体内的男性因素和男性体内的女性因素会随对方的增加而增强,减弱而减弱。一方面安东妮亚跳出了传统的男权社会的束缚,打破了传统的男性主导的桎梏;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位好母亲、好妻子把家里操持地妥妥帖帖、红红火火。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在安东妮亚身上灵活地转化,促进了家庭和谐稳步前进的步伐。“安东妮亚是女性传统的继承和延续者。她完全履行了一个女人所能担负的所有责任,其最终形象的神圣性暗示了女性美学对生命的蕴生和感召力。”(金莉2010:51-52)
当吉姆和安东妮亚穿过田野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文中写到:“太阳落下来,……月亮从东边升起……有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那么久,这两个发光体遥遥相对,停歇在世界相反的两端。”(Cather 2005:218-219)因着太阳月亮同时出现的这五分钟或十分钟,文中写到:“在这种奇异的光照下,每一棵小树……都挺得高高的,把自己突显出来……那种黄昏时分来自田野的庄严的魔力。”(Cather 2005:219)“在原始文化中,女性原则或厄洛斯以月亮为代表,男性原则或逻各斯则以太阳为代表。”(易小松2003:51)另外,月亮因其外形的变化周期与女性的月经周期极其相似,因此常常用来指代女性。代表女性的月亮与代表男性的太阳此刻同时出现,在太阳与月亮“合体”的片刻连植物也焕发了勃勃生机,可见“双性同体”的美妙,这正是凯瑟所倡导的理想的人格状态。
安东妮亚·苏珊·拜厄特这样评价薇拉·凯瑟,“她比任何作家都注意到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完整的、完成的。”(盛宁2001:152)安东妮亚在薇拉·凯瑟笔下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完美蜕变,她的人生既完满又完整。薇拉·凯瑟的墓志铭是引用《我的安东妮亚》的一句话:“这便是幸福,融于某个伟大完整的东西之中。”(金莉2010:52)可见凯瑟对这部作品的喜爱,安东尼娅的婚姻观、幸福感也是薇拉·凯瑟所推崇的吧。
四、结语
女性主义批评者认为“双陛同体”是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格,这反映了女陛在寻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历程中对和谐两性关系建立的憧憬和探索。男人和女人生来平等,传统的父权制阻碍了男女和谐相处的状态,而双性同体有利于打破性别二元对立的僵化局面。女性应该学会在困境面前坚强勇敢起来,男性并不需要时时刻刻保持坚强勇敢的形象,应该适当地学会释放内心被压抑的情绪。男女之间的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相互协调作用才有利于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安东妮亚兼具男性和女性特質,她既是位漂亮、体贴、温柔、热情的好女孩、好母亲和好妻子形象;又是位坚强、勇敢、独立、坚韧、有责任感的新时代女性形象。薇拉·凯瑟以敏锐的双眸、细腻的内心观察并感知着周围的女性,希望她们成为懂得两性和谐相处之道的完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