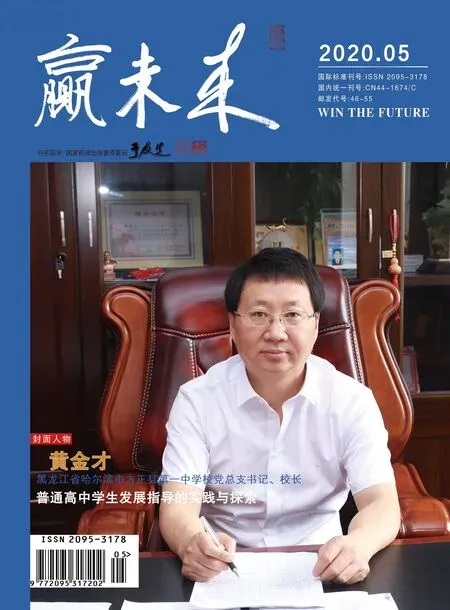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宠儿》解读
夏珺瑶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
《宠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非裔女性小说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文学界极大的关注。作品取材于美国《黑人之书》中一个著名讼案——玛格丽特•加纳案。在反抗《逃亡奴隶法》的斗争中,黑人女奴玛格丽特•加纳带着几个孩子逃离种植园,当奴隶主带人追到她的住处时,她抓起斧子砍断了小女儿的喉管,接着企图杀死其余几个孩子然后自杀,以免一家人再受无尽的折磨和奴役之苦。《宠儿》的创作源自对这一案件的改写。作品中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和自然意象,反映了作者对自然、女性、自我身份与种族身份的多重思考,抒发了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作者批判了白人男性构建的社会秩序所产生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呼吁重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男女平等、种族平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本文试图借助生态女性主义这一理论工具,通过分析《宠儿》中自然和女人、男人与女人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来实现文本对于现实的观照。
1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和自然的关系
1.1 自然观与女性命运
生态女性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名词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妮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陈世丹,167)她在该书中把生态思想和女性思想结合在一起,从女性主义立场和女性性别视角对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天然的联系,倡导消除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矛盾,推崇一种相互依赖的生态感知。
在《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第一代黑人妇女的典型代表。然而,奴隶主将贝比视为“他者”,没有对其负绝对责任。当奴隶主压迫她时,她越是反抗,就越受到更为惨痛的打击。尽管她始终在自然的怀抱之中,却选择封闭自我无视自然的存在。因此,贝比始终无法找到一种身份认同和心灵慰藉。
与贝比不同的是,主人公塞丝作为小说中第二代女性黑奴代表,始终和自然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关系。干活时,为了把丑恶剔除,塞丝会摘一些美丽的花草随身带着,以便能开心地干活;在结婚仪式上,她认为往头发里插点石竹花是特别必要的,会为她的生活增添新的动力;在逃跑的路上,在象征仁爱和自由的河边,她感觉自己身体里的羊水涌出来与河水汇聚,小船就像一个温暖的家。自然带给塞丝仁慈之爱与相互平等,让她享受到了人间的自由。她也把自己视作自然的女儿,从大自然中获得抚慰和支持。自然给予她的力量和勇气使她受到鼓励,决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争取精神独立。
1.2 女性与自然的联系
肯塔基农庄的黑人奴隶被禁锢于土地,这里虽叫“甜蜜之家”,实际上却是痛苦的深渊。黑人女奴像骡子一样无休止地工作,女人与土地之间的距离通过劳动得以拉近。“土地的生产与女人的生育之间存在神秘的类比关系”(波伏娃,16),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土地都扮演着人类养育者的角色。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和大地相似之处在于女性将所食之物转化为乳汁,以血肉之躯对儿女进行哺育,正如同大自然吸收日月之精华,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丰硕的物产,双方都承担着哺育人类,延续生命的天然使命。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必然联系,使二者在父权统治下所遭受的命运也是极为相似的:二者都处于同男性的“二元对立”,是男性眼中的“他者”。女性和自然都属于客体地位,被对象化,遭到了男性的利用和征服。女性被无限压榨与索取,正对应着自然被无穷尽地开发与掠夺。女性作为母亲惨遭虐待和压迫,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自然被无穷尽地开发与掠夺,环境遭到大面积的污染与破坏。在《宠儿》中,莫里森在热情赞颂自然给予黑人女性的温暖与庇护时,也强调自身的生态观念:人与自然是处于同一道德层面的,应该以爱、关怀和互惠为价值基础相互尊重,二者之间不应该存在二元对立,人类应当在自然中找寻自我。
2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和男性的关系
西方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在谈到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关系时指出,长期以来用男性作为定义和区分女性的参照物,决定了女性的附属地位:“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要把她看作另一种主体是不可能的。所以,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根据自身利益形成的、和男性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波伏娃,64)
美国南北战争胜利后,南方各州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大量黑人还是无法拥有土地。由于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黑人不得不留在种植园,依附土地所有者为生,被置于一个处处受控制、处处被压迫的境地,他们甚至被认为是低于人类这一物种的动物。在“甜蜜之家”时,“学校老师”曾带领学生用尺子测量塞丝,并记录下她的一言一行,告诉白人学生们,黑人奴隶只是拥有人形的动物。在奴隶主眼中,女奴只是扩展劳动力的工具,其作用是用来无条件交配生产出更多奴隶,奴隶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可以自由地进行买卖交换。
黑人不仅受到白人男性的奴役,黑人女性更是承受了黑人男性从白人那里“转嫁”来的压迫和愤怒。在《宠儿》中,塞丝一生经历了好几位黑人男性,但没有一个能够保护她免受外界伤害。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所有的男性都离开了她。哈雷•萨格斯是塞丝的第一任丈夫,他懦弱无能,自私冷漠。他在自己脸上涂抹黄油打算独自一人逃脱,弃妻子与孩子于不顾。奴隶制剥夺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权利,使其逆来顺受,而他自身的奴性使其不敢也不想去反抗。他没有勇气面对这一事实,从而选择离开这个家。保罗•D是塞丝的第二任丈夫,与塞丝认识已久。他将塞丝视为满足性欲的工具。他和塞丝搬到蓝石路124号,遇上了年轻漂亮的鬼魂“宠儿”。当宠儿试图引诱他时,他便沦落在了“温柔乡”,和宠儿越走越近,渐渐疏远塞丝。最终,塞丝的杀婴行为成为了压倒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无法与这样的塞丝开启新生活,最终也选择离开了这个家。塞丝的两个儿子也知道宠儿不是别人而是他们死去的妹妹的鬼魂,他们害怕这个鬼魂回来复仇,同时认为母亲总有一天会把他们也杀了。两个孩子决然地逃离这个家,不知当时母亲的杀婴行为是为了避免让自己的孩子重蹈奴役的命运。男人们的离开摧毁了塞丝最后的希望,她建立新家的梦想彻底破灭。塞丝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囚禁自己的内心。她原本和自然亲近,现在便和自然脱离开来,无助地面对着这个鬼魂缠绕的家。
3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人类与自然
黑人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逐渐丢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对自我文化的否定和排斥,导致黑人放弃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转而追逐“先进”和“优越”的白人文化。在《宠儿》中,作者揭示了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所遭受的精神迫害,以及黑人文化的流失与自身价值的否定带给黑人家庭的苦难。
莫里森认为在文化生态园中,应该也必须存有多元文化。因此,她把黑人口头文学、黑人音乐、黑人土语、布道和宗教仪式等有机融合到自己的创作中,强调只有对黑人文化的接受、保存和发展才能促进美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繁荣与多元。
《宠儿》中,塞丝与社区的联系总是体现在黑人的集体歌唱、舞蹈和宗教仪式中。黑人通过集体音乐和舞蹈,以一种疯狂的状态表达自己内心的热情和虔诚,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发泄后获得精神上的重生,强化了他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黑人之间心心相惜,有助于形成民族身份认同;黑人与自然之间休戚与共,有助于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4 结语
芭芭拉•克瑞斯蒂安指出,在当代美国小说家当中,很少有人像莫里森这位黑人女性作家那样,在作品中赋予自然如此重要的意义。托妮•莫里森从环境和性别的双重视角出发对自然和女性、男性和女性及人类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展开探索。她把“自然”和“女性”从人们遗忘的角落重新推向前台,从“缺席”变为“在场”。莫里森在《宠儿》中不仅揭露自然和女性受到了“父权制”的奴役与压迫,更为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价值观——只有当男性、白人、人类将女性、黑人和自然视为“自我”而不是“他者”时,一个和平、美好、博爱的世界才有可能实现。从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莫里森的《宠儿》兼具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这不仅是对文学批评前沿领域的一次合理尝试,也为推动构建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借鉴和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