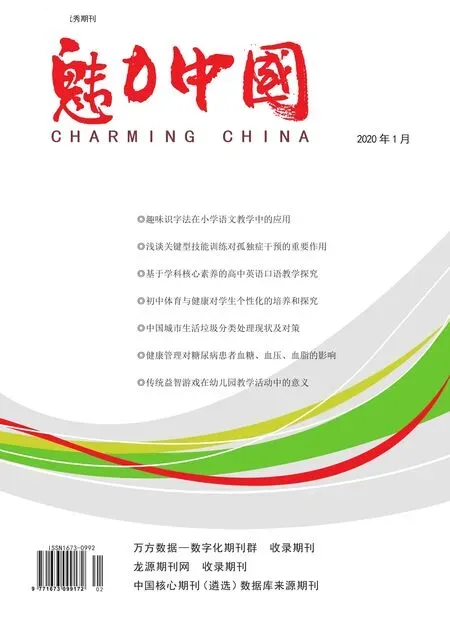梓潼木版年画在文昌文化语境中的建构
欧阳铭骏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一、梓潼木版年画概述
梓潼木版年画因其主要分布在梓潼县境内及周边地区而得名,是指产生并流传于文昌帝乡绵阳市梓潼县境内及周边县、市、区的一种反映农耕历史时期精神文化媒介的传统艺术。梓潼年画线条流动稳健、工丽古朴,画面圆润雅致,设色少但色彩厚重,且颇具节奏感,总体风格简约、质朴,主要以在梓潼地区流传的文昌神话及当地的民间故事为主。
二、文昌文化的内涵
文昌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包括文昌经诰、诗文、戏剧、音乐、医经、建筑、雕塑等,还包括了文昌绘画,即:文昌雕版木刻画、壁画等。本文笔者主要以文昌木刻画、年画为主进行分析其在文昌文化语境中的建构。文昌木刻画、年画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其已有1000多年历史,存世数量也较多,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存于七曲山大庙文物室的刻板数量居多,其用笔流畅,工艺精细举世闻名;其二是梓潼年画,其线条刀法稳健、工丽古朴,画面圆润浑厚,雅致且颇具节奏感,总体风格古朴简洁;其三是文昌剪纸,文昌剪纸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这三类传统工艺美术均具有其它地方画种不可替代的主题特征,均以《文昌帝君阴骘文》的内容为表现依据,用梓潼木版年画等形式劝人行善积德,必将得到善报的古代“天命论”思想的表现,共同构建了博大精深的“广行阴骘,上格苍穹”的文昌文化体系。
三、梓潼木版年画在文昌文化语境中的建构
建构一词是对英文“tectonic”的中文翻译。在西方,如德国、意大利、希腊和美国等,“tectonic”一词历经产生、发展和变化,它强调建造的过程,注重技术、结构、材料和表现形式等。本文所述梓潼木版年画在文昌文化语境中的建构是指木版年画在文昌文化体系构成中构成的逻辑表现形式,在对文昌文化体系的研究、社会科学和艺术批评上的作用,使读者可以运用一个解析的脉络,去拆解梓潼木版年画在文昌文化语境背后的因由和意识形态,从而找到发展的系统。在梓潼木版年画的发展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当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更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举措,多方面努力,促进其对文昌文化体系构建的积极作用,可从利用“互联网+”模式等四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充分利用“互联网+”模式去推动,实现开放、共享。梓潼木版年画的发展和传承,需要艺术家和文创设计师的广泛参与,这就需要有一个以梓潼文昌木版年画为主题的共享平台,让更多的艺术家和设计都参与进来进行文昌文化主题的艺术再创作,同时对梓潼木版年画的内容,也需要进行甄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第二,梓潼木版年画的创作与推广,要贴近新时代,新生活,不仅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不仅要注重形式,更要注重内容和内涵。第三,梓潼木版年画的传承,要从文昌文化的理论体系和艺术内涵中去提取创作元素,以市场发展的实际结合文化创新的理念,以文创设计公司或者“非遗”传习所的形式进行。第四,梓潼木版年画的推广,要借助于信息技术的手段,用喜闻乐见的形式,把一些精彩的制作影像和传承人的口述史保存下来,让更多的公众和专家参与进来了解和研究。在梓潼木版年画的传承过程中,要加强宣传力度,也要创新宣传方式,不能仅仅靠过去的传统宣传,如图书出版、报纸杂志,包括现在的电视等媒体,还应该用新的传播手段和形式来传播。比如说大家普遍使用的微信、抖音、博客、自媒体等,也可以采用VR技术将梓潼木版年画虚拟化呈现,达到跨越时空的艺术体验。目前,对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像梓潼木版年画这样古朴的艺术作品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探讨梓潼木版年画对文昌文化语境建构的积极作用时,要注重通过多种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传播和传承传统文化,使得传统文化的普及面和接受面更广泛。此外,还可以邀请一些梓潼木版年画创作人才,如相关领域的画家、书法家、篆刻家、设计师等,把他们关于梓潼木版年画创作中的思想观念、论文著作、艺术作品、文创产品等进行集中的整理和解析,通过不同的传播媒体,系列化、品牌化的推向社会,让大众认识到梓潼木版年画的内涵和重要地位。
四、结束语
在推动梓潼木版年画对文昌文化语境的建构视野下,也存在一定困难与挑战。例如,对其本身的文化艺术形式的讲解,就存在众说纷纭的问题;存在着注重形式、忽视内容的问题;也存在着曲高和寡的问题。因此要在梓潼木版年画的传承过程中注重避免其出现碎片化、平面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在继承和传播过程中坚定不移地保持足够的文化自觉与自信,要充分发挥传统手工艺者的积极性,勇于担当,发挥优势,选好切入点,踏踏实实以“工匠精神”为指导,为梓潼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创新做出贡献,为促进文昌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奠定基础。
——梓潼县文学创作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