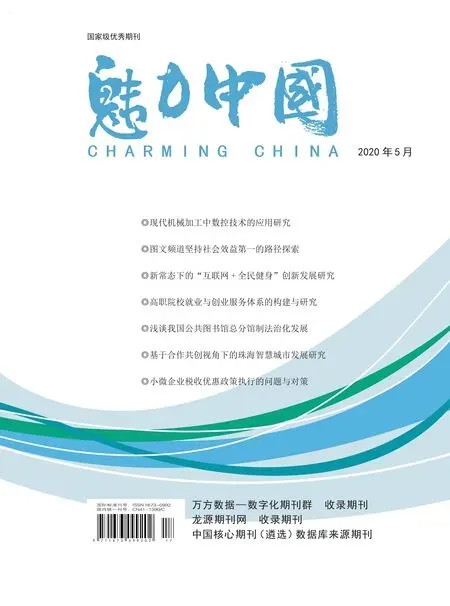基于网红现象对新媒体“浅薄化”倾向的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网红”即网络红人,是指在现实或者网络生活中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而被网民关注从而走红的人或长期持续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的人。他们的走红皆因为自身的某种特质在网络作用下被放大,与网民的审美、审丑、娱乐、刺激、偷窥、臆想、品味以及看客等心理相契合,有意或无意间受到网络世界的追捧,成为“网络红人”。“网红”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新媒体平台。“新媒体”,美国CE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即NTSC 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戈尔德马克(P.Goldmark)是“新媒体”概念的首创者。他在1967 年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C 电子录像(ElectronicVideoRecording)商品的计划中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New Media)一词。1969 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委会主席E.罗斯托(E.Rostow)在提交尼克松总统的报告(即著名的“罗斯托报告”)中更是多处使用了“新媒体”概念。由此,“新媒体”一词风行美国并很快蔓延欧洲,不久以后便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新名词。①“化”在现代汉语中意味着转变,或者是将某种事物普遍推广,所谓“新媒体的浅薄化”意味着新媒体正在逐渐走向“浅薄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网红在网络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他们自己的特定受众群体,作为新媒体平台重要的内容生产者,部分构成了整体,他们所生产的内容反映了媒体平台的整体风貌,体现了新媒体的倾向。
一、“网红现象”在新媒体中的具体表现
网红赖之生存的是关注度,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过气,不能再产生号召力和经济效益。在微博、抖音以及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上,网红打广告收费的价格就基于粉丝数量,还有些网红对发布的内容设置收费观看,直接地将流量变现,从中获利,经济利益驱动网红行为,网红们便费劲心思对自己的传播内容进行构思和策划,迎合受众的需要,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内容生产者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热度,吸引受众的眼球,在新媒体平台各显神通。用户喜欢什么他们就生产什么,有的靠实力获得网友的认可,但是更多的网红是靠着无营养的照片、段子或者短视频走红,而且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看,能在短时间内快速产生大范围影响的主要是迎合受众病态审美心理的网红。
在斗鱼,映客等一些视频直播平台上,不少网络主播打黄色差边球,裸露身体,言辞露骨等是他们的惯用伎俩,有时候为了打赏甚至不顾道德规范,突破法律底线,但往往这样的直播在线观看人数不少,观众在直播间送出了价值不菲的礼物,“高人气”让他们在网络上的言行更加肆无忌惮。还有郭老师等靠“土味”取胜的网红,他们迎合受众的窥私心理,在直播间做着各种私密的事情,打嗝、抠脚、喷鼻涕等,网红越疯狂受众就越开心,直播间的点击率和礼物齐飞,“公众可从中窥见他人的私生活和内心秘密,它也满足了人们了解别人、展露自我的欲望,但同时挤压了他人的隐私空间和独享的精神天地,使得私生活成了一种社会的展览品”②还有一些则抓住了受众的猎奇心理。
二、“浅薄化”倾向产生的原因
“浅薄化”倾向的出现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从新媒体平台用户看,他们是新媒体平台服务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媒体的价值取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用户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深层次的东西,他们喜欢浅显易得的,能够快速反馈的内容,于是几张照片,一个段子,一段短视频,碎片化文字都成了他们心仪的目标,他们热衷于消费这些产品。有时候上网也是用户缓解疲劳,放松身心的主要活动,在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之后,他们倾向于选择那些轻松幽默的内容,甚至是放纵基于“本我”欲望的各种病态心理,比如窥私心理,还有猎奇心理,在新媒体平台上搜索内容,寻求刺激和快感。
从内容生产者即网红的角度看,生产一些高质量高水平的内容比如知识科普,需要更加专业的技能,门槛太高,所以他们更倾向于生产那些简单的内容,比如上传自拍,拍摄生活日常,写段子,甚至是无节操的行为,都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成为网红的门槛低,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对其产生关注即可,受众的要求也不算太高,吸引他们的注意即可,所以网红为了迎合大部分受众的浅显需要,生产着浅薄化的内容,这就使得新媒体平台被这些低质量的内容充斥着,有些网红即使可以生产高质量的内容,但因为绝大多数受众不受用于是转型,比如papi 酱,本来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高材生,原则上是可以生产出优质内容的,但她却是因为原创吐槽短视频内容而为人熟知,所以,不仅网红在引导新媒体平台的方向,更是用户在引导他们,用户积极的反应推动着网红的生产热情和资本的流动。
从新媒体平台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利益是强驱动力,平台的信息生产以用户需求为宗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受众喜欢浅薄,平台就纵容浅薄的野蛮生长,受众的浏览量和点击率能为平台创造巨大的流量,并且吸引广告商、投资者的青睐。新媒体的特征也是“浅薄化”倾向产生的重要原因。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是内容的生产者,它的门槛较低,于是生产的内容质量良莠不齐;对比起过去的媒体,新媒体更加细化,能够满足受众的个性化需求,有些平台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普遍使用算法推荐,受众喜欢什么就推荐什么,以此来迎合受众;另外新媒体平台上内容众多,可供受众的选择也就多,只有抓住受众的刺激点才能获得成功;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可以将文本、声音、画面等进行融合,这也给浅薄化内容的生产提供了条件。
三、网红现象所带来的“浅薄化”影响
对于内容生产者网红来说,网红头衔使得他们“名利双收”,他们的受众不仅支持而且追捧网红,热衷消费“网红”同款,催生了“网红经济”等,这就使得网红不需要付出太多,就能拥有高关注度,享受着头衔带来的经济收益,越来越多的人渴望成为网红,尤其是某些三观尚未真正形成的未成年人,他们甚至在新媒体平台上拙劣地模仿网红,网红现象对他们产生的毒害是巨大的。
用户长期关注碎片化,娱乐化,刺激性的内容,会形成信息茧房效应,受众很难再去关注更深层次的内容,思维肤浅是他们的特点,尤其是迎合受众猎奇心理,窥私心理、病态审美等特点的网红,他们的心理大部分是病态的,无下限的行为经过炒作,对他们的受众的心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管理,长此以往将会导致社会文化畸形发展。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Our politics,religion,news,athletics,education and commerce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congenial adjuncts of show business,largely without protest or even much popular notice,the result is that we are a people on the verge of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③
对于新媒体平台,平台持金钱至上原则而枉顾道德,失掉了媒体平台该有的社会责任感,并且上述这些网红的行为会让网民对新媒体平台产生的“刻板印象”。比如快手,由于快手上影响力较大的网红基本上是以农村为内容生产背景,利用无节操行为进行炒作的“草根”,久而久之,使得快手带有一种略显低俗的感觉,这对媒体的发展而言是不利的,口碑,路人好感等都会下滑,间接损失掉了潜在受众。
其次,新媒体平台上形成了特别的亚文化。网红创造了众多网络流行语“集美”、“鸡你太美”、“一给我里giao”等等,这些简单易学、朗朗上口的语句红遍网络,甚至掀起了模仿的狂潮,也形成了特殊的亚文化群体,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说着圈外人不懂的语言,基于受众这样的心理,网红积极造势,策划热点,引发受众广泛讨论,形成现象级事件,受众为了不至于在群体中陷入孤立的境地,往往会不自觉地参与讨论,如此循环,新媒体就成了小众文化、亚文化和边缘文化的阵地,平台空间有限,受众的注意力也有限,于是主流文化就面临被排挤的危机。
最后,网红的行为影响着新媒体的整体环境。为了获取感官刺激和快乐,这些网红的铁粉每天都会赶到他们在新媒体平台上的直播间,蹲守他们的直播,浏览他们在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每一次关注都是在为这些新媒体平台创造着流量,所以平台往往持默许的态度。这间接地导致了新媒体平台的低俗化。基于病态审丑心理崛起的“网红”加快了新媒体的“浅薄化”倾向,而新媒体平台的“浅薄化”倾向也助推了此类网红的歪风邪气,促进了更多相似性同质性网红的诞生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新媒体环境呈现出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四、结语
以“数字媒体”为核心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激烈的媒体竞争过程中必将脱颖而出,成为无与争锋的万能媒体终端,并引领时代潮流奔涌向前。④新媒体技术狂飙突进,前景广阔,与此同时,新媒体平台亟需加强引导和管理,如果得到正确的运用,其将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社会各界应该予以重视,共同采取措施以期克服新媒体的浅薄化倾向,引导新媒体向更好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