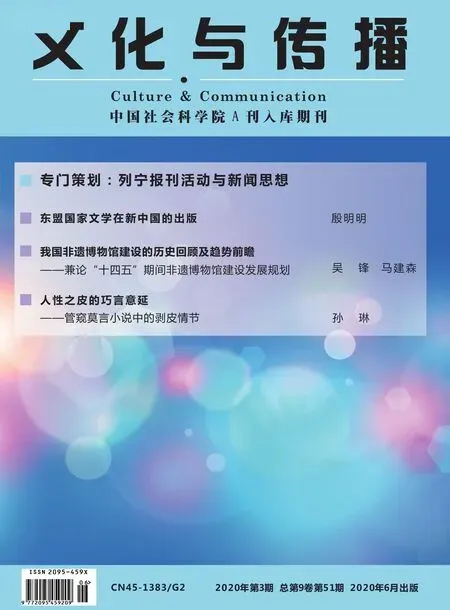通过仪式的表征与传播
——传播意义上“告”的文化阐释
赵 尚
特纳等人的“仪式过程”(又叫“通过仪式”)是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经典理论之一,该理论自提出以后,影响很快超出了人类学的范畴,在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领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理论解释力。最早提出“通过仪式”概念的阿诺德·范·杰内普认为,通过仪式是“伴随着每一次地点、状况、社会地位,以及年龄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1]人类社会自古至今,存在着诸多的通过仪式,这些通过仪式在传承社会价值与角色规范、进行社会整合等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想问的是,中国语境下的通过仪式,有没有比较专门的概念,来对之进行表征与指称,以体现仪式庄重、严肃乃至神圣等特征呢?另外,在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在报纸出现之前的古代社会里,这些在某一时空里举行的通过仪式,其传播如何突破空间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社会整合等作用呢?限于篇幅,本文仅把中国古代国家层面、制度化的通过仪式及其传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考订发现,中国古代国家层面、制度化的通过仪式及其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古就表示传播的“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研究就从对于“告”的考察开始。
一、商王面向神祖之“告”:面对风险与挑战时信仰性的“通过仪式”
“告”字在殷商时代就已经产生,且在甲骨文中出现得比较频繁,仅《甲骨文合集》中包含“告”的卜辞就达600余条[2]。“告”的本义到底是什么?这一点迄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告”在甲骨文中多通“祰”:“祰,告祭也。”(《说文解字》)表示人面向神祖的告祭之意。郭新和[3]、巫称喜[4]、梅军[5]等人的研究表明,商代以商王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在商王有疾病、天现异象,商王准备外出巡视、田猎、对外进行战争以及农作物即将成熟等关键时刻,都要对神祖进行告祭,祈求神祖的保佑,如“告于父丁。”(《甲骨文合集》33710)、“告土方于唐。”(《甲骨文合集》6388)、“告秋于河。”(《甲骨文合集》9627)。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商王有疾病、天现异象是商王朝遇到了现实的风险,而商王准备外出巡视、田猎,商王准备对外战争以及农作物即将成熟,实际上也是商王朝在面临着吉凶未测的挑战——商王朝周围的方国经常发生叛乱,因而外出巡视存在风险;对外战争胜负未知;商王的田猎一般也被认为是战争的演习(也同样关系到成败);农作物成熟时既可能丰收也可能歉收。因而,商王等人面向神祖告祭以求护佑,恰好可以看作特纳所说的通过仪式中的“阈限”时刻。“特纳对仪式进行过程性分析,借用杰内普的理论将仪式分为三个阶段:仪式发生前的社会状态是结构,即高度秩序化的社会生活……经过仪式的第一个阶段之后,个人便从原有处境和先前位置(即结构)中分离出去,进入到边缘阶段——阈限阶段,阈限是仪式的关键阶段,是一种介于旧结构和新结构之间的模糊状态……最后在第三阶段,仪式通过聚合环节重新回到结构性环境中。”[6]商王等人举行告祭之前的社会状态是结构,告祭之后的社会状态也是结构,而连接这两个结构的告祭则是脱离了日常社会状态的、庄严神圣的“阈限”时刻,以商王为代表的告祭者们相信,经过告祭,他们已经获得了神祖的护佑,相应地也就能够顺利地“通过”现实及潜在的风险与挑战,从而进入到新的结构性环境中——战胜了风险与挑战,获得胜利、平安与丰收等后的日常社会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商代的祭祀非常频繁,祭名也非常多,据李立新考证,至少也有二百多种[7]。在这么多的祭祀种类当中,告祭只是其中之一,其与其他祭祀种类的区别在于,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告祭经常是在商王朝面临风险与挑战时举行的。当然,自商代开始,“告”的应用范围已经很广,除了表示告祭以外,还表示人与人、国与国等之间信息传播的禀告、告诫、告诉等涵义,这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故此处从略。
二、西周春秋时期国家间的“赴告”之“告”:寻求他国认同的通过仪式
面对风险与挑战时,表示信仰性地通过仪式的告祭,在商代以后也同样存在,饶宗颐云:“按《通典·礼十五》有‘告礼’一项:‘周制,天子将出,类乎上帝,造乎祢,太祝告,王用牲币。’《大戴礼·迁庙》:‘凡以币告,皆执币而告,告毕,乃奠币于几东,小牢升,取币埋两阶间。’盖巡狩、迁庙、征伐诸大事,皆告于宗庙(及百神)也。”[8]但西周以后作为国家层面、制度化的“告”,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表示现实中而非单纯信仰性的通过仪式,如《礼制·王制》云:“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说的是在现实中出征并取得胜利以后,用献俘的方式向神祖禀告成功这个以求得神祖认可的“通过仪式”(商代卜辞中已有“告执”一词,表示的可能也是这个意思,但这一点学界有争议,还不能确定)。徐杰令先生经研究后认为,西周时期周王室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存在着“赴告制度”[9]——“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即一国有大事发生时要赴告他国的信息传播制度:“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赒委之。若国师役,则令槁桧之。若国有福事,则令庆贺之。若国有祸灾,则令哀吊之。”(《周礼·秋官·小行人》)这些情况下“赴告”的目的在于,当一国有大事发生时,让其他诸侯国派遣使者前去帮助或参加仪式(庆贺或哀吊),因而这里的“赴告”,更多的是“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信息”[10],以达到“控制空间和人的目的”[11]。但在一些史料中,也能找到表征西周时期国与国之间通过仪式性的“告”,如:“成王既崩……太子钊即位,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史记·周本纪》)讲的是西周时期,每当新旧周王更替时,除了要在周朝内部举行通过仪式以外,还需要把关于举行了通过仪式的消息传达到各诸侯国,这种传播通过仪式、以求得他国认同的过程也被称之为“告”。春秋时期,尽管周王室趋于衰弱,社会趋于礼崩乐坏,但在霸主诸侯国强大实力的维持下,国与国之间的礼义等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以维持,西周时期创立的“赴告”制度不仅继续得以存在,而且内容更加丰富,各结盟或建立邦交关系的诸侯国之间,但凡一国有某个比较重要的“通过仪式”,也须传播到周王室以及其他与之有着邦交或结盟关系的国家,以求得他国的认同与尊重,这也是一个对外建构自身合法性的过程。结合学者徐杰令所作的关于春秋时期赴告制度的分析,笔者认为,春秋时期国家层面、制度化通过仪式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诸侯国新旧国君的交替。“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后,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左传·隐公七年》)“干征师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左传·昭公八年》)“告终称嗣”、“告有立君”讲的就是诸侯国新旧国君的更替。
二是诸侯国内部的分封子弟或卿大夫采邑。“无曲防,无遏,无有封而不告。”(《孟子·告子下》)“昔吾先公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晏子春秋·外篇上二四》)“通之诸侯”其实就是告于诸侯。
三是诸侯之间结盟或媾和。“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冬,齐侯使来告成三国。”(《左传·隐公八年》)“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左传·襄公八年》)“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左传·襄公十一年》)
四是诸侯有征伐之事。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诸侯有征伐之事时,又需要“师出有名”,如:“卫成公不朝,使孔达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详,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左传·文公元年》)诸侯征伐之“告”,表示的是诸侯国之间,从彼此和平共处的合法化结构状态,过渡到一方(或几方联合起来)对另一方进行征伐这种新的合法化结构状态。
“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信息;那么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12]根据徐杰令先生的研究,春秋时期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告”,除了以上所列的四种情况,在国遭攻伐,国家有灾荒,国君、卿大夫出奔以及国有内乱发生时,亦须告于与之有邦交或结盟的诸侯国。显然,这些情况的“告”,其更多地带有出于控制目的、非仪式化的传递观色彩,而上文所列的四种通过仪式的“告”,显然更多地带有传播仪式观的色彩。特纳认为,通过仪式可以概括为:伴随着状况的改变而举行的仪式,“状况”一词可以“指代任何一种得到文化认同的情况”[13]。以上四类的“告”,恰好都表示诸侯国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从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过渡到另一种比较稳定的结构(诸侯之间“师出有名”的征伐,一般都是在确保能够取得胜利、能够让不礼或不义的被征伐方得到教训的前提下进行的)。“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4]春秋时期作为通过仪式的“告”,其传播的正是“礼”“义”“信”等既能维护社会秩序、又有亲亲尊尊等文化色彩、能够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念与规范,这些价值观念与规范对于维护春秋时期华夏这个共同体来说至关重要,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章怨外利,不义……内利亲亲”(《国语·周语中》)“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战国策·序》)“中国者……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战国策·赵策二》)(当然,这些史料里所说的“义”“礼”等,即包括诸侯国之间在物质上的相互帮助,也包括通过仪式性的相互传播)。反之,如果一国有这种通过仪式而不“告”,则意味着违反了邦交国家间的礼义等制度,因而不被别的诸侯国所认同,相应地也不被别国载入史册:“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左传·隐公十一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左传·文公十四年》)而严重的,还会因此而引发对方发动战争征讨,如“郑伯自栎入,缓告于楚。秋,楚伐郑,及栎,为不礼故也。”(《左传·庄公十六年》)讲的是郑厉公出奔时曾告于楚,后来归国复位两年以后,才告于楚,对于归国复位这种“通过仪式”,郑厉公因为迟了两年才“告”,就被楚国认为“不礼”而进行征伐。
但总体而言,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趋向于礼崩乐坏的时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至于许多非正常,甚至难以符合礼、义、信等价值观念的“通过仪式”——主要包括国君及卿大夫出奔及归国,国有弑君、杀戮大臣等,在春秋时期也不得不“告”,以求得诸侯国之间至少表面性、暂时性的相互认同与尊重,这实际上是“告”的制度在走向变异乃至异化。及至整个华夏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礼、义、信等价值观念已经行不通了:“行义约信,天下不亲”(《战国策·秦策一》),这种表示国与国之间通过仪式传播的“告”也就不复存在了:“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士无定交,邦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卷十三》)
三、汉代以后的布告:传播关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通过仪式
汉代以后,在报纸出现之前,由朝廷统一发布的官方布告或曰告示,是传播范围最广的媒介,尽管其发布的可能多是控制性的政令等内容,但也有一些“通过仪式”性的内容,据笔者梳理,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类。
一是上天表彰帝王的,这一般通过与天现异象相反的天降祥瑞的方式,例如:“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宁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长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茎叶紫色,盖紫芝也。太守沈酆遗门下掾衍盛奉献,皇帝悦怿,赐钱衣食。诏会公卿,郡国上计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并闻,吏民欢喜,咸知汉德丰雍,瑞应出也。”(《论衡·卷十九》)这里的“告示天下”,实际上是对上天对帝王(也即天子)“德丰雍”的“加冕”这个通过仪式的传播,而“吏民欢喜,咸知汉德丰雍”,则说明这个通过仪式的传播,很好地提升了人们对皇帝及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二是新旧皇帝更替或改元的,如:“上久寝疾,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十五》)用布告传播改元这种典型的“通过仪式”,不仅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需要,而且是通过“诏大赦天下”等方式来彰显圣德的需要。年号的变更以及“大赦天下”,显然是一种“反结构”的状态,经过这个短暂的“反结构”状态,社会又重新回到正常的法制化状态中,但这个短暂的“大赦天下”,却体现了皇帝的“仁”德,有助于增强皇朝统治的合法性。
三是朝廷表彰吏民的,这一般指皇帝对于表现突出的吏民进行加冕这种通过仪式的传播。有对于吏民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 “公义”(区别于偏私性的“私义”)的嘉奖表彰,如:“上于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说的是汉代的卜式在灾荒年散掉自己的许多家财以救助流民(属于仗义疏财的“公义”之举),因而得到了皇帝的嘉奖。也有对于吏民之“忠”的表彰,同样关于卜式:“齐相卜式上书,愿父子死南粤。天子下诏褒扬,赐爵关内侯,黄金四十斤,田十倾。”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说的是卜式父子主动请战,愿意为国捐躯,因为这种“忠”君的精神,卜式再次得到了皇帝的嘉奖。
可见,汉代以后由朝廷发布的“通过仪式”性的布告,主要用来传播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皇帝统治的合法性建构,以及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仁、忠、公义等)的典型人物的嘉奖表彰等。
结语
以上我们论述了中国古代作为国家层面、制度性通过仪式的“告”,其中商代的告祭之“告”主要是作为通过仪式的表征,而西周春秋以及汉代以后国家层面、制度化的“告”,则主要表示通过仪式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传播。凯瑞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15]无论对于现场参与通过仪式的人们,还是对于通过仪式传播到的、更大范围内的人们来说,都是一个社会价值、规范、角色等得以生产、维系或修正、转变的过程:在商代是对于神祖的信仰与崇拜,在西周春秋主要是“礼”、“义”、“信”等价值规范,在汉代以后则是“仁”、“忠”、“公义”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价值观念与规范,对于一个社会在时间性上的维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涂尔干认为,一个社会要想生存和发展,“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16]很显然,国家层面、制度化通过仪式的“告”,就正是这么一种在现实及想象中让人们聚合、聚集和聚会的手段,也是一个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与集体意识(包括价值观念)的过程,这种“仪式是一种战略行动,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防止相互攻击,驱除可能影响共同体和谐的危险因素。”[17]直到今天,“告”仍然常常被用作“通过仪式”的表征或传播,如宣告成立、案件告破、工程告竣、告终、告捷、告假、告病、告辞、告归、告一段落等。最为典型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各种单位的年度大会报告,它是年度性仪式的最重要内容,而年度性仪式“常常是在一年一度的生产周期之中规定的时间点上举行”[18](一般都是在春节前的年终时刻),报告的内容,一般都既有对过去的回顾与总结,又有对未来的展望与部署,让与会人员在参与会议的过程中既体会到了会议的庄重、严肃,强化了集体情感,又在思想上完成了目标、任务、角色乃至规范等的修正或转变,统一了集体意识。陈寅恪先生云:“凡解释一字即为一部文化史”,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告”的涵义虽然比较多,但作为通过仪式(无论国家还是集体等层面)表征与传播的义项,则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