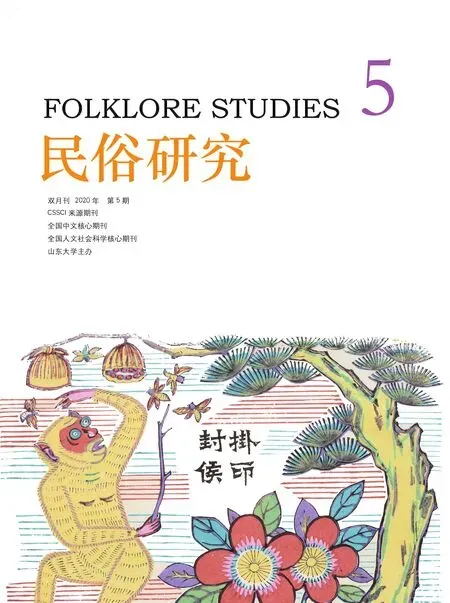美感何以得自由:歌谣的纯粹鉴赏判断
户晓辉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始于1918年2月在北京大学兴起的歌谣征集活动。(1)参见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2页。歌谣之所以首先成为现代学者征集的体裁形式并在后来几十年里一直成为学术热点,并非仅仅因为中国有历史悠久的采风传统,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对传统的另类发现”(2)陈泳超:《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借鉴与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具体而言,尽管歌谣在古代早就被视为直抒胸臆的天籁之音,但在康德的学生赫尔德以及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3)参见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7-129、155页;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92页;陈怀宇:《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卢文婷:《周作人与顾颉刚:“五四”民俗学的双重变奏——〈歌谣周刊〉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中国现代学者把新的目光投向歌谣的普遍情感和感性形式。
一、歌谣的普遍情感有多普遍
早在1922年,胡适在《北京的平民文学》一文中就主张从文学审美的角度选择并欣赏歌谣。早期极为推崇歌谣诗学价值的俞平伯在《诗底自由和普遍》(1921年)和《诗底进化的还原论》(1922年)等文中认为,“文学底质素”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性和意志,而歌谣恰恰正是这一质素的直接呈现。(4)参见陈泳超:《想象中的“民族的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在赫尔德以及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周作人对歌谣情有独钟,而且他对歌谣的理解依照的是德国福克斯(5)福克斯(Eduard Fuchs,1870-1940),德国文化学家、艺术史家和收藏家,尤其关注文化、历史和艺术中的感性现象,著有《情色艺术史》《插图风化史》(6卷)等。的说法(6)参见周作人:《猥亵的歌谣》,《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周启明:《一点回忆》,《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1922年底,周作人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搜集歌谣的文艺目的在于“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这种“国民心声”就是周作人1908年提到的“德人海勒兑尔(Herder)字之曰民声。吾国昔称诗言志”(7)陈怀宇:《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冯庆:《民族的自然根基——赫尔德的“抒情启蒙”》,《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其中的“海勒兑尔(Herder)”就是赫尔德。在周作人看来,歌谣乃至民歌的最大价值在于感性的“真挚与诚信”及其对“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8)参见周作人:《歌谣》,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页。,这与他强调“平民文学”表现人们“普遍”而“真挚”情感的观点遥相呼应,歌谣与平民文学最终都要符合真正的、普遍的“人的文学”标准。(9)参见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33页。同样,家斌译述的《歌谣的特质》一文写道:
歌谣是民族集合生活最强的感性的表现,一个民族的社会成训差不多要以歌谣和民族故事为其中心。诗人作的诗与歌谣的分别就在一个表现的是个人的感性与想像,一个表现的是民族的,群众的;一个是一个诗人写出的,一个是群众生活中产出的……歌谣的特色就是能把民众的感性热烈的质朴的表出来。歌谣一方面说是极带地方色彩的,但歌谣所描写的是人情,人情绝不会相差太远,所以歌谣又时常脱了地理的限制,竟能口传到很远。(10)家斌译述:《歌谣的特质》,《歌谣》第23号,1921年6月17日。
在此,歌谣被认为是与个人创作相对的、从“群众生活中产出的”作品,“歌德说这些歌谣的特色就是这些歌的感兴是直接由自然来的,不是硬弄出来的,是自然流出来的”。歌谣的特质被归结为“绝不会相差太远”的普遍人情,它要表达的并非“个人的感性与想像”,而是“民族的,群众的”普遍感性,即“能把民众的感性热烈的质朴的表出来”,所以歌谣的“地方色彩”才能“时常脱了地理的限制,竟能口传到很远”。也就是说,歌谣表达的不是个别的感性,而是普遍的感性。值得指出的是,1923年,顾颉刚在日记中专门对家斌译述的这篇文章做了三大段摘录,其中包括“这类表出普通都可感到的情感的歌谣,很容易传播,在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找得到”(11)参见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693-695页;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尽管顾颉刚后来在题为《我和歌谣》的回忆文章中未曾提及(12)顾颉刚:《我和歌谣》,《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但他编辑《吴歌甲集》和研究孟姜女故事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要彰显多数民众的普遍情感,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1928年他发表的《民俗》发刊词中。
可以说,歌谣表达普遍情感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几乎成为中国现代学者的共识,与欧洲浪漫主义歌谣观在当时被译介到中国有很大关联。例如,1931年1月7日《歌谣》刊登了为君根据法国《儿童诗歌的研究》一书编译的短文《歌谣的起原》。(13)为君:《歌谣的起原》,《歌谣》第4号,1923年1月7日。1936年10月24日和10月31日的《歌谣》周刊连载了西班牙的卡萨司原作、于道源根据世界语翻译的《歌谣论》一文。卡萨斯以典型的浪漫主义笔调写道:
歌谣是整个民众的可惊异的著作,是那些听着它唱着它的人们的著作;它是每个人的作品,同时又不属于任何人。歌谣经过一切人的传授,影响,修改和润饰。因为一切人全都是它的合法的主人,而没有人可以绝对的把它看成自己私有的东西。那些能够把它唱得很动听的,或是能够欣赏它的内容的人,都可以算是它的主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歌谣所达到的美丽是远非任何种的人类智识所可得而模仿的,因为在它里面包涵着歌唱它的人们底心灵的精粹;凡是唱它的人的灵魂都有一部分在内,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某种东西放到它的里面。歌谣有一种比任何最大天才作家的作品更为亲切动人的魅力。因为一个作家只能在他的作品中浸入他自己的灵感,而歌谣是藉了一切唱过它的人底灵魂的火焰而丰富起来的。
歌谣虽然是像一切带集体性的作品一样,是整个民族的产业,然而在开头的时候永远是独自一个人由灵感而结出的果子,这一个人在一种特别的恩惠情形之下把这歌曲记录下来。假若他晓得怎样可以藉了它使得民众底灵魂的弦发生颤动,假若他明白如何可以把民众的共同情感宣扬出来,那么第一个听到这首歌谣的人就把它记住而变成他自己的;他重新歌唱它,但是他并不是完全忠实的重复背诵它,因为歌曲有一些是出乎他底灵魂之外了。而且因为我们各人有各自的灵魂,每个人都不自觉的把所唱的歌谣加以修改使它适合于各单个灵魂。两个绝对相同的灵魂既是不会找到的,所以歌谣经过两个不同的口中歌唱以后也不能完全相同,每个人都依照他各自的感觉而加以润饰和改变,所以这件伟大的作品是被民众全体不自觉的创造出来的。(14)于道源译:《歌谣论——卡塔鲁妮亚·卡萨斯原作》,《歌谣》第2卷第21期、第22期,1936年10月24日、10月31日。
在此,浪漫主义的歌谣观跃然纸上。卡萨斯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歌谣创作和演唱的过程以及个人与集体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尤其强调“歌谣经过一切人的传授,影响,修改和润饰。因为一切人全都是它的合法的主人,而没有人可以绝对的把它看成自己私有的东西”,因为虽然“凡是唱它的人的灵魂都有一部分在内,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某种东西放到它的里面”,但“歌曲有一些是出乎他底灵魂之外了”,因为“歌谣有一种比任何最大天才作家的作品更为亲切动人的魅力。因为一个作家只能在他的作品中浸入他自己的灵感,而歌谣是藉了一切唱过它的人底灵魂的火焰而丰富起来的”。也是在1936年,复刊后的《歌谣》周刊主编之一李素英也指出,一方面,“歌谣里所表现的感性,只有比诗里的更为真挚,热烈,率真,因为民众没有名位的束缚,道德观念也不甚深,故言行思想都较士大夫们为自由而坦率。他们不懂也不必掩掩藏藏,半吞半吐地假斯文。何况歌谣又不是写在纸上留待慢慢推敲的,也不想到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只是迫于内心情绪的要求放情而唱的口占的诗句,所以除了情真意切以外,连技巧问题也不存心顾虑。”(15)李素英:《论歌谣》,《文学年报》第2期,1936年5月。但另一方面,歌谣表达的感性又与士大夫创作的诗歌有所不同,“因为歌谣虽然最初也是个人的创作,但经过众人的传唱和修改,就成为集团的产物,表现大众共通的情绪,故不得不浅显;而且目的在于传达感情和意思,多过自我表现。”(16)李素英:《论歌谣》,《文学年报》第2期,1936年5月。歌谣虽然“放情而唱”且“情真意切”,却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而是为了传达集团的“感情和意思”,为了“表现大众共通的情绪”。正是基于这个标准,李素英才对当时的大众文艺提出尖锐批评:“现在一般的文艺作品,无论其为普罗与否,皆与民众本身无直接关系。我国最大多数的民众,连自己的粗浅俚俗的歌谣也只能口唱而不会写下来,哪里够得上资格去欣赏大文豪的杰作!倒是歌谣,小调,俗曲等才真是民众自己的文学。因为歌谣俗曲里所表现的无论是欢乐,悲哀,怨愤,咒诅,愿望及无意义的嬉笑,都是他们最纯真的情绪之流露。他们自己能创作,能欣赏,能互相了解。他们唱着一些流行或新创的歌谣,一定能感到彼此间情绪思想的交流,引起内心的共鸣,获到同情和慰安的。歌谣所指示给文学的新趋向是以质朴的形式,简单老实的话语写出实际生活的内容。我们的所谓大众文艺若是永远写给自己看,那也罢了;如要它成为共通的文学,则惟有拿歌谣做参考,以民众的感情,思想,话语为我们自己的感情,思想,话语,然后表现出来。但是这样弄出来的结果仍是赝品。我们只能以这个为一种过程和手段,当作教育的工具之一,先使民众能欣赏和接受这种摹拟的文学,由程度之逐渐提高,达到民众能自己创作歌谣以外的文艺,那才是真正的大众文学。更由生活的提高,逐渐臻于平等,那时才有整个的共同的文学”。(17)李素英:《论歌谣》,《文学年报》第2期,1936年5月。在李素英看来,为民众创作的大众文艺只是“共同的文学”的“一种过程和手段”,或者只不过是一种“摹拟的文学”,而这种“摹拟的文学”之所以“惟有拿歌谣做参考”,恰恰因为歌谣被认为是普遍情感的感性形式,即“以民众的感情,思想,话语为我们自己的感情,思想,话语,然后表现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只有站在民众的立场才能创作出“共同的文学”。
正因为歌谣能够“表现大众共通的情绪”而且要“成为共通的文学,则惟有拿歌谣做参考”,所以李长之指出:
歌谣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是研究歌谣者首先当问的一个问题,而且如果答复得不正确,或者模糊了,便会影响到从歌谣研究而得的文学见解上去的。
大凡一种观念的错误,是有两个缘故,一是受文字上传统的影响,二是受同时代里其他思潮的影响。我们只说歌谣吧,由第一种影响,我们很容易想到《诗经》上的“我歌且谣”,不知不觉便把歌谣又送到士大夫的圈子里去了……我们只消清清楚楚地记得我们现在弄的是另一套东西,我们给它一个名字是歌谣罢了,和从前人用的意义合也好,不合也好,全不相干,这就行了……新文学运动不是在恢复大多数的平民的表现能力吗?注意歌谣也就是要以民间的东西作范本的呀……我们指为民间创造的东西,即是有意无意间以为是集团的东西了,其实没有这末回事的,这只是新士大夫们的一种幻觉而已,倘因此而认为歌谣的价值特别高,这只是由于太崇拜平民(一如过去旧士大夫之太崇拜贵族)之故,将必不能得到歌谣的真价值的;又倘因此而认为有了教养的诗人的作品反而是差些,那就根本走入魔道,歌谣反是不祥之物了。我们决不希望如此……Johannes Scherr(18)舍尔(Johannes Scherr,1817-1886),德国文学史家和文化史家,1851年出版《从远古至今的文学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auf die Gegenwart)。——引注在他的《世界文学史》里说歌谣是像风一样,我们不知道它是从那儿吹来的,也不知道它向那儿吹去,这确乎是很好的形容了,然而风终于是一个地方空气受了震动,歌谣也终于是一个天才心绪受了感触……现在我的意思只是:与其说歌谣与诗的分别是在作者,毋宁说是在流传,与其说那分别是在一为集团所创造,一为个人所创造,毋宁说同为个人所创造,不过一为在文化教养上所受的深些的个人,一为在文化教养上所受的浅些的个人而已……因此,所谓歌谣的集团精神,平民色彩,毋宁只在欣赏方面而已……话说回来,歌谣是什末的问题,倘若照我们那样解答的话,则我们可以知道它和诗人的作品同(同是个人的,天才的创作)和不同(一为士大夫所选择,一为民众所选择)的真正所在。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知道歌谣在艺术上的短长,也就是歌谣的真价值,再进一步,我们便可以发现它对于新文学的真贡献,以定我们的取舍了。(19)李长之:《歌谣是什么》,《歌谣》第2卷第6期,1936年5月9日。
这段论述堪称歌谣新观的点睛之笔。作为一位懂德语并且深受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李长之首先破除了歌谣的集体创作观。他明确指出,“我们指为民间创造的东西,即是有意无意间以为是集团的东西了,其实没有这末回事的,这只是新士大夫们的一种幻觉而已”。显然,李长之更强调个人因素,而且把关注点从歌谣的创作环节转向“流传”和欣赏环节。在他看来,“歌谣”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它的新颖之处首先是在感性方面普遍地“为民众所选择”,因此,“与其说歌谣与诗的分别是在作者,毋宁说是在流传”,而且确切地说,“所谓歌谣的集团精神,平民色彩,毋宁只在欣赏方面而已”;而在歌谣的欣赏方面则要保持中间立场,“太崇拜平民”与“太崇拜贵族”都“将必不能得到歌谣的真价值”。正因为歌谣在欣赏方面首先而且最容易诉诸普遍情感,新文学以歌谣为范本才有助于“恢复大多数的平民的表现能力”,而对歌谣表现普遍情感的强调体现的则是一种不同于古代风谣传统的现代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在这篇文章中引述了Hans Röhl(20)勒尔(Hans Röhl,1885-1945),德国学者,著有《德国文学词典》(Wörterbuch zur deutschen Literatur,1921)、《德国诗歌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ichtung,1926)、《浪漫派的精神》(Geist der Romantik,1930)等。的《文学辞典》中关于Volkslied的定义,认为“这里是所谓‘民歌’(Volkslied),但实在就是我们所谓歌谣”(21)李长之:《歌谣是什么》,《歌谣》第2卷第6期,1936年5月9日。。稍后,他在《略谈德国民歌》一文中明确指出:
“民歌”(Volkslied)这名字之起,是开始于海德尔。海德尔在一七七三年作了一篇《关于莪相与古民族诗歌》(Über Ossian und die Lieder alter Völker),在一七七八年出版了他所搜集的《民歌集》(LiederdesValkes(22)原文此处的德语字母拼写和说法有误。赫尔德于1778年出版了自己收集的《民歌》(Volkslieder);1807年再版时,亨利希·封·米勒把书名改为《民歌:歌谣中各族人民的声音》(Volkslieder. Stimmen der Völker in Liedern)。)。他所以注意民歌者,是因为受了卢梭的影响,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好的。(23)李长之:《略谈德国民歌》,《歌谣》第2卷第36期,1937年2月27日。
这里的“海德尔”就是赫尔德。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学者对歌谣感性特质的再发现与赫尔德和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有直接关联,这些学者基本上把“感性”“情感”“情绪”之类概念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当然,李长之的文章发表之后,寿生和卓循很快就在《歌谣》周刊上分别撰文表达了不同看法。卓循认为,“歌谣的创始可以是个人的,但它一经作成了之后,就被交给大众了,一首歌谣不管它是好是坏,总以适合一地域的大众的口味为止,所以它经过了甲地之后,甲地人便有一番改正,经过乙地,乙地人也有一番改正……我们知道,集团也脱不了个人,除开了个人,集团便无法存在,集团艺术,仍然是建在个人艺术上的,但我们不能因之遂否定了集团艺术”(24)卓循:《写给〈歌谣是什么〉的作者》,《歌谣》第2卷第10期,1936年6月6日。。李长之遂与寿生、卓循展开争论。(25)参见寿生:《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歌谣》第2卷第9期,1936年5月13日;李长之:《论歌谣仍是个人的创作——答寿生、卓循二先生文》,《歌谣》第2卷第12期,1936年6月20日;寿生:《答李长之先生》,《歌谣》第2卷第13期,1936年6月27日。但他们没有深究的问题是:即便最初的个人创作“经过众人的传唱和修改,就成为集团的产物”,它又如何能够“表现大众共通的情绪”呢?最初由个人创作、演唱和欣赏的歌谣如何能够像卡萨司说的那样“可以把民众的共同情感宣扬出来”呢?作为不同个体的我们如何“以民众的感情,思想,话语为我们自己的感情,思想,话语”呢?由此产生的情感就是普遍情感吗?如果歌谣的普遍情感仅限于民众,那么它的普遍性能达到多大程度?多数是否就等于普遍呢?
二、歌谣欣赏:普遍情感的反例
进而言之,个人与集体的潜在对立在歌谣的欣赏环节表现得更加突出。因为在创作和流传环节还可能同时或先后有多人参与,而歌谣的欣赏则大多由个人做出判断。欣赏者从歌谣中欣赏出什么样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歌谣具有什么样的情感。因此,欣赏环节的突出问题是:欣赏者的个人情感能否以及如何代表普遍情感。也正是在歌谣欣赏的环节,歌谣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刘半农表达了与普遍情感论相反的看法。(26)李素英曾写道:“然而当代的文艺界因为成见太深,以贵族自居,总有一点瞧不起平民的作品,不肯干脆的承认歌谣是我们中国的诗;却生怕把自己的贵族文学作品降了格,故必曰歌谣是民间文学,是民众的诗歌,其中只有一个例外,那是采歌谣格调创作《瓦釜集》的刘半农先生”(李素英:《论歌谣》,《文学年报》第2期,1936年5月)。他说:
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另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其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的。
说到文艺这一件事,可就不容易说出具体的理论来了。干脆的说,文艺的欣赏完全是主观的——你说它好,就是好;你说它不好,就是不好。你要在这好与不好之间说出种种道理来,亦许也能说得很对;但这所谓对,也只是你所说的别人不以为非,换句话说,便是你的主观,偶然有多少和别人的主观相合;而就全体说,终还是你自己的主观,终还有许多地方是你自己的偏见。
何以呢?因为我们要在某一种事物上作理论的推断,我们所用的是理知。而理知这东西,却只能用在含理知的事物上;换句话说,理知是几何性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用在几何性的事物上。譬如你要说明什么是圆,什么是三角,你只须稍稍用一点功夫,就可把它的界说规订得明明白白;到规订明白了,你就可以说:圆与三角所具的条件应当怎样,合条件的就对,不合条件的就不对。至于文艺,它根本就不是理知的,是情感的。你尽可以天天说着“好”,“坏”,“美”,“丑”等字,你断然没有方法把它的界说规定得和图与三角一样的明白。既然连界说也无从规订起,讨论起来,当然就不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只能看作品中的情感,与我自身的情感是互相吸引的或者是互相推拒的:是吸引的就叫作好,叫作美;是推拒的就叫作坏,叫作丑……我并不说凡是歌谣都是好的,但歌谣中也的确有真好的,就是真能与我的情感互相牵引的。它的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人类之所以要唱歌,其重要不下于人类之所以要呼吸,其区别处,只是呼吸是维持实体的生命的,唱歌是维持心灵的生命的……因此,当私塾先生拍着戒尺监督着儿童念“人之初”的时候,儿童的心灵是厄塞着;到得先生出了门,或者是“宰予昼寝”了,儿童们唱:
人之初,鼻涕拖;
性本善,捉黄鳝……
这才是儿童的天性流露了,你这才看见了儿童的真相了。
村夫野老游女怨妇们所唱的歌,也就像儿童们趁着先生瞌睡的时候所唱的“鼻涕拖”“捉黄鳝”一样。譬如就男女情爱这一件事说,他们也未尝没有听见过“周公制礼”“周婆制礼”这一类的话,但他们全不在意,以为这只是大人先生们闹的玩意儿,于他们没有什么相干:他们当着大人先生的面当然不敢“肆无忌惮”,背了大人先生可就“无郎无姐不成歌”了。在别件事上,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他们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怕:他们真有最大的无畏精神。好在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素。因此,我们在歌谣中,往往可以见到情致很绵厚,风神很灵活,说话也恰到好处的歌辞……这又要回说到歌谣的根本上:它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要表现。有意的表现,不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的流露既无所用其拘,亦无所用其假。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
歌谣在这一方面,能把人事人情表现得如此真切,在另一方面,它又并不胶粘在人事人情上:它也能有很超脱很奇伟的思想……
我把我所以爱赏歌谣的原由大致说完了。但是,这种的原由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从情感上发生的,是并没有理智上的保障的。与我见解不同的人,当然可以说我不对,我也当然没有方法可以和他辩论。(27)刘半农:《国外民歌译》第一分册“自序”,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第2-3、5-7、13页。相关讨论也可参见杨扬:《刘半农和中国俗文学审美特征研究》,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七十年——“纪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创刊七十周年暨俗文学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3-214页。
在这段颇具代表性的论述中,刘半农指出,一方面,歌谣的演唱超脱名利和礼制的“裁制”,“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歌谣的欣赏也不仅“完全是主观的”,而且“完全是从感性上发生的,是并没有理智上的保障的”,无法借助概念来“界说”和“规订”。因此,歌谣的美丑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感性喜好与主观判断;另一方面,歌谣的演唱和欣赏既不是为了增长知识,也不是为了吃喝拉撒睡,歌谣“并不胶粘在人事人情上”,其“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而仅仅是为了不受“裁制”的、“纯洁”的情感愉悦。这种看法与他在1926年为顾颉刚《吴歌甲集》做的序中表达的观点是相似的:“吃饭穿衣等事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以要研究各民族特有的文明,要彻底了解各民族的真际,非求之于吃饭穿衣等事之外不可。而民歌俗曲,却便是这项研究的最真实最扼要的材料。何以说最真实,因为这是蚩蚩者氓自己用来陶情适性的;他们既不比考生们对着考官对策,又不比戏子们对着听众卖艺,所以唱起来只是有话十搭十的说,不求讨好,不受拘束。”(28)刘复(刘半农):《序五》,顾颉刚编:《吴歌甲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页。在刘半农看来,歌谣的演唱和欣赏都离不开“自由的空气”,并且不该受到“别种东西的激扰”。
然而,在赞叹刘半农的非凡见解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他陷入难以自拔的主观相对主义困境。显然,刘半农不仅意识到欣赏歌谣“不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而且默认其主观标准,只不过在他看来这种标准仅仅“终还是你自己的主观,终还有许多地方是你自己的偏见”。这就意味着,在欣赏歌谣时,我的个人情感只有特殊的主观标准,我的个人判断也只能是孤立的,因而也是难以与他人分享和交流的。如此一来,歌谣如何“是一个民族自然而共同心音的表现”(29)王肇鼎:《怎样去研究和整理歌谣》,《歌谣》第45号,1924年3月2日。呢?如果歌谣不能被欣赏出普遍情感,那其他学者又有什么理由说歌谣能表达普遍情感呢?歌谣欣赏者又有什么资格来反对甚至取代贵族文学的审美趣味,他们又如何避免重新陷入“新士大夫们的一种幻觉”呢?
看来,刘半农不仅把个人情感与普遍情感的对立问题突显出来,而且推向了极端。尽管现代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触及歌谣审美的一些根本特征,却未能从理论上把问题引向深入。但是,既然赫尔德和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直接源于康德哲学,而中国现代学者们对赫尔德和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理解深度和接受程度无论是深是浅,都让我们有理由回到其重要源头——康德哲学来继续推进前辈学者开创的未竟事业。
本文仅以歌谣的纯粹鉴赏判断为例,以重新阐释康德感性学的(30)康德的原文是ästhetisch,旧译“审美的”很不准确,因为它不仅包括纯粹的审美判断或鉴赏判断,也包括不纯粹的和质料性的感官判断,但感官判断在康德看来并非真正的审“美”判断。虽然康德也把依附于概念的美称为依附的美,但这种美并非自由的美和真正的美,而且他在《判断力批判》第44节一开始就认为既没有“美的东西的一种科学”(eine Wissenschaft des Schönen),也“没有美的科学”(schöne Wissenschaft)。本文采用倪胜的建议,把康德的sthetik译为“感性学”,把ästhetisch译为“感性学的”。相关讨论,参见倪胜:《论Aesthetik在康德第三批判里的译法》,《世界哲学》2004年第6期;谢地坤:《如何理解康德哲学——〈纯粹理性批判〉中一些概念的辨析》,《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王奎:《康德论美的双重特性》,《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卢春红:《从康德对sthetik的定位论“ästhetisch”的内涵与翻译》,《哲学动态》2016年第7期;薛霜雨:《康德鉴赏判断之语义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Manfred Frank, “Kants 〉Reflexionen zur sthetik〈: Zur Werkgeschichte der 〉Kritik der sthetischen Urteilskraft〈”,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44, No. 175 (4), S.557, S.562;Stephan Zimmermann, “Reflexion und Freies Spiel: Kants Schlüssel zur Kritik des Geschmacks”, in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Vol. 56 (2014), S.47.自由理念为基础,尝试为歌谣的情感对立问题提供一个论证思路。尽管歌谣在创作和流传环节产生的情感不同于在欣赏环节产生的情感,也不等于鉴赏判断产生的美感,但在歌谣创作、流传和欣赏环节都可能包含着鉴赏判断,而且这些情感毕竟有息息相通之处。对美感何以得自由的论证尝试,不仅能够在学理上扬弃歌谣的对立情感,也将有助于重新理解在歌谣创作、流传和欣赏诸环节产生的情感。
三、鉴赏判断:私人性还是公共性
要想调解现代歌谣研究者之间的观点分歧,我们就不能满足于站在外部做一些大而化之的断言,而是要深入歌谣情感的内部来进行细致区分和学理辨析。与此同时,既然歌谣的个人情感与普遍情感在经验层面难以兼容,我们就需要从先验感性层面来寻求解决之道。
如果我们承认欣赏歌谣并非在个人心里“独乐乐”,那就要承认这种“乐”的情感需要传达出来并且形成判断。这种主观判断可能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这首歌谣是适意的”,它依据个人主观的适意感受,关心歌谣表象的质料或歌谣对象是否存在,因而是感官判断或经验性的判断;另一种是“这首歌谣是美的”,它诉诸人类的共通感,只关心歌谣表象给反思的判断力造成的合目的形式,因而是纯粹的反思判断,也就是形式上的感性学判断或鉴赏判断。(31)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62, S.53.
感官判断以个人的主观感觉为依据,所以仅仅具有私人性,而鉴赏判断虽由个人做出,却不依靠感觉内容和概念,而是依照普遍有效的自由根据,因而具有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公共性。(32)康德说:“因为如果它仅仅让他喜欢,他就不必称它为美的”(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50)。也就是说,虽然像适意这样的私人感觉也能够被我传达出来,但我不能期待每个人都将赞同我的私人判断。(33)参见Johannes Keienburg, Immanuel Kant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der Vernunft,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2011, S.143.正因如此,当我做出“这首歌谣是美的”判断时,不仅意味着这首歌谣对于我来说的确无利害地是令我愉快的,更意味着这首歌谣对于我以及每个人来说都必然是无利害地令人愉快的。(34)参见薛霜雨:《康德鉴赏判断之语义分析》,《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这时,我给这首歌谣的表象附加的谓词并非某个概念,而是我在主观上普遍可分享或可传达的先天情感。“这首歌谣是美的”这个判断表面上是我把自己的愉快当作谓词加给这首歌谣,但实际上,我给这首歌谣加上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愉快,而是我自己的愉快的普遍有效性。我的特殊情感不是原子化的和完全孤立的,而是应该与普遍情感息息相通,甚至本身就是真正的普遍情感。
我之所以能够在鉴赏判断中应该并且能够把自己的特殊情感变成普遍情感,不仅是因为我在情感上不是唯我独尊、妄自尊大的“独乐乐”,而且是因为我应该完成一个至关重要的“神操作”,即通过判断力把我的特殊情感归摄到主观的普遍规则之下。在鉴赏判断中,我应该把我的愉快情感的普遍有效性“先天地表象为对判断力、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普遍规则。我用愉快去知觉和评判某个对象,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判断。但我觉得它是美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奢求那种愉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然的,这却是一个先天判断”(35)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39-140.。因此,鉴赏判断不仅必须由鉴赏者个人独立自主地做出,而且还是“对判断的某种判断”,即一方面是“一种对判断的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所产生的愉快的判断”(36)Daniel Dédeyan, “Justitias blinder Fleck—Über Kants sthetik”, in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Vol. 91, No. 4, 2005, S.505.,另一方面也是对经验性判断的再判断,看看自己做出的经验性判断能否以及如何才能成为鉴赏判断。由此来看,歌谣的鉴赏判断不是也不依赖于心理过程,即便你说你没有发生和我同样的心理过程,也不能以此来否认我的鉴赏判断。(37)参见Arata Hamawaki, “Kant on Beauty and the Normative Force of Feeling”, in Philosophical Topics, Vol. 34, No. 1/2, 2006, p.124.换言之,既然鉴赏判断做出的断言只是一种主观宣称,那就需要鉴赏者反思自己的主观根据应该具有经验感性的性质还是先验感性的性质。所谓鉴赏,是摆脱了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的束缚而仅仅依靠普遍有效的情感能力和主观根据来进行判断的能力,也就是不借助概念而对这种与给定表象相连的情感的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做出先天判断的能力。(38)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27, S.147.歌谣的鉴赏判断虽然离不开个人体验和私人性,却应该从先天根据来反思并且具有真正的公共性。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从先验感性的立场来理解歌谣的鉴赏判断。
具体而言,如果我们承认鉴赏判断不是原子化的和完全孤立的感官判断,那就不能否认鉴赏判断产生的情感应该具有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关键是这种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的普遍性应该具有先验感性的性质而不是感性经验性的性质。
从范围来看,如果仅仅满足于让多数人可分享或可传达,这种普遍性就仅仅是经验性的和相对的。因为这种“普遍性只是比较得来的”,所以只有一般的规则(generale Regeln)而没有普遍的规则(univesale Regeln)。(39)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51.相反,“鉴赏判断带有普遍性的亦即对每个人都有效的一种感性学的量,这个量在关于适意者的判断中是无法找到的”(40)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51-53.重点原有。。这种主观的量表示鉴赏判断产生的愉快或不快的感性关系,来自判断力把特殊归摄到主观的普遍规则之下的能力,由此产生的美感才具有普遍有效的公共性。既然这种对“每个人都有效的一种感性学的量”在经验中“是无法找到的”,这就表明它属于先验感性的范围。
从性质来看,“对每个人都有效的一种感性学的量”不能满足于仅仅适用于多数人的相对普遍性,而是应该达到对每个人普遍有效的公共性,因为这种要求是由人与人之间先验地具有的交互主观关系决定的——只有我为人人,才能人人为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承认由个人做出的鉴赏判断应该具有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那就只有按照人与人之间先验的交互主观关系的普遍性来判断,才能让自己的鉴赏判断产生的个人情感成为应该得到每个他人赞同的普遍情感,才能让这样的普遍情感成为自由的美感。这个普遍性不是在经验统计意义上的绝大多数,而是在先验感性意义上的真正普遍性。因此,对鉴赏判断而言,“虽然谓词(即与表象结合着的自己的愉快这一谓词)是经验性的,然而就其向每个人所要求的同意而言却是先天判断或者想要被看作先天判断”(41)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39.重点原有。。鉴赏判断之所以不是直接的感性学判断而是反思的感性学判断,也是因为它不是直接从鉴赏者个人的感觉和概念认识出发,而是只有从“美”的先验反思立场出发来做判断,才能做出“美”的判断。如果这种愉快是无须概念而普遍地让人喜欢的东西,甚至是无须概念就被认作必然让人喜欢(notwendigen Wohlgefallen)的东西(42)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58, S.82.,它就是一种自由的“美”。
四、鉴赏判断的自由根据
因而,要想“断言美”(claimingbeauty)(43)Arata Hamawaki, “Kant on Beauty and the Normative Force of Feeling”, in Philosophical Topics, Vol. 34, No. 1/2, 2006, p.116.,就必须按照自由的根据来进行反思的判断,让由此产生的美感在先验感性的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即自由意义上的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简言之,鉴赏判断应该具备这样的自由根据:
一方面,在表象方式的感知层面依据形式上的合目的性。鉴赏者不考虑歌谣的认识目的、实用目的和创作目的,而是仅仅反思歌谣表象在形式上的主观合目的性。(44)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68;康德写道:“一个单称的经验判断,例如在一块水晶里发觉有一滴流动的水珠的人,有权要求其他任何一个人必定同样发现这一点,因为他是按照规定性的判断力的普遍条件而在可能经验的一般规律之下作出这一判断的。同样,一个人在对某个对象的形式的单纯反思中没有考虑到概念而感到愉快,尽管这个判断是经验性的而且是单称判断,他也有权要求每个人的同意;因为这种愉快的根据是在反思性判断的普遍的、尽管是主观的条件中,也就是在一个对象(不论它是自然的产物还是艺术的产物)与诸认识能力相互关系之间的合目的性协调一致中被发现的,这些认识能力是对(想象力的和知性的)任何一个经验性的知识所要求的。因而鉴赏判断中的愉快虽然依赖于某个经验性的表象,并且不能先天地与任何概念相结合(人们不能先天地规定何种对象将适合还是不适合于鉴赏,人们必须品尝它);但愉快之所以是这个判断的规定根据,毕竟只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它仅仅基于反思及其与一般客体知识协调一致的普遍的、虽然只是主观的诸条件之上,对这种反思来说客体的形式是合目的的”(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28-29)。这是被反思到的一种主观的形式合目的性,也叫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因为一切目的都受概念的规定,合目的性却是无须概念而使想象力与知性通过自由游戏产生的和谐关系,通过对这种和谐关系的反思产生的愉快情感才是“美”的,这就要求“各种认识能力在某个对象借以被给予的某个表象这里的自由游戏的这种状态,必须是能够普遍分享或传达的”(45)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56.。正因为这种和谐关系让想象力摆脱知性概念的制约而获得自由并且在这种自由中与知性保持和谐关系,所以这就完全解放了想象力,让想象力既不为认识能力效力也不为欲求能力效力,而是无功利、无目的地与这两种能力处于自由游戏的状态,所以,由此产生的美感才是能够让每个他人普遍可分享的。具体而言,歌谣的表象方式在形式上的合目的性就是摆脱感觉内容和概念而使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达至和谐的内心状态,而这种内心状态应该使每个他人产生愉快情感。我作为反思的鉴赏者仿佛只是替每个他人判断并说出了这种应该得到每个他人赞同的个人情感,正因如此,这种情感才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因而是自由的美感。
另一方面,在交互主观的分享和传达层面依据“共通感”(46)德语是Gemeinsinn,拉丁语是sensus communis,邓晓芒译为“共通感”,李秋零译为“共感”。关于这个德语词的概念史梳理,参见Joachim Ritter (Hg.),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Schwabe & Co., Verlag, 1974, S.243-246.理念。如果歌谣的鉴赏判断产生的美感是普遍可分享或可传达的,那就先验地需要每个他人都应该具备一种共通感。所谓“共通感”是一种共享的鉴赏力理念,它指的是在对表象方式的反思中摆脱主观的私人条件可能对判断产生的不利影响、从而置身于每个他人的位置上来进行判断的能力,也就是“把在表象状态中是质料即感觉的东西尽可能除去,仅仅注意自己的表象或表象状态的形式上的特性”(47)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44-145.的能力。共享的鉴赏力(gemeinschaftlicheSinn)不仅仅是共同的鉴赏力(gemeineSinn),用英文来说,即communal sense不仅仅是common sense(48)参见Albert Hofstadter, “Kant’s Aesthetic Revolution”, in The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 3, No. 2, 1975, P.182;阿伦特主张把gemeinschaftlicher Sinn译为“共同体感”(参见[德]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115页)。但在康德的语境里,这个译法过于政治化。本文不在“美是自由的象征”意义上讨论美感何以得自由,而且限于篇幅,本文暂不涉及审美与道德、政治的关系问题。,它指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先验地享有却在经验上或然地具有的鉴赏能力。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在先验反思的意义上而不能在经验心理学的意义上理解共通感或共享的鉴赏力。
共享的鉴赏力意味着应该从适合并适用于每个人的普遍感性层面来反思表象形式的合目的性,这也就需要以每个人都能够具有“共通感”为逻辑上的前提条件。由此来看,对合目的性形式的反思判断能力与共通感是一种共同的感性形式能力,可以把它们看作同一种自由理念即共享的鉴赏力理念,因为只有站在共通感的立场上才能反思到这种普遍有效的合目的性形式,才能让美感成为普遍可分享或可传达的。共通感并非偶然的经验假设和实证结论,而是必然的先验预设和理性要求。“预设”,康德用的动词是voraussetzen,意即相信某种东西是可靠的或存在的、要求某种东西是另一种东西的必然条件。(49)参见叶本度主编:《朗氏德汉双解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905页。既然美感是普遍可分享或可传达的,那么共通感“就无须立足于心理学的观察之上,而是必须被预设为我们知识的普遍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的必要条件,这种普遍可分享性或可传达性是在任何逻辑和任何并非怀疑论的认识原则中都必须被预设的”(50)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81.。共通感不是逻辑论证的经验对象,而是逻辑论证的先验前提。(51)恰恰从先验的逻辑层面来看,康德并没有进行循环论证,因而我不大同意如下理解:“康德并没有对共通感概念的实在性予以论证,而只是出于对鉴赏概念进行先验分析的需要,将其作为一种可能性被设定出来了。它不能作为知识的充分条件被确定下来,进而为论证审美的必然普遍性做贡献,而只是作为鉴赏的必要条件被引入,也仅为了更全面地展示鉴赏的必然普遍的属性。这样,共通感当然不能作为论证鉴赏判断之普遍有效性的根据,因为它自身的有效性反倒是被后者赋予的”(周黄正蜜:《论康德的审美共通感》,《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康德请出来的‘审美共通感’是一种设定,是一种假设,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而对‘审美共通感’存在的论证也显得比较粗糙,令人难以信服,这也是康德美学一直造[遭]人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胡友峰:《论康德鉴赏判断的先验理据》,《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2期)。
由此来看,歌谣的鉴赏判断始于主观经验,它的根据却并非源于主观经验。首先,从立场来看,只有基于每个他人都能够具有的共通感来做出感性学的反思判断,才能站在每个他人的位置上,即仿佛站在人类共享鉴赏力的位置上进行自由判断,如果这是一种换位思考,那么这时候与判断者换位的就不仅仅是某个他人,而是每一个他人;其次,从形式来看,应该尽可能超越个人喜好和感觉,只关注表象的合目的性形式。因此,鉴赏判断的感性学反思关注的不是表象的内容与我们的利害关系,而是表象的形式给我们的各种官能造成的和谐关系。歌谣的鉴赏判断并不关心某首歌谣的用处以及它的内容是否健康、是否粗俗(52)1928年,钟敬文因为经手付印夹杂“秽亵歌谣”的《吴歌乙集》而被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辞退(参见施爱东:《私情歌谣与〈吴歌乙集〉风波》,《民俗研究》2001年第3期;施爱东:《顾颉刚、钟敬文与“猥亵歌谣”》,《读书》2014年第7期),假如当时的校长能够站在鉴赏判断的立场,这样的事情就可能避免。,而是判断它是否具有形式上的主观合目的性、能否引起普遍可分享或可传达的自由美感。
当此之时,歌谣的鉴赏判断又有纯粹的和应用的之分。纯粹的鉴赏判断不考虑歌谣应该是什么的目的概念以及歌谣自身的目的,让知性为想象力服务并且让想象力获得解放,所判断的是歌谣的自由美;相反,应用的鉴赏判断以歌谣应该是什么的目的概念为条件并且顾及歌谣自身的目的,让想象力为知性效力,所判断的是歌谣的依附美。(53)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69-72.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差别也取决于歌谣被看作自然产物还是人工制品。如果认为歌谣是人为创作、传唱、表演和鉴赏的对象,“歌谣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全是自然的流露;它有它的传统的技巧,有它的艺术的意识。它一方面流转无定,一方面也最富于守旧性”(54)朱光潜:《从研究歌谣后我对于诗的形式问题意见的变迁》,《歌谣》第2卷第2期,1936年4月11日。,那么,对这种歌谣的鉴赏判断就以歌谣应该是什么的目的概念为条件,这种判断就不够纯粹,就是一种应用的鉴赏判断,由此产生的就是依附的美而不是自由的美。反之,如果认为歌谣是天籁之音,正如邵纯熙指出的那样,“人类处天地之间,耳鼓中充斥自然的音响。遇着春日,万花齐放,红绿争艳;那一般的小鸟,飞来飞去,极为得意。叶底林末,鸣声喈喈。即是韩愈所说的‘以鸟鸣春’……自然界的声音既如此复杂,人类的情绪,于不知不觉间,起了一种感想。遇着欢喜的事情,便唱出一种语调,表现欢喜的状态。遇着忿怒的事情,复唱出一种语调,表现忿怒的状态。如是则悲哀时表现悲哀,恐惧时表现恐惧,亲爱时表现亲爱,恶憎时表现恶憎,欲望时表现欲望。所以农人在田野间,高唱秧歌,渔人在江湖间,高唱渔歌。闺女小孩则在房屋中唱歌,游人旅客则在深林旷野唱歌。都就自然界的音响,以为志喜遣怒举哀示惧可爱可恶可欲之事情。我以为歌谣的起原[源]是如此。现在我又想到歌谣二字的意义,尚有商确[榷]的余地。歌字的意义,是咏的意思,引长其声之谓;以曲合乐唱之者。徒歌而无章曲者,是名曰谣,从此看来,歌谣二字的意义,既然有区别,自不能混为一起。”(55)邵纯熙:《我对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见》,《歌谣》第13号,1923年4月8日。如果认为“歌谣是社会上的人情风俗……驱使他,使他自自然然的产生出来”(56)孙少仙:《研究歌谣应该打破的几个观念》,《歌谣》第43号,1924年1月27日。,如果认为“歌谣本是从穷乡僻壤间,毫无知识的平民的待遇和感觉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的词句中,很是自然的,并且还是丝毫不知避讳”(57)杨德瑞:《读歌谣周刊后所采集的几种歌谣》,《歌谣》第44号,1924年2月24日。,那么对歌谣的鉴赏判断就无须考虑歌谣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和歌谣自身的目的概念,这种判断就是纯粹的鉴赏判断。
虽然应用的鉴赏判断不如纯粹的鉴赏判断自由和纯粹,但它也应该有自由的判断根据并且应该关注歌谣的形式。这里需要区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歌谣自身具有的韵律、节奏等客观的形式,另一种是这种客观的形式给演唱者、听众和读者带来的主观合目的形式。前一种形式是有形的、可感的,是能够诉诸声调和言语的,后一种形式则是无形的、不可感的,是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比较而言,前者具有非反思的、直接的、客观的普遍性,能够成为研究和认识的对象,而后者具有反思的、间接的、主观的普遍性,是歌谣的鉴赏判断应该反思的主观形式。这两种形式或有重叠,却有所不同。例如,杨世清曾指出:
歌谣是有韵的,所以音节的美,在歌谣艺术里边,占很重要的位置。往往有些歌谣,并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凑几个顺口的韵脚,使唱的人唱得好听罢了。例如吾乡的(河南新乡)的《小老鸹歌》:
小老鸹,齐打滚,
说他男人不买粉,
买了粉,不会擦,
说他男人不买麻,
买了麻,不会搓,
说他男人不买锅,
(下略)(58)杨世清:《怎样研究歌谣》,《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
首先,从形式上来看,这首歌谣以“并没有什么意义”的叠句形式表明,尽管歌谣的美感在感性上的确可能受到意蕴的影响,但在鉴赏判断中,歌谣的美感重在演唱和诵读歌谣时通过朗朗上口的韵律、节奏等客观形式产生一种令每个人赏心悦目的主观合目的形式。因此,尤其是演唱的歌谣,即便对不懂汉语因而无法理解歌谣含义的人而言,也照样能够通过对这种“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的客观形式的感知和鉴赏判断产生一种主观合目的形式美感。正是在演唱和表演而不仅仅是读懂的意义上,李素英的如下断言才更站得住脚:“吴歌里确是一致地充溢着一种希有的灵秀之气,婉妙之情;任何人读了都会觉得神志清明,中心愉悦,何况‘吴侬软语’一向是被认为声调最优美的方言!”(59)李素英:《吴歌的特质》,《歌谣》第2卷第2期,1936年4月11日。这也正是赫尔德在《民歌》中所谓“歌的本质是唱”,“歌一定是被听的,不是被看的;用灵魂的耳朵来听……”(60)户晓辉:《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9、90页。。这种唱出和听出的“灵秀之气”和“婉妙之情”具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主观合目的形式,或者说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主观合目的形式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灵秀之气”和“婉妙之情”。
其次,从性质上来看,如果我把这首歌谣看作有目的和有意义(尽管它的意义显得游移不定甚至含糊其辞)的创作,那么我对它的鉴赏就是应用的鉴赏判断;如果我认为这首歌谣中忽而肯定、忽而否定的说辞并没有确指的含义,反倒更接近无内容的、无意义的叠句形式,这种叠句形式好像并没有客观的目的,只有对鉴赏者而言的主观合目的形式;或者,即便有目的,好像也仅仅是为了“好听”和“逗你玩”,那么,我就无须考虑这首歌谣的内容和创作目的,我既不关心它的作者是谁以及它的实用性何在,也不想认识它在结构、韵脚等等方面的完善性,更不会拿它当吃当喝,而只是把这首歌谣看作妙肖自然的天籁之音,如风行水上、浑然天成且不择地而出,这时,我仅仅反思它的表象方式能否给每个人带来主观合目的形式,由此对它做出纯粹的鉴赏判断。
尽管应用的鉴赏判断在纯粹性和自由度上不如纯粹的鉴赏判断,但它们都应该以自由的判断根据为准绳,从而共同区别于歌谣的适意判断。当我说“这首歌谣是适意的”时,我只需考虑这个判断内容对我有效即可,这时我是在逻辑上先感到适意然后再进行判断。但是,当我说“这首歌谣是美的”时,无论我做出的是纯粹的还是应用的鉴赏判断,我都不仅要考虑它对我个人的主观有效性,更要反思它对每个其他人的主观有效性,这时我在逻辑上是先进行判断然后形成愉快情感。也就是说,我先反思到这首歌谣的表象形式给我带来的心灵和谐关系具有普遍可分享或普遍可传达的主观合目的形式,然后才产生对它的愉快情感。(61)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55-58, S.131-132;程培英:《对对象之评判与对对象之愉悦的情感的先后问题何以可能是“理解纯粹鉴赏判断的钥匙”?——以〈判断力批判〉第九节为基础,对康德纯粹鉴赏判断原理之阐明思路的深入分析》,《兰州学刊》2018年第2期。这时,美的愉快情感依赖的不是概念而是反思,由此产生的情感既不依靠概念又摆脱了我自己的适意和偏好,因而是一种自由的美感。这种美感具有使每个人都愉快的自由根据,我作为鉴赏者应该以这种自由根据来做判断,也就是应该站在每个他人的位置上做出反思判断。这时候,我必须把我的愉快情感看作是由我“也能够在任何别人那里所预设的东西引起的”(62)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48.。这就意味着,鉴赏者个人的教养或文化不仅与人类的文化密切相连,而且是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发生的。(63)参见Bradley Murray, The Possibility of Culture: Pleasure and Moral Development in Kant’s Aesthetics,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5, p.2.鉴赏者应该努力在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个他人在思想中的表象方式,把自己的判断持守在每个他人都可能先验地具有的判断而不是在主观体验中实际具有的判断上,也就是仿佛(gleichsam)持守在所有的人类理性(die gesamte Menschenvernunft)上(64)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44-145;Gathleen Muehleck-Müller, Schönheit und Freiheit. Die Vollendung der Moderne in der Kunst; Schiller-Kant, Königshausen & Neumann, 1989, S.44.,即便做不到绝对、也应该“仿佛”绝对地持守在这个层面上。这时,鉴赏者不是站在自己的私人立场来直接看,而是站在人类理性立场来反思并且依据共通感来自由地判断,由此产生的才是应该得到每个他人赞同的、在个人体验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情感,也就是自由的美感。
每一个鉴赏判断都应该是依据共通感来自由判断的一个范例。(65)正因如此,康德才说:“在我们借以宣布某物为美的一切判断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有别的意见;但我们仍然不把我们的判断建立在概念之上,而是仅仅建立在我们的感性之上,因此,我们不是把这种感性作为私人感性,而是作为一种共享的感性奠定为基础的。那么,为此目的,这种共通感就不能被建立在经验之上;因为它要授权人们做出包含着一个应当的判断:它说的不是每个人都将与我们的判断一致,而是每个人都应当与它一致。因此,我在这里把我的鉴赏判断说成是共通感的判断的一个实例,因而我赋予它示范的有效性,{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单纯的理想范式,在它的前提之下,人们就能够有理由使一个与它一致的判断以及在该判断中表达出来的对一个客体的愉悦对每个人都成为规则:因为虽然原则仅仅是主观的,却仍然被假定为主观上普遍的(一个对每个人都必然的理念),在涉及不同判断者的一致性时,只要人们肯定已经正确地将之归摄于这个原则之下,就能够像一个客观的{原则}那样要求普遍的赞同”(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81)。“共通感”虽然是被预设的纯粹理念即“人性的超感性基底”或我们身上“超感性东西的不确定理念”(66)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99.,但每个想要做出鉴赏判断的人都必须在自己内部产生出这种作为鉴赏原型的理念,而不能通过模仿他人来获得。鉴赏者应该追随做出典范式鉴赏判断的先行者,即“从那个先行者自己曾经汲取的同一个源泉汲取,并且向他的先行者仅仅学习在这方面的行事方式”(67)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33.。这就要求鉴赏者超出经验因果范围,从自己内部发现先验感性层面的自由要求。也就是说,鉴赏判断的自由根据是判断力自我立法的一种先天规定性,并不等于实际的鉴赏判断过程。尽管在做出鉴赏判断时常常夹杂着鉴赏者的个人感受、鉴赏者对歌谣的实存的兴趣、理智的兴趣或实用的偏好,但这些经验性的东西不该被当作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68)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47-148.歌谣的鉴赏判断是否纯粹,主要看它的判断根据是否纯粹,而不是要求它完全脱离鉴赏者的个人体验。无论在歌谣的鉴赏判断过程中有多少经验成分,鉴赏者都应该并且能够按照鉴赏判断的自由根据来进行判断,并以此衡量鉴赏者做到什么程度。做到的程度越高,由此产生的情感就越自由。
五、结语:在先验感性层面培养公共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尽管应用的鉴赏判断在纯粹性和自由度方面比不上纯粹的鉴赏判断,但它们都是通过反思的判断力练习自由的有效途径。因为无概念、无功利和自由的鉴赏判断磨练的不仅是普遍化和公共化的感性能力和判断力,而且是站在理性立场来看待并思考公共事物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康德所谓公共的思维方式(öffentliche Denkungsart),它体现为三个准则,即自己独立思考(知性准则)、站在每个他人的位置上思考(判断力准则)和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考(理性准则)。(69)参见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Verlag von Felix Meiner, 1922, S.145-146.第二个准则是判断力通过站在每个他人的位置上反思所带来的被扩展的思维方式(erweiterte Denkungsart)。所谓站在每个他人的位置上,就是站在真正的普遍性立场上,为自己的特殊情感寻找到主观的普遍规则,只有这样才能带来被扩展的思维方式,才能进行纯粹的鉴赏判断并且产生自由的美感。这在歌谣的鉴赏判断中体现为:一方面,抽离和净化的反思程序能够使鉴赏者摆脱主观偏好,保证感性学的活动在不受感官兴趣影响的意义上独立自主,实现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或者说从鉴赏者内在层面使经验性的自我逐步提升到与自己一致的先验自我和理性自我状态;另一方面,社交性的反思程序能够使鉴赏者的想象力得到扩展,知性得到增强,逐步达到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也就是使鉴赏者超越自身体验的有限性而达成一种公共性和普遍性。(70)参见周黄正蜜:《向普遍性的提升——康德论教化与艺术文化的融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歌谣乃至民间文学的鉴赏判断无论是纯粹的还是应用的,都能够超越感官欣赏的主观性和私人性,恢复美感的公共性和普遍可分享性。(71)约翰内斯·凯恩堡在《伊曼努尔·康德与理性的公共性》一书中认为,感性学的公共性是康德继公民的、理论的和实践的公共性之后的第四种和最后一种公共性。参见Johannes Keienburg, Immanuel Kant und die Öffentlichkeit der Vernunft,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2011, S.186.只有达到这种公共性和普遍可分享性,我们的判断力才能摆脱各种主观偏见和条条框框的束缚而臻于自由之境。也只有这样,审美才不是沦落于社会边缘且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关乎每个人的理性成长和思想自由的大事。
由于歌谣的鉴赏判断无关乎知识水平的高低和欲求能力的大小,因此,普通民众即便搞不懂鉴赏判断的先验原理,也完全能够对歌谣做出鉴赏判断,这就表明,这种诉诸先验感性能力的审美启蒙比单纯经验性的知识启蒙更容易、更优先。通过歌谣的鉴赏判断来培养健全的判断力和理性的公共思维方式,是实现从私民到公民转变的一条主观必然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