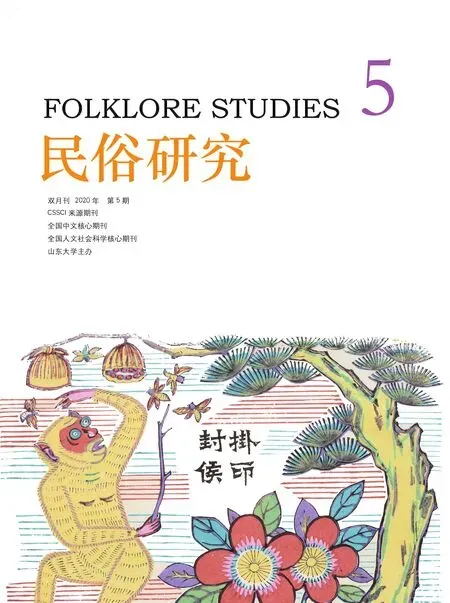匮乏与获取:龙王结亲传说的社会隐喻
郭俊红
20世纪的中国传说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范式:一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历史流变研究,这类研究着重勾勒传说或传说类型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努力解说这些变化的原因;二是以刘守华先生为代表的形态机能研究,这种研究不区分“传说”与“故事”,将传说视为与故事无异的材料,研究者将某些传说类型从各自的时空背景中抽离出来,进行共时态的形态分析;三是意义审美研究,即将某一传说类型的诸多异文当作一个共同体,对其整体的或局部的情节进行广义的文化阐释和美学判断,这三类研究皆以文字记录的文本为研究对象,对于生产、传承、消费这些文本的“人”及“语境”缺少关注。
20世纪末,受西方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影响,国内的民间传说研究者开始关注传说演述的“语境”和传说的“讲述者”,他们走入田野,从区域内的日常生活中考察各类传说及其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赵世瑜的识宝传说(1)参见赵世瑜:《识宝传说:一个关于本土和异域的华北民间历史隐喻》,《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164页。、移民传说(2)参见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皆属此类,这类研究关注了传说产生的语境,但征引的传说却还是侧重文字记录本身,鲜少使用研究者自己深入田野搜集的活态文本。叶涛、陈泳超的研究在关注传说“语境”的同时特别注意搜集活态文本,他们用这些活态口述文本考察当地社会的诸多面向,叶涛借助山东沂源的牛郎织女传说探讨地方的家族、信仰以及民众的日常生活(3)参见叶涛:《民间文献与民间传说的在地化研究——以沂源牛郎织女传说为中心的探讨》,《民族艺术》2016年第4期。;陈泳超借山西洪洞“二妃身份传说”及当地的“接姑姑迎娘娘”仪式不仅探讨传说在地方人群中的作用,还解析地方社会中人群主体性的建构实践,更关注这些活态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动力机制,与其说这种研究是对传说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传说演述的地方社会的社会学研究。(4)参见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近年来,民间传说(属于广义上的民间故事)日益引起其它学科的关注,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王明珂将岷江上游地区的“毒药猫”故事置于村落结构、资源竞争框架内加以解读(5)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77-113页。,龙圣、李向振把我国西南地区的“变婆”故事与区域开发、族群认同等社会背景进行联系,认为该故事是民间对现实生活中被驱赶和被活埋的两类病患及其命运的隐喻。(6)参见龙圣、李向振:《病患:变婆故事的社会隐喻》,《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这些传说故事因为有了具体的社会情境而变得更容易理解。受上述研究成果启发,笔者从生产资源缺乏和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缺乏这一社会视角出发,对山西民间广为流传的“龙王结亲”故事进行分析,所援引分析的传说文本不止记录在地方文献中的文字记录文本,还有笔者深入田野搜集的活态口述文本,旨在得出传说不止是地方性知识,还生产“地方性知识”,并且它依托这些地方性知识不断地被“生产”着。
一、龙王结亲类型传说
山西有丰富的与龙相关的传说故事,这主要是由特殊的地理条件以及气候环境造成的。山西境内地形复杂,气候干旱,民众的生产生活无不受水的掣肘,雨水成为重要的资源补给。当地民众认为,雨水的水量多寡与降雨时机都由龙王掌控,“泽州县南岭乡的李沟村,过去有个龙王庙,能预示风雨旱涝。庙前青石小池,清澈见底。池水若在小池的三分之二处,两条小鱼在水中欢快地往来嬉戏,必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池水若低于三分之一,两条小鱼沉入水底不动,必定是大旱之年。池水若涌出小池,小鱼不断跃出水面,必定阴风怒吼,连降暴雨,山洪暴发,水害不断”(7)《秃闺女嫁给龙王爷》,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33-134页。。如此一来,民众对雨水的仰赖就转化为对龙王的崇信,龙王成为山西民众最重要的崇奉偶像。清道光十二年(1832),沁水县南沟社制定祭祀诸神的条规,明确规定全社每年祭祀诸神十六次,而以龙神为主的祭祀就多达三次。(8)条规中规定四月十五祭祀白龙、五月初一祭祀龙王、五月十九祭祀龙王。此碑现存于沁水县龙港镇南瑶村大庙内。碑文引自车国梁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337页。
在地域生活中,民众借助各种各样的龙王传说故事来表达对龙王的尊崇以及龙王对他们生活造成的影响。按照不同的叙事情节,山西境内流传的龙王叙事(9)本文所引用的传说文本材料均来自于山西省各地市县的《民间故事集成》,这些资料均为内部资料,没有明确的编著者以及出版信息。引用资料主要有:《大同民间故事集成》(1989)、《忻州地区民间故事集成》(1987)、《襄汾民间故事集成》(1987)、《曲沃民间文学三套集成》(1987)、《阳泉市民间故事集成》(1989)、《长治市民间故事集成》(1988)、《浮山民间故事集成》(1986)、《平定民间故事集成》(1988)、《尧都故事》(1989)、《永和故事、民谚、歌谣选》(1989)、《晋中民间故事集成》(1990)、《长治县民间故事集成》(1988)、《临汾市民间故事集成》(1989)、《夏县民间文学集成》(1987)、《永济传说》(1993)等。下文列举故事叙事内容时不再一一详细说明文献出处。可以分为龙王报恩类型(10)这类故事的内容情节与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所列内容基本相同,灵石民间传说《撒金钱救老龙》、大同市《玉龙洞》、乡宁县《龙女的故事》等都属此类型。、龙母型(11)此类故事的内容情节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没有列出,但其内容情节与山东省、黑龙江省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内容情节相近,故事内容主要强调平凡女子神奇受孕,诞下龙子,与山东地区《秃尾巴老李》传说强调龙子降雨不同,山西的这类传说重点强调诞下龙子的龙母兴云造雨,造福一方的功绩。山阴县《九龙湾的传说》、寿阳县《五龙洞和五龙圣母庙》、盂县《五龙圣母》、平顶县《五龙庙的传说》、古县《龙母沟的传说》、汾西县《五龙山的传说》、文水县《九龙圣母的传说》、岚县《上明龙灯的传说》、武乡县《灵湫洞的传说》等都属此类型。、龙子神奇出生型(12)这类传说类型与龙母型故事的内容情节相近,但故事结尾强调的重点不同。龙母型故事强调凡间女子因神奇受孕,诞下龙子后成为龙母,她具有了神奇的法术,被一方百姓尊崇,龙母本身成为当地百姓崇信的对象,围绕龙母形成信仰与庙会;而龙子神奇出生型故事的结尾重点强调神奇出生后的龙子具有庇佑一方的超能力,当地百姓围绕龙子形成龙王信仰与庙会。忻州市《翠珠与白龙》、朔州市《神头三大王的传说》、临汾市《五龙宫》。这种类型常常与龙母型粘合在一起。、恶龙作祟型(13)此类故事的内容情节在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没有明显体现,此类型的主要内容为龙是造成干旱或洪涝的原因,危害一方百姓。如襄垣县《九龙和常隆》、长治市《桃花女逐龙救百姓》。、斩龙型(14)这类故事受通俗文学影响颇深,主要内容为魏征无私斩杀触犯天条的龙王。朔州市《魏征梦中斩老龙》、阳城县《魏征圣王坪怒斩泾河小龙王》、沁县《耍龙灯的传说》等。、龙斗型(15)这类故事又可以细分为善龙/恶龙相斗型和善人/恶龙相斗型,主要内容为恶龙为逞私欲,降暴雨或者不降雨,祸害百姓,善龙或者具有正义感的凡人出于保护百姓的意愿,与恶龙相斗,最后牺牲,当地百姓为了感谢善龙或者善人,修建某座建筑或者形成某种风俗以资纪念。善龙/恶龙相斗型的传说有:浮山县《龙骨沟》、曲沃县《西海龙王庙和温泉》、临汾市《乌龙潭》、浮山县《除恶龙》、夏县《五龙庙》、夏县《涑水河的传说》、沁源县《五龙庙里四条龙》、永济县《黄龙庄》、襄垣县《龙女报善惩恶》、大同市《独角龙的传说》;善人/恶龙相斗型的传说有:偏关县《石湖龙的传说》、曲沃县《七星海的传说》、平定县《五龙二虎一条鱼》、浮山县《圣母娘娘降恶龙》、霍县《白龙村的传说》、安泽县《南子斩恶龙的故事》、蒲县《吕梁山的来历》、平遥县《擒龙夺水》、忻州市《斩石龙》、长治市《桃花女逐龙救百姓》、沁县《五龙》、襄垣县《九龙和常隆》。等故事类型。在这些故事类型中,“龙母型”故事类型流传最广,最为民众熟悉。有关“龙妻”的故事却并不多见,笔者在精读传说文本的基础上,概括出其主要情节内容为:
1.村中有普通女子,因某种原因离开村落或者离奇死去。
2.村中的人在某个水潭发现她的遗物。
3.女子露出水面或者托梦告诉村民,自己已经嫁给水潭内的龙王,村民若遇干旱,可到此地祈雨。
4.某年村庄发生干旱,村民听从女子的建议,到女子所言的龙潭祈雨。
5.祈雨异常灵验,且女子所属的家族和村落在同区域内的祈雨仪式中具有主导权。
这类传说与以往的“人兽婚”不同,其讲述重点不在生育和族的繁衍(16)参见王宪昭:《中国北方民族神话人兽婚母题探微》,《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而在后半部分的“祈雨灵验”,即神圣的龙王与凡间普通女子结为夫妻后,龙妻的人间娘家一劳永逸地获得了龙王赐予的雨水。“从此以后,千百年来,每当遇到天旱不雨时,北次营村人就带上那四个瓶子来这末末潭求雨,每次都有求必应,打潭后不过三天,北次营一带必降喜雨。”(17)《投凡胎黑女嫁龙王》,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有的故事还会继续生发,讲述龙妻所属的家族或村落据此在区域社会举行祈雨仪式时拥有祈雨组织领导权,“当地起了农历四月初三庙会。说来也真神,从此,祈雨有求必应,无一落空。祈雨的风俗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赵家是祈雨的主持者,任何人都不能代替”。(18)赵雪梅主编:《南村镇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8-169页。更有甚者还会谈到龙妻娘家村落据此在区域社会中成为村落交往中心,形成市镇,陵川县夺火村董氏家族因为其女儿嫁给龙王,致使夺火村成为当地“一镇八庄十二全庄”的交往中心。(19)访谈对象:张贵红;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5年10月20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镇夺火村李忠仁家。在传说的言说中以及仪式性馈赠的流动中,多村落的仪式联合得以建构和生产,成为区域集体仪式、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龙妻:给神的礼物
龙王结亲传说中的“人神结亲”之说违背自然规律,让人难以理解。那么,为何民间却又传之不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涉及人类对缺乏生产资源的恐惧以及对如何获取资源的思考。
传统社会中,农业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有学者指出,农业生态系统的变化(恶化和改善)主要通过水的作用来实现,“人类面临的第一个生态问题就是水分亏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居于首位。据估计,在世界范围内,干旱缺水对农业和社会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其他各自然灾害造成损失之总和”(20)山仑、黄占斌、张岁岐编著:《节水农业》,暨南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旱灾(尤其是特大旱灾)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是任何其它自然灾害都无法比拟的。降水量下降100毫米,粮食产量就会下降10%。(21)参见张家诚:《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初探》,《地理研究》1982年第2期。更为严重的是,旱灾发生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蝗灾,“旱极而蝗是一个客观规律”(22)郑云飞:《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分析》,《中国农史》1990年第4期。,这会给农业生产造成致命性的打击。龙王结亲传说的生成背景就是农业社会中民众对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资源匮乏的恐惧,尤以水为甚。面对旱灾的侵扰,人们往往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于是求助神秘力量的帮助,衍生出各种求雨仪式。
山西境内环山林立,山高沟深,开发利用境内的支流减缓旱情几乎不太可能。对于山西百姓来说,将希望寄托于行云布雨的龙王反倒成了一种可行的解决途径。但如何才能长期有效地建立这种沟通机制呢?男子赤身求雨、寡妇求雨、独闺女求雨、苦求雨、骂龙王等求雨方式应运而生。在这些求雨方式中,民众胆战心惊地遵守着各种禁忌,稍有“差错”,龙王便不予理睬,不施甘霖。(23)与山西各地丰富多样的求雨仪式相一致的是这些仪式总是充满了禁忌,比如不能男女同房、女性不能自由出入等,在描述求雨失败的民间传说中也总是提到某人触犯了禁忌导致求雨失败。诸法之中,民众掌握了一种屡试不爽的求雨方法——与龙王结亲,将人间凡俗女子作为礼物贡献给龙王,用女子来换取龙王的降雨。陵川县有些地区的祈雨仪式就属此类。“首先由当地绅士主持选龙妃,全村人所出粮钱,由龙妃取得。选妃要到龙王庙抽签,祈祷完毕后,让村里未婚女子排成一行,抬头端立,请龙王爷挑选,谁中选谁就是龙妃,龙妃选定后,祁(应为‘祈’,笔者注)雨的人抬上龙王偶像和头戴凤冠、身穿绣裙的龙妃,到龙王祠求雨。摆上供桌,放上猪头等供品,再斟上酒,磕头祈祷。接下来,是龙妃摸雨,栽十个木桩,拿来十个大碗放在木桩上面,五个有水,五个无水。龙妃用布蒙住双眼,用手去摸,若摸见有水的碗,就意味着有雨,大吉大利。如摸着空碗,就意味着无雨,在这种情况下,就痛打龙妃,让龙王爷动心,赐下雨来。”(24)陵川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陵川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编:《陵川民俗》,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243页。
传说中,被嫁给龙王的凡间女子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容貌美丽的女性,“润城镇明以前叫小城,小城村有位张员外,心地善良,为人热情厚道,家里种几十顷地,身边只有一独生女,如花似玉,聪明伶俐”(25)《小黑龙乘龙快婿》,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但这种文本数量不多;另一类是心灵手巧但容貌欠佳的女子,她们在未与龙王结亲之前,被唤作“黑女”“秃闺女”“憨女”“秃姑姑”“黑姑姑”等,出身贫寒,甚至没有父母,寄身于哥嫂家中,遭到嫂嫂虐待,可以被视为家中的“多余人”。“马邑村有个女子,长得又黑又丑,人们都叫她黑姑。黑姑自幼失去双亲,跟着哥嫂度日,嫂嫂经常刁难她,哥哥也不敢惹这母夜叉。有一天,嫂嫂让黑姑去放牛,又给她五斤棉花让她纺线。嫂嫂恶狠狠地说:‘纺不完棉花就别回来吃饭。’”(26)《黑姑姑与龙王爷》,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43页。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需要而不是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而存在,下层妇女跻身上流社会或自主选择命运的唯一可能就是拥有倾倒男人的性魅力——美貌。(27)参见施爱东:《英雄杀嫂——从“萧峰杀敏”看金庸小说对传统英雄母题的继承和改造》,《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但是在传说中,为什么与龙王结亲的却多是肤黑貌丑的女性呢?这可能与龙王在世人心目中的位置有关。传说中,龙王以“龙”“蟒”“蛇”的动物形象示人,奇丑无比,它虽然具有行云布雨的能力,但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低人一等的“动物”,虽然它有时可以幻化为人形,但终究是“动物”,它们这种精怪、妖异的变化违反了认识原则和宇宙秩序。(28)访谈对象:刘建平;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7年12月16日;访谈地点:晋城市城区。物类间的互变、互化,触犯了生命繁殖的秩序。人们对其的认识也就从“非常”转向具有负面语意的“反常”。认为物精变化成的“人”冒犯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本质尊严。其对男女两性所造成的“性的侵犯”,颠覆了人类的家庭、社会秩序,从而根本上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秩序。(29)参见李丰懋:《神化与变异:一个“常与非常”的文化思维》,中华书局,2010年。这些貌丑的女子对于娘家来说也是“多余人”,在人世间原本也找不到接受她们的男子,因此把她们作为“交换资源”嫁给龙王,既能满足龙王求娶妻子的需求,又可以与龙神建立“关系”,更能解决这些“剩女”的出嫁问题,可谓是“一举多得”。
凡间女子嫁给龙王意味着从凡俗进入神圣世界。传说中,女子与龙王的结亲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类是龙王来到人间,化身为人形男子,或主动示好女子,或在与女子的相处中二人互生好感,私定终身,或凭借自己的容貌、能力获得人间女子和其家长的赞许。“有一天,月仙姑娘到村前的小河潭去担水,突然河水翻滚,一阵狂风起,一条大黑蛇朝她爬来,吓得她丢下水桶就跑,一连几天都不敢去担水。过了几天,月仙的爹娘又催月仙去担水,月仙担上水桶,硬着头皮朝河边走去。到了河边,河岸上有一个标致的小伙子见她打水,便走过来帮忙。小伙子对月仙表明心意,愿意给她当丈夫,愿意侍奉月仙的双亲。月仙说:‘天下大旱,粮食颗粒未收,现在还不是时候。’小伙子告诉月仙,只要跟了他,天就能下雨。月仙听了小伙子的话,信以为真,就与小伙子成了亲。”(30)《黑龙潭月仙遇黑龙》,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26-127页。虽然后来女子知道丈夫为龙王,但由于龙王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女子,因此女子也就不再计较龙王的“动物”身份,它除了具有行云布雨的能力之外,与人间男子并无异处,传说中龙王与龙妻过着类似人间普通男女的幸福生活。
第二类是女子离奇失踪或死亡,家人遍寻无果,最后在水潭边发现她的衣物或鞋子,才知她已嫁给龙王,成为龙王的妻子。“很早以前,马村有个美貌的妇人,不慎把脚扭伤,在求医途中,猝死于长河岸畔。据当地老百姓传说,这个美貌妇人的亡灵,为龙王所娶,做了白龙王的老婆,也就是白龙娘娘。”(31)《美丽的白龙娘娘》,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35-136页。另一则秃姑姑的故事也是这种情节结构,“一天,突然狂风四起,把秃姑姑和她纺的线刮跑了,家里人非常担心,找了许多时日仍无下落。就在这时,一只喜鹊在秃姑姑家门口叫个不停,嘴里还叼着秃姑姑的纺锤,家人很奇怪,跟着喜鹊,走到后窑村南山后的小会河。这时,又一阵狂风四起,待狂风平息后,秃姑姑从水中走出,和家人说她已经嫁到这里了。母亲听后,便要求见见她的丈夫,秃姑姑就让她的母亲闭住眼,背着母亲入了水,当母亲睁开眼时,看见一条大蟒蛇,秃姑姑说它就是她的丈夫,母亲非常吃惊”(32)《秃姑姑纺线遇龙王》,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凡俗之人彻底脱离尘世的唯一方法就是舍弃整个生命。(33)[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页。凡俗-个体与神圣-社会的结合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很多情况下都是要以凡俗-个体舍弃整个生命的自我牺牲为方式。在龙王结亲传说中常常体现为龙妻在凡俗世界中的离奇出走与死亡,这种故事情节意味着她脱去了世俗的外衣,成为具有神性的牺牲,拥有了嫁给龙王的资格与权力。笔者在对陵川夺火的实地调查中曾搜集到这样的传说,夺火董姓的闺女外出,路过了正在修建的龙王庙,给龙王奶奶塑像的师傅不知该如何给奶奶“拔眉眼”,看到董氏后,就按照她的模样给龙王奶奶塑了像。董氏回家后就无故死亡,后托梦给家里的人,说自己已经嫁给了当地的赤龙王,以后若遇干旱,可以来找她求雨。(34)访谈对象:张贵红;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5年10月20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乡政府大院内。
三、雨水:神给的回礼
人们进行社会交流是为了从他人处获取回报,换言之,与他人交换是符合自我利益的。通过交换获得的资源给人愉悦及满足感,即为回报。传说中,为何龙王对百姓的祈雨要求有求必应,及时回报以雨水呢?彭牧指出:“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和逻辑,正是理解民间信仰实践中人神关系、人神互动方式的关键所在。”(35)彭牧:《祖先有灵:香火、陪席与灵验》,《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2期。龙王与人间凡俗女子结为夫妻后,就意味着神龙与凡俗社会结成姻亲关系,人类是给妻方,龙神是受妻方,原本人/神之间的神高于人的人神关系转变为给妻/受妻的姻亲关系,姻亲关系取代了人神关系。笔者通过梳理总结山西境内的婚礼习俗,发现亲迎前诸多仪式中礼物由男方家向女方家单向流动,据此可知婚礼对传统社会从夫居模式中利益受损的女方家庭给予了富有人情味的经济补偿,并且这种补偿持续至婚后,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受妻方处处时时要以金钱、劳务等多种形式补偿出妻方。(36)以当地过年、清明、三月初三、端午、六月十三、八月十五、九月初三、十月初一、冬至为例,在这些节日里,出嫁的女儿都必须带礼物看望父母。刁统菊通过对姻亲关系的研究也得出:至少在华北地区,姻亲关系规定了双方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其中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等级秩序:给妻家族明显优越于受妻家族。(37)参见刁统菊:《不对称的平衡性:联姻宗族之间的阶序性关系——以华北乡村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在山西民间,妻子的娘家被称为“后家”,他们在处理嫁女婆家所有的事物方面都有优先决定权,大到红白喜事,小到婆媳吵架,后家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8)访谈对象:郭小龙;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20年1月29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城西社区。人神之间构建的姻亲关系亦是如此,重新分配龙神与人类之间各自承担不同的义务与责任。“姻亲是往来极密切的亲戚关系,彼此要承担重大的义务”(39)陵川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陵川县三晋文化研究会编:《陵川民俗》,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96页。。原本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回礼的龙神,因为其凡俗之人的女婿新身份,于是自由变成约束、权力转变为责任与义务,它必须回报给予它妻子的人类。
既然回报人类是必须的,那么回报何物呢?由于龙王与人类之间缔结了姻亲关系,这致使它回报给人类的物品应该与收到的物品价值相当或持平。对于人类来说,未婚女子是最高等级的“礼物”,对于龙来说,雨水也是其最珍贵的所有物。“龙得水则神,无水则蝼蚁之匹也。故知水存则龙在,水竭则龙亡”(40)王溥:《唐会要》卷二十二,中华书局,1955年,第432页。,龙王在答谢赠礼的时候也要让渡自己最珍贵的物品——雨水,而雨水恰恰是农业社会中最珍贵的物品。娶妻的龙王将雨水回赠给人类,这种礼物回赠在现实社会中就表现为龙妻娘家人天旱时的祈雨灵验。“姑侄俩一见面,抱头痛哭起来。小黑牛向黑姑姑哭诉了家乡的旱情,黑姑姑仔细询问了她走后家中的变化。最后,黑姑姑对小黑牛说:‘我嫁给了龙王爷,以后每遇天旱,你就和乡亲们戴上柳叶帽,光着脚,筛上锣,来求雨,我一定尽力相助。’说完,黑姑姑就不见了。从那以后,小黑牛再没见过黑姑姑。从那以后,附近各村的人们都来这里求雨,一祈求,就下起了雨。从此,这一带风调雨顺,吸引了许多人来这里定居。”(41)《黑姑姑与龙王爷》,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44页。
世俗社会在缔结婚姻关系时,出妻方会得到受妻方的财礼,作为赔偿女性家庭的损失。在龙王结亲传说中,女性被作为馈赠的礼物奉献给龙王,人神在联姻之际,龙王并没有付出财物或其它形式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损了联姻双方的姻亲关系,但龙妻这种主动馈赠更增加了龙王日后回报的分量,它必须更加谦卑地回报他的丈人家。在当地,这些龙妻娘家人参与的祈雨仪式不叫“祈雨”或者“求雨”,而叫“取水”,另外在祈雨时他们对龙王的态度既粗野蛮横又理直气壮,常常出言不逊,甚至威胁龙神,侮辱神像,经常说些“如果再不降雨就把龙潭砸掉”之类具有威胁性的话语。此种情况下,龙神往往会“受迫给雨”,在现实生活中就表现为祈雨的屡试不爽。“每当大旱之年,人们急于农事,纷纷求神祈雨,到崦山,去郭峪,折腾来折腾去,仍不下雨,往往还得寻找小黑龙。方圆几十里到黑龙潭求神祈雨的人们,毕恭毕敬,十分虔诚,唯有小城人,只烧香不敬献,并抬上碌碡、石头往潭里砸,用铳对着小黑龙的神像放。小黑龙是小城人的女婿,吃住都在小城,非下雨不可,这是娘家人的特权……祈雨之后,必会降雨。”(42)《小黑龙乘龙快婿》,靳虎松:《晋城传说》,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陵川县夺火乡鱼池村下辖鱼池、军寨、井沟、浸水洼、华金掌、冯家湾六个自然村,该地盛传军寨姑娘嫁给本地的红龙王,因此军寨在多村联合举行的祈雨仪式中不仅拥有主导权,而且敢于威胁恐吓龙王。
访谈人(郭俊红):鱼池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祈雨的?
访谈对象(李建旗):鱼池祈雨的时候,得军寨的人去,军寨的人拿上瓶瓶去取水,端老爷。军寨的老姑姑,就是军寨的闺女嫁给了龙王爷,所以军寨的人去了能“端老爷”,把龙王老爷端回军寨,这个不犯法,老爷也不做甚。鱼池是行政村,它就不能端,只能去那儿烧个香,拜一拜,它不能往回端老爷,它端回来送不走。把老爷端回来放到庙里,烧香磕头,许愿,三天之内可严哩,不能推碾,不能让狗叫唤。一般三天,稳不当当地要下。(43)访谈对象:李建旗;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5年10月20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乡政府大院内。
四、妻子与雨水:人/神之间的交换与交往
中国儒家文化在对人与神的关系的处理上,恰如其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设计,强调的是二者之间的和谐与相互依赖关系。人从祖先和其它神灵那里祈得健康、子孙和雨水等,而神灵则从人那里得到香火、供品和敬畏。但人们需要神灵的帮助,不是像西方民族那样是出于精神上或伦理上的需要祈求神灵拯救灵魂,而只是为了各种各样世俗的实际目的。(44)参见汪龙麟:《〈搜神记〉异类婚恋故事文化心理透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美国学者迈克尔·E·罗洛夫从“社会交换”这一角度谈到施惠、回报以及关系确立的问题。“当某人首次向另一人提供回报时,就标志着关系的开始。如果该回报被接受,接受者就已受惠于给予者。反过来说,给予者已承担了一个风险。接受者可能不愿意回报给予者的施惠,但他也可能希望关系延续下去而以某种方法回报。回报之后,第一个给予者或许得到鼓舞,因而提供更多的回报,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就这样,随着受惠-回报的进行,双方渐渐彼此信任,这又促使了进一步的交换。如果施惠而得不到回报,或者回报不被接受,可以预料,双方会互不信任,并避免进一步的交换。”(45)[美]迈克尔·E·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王江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39-40页。山西境内龙王结亲传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取水仪式为这一说法提供了精彩的案例。民众缺乏水资源,希求获得水资源的刚需促使他们构建出与龙王结亲的口头叙事和行为仪式,以获取龙王的水资源。这是一种存在于人/神之间的社会交换,这一交换受自我利益——从他人身上谋取回报的倾向——的指导,人类自愿地将女性作为资源转移给龙神,其结果是希望自己最大限度地获取扣去代价的回报——雨水。
社会交换的指导力量是自我利益。进行社会交换的人以符合自我利益的方式转让资源。凡俗世界的人类和神圣世界的龙神都在让渡自己的资源并从对方那里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这种交换让两者各取所需。龙神虽贵为一方神灵,但却缺少一个温柔可人的妻子,人类虽不缺少温柔善良的女性,却缺乏滋养万物的雨水,于是人/神之间“自愿地”交换就发生了,而且在二者之间产生了义务感、感激和信任之情。对于神灵关系,当地百姓喜欢用亲属关系称谓,他们世代亲切地称呼龙妻为“老姑姑”,龙神为“老姑父”。民众把龙神降雨视为一种“回报”,民众在这种“回报”中获得了满足感,并在日后积极地增进交换,使人/神之间的关系从“交换”转变为“交往”,每年例行的祭祀龙王仪式、非常时期的祈雨仪式类似于普通民众之间的“亲戚走动”,成为一种礼尚往来。
作为非日常的、群体的仪式性交往行为,当地的龙王庙以及祈雨仪式在维系、再生产及改造村落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积极的作用。在传说中,来自凡俗世界的女子被人类作为最初的礼物与神灵创造了关系,日后的庙宇修建、祭祀仪式成为维系这种关系的“礼物”,仪式即礼物,通过这种仪式性的礼物,人与神之间形成长期、稳定的交往关系。这种交往行为创造了一种共同体的情感、团结以及村民之间的相互关联,对村落关系网的缔造和维系起着重要作用。(46)参见徐天基、罗丹:《村落间仪式性馈赠及交往的变迁——以京西黑龙关庙会为例》,《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
凤凰欢乐谷这的老百姓每年都要举行祈雨仪式,求龙王爷下雨。苍龙王住在窄相,娶的是夺火董家的闺女。天旱祈雨,必须有夺火的村民和窄相的村民参与,没有这两个村的人的话,不管怎样求,都不会下雨。求雨的时候,窄相拿着钥匙,夺火拿着锁,其他村的人跟在这两个村的后面,与这两个村的人一起排着长长的队,很威风。苍龙王看见老家的人和丈人家的人拿着行头来了,不敢怠慢,不大会儿,就下雨了。(47)访谈对象:张贵红;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7年8月12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乡政府大院内。
双方对对方采取某些人际行为,可能是因为在过去这样做曾一直使双方得益。除非双方都发现对方的反应有利可图,否则就可能无法继续做出对方所期望的行为。(48)参见[美]迈克尔·E·罗洛夫:《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王江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37页。礼物交换与声望、权力、地位紧密相连。社会交换时对所涉及的义务、履行义务的时间、形式都不会明确规定,并且主动的给予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回报。(49)参见[美]哈里·李伯森:《礼物的回归:全球观念下的欧洲史》,赖国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那些日后在祈雨仪式中拥有主导权的家族或村落就是那些主动馈赠礼物给龙神的家族或村落。夺火董氏因为女儿嫁给龙王,于是在祈雨仪式中董氏充当实际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访谈人(郭俊红):夺火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祈雨的?
访谈对象(张贵红):夺火的人去龙王潭祈雨哩,凤凰那个景区里头,祈雨的时候不能乱说话,龙王老爷和人家是亲戚,是娘家,姓董的才能去哩,人家是当领导,龙王老爷娶了姓董的闺女,用瓶装上水,意思也就是雨跟上回来了。
访谈人(郭俊红):夺火除了姓董的祈雨,其他姓的呢?他们祈雨吗?
访谈对象(张贵红):其他的就不行了。其他姓的能去,姓董的是主持的,姓董的领上姓张的、姓王的去,姓董的领上杂姓人去。
访谈人(郭俊红):那姓董的是怎么求雨的?
访谈对象(张贵红):祈雨的时候,人家姓董的能随便发言,祈雨的时候和龙王老爷说,我今回来祈雨,假如你不给我雨,就把你的潭给你砸了。人家去祈雨的时候就是这么去求的。以前不是有那种炸药雷管的,就崩了潭了。董家能这么说,其他姓的就不能这样说。(50)访谈对象:张贵红;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5年10月20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乡政府大院内。
多村落的仪式联合有效地整合了地方社会的各种资源——既有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资源方面,又包含了庙宇、仪式专家、花会等宗教性资源——它使得各个村落处于一个互惠的体系之中。尽管这种互惠可能纯粹是仪式性的,但它的形成与日常生活的互惠关系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仪式性的互惠或馈赠是对日常生活领域互惠关系的重写,它们均指向主体间关系的生产,以礼尚往来为其核心准则。(51)参见徐天基:《礼物、关系与地方宗教:当代华北多村落的仪式联合》,《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夺火乡的祈雨仪式是典型的多村落仪式联合,参与的村落波及周围的“一镇八庄十二全庄”,在诸多的村落中,董氏所居住的夺火村是核心,参与祈雨的所有村庄都必须听从夺火村的协调分配。
其中与夺火村相邻的三流泉、窄相较其它六个村庄更接近权威的中心,祈雨仪式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工具钥匙、锁分别被这两个村子保管着。当地民众认为(52)本人针对夺火乡的祈雨调查主要有三次:2015年10月20日;2017年8月10-13日;2019年8月23日。在这三次调查中,笔者走访了夺火村、窄相村、凤凰村等多个村落,与当地多位村民交谈,交谈中大多数访谈对象(60岁以上)都会提到以夺火村为核心的祈雨仪式与路线。,龙王给某地的雨量及降雨的时机都有限制,雨水平时被龙王老爷锁着,以免被偷。夺火村董氏与苍龙王之间存有姻亲关系,因此董氏沾亲带故地也具有了分配降雨的职能。董氏将锁雨的锁交给窄相保管,钥匙交给三流泉保存。祈雨仪式中,保管锁雨之锁的窄相与开启降雨钥匙的三流泉是祈雨的必须参与者。从夺火村出发至走背的祈雨路线上,沿路的黄家营、上窄相、下窄相、凤凰、水章、安驼、潭头上(走背)八个村庄是祈雨仪式的次中心力量。
相传,董氏原来居住在三流泉,后来迁至夺火,因此三流泉保管着象征可以带来雨水的钥匙,它在祈雨仪式中地位略低于夺火,并且三流泉村可以不与其它村落商量,到苍龙潭“偷雨”。当地民众对三流泉的“偷雨”与夺火村领导的“祈雨”有着泾渭分明的认识。他们认为在夺火村董氏的组织下八庄共同组织参与的求雨行为,叫“祈雨”,而三流泉本庄单独举行的求雨仪式叫“偷雨”。沙流泉偷雨时,因没有其它村庄的参与,因此其偷雨的路线与祈雨路线不同,即所谓的“走小路”。窄相村(53)此村在夺火东北5公里处,包括八个自然村,即上窄相、下窄相、马林庄、黄家营、小庄、掌口、外口、水泉沟。的村落实力并不像三流泉那样强大,但是其距离夺火村最近,在空间上与夺火村有更为亲近的地缘关系。并且窄相村是夺火祈雨的必经之地,包括三流泉去偷雨,也必须经过窄相村。地理上的优势给这个村落也带来了祈雨仪式中地位的优势,他代替龙王保管着锁雨的锁。(54)访谈对象:王爱军;访谈人:郭俊红;访谈时间:2019年8月23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乡窄相村。这个问题属于本人每次都会询问的问题,最早的访谈是在2015年10月20日,行文时采用访谈效果最好的一次。
“礼物”是一种以特定交换为形式的社会营造方式。(55)参见赵丙祥:《神给的礼物和给神的礼物:“礼物”作为历史研究之一般概念的可能性》,杨念群、黄兴涛、毛丹:《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8页。龙妻娘家所在的村落不仅祈雨灵验,而且该村落或家族也与其它村落或家族形成地位差异,它们在当地社会网络中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礼物交换既表现了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也对维持社群内外的地位阶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塑造了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村际交往关系。这些不同的村落与神灵的关系与费孝通指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交往一样,也存在着差序等级。离夺火村较远的附城镇南马村以造纸制香为业,其参与祈雨的表现就是将每年本村造出的第一批纸和香都留给夺火村祈雨使用,不能外卖给他人。而贡献龙妻的夺火村在整个地方社会中处于村际交往的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不同的村落散落四周,依靠每年六月十三的祈雨龙王庙会,这二十多个村庄友好而亲密地世代相处着。(56)访谈对象:秦建平;访谈人:郭红霞;访谈时间:2019年8月23日;访谈地点:陵川县夺火乡凤凰村。在这个社会网络中,人们受到确定的关系和互惠责任的约束,大家都必须遵守共同和非常细致的规则及礼俗。人神之间、村落之间不同的义务与利益、慷慨与希图、无私与自利完全隐晦地混杂在当地龙王结亲的传说中。
五、余 论
传说不止是讲述故事,更是区域群体现实生活的折射与反映。山西域内的龙王结亲传说隐喻着当地民众水资源匮乏的现实困扰和由此形成的灾难记忆以及缓解困境的纾解方法。透过传说,现实生活是这样的:
1.某地干旱异常,人类需要降雨。
2.将女性作为礼物奉献给龙王(龙王结亲)。
3.龙王与龙妻娘家缔结为姻亲亲属关系。
4.这种亲属关系规定了互惠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作为出妻方的村落或家族垄断了祈雨权,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民间社会正是透过隐喻的修辞学途径来模仿国家的行政和祭祀系统等,并将之逐渐地内化在地方习俗背后。(57)参见徐天基:《礼物、关系与地方宗教:当代华北多村落的仪式联合》,《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我们透过龙王结亲这种隐喻性传说可以领略到当地的口头传统、仪式行为以及社会关系的整体图像。对于山西区域社会而言,人与降雨的神灵(龙神)之间的关系生产与认同是乡村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面向之一,它作为基本的深层逻辑贯穿于口头传统及日常生活中,小到家户内部,大到村落之间都在指向这一关系的生产与维系上;人神之间形成的关系也在建构和约束着乡村生活的秩序,为当地社会的正常运行提供着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动力,村落交往中处于上位的家族或者村落以及由此形成的村落友好关系都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证明。龙王结亲传说与其说是一种口头传统,不如说它是当地民众的一种社会关系营造方式,通过这种“妻-雨”的礼物交换,不仅人/神之间确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区域社会也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人类对于雨水匮乏的需求得以解决,人类重回平静的日常生活。
日本学者直江广治在对山西境内的祈雨仪式进行分析之后指出:通常情况下中国人的协作意识非常淡薄,乡村民众只有在面临类似祈雨这样大的事件时协作意识才会发生明显高涨。(58)参见[日]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王建朗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这与笔者的研究稍有出入。例如,阳城县章训村与泽州县辛壁村因为龙王李小三与冯氏的婚姻关系形成世代友好关系,辛壁村称呼冯氏为“姑姑”,章训村称其为“奶奶”,冯氏嫁给龙王之后随着龙王居住在章训龙王殿,每逢神像破损或者神殿倾塌都是由章训和辛壁两村合力修缮,至今章训、辛壁两地一直是遇事相帮,遇难相助,两村村民世代友好,交往不断。在龙王结亲传说圈之内,类似章训、辛壁这种世代交好的村庄比比皆是,泽州南岭乡李沟村和冶底村、泽州山河镇龙门、列铺、水域三个自然村、陵川夺火乡夺火村和窄相村、阳城横河镇横河村与驾岭乡护驾村、沁水县王必乡龙渠村和马邑村等皆是这种世代保持协作关系的村落。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及民众的协作意识是否真如日本学者所言那样淡薄,或者协作是否仅保留在祈雨这种重大事件之际,诸如此类问题,笔者深感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与价值,但囿于个人能力及所见材料等问题,笔者还不能给出很好的回答,只能留待日后继续发力,得出圆满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