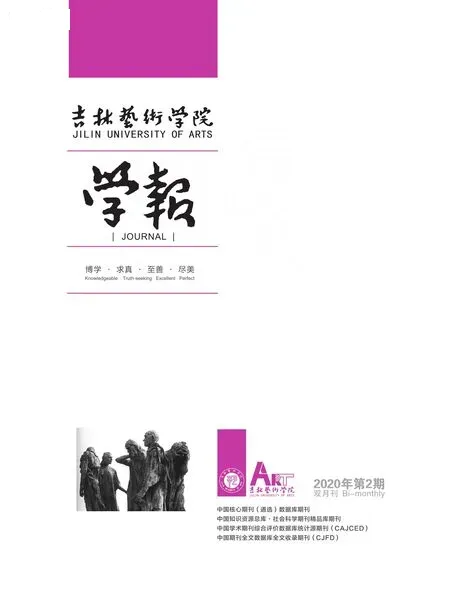2019 年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述评
王宁 刘振华
(吉林艺术学院,吉林 长春,130021)
一、戏剧起源至隋唐时期戏剧史研究
回顾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溯原始时代的歌舞,历经奴隶社会的俳优、秦汉的百戏、角抵,隋唐时期的参军、弄戏,中国古代戏剧史在这一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诸多灿烂的成果。
张申波的《郑振铎与戏曲起源—梵剧说》(《戏剧之家》第19期)通过对郑振铎先生“梵剧说”观点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文中详细论述了郑振铎先生提出这一说法的原因,但笔者对于“梵剧说”还是持有保留意见。相对而言,“巫觋说”的证据更加充分,论据更加详实。近百年来,有关于戏剧起源的说法争论不断,期待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给予戏剧起源一个最终的定论。郝勤、张济琛的《秦始皇帝陵K9901出土角抵俑及铜鼎考——兼论战国秦汉角抵百戏的演变》(《体育科学》第6期)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调研、实证研究等方法,认为秦始皇陵K9901陪葬坑出图的陶俑为角抵佣,同时对角抵戏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为当代进行角抵戏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考古方式进行戏剧研究的,还有杨艳军的《略论汉代的俳优艺术——以济源地区出土的俳优俑为例》(《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作者通过对济源地区出土的俳优俑进行考证,讨论了俳优戏的起源、发展及表演艺术特色,并对其进行了有序的梳理。为俳优戏的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论据。李小满的《论汉乐府的综合性艺术价值—兼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出版广角》第15期)通过对著作《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的解读,阐述了汉代乐府与乐舞百戏间的关联性,同时对《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进行了细致的点评。付东博也从乐府入手,在其《汉代乐府诗戏剧性对后世戏剧文学的影响探析》(《文学艺术》第31期)中,对乐府诗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通过这两篇文章,可以了解到乐府的功能不仅囊括了对音乐的创作,对诗的内容也有所涉及。无论是对乐舞的影响,亦或是对后世,对乐府诗改编的乐府诗戏,乐府诗都对汉代戏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硕的《唐代音乐与文艺研究》(《齐鲁艺苑》第1期)对任半塘先生的《唐声诗》和《唐戏弄》进行了研究。首先说明了音乐与唐诗的关系,其次论述了音乐在唐代戏剧中起到的作用,以诗论乐,以乐论戏,层次分明,脉络清晰。涉及到唐代戏剧研究的,还有罗世琴的《以戏谑赏“悲”情——唐代<踏摇娘>故事演变律令背景考》(《北京舞蹈学院学报》第3期)及范德怡的《唐代参军戏未更名原因考》(《戏曲研究》第105辑)。罗世琴的文章首先考证了戏剧《踏摇娘》的三种文本出处,其次分析了戏剧《踏摇娘》中悲剧成因的社会观念与合法性,总结了《踏摇娘》的艺术价值。范德怡的文章对参军戏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分析了参军戏的命名依据及未改名的原因,论证充分,有理有据。
二、宋元戏剧史研究
进入宋代,国力空前强盛,经济、政治、文化迅速发展,中国戏剧踏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元代的统一结束了政权并立的局面,同时摧毁了文人士族进入仕途的道路。因此,大量文人墨客涌入戏剧创作的行列,中国古代戏剧也迎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
刘小梅的《论前期南戏社会心理的独立性》(《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1期)从地域、受众与思想的研究角度,阐述了早期南戏在社会伦理方面所具有的非主流性、市民化与世俗化的表现特征。李文在《金代河东南路杂剧的沉淀融合及其体量态势——以戏曲文物为中心》(《戏剧艺术》第4期)中,通过对金代河东南路戏曲文物的样态分布考察,认为金代杂剧的艺术体量具有承前启后的趋势。张正学的《从“杂剧”命名看元人的戏剧理念》(《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3期)以元人对杂剧命名为支点,得出了元人对“脚色”意识的重视与对“戏”“剧”界限的模糊的结论。查洪德在《元杂剧的淑世精神与社会重建意识》(《南开学报》第5期)中,从戏剧的教化功能入手,提出了“淑世精神”这一概念。在《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中,总结归纳了元代剧作家们试图通过作品,呼唤社会道德的群体行径,意在维护封建统治,论证详实,有理有据。康相坤在《元杂剧所体现的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的融合探析》(《戏剧文学》第10期)中通过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的探究,对元杂剧创作进行了分析,充分解释了“雅”“俗”的融合根源在于两种文化的碰撞。赵忠富在《元杂剧在真定与大都的兴起及传播考略》(《大舞台》第1期)对元杂剧的两个中心进行了考察,充分论证了元杂剧能够在真定与大都两个中心兴盛,主要是通过剧作家与艺人来实现的,观点鲜明,有着独到的见解。在《元杂剧<窦娥冤>中盛夏处斩及其法理依据》(《文化广角》第111期)中,林宪亮以季节为切入点,展现了古人的“天人感应”理念与刑罚意识间的联系,阐述了窦娥为何会在六月被处决而不是秋后问斩。有关元杂剧《窦娥冤》的人文研究还有孟筱宇的《男权桎梏下的女性悲歌——<窦娥冤>解读》,文章着眼于封建制度下的思想,展示了古代男权社会中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女性受到的压迫,揭示了窦娥凄惨命运实则注定的结局。
刘勇在《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戏曲文献学意义》(《戏剧艺术》第3期)中详细论述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的成就表现,得出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是南戏校注的最高水准的结论。有关南戏文本的研究,俞为民在《南戏<东窗事犯>的流传与衍变》(《艺术百家》第1期)一文中也有着独到的见解,详细阐述了南戏《东窗事犯》在流变中与原文本间的差异,学术之严谨,考证之详实,实是我等后辈之模范。关于《窦娥冤》的文本研究,李山岭《<窦娥冤>解读管见》(《戏剧文学》第3期)与陈燕《论元杂剧<窦娥冤>的配角设置》(《大舞台》第3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李山岭主要侧重于人物形象的解读,唯一的亮点在于“窦娥并非觉醒者”这一结论。同历史长河中众多戏剧人物进行对比,窦娥始终是一个维护封建统治的形象。这一论断很有新意,但对其他人物的解读则无法跳出前人研究的“桎梏”。陈燕则从配角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侧面体现出元代社会的经济状况与社会风气。这两篇文章的论述少有创新,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若不能从其他角度另辟蹊径,很难在《窦娥冤》的文本研究上有所突破。《元杂剧中长安叙事的意蕴》(《文化艺术研究》第1期)的三位作者伏漫戈、于展东、杨晓慧从众多元杂剧文本中提炼出长安历经沧桑后的深刻寓意,既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又有浓郁的理想色彩,具有别样的双重格调。关于元代散曲的研究,查洪德又赋予其新的涵义。他在《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中,脱离众多学者对散曲的陈旧概括,以“野逸”二字赋予散曲灵动与洒脱,不羁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任红敏的《元曲的雅俗融合及其转换》(《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以浓重的笔墨讲述了元曲的高雅,关于“俗”的内容则寥寥数笔,“雅俗”如何转换含糊不清,不禁令人遗憾。公案剧作为元杂剧中的代表,诸多学者都对公案剧有过深入的研究,赵忠富在《元代公案剧清官形象所折射的社会舆情》(《大舞台》第4期)中也试图有所突破,无奈其结论与其他公案剧研究出入不大,没有太多创新。同样突围失败的还有庄秋月的《元杂剧“金榜题名”桥段程式化历程——以才子佳人剧<西厢记>为例》(《名作欣赏》第24期),她将张生进京赶考的理由归结于剧情的需要、文人的主观意识与社会现状,然而诸多前辈早已对此有过定论,此文未免有老调重弹之嫌。黄春枝在《元代婚变戏的文化意蕴解读》(《戏剧》第5期)中对元代婚变剧这一题材进行整合归纳,透过对戏剧文本的解读,窥探到了元代社会的真实状况与基本特征。姜彦章则在文本研究中独树一帜,在诸多元杂剧文本中找到有关“洞房戏”的内容。他在《论关汉卿杂剧中的两折“洞房戏”》(《名作欣赏》第8期)中对比了关汉卿的《温太真玉镜台》和《山神庙裴度还带》洞房戏的不同之处,为解读关汉卿的作品增添了更多有趣的意味。张勇风的《<琵琶记>主旨“隐喻说”探微》(《文艺研究》第5期)认为《琵琶记》的主旨并非是宣扬忠孝,而是“隐喻”中的辞仕,这一论断富有新意,合情合理。
三、明代戏剧史研究
自朱氏王朝取代元蒙统治后,统治阶层对文化思想界进行了强制干预。“时文风”“道学风”盛行,严重破坏了戏剧的创作,使得杂剧日渐式微。直至16世纪,中国戏剧迎来了新的转机:南戏的崛起,传奇的兴盛,结束了中国戏剧史长期岑寂的局面,中国戏剧再度焕发出新的活力。
彭秋溪在《明太祖反“胡俗”及其与明初戏曲发展之关系》(《文学遗产》第5期)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明初为了巩固政权,通过戏剧的教化手段,重构礼乐系统,强化儒家道德,这也正是明初“时文风”与“道学风”的核心之处。王小岩先生对臧懋循颇有研究,在《地方演剧风尚对臧懋循传奇改本的影响》中,王小岩先生详细考察了吴地的演剧风尚,同时对臧懋循及其他剧作家的传奇改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通过对比后得出结论:吴地的演剧风尚影响了剧作家们的改本,剧作家们的创作彰显着演剧风尚,二者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有关汤沈之争的研究,向来是通过文本与音律为切入点进行考察的。张哲俊在《从一字一音到依字行腔以及汤、沈之争》(《文艺研究》第9期)一文中对古代曲律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由此对汤沈之争进行了辩证。作者认为这场冲突并非文学与音乐的冲突,而是不同辞、乐的冲突。刘宝淇试图通过不一样的视角对汤沈之争进行解读,然而在其《另一种视角下的“汤沈之争”》(《戏剧文学》第11期)中,并没有通过王骥德对汤沈二人的评价得出有关汤沈之争的新的论断,味如嚼蜡,实属遗憾。
李碧的《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与词曲的互动》通过对明代戏曲填词的量化考察,归纳了具有代表性的变体形式与来源。辜梦子的《<四友斋丛说·词曲>三种版本校勘发覆》(《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1期)对《四友斋丛说》的三个版本进行校勘,发现了《词曲》一卷中的差异,并通过总结对比,进一步解读了何氏戏曲理论的演变过程。有关明代传奇《牡丹亭》,有五位作者各自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俞晓红从叙事结构入手,在《论戏曲文本在非线性叙事中的构成——以<牡丹亭>为考察中心》(《戏曲研究》第106期)中对剧情的脉络与发展进行剖析,以非线性叙事的视角进行解读,使人眼前一亮,对于《牡丹亭》的故事发展有了新的认知;杨榕侧重的是诗文观念,《从<牡丹亭>看汤显祖的诗文观念嬗变》(《广西大学学报》第5期)通过对《牡丹亭》中的曲辞分析,展示了汤显祖诗尊杜宗唐和文宗韩柳的诗文观念;同样对《牡丹亭》中的诗文进行研究的,还有叶烨的《<牡丹亭>集句与汤显祖的唐诗阅读——基于文本文献的阅读史研究》,通过对《牡丹亭》中的集句分析,分层考察了文本、书籍、阅读与知识的关系,重新审视了古代作家的阅读局限及知识来源问题;王翼的《春深劝农焕烟霞——论<牡丹亭·劝农>中的意趣》(《文化艺术研究》第4期)与黄若瞬的《<牡丹亭>与汤显祖的“戏教”思想》(《文学研究》第2期)都以戏剧的教化功能为支点,通过对剧情的分析,展示了汤显祖隐于其笔下的大儒思想。在续作文本的考察上,冯王玺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对《西厢记》续作进行了总结。首先,作者第一篇文章《明代<西厢记>续作中婢女红娘身份的抬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通过对几个续作版本中的红娘进行分析,展示出明代文人向往平等和解放的价值观;第二篇文章《论<西厢记>续作中遇仙情节的应用与新变》则对比了《西厢记》原作与续作中的情节,揭露了“神仙道化”外衣下的儒家思想内核,这一观点有着作者独到的见解,对于续作的理解上赋予了全新的观念。
四、清代戏剧史研究
自清军入关,直至南明政权灭亡,众多文人心中生起了“国破山河在”的悲凉之情。也正是这个时期,产生了诸如《桃花扇》《长生殿》等戏剧,推动中国古代戏剧史进入最后的余韵。而后,徽班进京,雅部节节败退,地方戏迅速崛起,中国古代戏剧史也随之走入末路。
罗冠华的《清雍正时期的戏曲文化政策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第1期)通过戏曲与文化政策的解读,得出雍正促使了清代戏曲的发展,对文教治吏有了新的贡献的结论。彭秋溪的《清代新疆查禁戏剧演出考》(《戏曲研究》第106辑)通过对新疆地区戏剧发展与活动的考察,阐述了清代中后叶对新疆实行禁戏政策的原因是为了稳固边陲;同时,禁戏也阻碍了新疆与内地的文化融合,体现了清仁宗、宣宗以后的眼界之狭。陈志勇则从“侉戏”入手,在《清中叶梆子戏的宫内演出与宫外禁令——从内廷档案中的“侉戏”史料谈起》(《文艺研究》第9期)中对于梆子戏在宫廷内外的考察,展示了当局统治者对待民间戏曲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和立场。武迪、吴佳儒的《论晚清宁波串客戏的禁毁及其影响》(《文化艺术研究》第2期)同样从地方戏中的“宁波串客戏”出发,通过对串客戏的发展与禁毁进行研究,得出禁毁虽阻碍了串客戏的发展,但客观上为宁波摊簧和甬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结论。赵林平的《清代前中期戏曲的商业出版略论》(《艺术探索》第2期)考证了清代前中期戏曲商业出版的特征,展示了戏曲在当时环境的生存状况。
有关李渔的文本解读,付谨先生的《李渔“立主脑”小识》(《文学遗产》第5期)对于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所提出的“立主脑”一词进行了重新的解读。付谨先生认为,“主脑”实际上指的是使剧情发生重大逆转,向着原本不可能的方向发展的关键性的转捩点。这一观点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解读,末学不足以评判付谨先生的观点,但有幸学习到先生的“一家之言”,也足以给末学很多的启示。赵静静的《李渔戏曲传播思想研究》(《四川戏剧》第8期)将传播学与戏剧相结合,通过三个角度对《闲情偶寄》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进行了分别解读,以交叉学科的方式提炼出新的观点,富有新意。沈新林则另辟蹊径,从地理方向入手,在其《论李渔小说、戏曲中的如皋元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2期)中通过李渔的出生地如皋七夕的细节捕捉和描绘,展示了李渔的创作风格、创作习惯与创作特征。李良子的《论李渔人格在戏曲中的多角度投射》(《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对李渔的十种曲进行了研究,通过三个角度写出了李渔的经世之心、处世之道、历史之思,虽尚显浅显,但仍不失为一个好的角度去解读李渔。有关戏剧《桃花扇》的研究,王正的《<桃花扇>的小说化倾向及其意义》(《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1期)详细分析了戏剧《桃花扇》的结构,并得出《桃花扇》的小说化倾向在戏曲发展史上具有范式的转型意义,对清中晚期的传奇杂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结论。卢燕娟的《作为文学叙事的明清鼎革——以<桃花扇>的写作、接受和重写为中心》(《文艺研究》第8期)以明清朝代更迭为背景,透过《桃花扇》的文本,对孔尚任的创作理念、创作过程与隐含的思想进行分析,同时对《桃花扇》在民国抗战阶段的继承与发展进行探求,将一系列的变革、创新进行归纳,实为一篇有理有据的佳作。田纪伟对《桃花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在《乱世辨忠奸——论<桃花扇>中的武将形象》(《戏剧之家》第27期)中将武将分成了三类,并详细列举了忠臣良将、祸国殃民、愚忠无能三种形象的代表,但结论不足,仅仅总结了对于武将分类的辨别标准,没有余味。同样对《桃花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的,还有潘玉林的《小议<桃花扇>中主要人物形象》(《文学教育》第7期),文章寥寥两千余字,对于主要人物仅限于简单的概述,浮皮潦草,意义不大。在《略谈<桃花扇>悲剧的多重表现》(《蚌埠学院学报》第8卷第4期)中,王怡、任强通过对《桃花扇》中的爱情、政治、哲学三个层面的分析,从三个角度展示了《桃花扇》中的悲剧内涵,以及悲剧意味下的《桃花扇》所带来的戏剧体悟。郭小小的《<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是折扇还是团扇?》(《戏剧与戏曲》第7期)另辟蹊径,从一把扇子入手,对《桃花扇》中的扇子到底是何形状进行了文本考证与推断,并最终得出扇子是折扇的结论。这篇文章很有新意,从一个全新的立场对戏剧文本进行了别样的解读,区别于普通的研究,又有其合理的结论,令人眼前一亮。另外还有关于其他传奇或戏剧的文本研究,杨惠玲的《清董榕<芝龛记>编刊考述》(《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3期)对于戏剧《芝龛记》进行了版本与编刊考述,详细列举了版本与编刊间的区别,并总结了《芝龛记》编刊的文化价值。汪宏超的《清代传奇三考》(《文学遗产》第2期)考证了《芙蓉峡》《空谷香》《绣帕记》这三篇传奇,其中得出了《芙蓉峡》的作者有很大可能是林以宁,小说《忠烈全传》基本脱胎于传奇《空谷香》,以及《绣帕记》是一部窃取他人之作的结论,有理有据,考证详实。在《新见清宫大戏<兴唐外史>考论》(《戏剧艺术》第4期)中,柯尊哲考证了这部特殊的戏剧,详细整理了《兴唐外史》的剧目内容及演出情况,并总结了咸丰帝促成这部连台戏剧的原因,主要由于时局的动荡,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五、戏剧理论研究
戏剧理论研究方面,伏涤修在《中国古代曲史观发微》(《东南大学学报》第4期)中以“曲”论“史”、以“史”成“曲”,有机地论述了曲与史的关系,同时展示了不同时期古人对于戏剧创作中的史学观念。有关史学剧的概念研究,还有陈云升的《史剧定义辨析》(《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1期),作者分别列举了郭沫若、冯其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以及其他史剧的定义,通过对比归纳以上作家作品的结论,并最终提出了作者个人对史剧的定义,自圆其说,合情合理。安葵的《戏曲美学范畴之教化论》(《四川戏剧》第1期)首先解读了中国古代关于教化的态度及戏剧中的表现,而后分析了教化观念在近现代的流变及当代社会中的作用,脉络清晰,内容完整,引人深思。刘于峰在《中国古代戏曲批评形态研究的开创之作——评李志远<中国古代戏曲批评形态研究>》(《戏剧艺术》第3期)中点评了《中国古代戏曲批评形态研究》一书中关于戏曲批评的观念及观点,并对其有很高的评价,也为戏曲批评方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傅涓的文章同样涉及了戏曲批评的内容,在其《“艳”范畴在戏曲批评中的积极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第3期)中提出了“艳”这一概念,并详细阐述了“艳”在诗文与戏剧中的积极作用。袁国兴的《论戏曲“代言”》(《广东社会科学》第3期)区分了“代言叙事”与“代言体”,并以戏曲为例,逐一拆解了二者间的不同,最终解读了王国维“曲文全为代言”的观点。张小芳从“题目”入手,在《古典戏曲批评学“题目”说——以“影儿里情郎”“画儿中爱宠”为例》中通过对戏剧《西厢记》中“题目”的分析,梳理了相关的批评,并得出“题目”可以丰富文学史,拓宽戏曲批评学的结论。刘晓静的《从古谱文献遗存窥俗曲发展历程》(《民间艺术》第6期)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搜集与整理,理清了“俗曲”的大体发展脉络,为“俗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郭英德、李志远的《精心构筑戏曲理论宝库——谈明清戏曲序跋的整理》(《中国戏曲学院学报》第3期)首先梳理了古代戏曲序跋与古代戏曲研究的学术价值,其次提出了完整全备、信实可靠、丰富详实、明晰实用这四条整理明清戏曲序跋的原则,为研究明清戏曲序跋树立了规范与标杆,同时也为其他学者研究明清戏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彭然、徐伟的《规约礼法与凝于传神: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场所特征》(《学习与实践》第8期)对中国戏剧的表演场所进行了考证,总结归纳了表演场所规约礼法的特征以及凝于传神、诗意情趣的舞台设置,并对比了中西剧场的差异,文字详实而严谨。朱碧原、黄爱华的《历史编纂·文本互涉·“再戏剧化”——田沁鑫戏剧改编策略探析》(《戏剧》第2期)对田沁鑫导演改编的剧目进行分析,通过对事件人物的“史料化”、文学与舞台间的转译、经典作品“再戏剧化”三个方向的逐一探索,证明了田沁鑫导演的做法是成功且可取的,中国古代戏剧也因此在现代舞台上焕发了生机。
六、结语
回顾2019年度的中国戏剧史研究,成果丰硕,内容凸显,研究视域与方法均有了不同程度地提升。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众多学者的加入为正在路上的同辈们注入了新的动力。研究成果的增加、学术领域的扩大、由古入今的融合,也为国家提供了智库成果。中国戏剧史学从未停下脚步,正在朝着前方不断行进。在进行相关研究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如下问题。第一,新的学术观点数量不足。目前的戏剧史论研究,大部分比重仍然拘泥于名家作品之上,然诸多观点早有定论,如不能有新的突破,则很难于前人的基础上跳脱出来。第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虽有明显的数量提升,但仍显薄弱。或可通过行为学、心理学、民俗、宗教等入手,拓宽方向,从而更深入地进行戏剧研究。第三,缺少学术争鸣,研究方向具有较高的同一性。需要拓展视野,从更多角度出发,方可再次重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相信在众多学者前辈的引领下,诸学在中国古代戏剧史的研究方向、学术水平、创新等方面定会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为中国戏剧史学做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