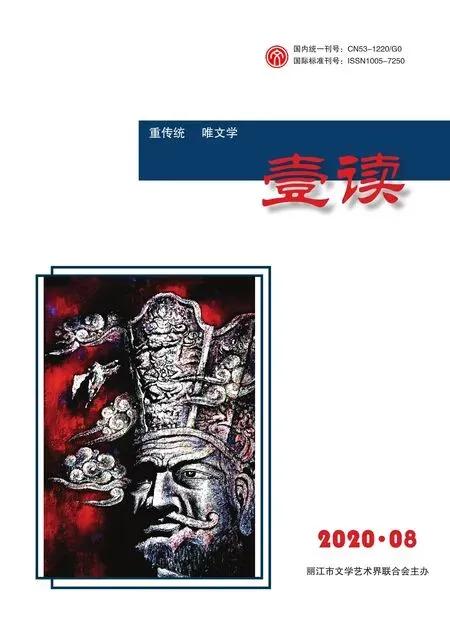草药记(组诗)
◆华秀明
半神记
我们在河边的牛蹄窝里灌上水
让太阳、月亮、星星和白云,这些高远的
事物,和几个小蝌蚪
还有旁边一朵灯盏花的倒影
一起低入尘土,且入土三分
这样做,仿佛有神谕
——不,不是神谕。那时我们是半神
一个灌水的牛蹄窝
就足够我们用来规划万物的秩序
多年后,当我读到《观沧海》
才发现牛蹄窝里的
那一汪水,约等于曹孟德的整个沧海
小池塘记
池塘底龟裂的泥块,让人想到
古代遗址上的陶片
一群头顶瓦罐的女子
在某一个早晨,穿过一片林子
和几声鸟鸣
到塘边汲水。可是一夜之间
她们发现
塘水已经干涸了
一只羊子过河,十只羊子过河
像要完成某种仪式
她们把头顶的
瓦罐,一只只投向塘底
不,不,我不能这样
写人间事
我相信此前的一只瓦罐,取走了
最后一罐水
仿佛地下的泉水是一种宗教
大风起兮
一队枯草一样的部族,马背上驮着
风沙与烈日
去远方朝圣
夜行记
夜行人走在路上,手电筒的光柱
像一根发光的棍子
他用这根棍子探路,甚至打草惊蛇
有几回,我还看见夜行人
从夜里走来
帽子上响着风,黑暗像麻袋一样
压在他们背上
他们是杵着几条光柱走来的
这些光柱分担了
他们身上的一部分重量
夜行者在内心建立强大的帝国
人世间抱团取暖的灯火,缺少尖锐的犄角
只有他们手中的那束光
像长矛刺穿原野
夜黑风高,他们鱼贯而行。像古代军中的
一支小分队
他们从山中来。小镇上的灯火为他们蜕去
一身铠甲一样的夜色
放生记
周日,某公园
在一条长椅上听手机里的肖邦和贝多芬
三十米外,一条河在大坝下喧嚣
在巨大的水声里
我觉得我是一尾被我放生的鱼
在坝下逡巡
作为一条劫后重生的鱼
我看见暮年的
金毛狮王一样的贝多芬指挥一条音乐的河
向我俯冲下来
在那些携带闪电的漩涡中
一条来自人世下游的鱼,在河水里磨亮了
它梭镖一样的肉身
病中记
天气晴和的日子,一般是上午,我在自家
阳台上练习打坐
内敛笃定,把自己当作一株盆栽植物
蓝天,白云。轻风高于楼顶
有时楼下
传来一阵豆芽菜过油的轻响和它的味道
我确信我离地面远了一点,离飞翔的鸽子
近了一点
我不喜欢尘埃落定
这种处境让我想到许多悬而未决的事物
比如,藤上一只风干的丝瓜
或一片挂在树梢的塑料薄膜
说实在的,我至今还不能做到禅定无为
比如,今天上午吧,我听见
一辆消防车从大街上呼啸而过,接着又是
一辆救护车
我知道它们
来自一些底层的纷扰和人间的疾痛
端午记
这一天,我们使用
古老的捆绑术
给一团月光一样的大米穿上外衣
这一天,洪大的江涛
在江水里歇息。在江水慢下来的节奏里
涉江者听见鱼在江中合唱
这一天,从山野归来的人
手持菖蒲和艾草
旧时南方多瘴气,正午如云霞
这一天我们在自家的阳台上,擎一杯雄黄酒
对着一枚落日吟诵
当日你奔出楚国郢都的城门
从你跌跌撞撞的
衫子上滑落几行发光的句子
草药记
在乡下,有个头痛脑热的
提一把锄头就出去了
房前屋后,田边地角。草药遍地都是
比我们开了处方
去药房取药,要方便得多
在乡下,你是你的医生,你也是你的病人
——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全凭你自己拿捏
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
在乡下,许多草药是用来医心的
车前草、蒲公英,何首乌与马齿苋
小桃红、夏冬发,张二妹与李三娃
这些一辈子吃草药的人
活得像一株草
还乡记
穿黑色服装的人,其实是太阳底下
行走的一个影子
他扶过一面墙壁,像人类的幼年
或树枝上的蛇那样练习站立
然后他钻进
一个黑布袋子一样的柔软的影子
在这个城市,他经过我时
我听到了
他体内有一只小小的鸟鸣
穿黑色服装的人
其实是一只囚着画眉的笼子
他走向黄昏,走向迎面而来的自己
在故乡的
某一道山梁上他们狭路相逢并握手言和
很多年后就像很多年前
他舍弃了夕阳
穿黑色服装的人
身披一袭宽大的夜色还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