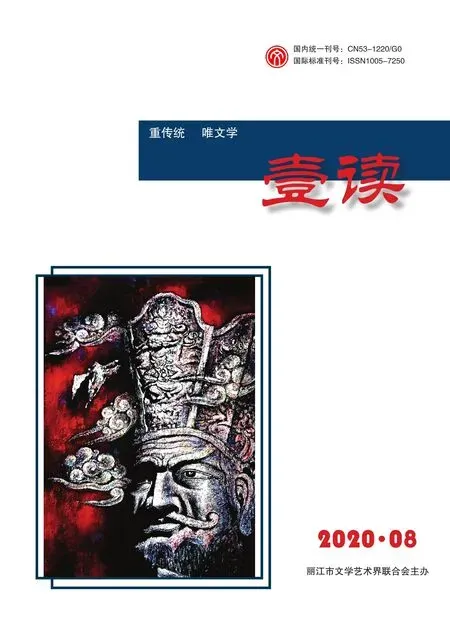财神来敲门
◆马庆华
一
田三从县城农贸市场回家后,径直往后院的猪圈奔去。
见两头火毛大肥猪正四平八稳地躺在圈里熟睡,田三搓着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在圈门口来回地踱步。肥猪偶尔发出的哼哼声让田三显得异常兴奋,加快了来回走动的步伐。
当田三反复瞟着那两头耳朵不时扇动着的肥猪时,他将心思全部转移到让其心心念念的两桩事情上来——给即将在省城上初中的孙子买辆名牌自行车,及给他的老伴买把全自动按摩座椅。
这些想法似乎全然背离了养猪时的初衷——一头猪腊月里宰了春节享用,一头猪待价而沽。
翻飞的思绪似乎开始让田三有些失控,他竟然想到两头肥猪出栏时自己点钱的场景,往腰包装钱的舒畅感觉让其脸上洋溢出一丝丝笑意。
田三之所以如此高兴并非全然没有道理。以前生猪价十一二元每公斤,眼下非洲猪瘟疫情愈演愈烈,生猪价格随之水涨船高,目前生猪价格已经快涨到三十元每公斤了,这几乎翻了两翻了。按照目前的行情,田三猜测生猪价格还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
吱呀的开门声打断了田三放飞的思绪,他转身往门口奔去。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要将县城农贸市场的所见所闻一字不漏地告知老伴王兰。
此时,王兰正背着一背篓青菜叶钻进屋里来。田三一边帮老伴卸下背篓,一边噼里啪啦地将城里头生猪的行情一一告知王兰。
王兰揩了揩额头即将滚落的汗珠,露出绚烂的笑容。并将背篓里的青菜腾出,一把一把地将其捋齐整,搬到一台锈迹斑斑的打菜机前放好。这一连串的动作似乎比以往麻利了许多。
然而,在王兰的心头,她并没有丈夫田三想的那么长远,她只是想到今天剔的青菜能让两头肥猪饱饱地美餐一顿。接着她又回忆起火毛猪刚从街上买回来的样儿——板凳高矮的双月牙猪,劁猪匠劁猪时那牙猪的惨叫声好像还有耳边回响,之后便是像服侍大爷一般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操劳了。
现在看来,这些艰辛付出都是值得的。
田三夫妇一边欣忭地吃晚饭,一边给煮猪食的灶肚添煤。待老两口吃完晚饭时,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内的猪食已经熬熟了。田三在灶旁的蛇皮口袋内舀了几瓢包谷面掀入锅内和猪食一并搅拌均匀。想到猪价行情时,田三又将所有剩汤剩菜全部倒入猪食锅内。换作平时,在十分节俭的田三家里,这举动绝对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了。
养了一辈子的猪,田三夫妇也总结出一套独有的办法。在老两口看来,猪喂生食是完全不可取的办法,连同拌到猪食里的包谷面也得在猪食起锅前熬上一会,猪才爱吃坐肉。另有,他家的猪是一粒猪饲料不肯喂食的。他一直觉得猪食用饲料后,猪皮发红,身体太热,容易得病。
这已是全村老少皆知的事情了。
是以,畜牧站工作人员到他家里推广青储饲料制作方法时,田三总是嗤之以鼻。每到年关,他家养殖的肥猪皆不愁卖。确切地说几乎被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预定了,且价格总会比市场价高一些。这才是田三夫妇最引以自豪之处。
以前,田三夫妇年经时,姑娘儿子在外念书,家里开支大,夫妇俩每年都会养上十头八头大肥猪,待娃娃开学之际,卖上几头给屠户们,学费问题就此轻松解决。这种美妙的感觉,成为夫妇俩起早贪黑,想尽一切办法,长年累月地在猪身上忙活。
因而,他家园圃里一年四季皆种满白菜、青菜、莲花白、甜菜和汉菜,田地里除种植点经济作物烤烟外,其余地块皆大面积种上包谷、麦子、苦荞、洋芋、萝卜和南瓜。这些园圃和田地里的蔬菜和农作物几乎都是为家里的那些猪猡准备的。
每年十多吨包谷和麦子,十四五吨洋芋和南瓜,还有三四吨苦荞构成了十余头肥猪的主食。再适时在园圃里种植些蔬菜,偶尔也要到荒地里、田埂上和小河边割些野菜野草添补着,这才让猪猡们长得膘肥体壮。
每年进入腊月后,田三夫妇需将数吨青菜和萝卜用机器打细晒干,以备来年春季喂猪。这算是在猪食方面上了道保险,也是这对勤恳夫妇过人及厉害之处。
如此繁重的农活和生猪养殖,一直持续到姑娘儿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扳指算来,已有二十余年了。
二
在省城跟儿子生活了一段时间后,田三夫妇不顾儿子儿媳的百般挽留,毅然携手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个祖祖辈辈生活的小山村。这并非跟儿媳吃不甜,恰恰相反,儿媳本分大方,懂事随和,对老俩口又殷勤又体贴。
街坊邻居们都笑田三夫妇傻,有着清福不肯享受,偏偏要回到这山高皇帝远的山旮旯来,还弄几头猪来辛苦喂养。住老的山坡不嫌陡。这是田三夫妇能想到的,也是搪塞邻里最管用的一句话了。
然而,在田三夫妇看来,城里头固然好——高楼大厦,街道宽阔整洁,交通十分便捷,看病购物方便。可城里人见他老两口长得黑瘦,穿着朴素,说话土气,总会用一种睥睨的眼神看人,这已经让两位远道而来的农村人很不舒服了。
孤独成为压垮老两口心里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村里头,他们可以跟邻里乡亲拉拉家常,说说笑话,串串门子,有什么好吃的就相互送彼请此。干活累了时,可以跟庄稼诉诉苦,可以跟牲畜谈谈心,可以听虫儿鸟儿唱唱歌,也可以对着蓝天白云祷告求福。好不安逸快活。
城里的小区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门对门的邻居竟然不相互说话,走路擦肩而过皆不打招呼,形同陌路。人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俨然养猪场一般忙碌。年轻人有忙不完的事,这可以理解。
但老年人每天围着麻将桌打牌,双眉紧锁地对弈,没日没夜地在广场上舞蹈陶醉。而这些城里人自以为老有所乐的活动,田三夫妇一样不会,一样不好。时间一长,田三夫妇越发感到孤独,开始怀念更加适合自己的农村田园生活。最终老两口踏上了回家的路。
毫无疑问,回老家生活对于田三夫妇来说是个正确的决定。拣两亩距家近且肥沃的地块种上包谷荞麦,再在房前屋后种几畦蔬菜,养上几头猪,喂上一群鸡,日头辣了到树下坐着乘凉,打雷落雨了回家歇息,早晚搬个凳子坐屋檐下听风看雨,又有盼头,时间又好消磨,筋骨又得到了活动锻炼,心情又舒畅怡悦。
逢年过节,姑娘儿子带着孙女外孙回来,想吃肉,灶头割块腊肉切了炒,不用担心有瘦肉精。想吃鸡肉,院内看哪只鸡不顺眼逮到宰杀了放沙锅里爊,不用担心速生鸡。想吃蔬菜,园圃里各种应时菜蔬皆有,不用担心菜叶上残留下的农药。想吃鸡蛋,鸡窝里刚下的新鲜蛋多的是,不用担心买到假鸡蛋。这些大城市无法买到的肉、鸡和蔬菜,让那孙女外孙吃得流连忘返。临返城时,姑娘儿子的车后备箱内都满满当当地捎上蔬菜、瓜果和鸡蛋这类大城市难于买到的东西。
这让田三夫妇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三
幸福的烦恼,就算对于田三夫妇这种桑榆圆满之家,也并非常有之事。
从县城农贸市场回来之后,田三血管里的血液开始快速地流淌,再也无法淡定了。屠户们那种爱买不买的神气,市民们惊愕却无可奈何的样儿,以及街头巷尾人们因为猪价猛涨而爆粗口,在田三的脑壳里折腾捣乱,平静的海面骤然间激起的大浪。而非洲猪瘟正是那激起千层大浪之石。
田三在车站旁吃了碗米线,给钱时才得知已经涨价两块钱。这对使钱极其悭吝的田三来说,算是吃了个哑巴亏。田三索性回到原位,压着心头的火气,赌气将那碗剩下的少许米线和汤一并喝干净了。
坐车回家的路上,乘客们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议论非洲猪瘟及猪价上涨之事,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鱼肉价张了五六块,鸡肉价涨了十余块,牛肉涨了二十多块。人们似乎从这种谈论中看到商机。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织网。乘客们又把话题岔到今后的增收生计上来。有个小伙说,他要即刻在院子里扩建数间猪圈,弄些猪秧儿来养着,一年半载后,拿不准就发了。有位妇人说,她要立马给家里的老母鸡弄些新鲜鸡蛋来孵小鸡,七八个月后就可捉到街上去卖个好价钱。有个老汉说,他要在门前的那水塘内养一潭鱼,水面上再弄一群鸭子在上面浮着,到时鱼涨价卖鱼,鸭涨价卖鸭。
那跑客的司机再也不淡定了,他一边轰油门,一边忿忿不平地道,看来拉客这门子生意是干不成了,整天累死累活地往返开车,也就弄得个百把块钱。今后我也得改行,我这客车今后就给你们拉猪拉鸡,收入应该不赖。
一个戴黑框眼镜的斯文男子接话道,我劝你们还是去养牛吧,成规模后,不但能搭乘猪价上涨的红利,还能享有政府部门的养殖补助经费,一举两得。
话音刚落,车内顿时聒噪起来。大家有说对的,有说不妥当的,争论得没完没了。只有田三嘴巴紧闭,愁眉不展,心神不宁,脑袋里全是家里那两头火毛肥猪在圈里头窜来窜去的场景。
刚吃完晚饭的田三将灶肚红彤彤的碳火,用个火盆弄了些出来,抓一把茶叶放在那熏得黑黢黢的茶罐里,然后放在碳火上炕香后,再将开水往茶罐里一倒,沏开的茶随着茶罐里的水沸腾后,满屋的茶香味儿直让人嗅得欲罢不能。
田三夫妇围着碳火和茶罐十分惬意地坐着品茶。茶过数巡后,就将话题岔到家里的那两头肥猪身上去了。一时间,夫妇俩就肥猪卖与不卖的问题上争执不休。
王兰认为两头肥猪皆在一百公斤上下,二指厚的膘,正是长肉的时候,现在卖了怪可惜的。再说,她养了一辈子的猪,还从未卖过如此般膘薄的架子猪。而田三则不这般认为,他觉得要抓住目前猪价奇高的行情将两头肥猪尽快卖出去。这样一来,钱也没少挣,养殖风险也不用担。
老两口正为此事争执不下时,隔壁的赵老汉钻进屋头来串门。赵老汉算是田三夫妇最谈得拢的街坊了。然而,田三夫妇并未因赵老汉的到来而停止争执,反而越说越起劲,大有一种想要赵老汉评理的味儿。赵老汉是个老好人,他对于田三夫妇的争执并未选边站队,更没有冒然说谁对谁错,而是一边静静地听,一边微微地笑。
赵老汉见田三夫妇再争吵下去,担心矛盾升级,便以一种极为中肯的语气道,你们老两口完全没必要这般争执和纠结,我觉得你们不妨问一问你那省城工作的儿子。
田三夫妇一听便开窍了,立即给儿子打了个电话。儿子听懂了父亲的来电之意后,便爽朗地说道,眼下非洲猪瘟影响确实较大,省城肉类价格都因此而猛涨,但并不一定会持续涨下去。至于是养是卖,得看老家那边的县情村情才能定夺啦。
末了,皮球再次踢给田三夫妇。其实田三多少听出了儿子的意思,便开始问身旁的赵老汉,某某村的那个小型养猪场,前几天是不是因为害猪瘟被畜牧监管部门清了场,还有某家某户的猪得了瘟病,被乡上畜牧站的工作人员拖去焚烧了。因为确实是近来发生过的事,所以赵老汉想不表态都难,只得不住地点头示意。
王兰似乎从丈夫和赵老汉的一问一答中听出些名堂来着,便用一种服软的口吻对田三道,你自己掂量着办吧。说完后起身径直往后院去了。田三心里明白,老伴这是放不下那两头火毛大胖猪哩。
四
当生杀大权掌握在田三手头时,他反而举棋不定了。他认真地揣摩着儿子和老伴的话语,并反复在心头掂量。心想,假如猪肉价格持续上涨,数月后那两头猪也各自长胖了数十公斤,到那时再出售,不就发大了吗。可转念又想,假如疫情蔓延到村里头,那到手的六七千元钱不就打水漂了呀。
两头火毛肥猪是卖是养,对于田三来说确实伤透了脑筋,直弄得其首鼠两端。
家家户户的狗吠声和猪叫人嚷声,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小山村的寂静。人们从房屋里头钻出来,打着电筒倚门观望,侧耳细听,巴不得即刻将这突兀事情弄个清楚明白。
正巧刘才家那游手好闲的小儿子从门口经过,田三夫妇便向其问明事情的始末情由。原来,收废铁的张大麻子从外县某村低价捎回头病猪来,乡上畜牧站得知情况后,随即向乡长报告了情况。乡长立马组织了数十名干部职工向村里扑来。
那张大麻子捡便宜弄来的那头肥猪,经畜牧站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后,有疑似感染非洲猪瘟的症状,遂不由辩解,十多位着迷彩服的汉子蜂拥而上,将那病猪连拖带拽地弄上一张密封得极为严实的货车上,开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进行销毁处理。
夜在和时间的赛跑中慢慢沉静下来,山村被一床皂色的被子覆盖得严严实实,再次进入了酣睡。房前屋后的虫声甚密,换往常,这些虫儿的欢叫声如同催眠曲一般,在不知不觉中把人哄睡。然而今晚田三听起来却有些聒噪,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因为他心里头怀揣着件事,却越想越让其心乱如麻,他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认真思考。
在无法入睡的痛苦煎熬中,田三索性起床抽起烟来,几根烟烧完后,田三似乎有了主见。他推了推熟睡中的老伴王兰,见其没有反应,便摇核桃树上的核桃一般,两手用力地摇动王兰。
王兰睡梦中惊醒,翻骨碌爬起来,睡眼惺忪却又极为恼火,忿忿地对田三道,老不死的,深更半夜地把人弄醒,难不成你诚心要人老命吗。田三慌忙解释道,我是个心头揣着事便睡不着觉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见老伴闭着眼又躺下身睡了,一副不耐其烦的样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得怀着烦恼跟无尽的长夜抗争。
田三心头装着事,天不亮地不白就早早醒来,却又把老伴吵醒。王兰听见有鸡鸣狗吠,知道天快亮了,便起床扫地生火去了。田三洗漱妥当后,就围着老伴生的炉火兜圈,还是那副忧心忡忡的表情。
王兰听街心里已有响动,知是早起务农的农民,便开了门,见东边已现出鱼肚皮了。田三背绰着手出去街上转了一圈,复又心急火燎地回到家中,见王兰已经在厨房里准备熬猪食。田三犹豫了下,还是开腔道,我琢磨了整整一夜,觉得还是把两头胖猪卖掉最为妥当,就目前的形势,养一天风险大一天。王兰一边将切猪菜的节奏放慢,一边默默地听着丈夫的话语,全然一副爱咋办咋办的神气。
见老伴没有反对的意思,田三敞开说道,事不宜迟,乘现在还早,你去喊丁屠户,就说我家那两头大胖猪要卖,看他能出多少价钱。我去黑七家知会一声去。王兰听田三要去知会黑七,便冷言道,你卖猪知会人家黑七干嘛,他又不做生猪买卖,人家小儿子再隔几天就要娶媳妇,正忙里忙外的。
真个是头发长见识短,这事你甭管。田三拿出家长的派头说道。
待王兰忡忡地朝丁屠户家方向远去后,田三自言自语道,他家办喜事难不成吃素吗?他家亲朋好友这么多,少下两三头胖猪来,这酒席能办圆满吗?
五
田三带着黑七赶回家里时,丁屠户早先一步赶到了。丁屠户迫不及待地赶到后院猪圈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两头大肥猪瞧,不时洋溢出满意的微笑。见田三带着黑七走近时,大抵知道其用意,也不打招呼,索性开了猪圈门,伸出右手掌在那两头酣睡的猪身上拃来拃去的。
王兰慌忙制止道,丁师,咱家卖猪都要过称走明路的,从不玩估价。再者,我家猪怕生人,受不了这般惊吓,你还是别瞎忙活了,快快出来说话。丁屠户听王兰这样说,一边拍着手上的灰,一边嘻笑着道,你说的我都晓得,我这样做自有道理。其实王兰怎会不知,丁屠户这样做是想凭经验估计出猪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猪的重量砍价罢了。
丁屠户从猪圈出来后,也不打话,便从衣兜里掏出包烟来,用鸟爪一般的手指拈出两根,颤抖着手给田三和黑七递了过去。三个男人一边抽烟一边将话题扯到了两头肥猪上来。田三反复解释道,是他自己忙昏了头,老伴听错了话,糊里糊涂就将两人叫来,并没有其它意思。
然而,田三欲盖弥彰的解释岂能瞒过丁屠户和黑七。换平日里,大家乡里乡亲的,谁买都一样。此一时彼一时,现今猪价上涨迅猛,一天一个价,关键是很难买到头膘肥体壮的肥猪,更别说像田三家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猪了。原本丁屠户第一眼望着两头肥猪时,好不开心,再想到即将大赚一把,难免激动得声颤体抖。
当黑七也在猪圈门口反复地瞧、仔细地瞅那两头猪时,丁屠户似乎才觉察到大事不妙——有人想要虎口夺食。便立即收住了激动万分的内心,愀然作色道,黑哥你不安心在家迎接即将进门的儿媳,却跑来这里瞧猪,难不成也改行啦。
黑七听得出丁屠户话里藏针,觉得有些气恼,便脱口道,你这话听起来让人刺耳,这两头猪你过了称?还是给了田三定金?我看都没有嘛。再说了,他田三家养的猪,他想卖给谁就卖给谁,又不是非你丁屠户不卖,也不是咱买不起。
眼看丁屠户和黑七说戗了,大有吵起来的可能。田三忙往两人中间站定,解释道,此事都是我和老伴慌乱中出了差池,才会同时叫了你们两人来。其实田三内心极为欣喜,这场景是他最想看的场景,他就是要盼着两位鹬蚌相争,他好渔人得利。一旁的王兰明知丈夫扯谎,却又不便当场拆穿,只好干站着强颜欢笑。
还未等田三把话说完,丁屠户已大声道,三十五元每公斤,两头胖猪我都要了。田三一听,喜不自禁,这价钱每公斤足足高出市场价五块钱。
我出价三十七元每公斤,两头猪连毛带屎我全要了。黑七大声接话后,铁青着的脸扭朝一边,一副非买不可却你们看着办的架势。丁屠户一听,觉得黑七这分明是要夺人所爱,气得咬牙切齿,一股怒火隐隐从脚底冲上头顶。厉声道,我出四十,四十元每公斤。
黑七毫不示弱地道,我出价四十五元每公斤。丁屠户忿忿地道,我出五十元每公斤。黑七立即回答到老子每公斤出价五十五元。
此情此景,把在场的人惊掉了下巴。田三心想,这回发大了,想不到我家这两头肥猪竟然能卖如此高的价钱。
然而,王兰的见地却全然不同。她觉得此事首先是丈夫的做法欠妥。两个买家之所以把猪价抬得如此高,无非是心里头堵着口气。
于是,王兰便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说道,我知道二位说的是气头上的话,就你们出的这个天价,就算你们铁了心要买,我也不会卖,也不敢卖。你们想想就这价格,几乎快要赶上牛价了。我若照此价将猪卖给你们,传出去,那些高价掏钱买猪肉吃的老百姓们,非得将咱家十八代祖宗都得骂个遍不可。
田三眼见到口的肥肉就要被老伴搅黄,便悄悄地伸脚去踩老伴的脚。王兰岂会不知,只是装作什么都未察觉。
丁屠户和黑七听王兰如此般说,无不默默称赞眼前的这个女人,也算是亲自见识了其做人做事的风格,确实如坊间传扬的那般令人钦佩。而王兰这番话语更妙之处还在于——给两个火气冲天的汉子一个台阶下。
于是,黑七和丁屠户皆面露惭色,且静静等着田三再说句让场面不至于尴尬却又能使大家有脸有面的话语。然而,田三到底没有说出一句像样的话,反而用一种不甘心的语气说道,你们都是村里有头有脸之人,一口唾沫一个钉,这回骑虎难下了吧。
听话听音。显然,田三并不想就此罢手,他并未打消借机大捞一把的想法。见丈夫心心念念的样儿,王兰还是对着丈夫怒道,黑七和丁师是外村人吗?你忘了他们以前帮我们家的那些事了吗?你觉得钱真的那么重要吗?你平时教导娃娃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难不成是信口雌黄吗?
王兰一番斥责将丈夫田三说得哑口无言,一旁的两个买家皆瞠目结舌,面面相觑却又默默称快。
这猪今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卖了,你们都回家去吧。明天,如果你们诚心要买我家猪的话,价格就按市场价,多一分钱咱家也不要,少一分钱咱家也不干。至于卖给谁,这就有些伤脑筋了。要么一家卖一头,要么抓阄,到时由你们商量着办吧。
六
黑七和丁屠户一边讪讪地从田三家走出去,一边暗自庆幸,两人手里头捏着的冷汗总算停止了流淌。不用说,两人皆对王兰的为人处事心悦诚服,同样对田三的做法极为愤懑。遂各自回家。
两户原本两个方向,一家住村东一角,一家在村西边河畔。丁屠户走了一段路,觉得先前之事确实是自己利令智昏,话语上确实过于激动和毛糙。于是,折返回去追上黑七,忸怩着道,黑七哥,刚才确实是兄弟出言不逊,冲撞了你老,你老大人有大量,此事就一笔勾销吧。我反复想了,田三家那两头大肥猪,你小儿子讨媳妇正好派上用场,你就照市场价买了吧。
黑七正因丁屠户没尊没长地顶撞自己而心头窝火,加之田三利欲熏心,更是让黑七憋了一肚子的气,一路正骂骂咧咧地发泄着心中的不快。见丁屠户主动撵上自己服软道歉,内心堵着的那口气顿时顺畅了,彼此间的那点小误会也就瞬间烟消云散了。
于是,他答道,丁师你也别这样地说,我这人年纪大了,说话做事便倚老卖老了,望多多包涵。至于你说田三那两头肥猪,趁现在猪价高,还是你宰杀了去县城卖吧。你不比我,你肩膀上的担子重着哩。
黑七哥这样说就是还恼着我了,你家隔几天要办喜事,亲朋好友多,非杀两头猪无法圆满。现在这非洲猪瘟疫情愈发不明,你若用外地买来的猪肉办席,难免让客人吃了不放心。你就别执拗了,再推辞下去反而不直爽了。丁屠户忙答道。
我想好了,我去村头秦老汉家买头牛来宰算了。黑七忙答道。
你只宰牛不成呀,客人中定然有不吃牛肉的,你还是得宰头猪掺和着吧,再加上弄些鸡鸭鱼肉的拼着,才能让客人吃好喝好。丁屠户很体贴地说道。
黑七竟然被丁屠户一席话说得哑口无言,好会才结结巴巴地道,现在的人生活好了,并不一定吃太多肉,再说办法总会有的。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相互谦让着,没完没了。此时,从地头干活回家的陈大爷刚好路过此地,了解到两人为买猪之事你推我让的,便大声道,老七,小丁,你们用不着如此为难。我看一家买一头,明早便去过称给钱。
陈大爷在村里头德高望重,说话做事不偏不倚、公道合理,这是全村人一致公认的。黑七和丁屠户见陈大爷这样说,相视而笑,皆点头同意了。
田三望着黑七和丁屠户走远后,气得直跺脚,心想到口的肥肉被老伴三言两语说丢了,心头好不窝火,便对老伴王兰大发雷霆,骂她装大尾巴狼,说她白到大城市见了世面却改不了老实巴交的坏毛病,说她在外人面前装大好人却将骂名给自己背,说她一根筋的心性已经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了。
王兰背着身一动不动地站着听着,一副镇定自若却坦荡无悔的神气。听丈夫说骂够了,再找不到任何能想到的难听词语了,便慢悠悠地转过身来,讪笑着道,老田呀,咋你都到这把年纪了,还不明白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呢,其它道理我说不来,就说这黑七哥,那年你大病在家,咱家的那些田地,不都是人家黑七哥赶着他家那两头水牯牛帮咱家犁了的,人家喝过你家一口水?吃过你家一顿饭?还有那丁屠户,虽说人家是生意人,那年咱家娃开学等着要用钱,又恰逢生猪滥市,我去喊他来买咱家的猪,人家都没咳一声,还是按市场价买了咱家的猪。这些难道你都忘了吗?咱们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岂能趁火打劫。
见丈夫终于放下那盛气凌人的样儿,王兰又说道,原本你同时喊两人来买猪抬价就错在先,之后黑七哥和丁师皆因买猪心切,不但话语上相互戗起来,更是将猪价抬了又抬,跟市场价相比,几乎翻了两番。如果我们冒然高价卖给谁,我敢断定,他们两家将从此结怨。自然,他们两家跟咱家也将埋下心结。就为区区几千块钱,你觉得做人能像这样吗?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想,怎么做,反正我永远不会干这种事。
王兰一席话终于让田三闭上了嘴。
七
第二天,天麻麻亮,丁屠户慌慌张张地跑往黑七家去敲院门。黑七听敲门声急切,便披上衣服,趿了鞋子出来开门,见是丁屠户,道,大清早的,这又是咋回事。
丁屠户忙道,黑七哥,昨天我们敲定了买猪的事后,回家时我顺便将买猪的事告知了田三。昨夜躺在床上时我突然琢磨到一个问题,以田三那德行,定要早起将两头肥猪喂得饱饱的。那猪吃了食,自然要比平时重几公斤。所以,今早我特意天不亮地不白的就起了床。果不其然,刚才我从他家门口经过时,见他家灶房的烟囱已冒着烟了,田三十有八九在忙活猪食的事了。
黑七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忿忿地道,田三这人,都儿孙满堂了,还改不了这般小人行为。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称猪去。于是黑七和丁屠户仓促往田三家赶去,到田三家门口敲门时,天已经大亮了。
田三慌脚慌手地开了院门,见是黑七和丁屠户,有些猝不及防,一边将手上沾着的猪食不停地往身前的围腰上擦抹,一边强颜笑着道,你们起这样早,估计我家那两头肥猪都还没睡醒,这如何过称。
黑七接话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子吃,人家丁师还得把猪宰了运县城里去卖呢。这去晚了摊位不说,买菜的高峰时段一过,卖谁去。丁屠户忙帮腔道,还是七哥了解我们生意人的苦处。
田三一副极为难的脸嘴,好会才道,你们坐客厅吃口茶吧,我去后院把猪弄醒。丁屠户忙道,不用了,我们还是去后院称猪吧。说完话后,黑七和丁屠户索性径直往田三家后院走去。
猪圈门前的猪食槽内热气腾腾,黑七忙将头凑近一瞧,见食槽内满是才起锅的猪食,便用一种挑逗的语气对身后的田三道,原来你家养猪长膘,每早还要吃顿早点呢。
田三觉得丑事败露,便用一种惭愧的语气道,我本以为你们要到晌午才来拉猪的,遂将昨晚剩下的这些猪食爊热,打算喂牲畜一点,也不至于让两头猪空着肚子上路。这猪跟人在一块时间长了,总有些割舍不下的情结,这让你们见笑了。
丁屠户边听边捂着嘴笑,咕咕的笑声让田三害臊得无地自容。黑七见状,忙道,小丁呀,你可能有所不知,老田之所以放着大城市的舒爽日子不过,回到这拉屎不生蛆的边远农村来,心里头不就是割舍不下这些猪儿鸡儿的嘛。
田三听到黑七挖苦开涮的话语后,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好不尴尬。恰好此时王兰一手拿香一手拿纸,朝后院走了进来。见大伙望着冒热气的猪食揶揄田三,全然明白了关键所在,便狠狠地睃了田三两眼。丁屠户眼尖,早看到了这一细节,为避免老两口拌嘴,便忙道,乘着天早,咱们将两头猪赶出来过称吧。
王兰在猪圈门边点燃了纸,并就着纸烧起的火苗点着了香,嘴巴一阵咕嘟后,极其虔诚地对着猪圈门作揖三下,再将香火插到圈墙的一个罅隙上,才去开圈门唤猪。
说来也是奇怪,换往常,那两头猪听到王兰的说话声就嗷嗷地叫,如是听到王兰独特的唤猪声则是更加兴奋异常,基本上是一开圈门两头猪就会抢着、挤着蹿出来。
然而,今早两头猪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无论王兰变着调子唤那两头猪,两头猪皆纹丝不动,四平八稳地睡着。直到四个人一齐开腔都无法将两头肥猪唤起来时,大家都有了不祥的预感。
丁屠户用小心却吞吐的语气道,莫非猪儿身体有恙。
乌鸦嘴,别信口雌黄,咱家这两头猪昨天还活蹦乱跳的,这隔一晚就出问题?绝不可能有啥事。田三一边用一种惶恐的腔调答话,一边躬着腰钻进猪圈,两手用力地揪那猪的尾巴,直揪得猪嗷嗷怪叫,就是不见有起身的迹象。
田三没辙,只好郁郁不乐地钻出猪圈,铁青着脸,狠狠地踢了食槽一脚。黑七忙安慰道,你别焦躁,这张嘴货吃了五谷杂粮,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些小毛病,也许是患了肠胃病或感冒,都是再正常不过之事。现在当务之急是快去请徐兽医来看看到底这猪是咋回事呢。田三听黑七这样说,内心的惶恐和忧虑稍微平复了些。
王兰觉得黑七的话在理,往门外趱去。田三见老伴去喊徐兽医,犹豫了片刻后,随即又小跑着跟了上去,赶上了老伴,一把拉住。
王兰道,老田这又是般古怪。
田三忙将老伴拉到路边的一棵大树背后,轻言轻语地道,你怎么这样憨,要是那两头猪果真被徐兽医诊断出什么问题来,那到手的七八千块钱不就泡汤了吗?我觉得还是别去请徐兽医为妙,回去降点价把猪卖了才是上策。
王兰听完丈夫的话后,瞪眼望着身前的这个男人,这个一起生活了数十载的老伴儿,这个利欲熏心的老头,让她越发感到陌生。丈夫已经年过六旬,说话做事却与这年纪全然不称。她用力地甩开了丈夫那只手,那只紧紧抓住自己不放的手,那只把自己手臂捏得发麻发疼的手,毅然往徐兽医家而去。
田三望着老伴渐行渐远的背影,心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八
当徐兽医背着医药箱尾随王兰进入田三家后院时,田三正热锅上的蚂蚁般在猪圈门前兜圈。黑七忙掏出包烟来给徐兽医递了一根,颤抖的手险些将香烟弄掉。当大伙都拢在徐兽医身旁抽烟时,死寂的氛围才被弥漫在空气中的香烟打破。
在大家惶惶的眼神下,徐兽医边噙着香烟,边慢悠悠地从医药箱内拿出双一次性手套戴妥,点着明晃晃的电筒钻进了猪圈。于是大伙便一窝蜂似地围拢到猪圈门口,看徐兽医如何给猪看病。
只见徐兽医先将电筒往猪身上通彻照了遍,再将电筒光和注意力全集中到那带红斑的耳朵上,反复观察后,又将电筒光照到那猪鼻孔上的那些碎泡沫上,最后将那带着薄塑料手套的手紧贴着猪脖子感觉体温。待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后,徐兽慌慌张张地从猪圈跳出来。
徐兽医入圈前后的动作心态判若两人,大家紧紧地盯着他。好会徐兽医才颤动着双唇道,就这两头胖猪的症状来说,十有八九是患病了。
患什么病?田三忙接话问道。猪瘟,我虽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但我奉劝你最好还是向乡兽医站汇报下实情,以免节外生枝。徐兽医在医牲畜方面也算是有几把刷子的人了,全村老少也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田三听到徐兽医的话后,吓得面青唇白。他忙扯住徐兽医的衣角哀求道,看在你我一起长大的份上,你再仔细瞅瞅,看这猪会不会是得了其它小毛病。
我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非要让我说不切实际的话,或说违背良知的话,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徐兽医干脆直接地回答了田三的话后,背起医药箱转身走了。
黑七和丁屠户见状,也再不敢提买猪之事,一个个走了。
田三愣愣瞌瞌地干站着,半晌作声不得。待隐约听到老伴在堂屋内的电话声响时,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将两手不停地用力捶打着地面,发出阵阵刺耳的声响。
王兰打完电话后,似乎听到后院传来的异响,转到后院一看,原来是丈夫难过得瘫坐在地上,两手不知疼痛地敲打着地板。见丈夫如此气量和胸襟,心中的火气发作起来,便厉声斥责田三道,照你这德行,那电视里报道的那些害猪瘟的老板,早一个个上吊吃农药了吧。
待田三的情绪稍微平复后,王兰又接着说道,这牲畜不就跟人一样嘛,谁敢拍着胸脯说一辈子不生病带痨,你这样难过,无非是昨天我阻止了你高价卖猪嘛。跟你说,幸好没将猪卖出去。你想想,要是这猪卖给黑七,他家亲戚吃了这猪肉出了问题,追究下来难道你脱得了干系。或者说这猪被丁屠户宰杀了到县城里卖了,假如恰巧被你二哥或者其他亲戚朋友买了回去,全家老老小小吃了这病猪肉,弄出什么问题来,难道你心里忍心好受?跟你说吧,如果真是那样,我会夜夜睡不着觉,内疚一辈子的。
田三听妻子王兰这样说,竟然找不到一句挽回颜面或应对老伴嘲弄的话语,只得将嘴巴闭得铁铁的,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儿。
就在田三夫妇静静地坐在后院猪圈门前喟然长叹时,忽然间听到门外大路上车鸣人嚷,嘈嘈杂杂。那阵仗老两口前天晚上见识过,知道是乡上畜牧站处理病猪的队伍到了,王兰便慌忙起身去开门。门敞开时,一大群身着浅蓝色卫生衣的人站在了门口,为首一位中年男子介绍了自己身份和来意,王兰面无表情,沉默不语,转身引着大伙到后院去逮猪。显然,她的脚步不如往常那般利索,像有根隐形的绳索牵绊着。
两头胖猪被一辆密封的小型货车拉走后,田三还一直立在门口抽烟。他郁闷地眺望着那辆拉猪的货车消失在村庄的尽头,许久都不愿进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