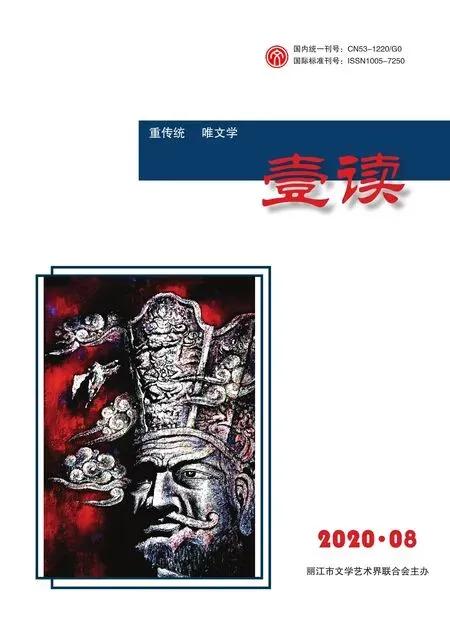鲤鱼河边的太师椅
◆马海
1
城东,鲤鱼河鸣吼得厉害。河上唯一的一座廊桥,在洪流中颤抖着瘦瘦的身子。
桥头,镇水铁牛也潜进了水里,似乎忘了身负的职责,与河底鱼虾嬉戏去了。
立在堤上的历届县知事的德政碑,被浪花刷得透湿。顺河而来的臭狗、死猪、烂木柴,被恶浪卷上堤坝,在这些离任的县太爷们德政碑前逗留不走。
县衙当差的刘四,举着伞,被脚下一只死狗尸首绊了一跤,顾不得体面,爬起来,踉踉跄跄穿过廊桥,直奔县衙。
“老爷,不好啊,县南四乡全部受灾,村庄都泡在水里了。” 刘四报告说。
县知事马宗彝望着木窗外面的鲤鱼河,面色铁青。
“去葛土司家借粮的邵三有没有消息?”马宗彝问。
“葛土司家拒不借粮,邵师爷又去城北几家绅粮家想办法去了。”刘四回答。
马宗彝恨恨地说:“葛狐狸,真是不顾恩情,前年被贺二麻子围攻,要不是我们及时救援,他葛府早已覆灭葬身火海!”
刘四说:“老爷不要急坏了身体,下午邵师爷回来,说不定就有好转,到时候我们街头煮粥赈济灾民,也可以度过难关。”
马宗彝没有言语,披上蓑衣,戴着斗笠,带着县衙几名差役,通知民团练勇,向城南灾区而去。直到傍晚,安顿了大部分灾民,粒米未进的马宗彝回到县衙,累倒在塌上。
今年全县遇到百年难遇的旱灾,去冬到今夏未降滴雨,所有农田无法种植,灾难日重,马宗彝下令开仓赈灾,县衙粮仓已空,绅粮家资也被消耗大半。没想到的是,近两日全县突然普降暴雨,全县瞬间从抗旱救灾的模式进入抗洪抢险模式,祸不单行啊!
县域良田被淹,百姓流离失所。县衙存粮告罄,朝廷赈粮未到。凄风苦雨中,满目是扶老携幼的灾民。
历史的考验,摆在马宗彝面前。这是他做官二十年没有遇到的难题。
夜黑时分,到葛府借粮的邵师爷邵三骑着马宗彝的黑马回来了。芭蕉廊下,邵师爷走进了马宗彝的视线。
马宗彝说:“邵师爷,事情办得怎么样?”
邵三说:“马大人,我都去葛府守候三日了,可无论我怎么求他,葛土司就是不肯借粮给我们。”
马宗彝说:“你没跟他说明年加倍还他吗?”
邵三说:“说了,差不多都给他下跪了,但没用。他倚仗自己朝中有人,不想帮这个忙,反而还趁火打劫,想借机哄抬粮价。并且,就在今天早上,葛土司居然还有兴致,带着几个家丁去观赏鲤鱼河洪流,不顾民生多艰,吟诗作赋,当时正好从上游漂来一具女尸,他不但不叫人打捞,反而琢磨出几句歪诗来,什么‘凫女依岸白,窥鸟栖苇翠’,真是为富不仁啊!”
马宗彝“啪”地一巴掌拍在廊柱上,骂了句“贼日的!”。
雨水越来越密,雨打芭蕉,如战鼓擂,如兵戈杀伐,如楚兵哀嚎。
马宗彝的脑海里突然浮上一个人的影子来。
马宗彝咬了咬牙,说:“邵师爷,今晚你陪我去趟监牢。”
夜色沉沉,冷雨敲窗。马宗彝和邵三披着蓑衣,刘四打起灯笼,闪电中,三个人瞬间就被雨水吞没了。
马宗彝说:“你们两个是我多年心腹,不瞒二位,今晚我要做一件可能丢乌纱帽甚至是性命的事,望二位齐心。”
邵三抱拳说:“愿意生死相依。”
刘四也应诺。
三人像鬼魅出现在了死牢里。马宗彝让刘四支开衙役,死牢里只剩马宗彝和邵三。
马宗彝看见,死牢里,一个披头散发、胡子蓬乱但又不失精神的中年囚犯,坐在草铺上,正在闭目养神。
马宗彝听到了死牢屋顶雨水炸裂之声。他想起前年在救援葛土司并围剿绿林大盗贺二麻子的夜里,抓获了这个杀死两任县知事的恶匪,也就是眼前的这个气定神闲的中年囚犯。朝廷本要问斩,但马宗彝认为贺二麻子罪不该死,因为他每次抢劫的都是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没有乱杀穷人,偶尔将劫来的财物救济穷人。在马宗彝一再上书的情况下,贺二麻子得以缓刑处死,留在县衙死牢。
马灯忽闪忽闪,几道黑影留在三人脸上。马宗彝对着贺二麻子说:“贺二,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做一笔买卖……”
鲤鱼河畔,一夜电闪雷鸣。
次日,县城传出沸沸扬扬的新闻:绿林大盗贺二麻子越狱出逃,并连夜洗劫了葛土司家粮仓,带领千人饥寒队,把粮仓搬运一空。
雨水骤停。
县衙外,葛土司率卫队练勇闹得不可开交,葛土司挥鞭指着马宗彝说: “马大人,一个官府死囚,人人皆知的大盗,硬是在你眼皮下越狱成功,并洗劫土官粮仓,你不怕问罪?”
马宗彝背着手,冷冷地望着天空。
午后,马宗彝一副草民着装,身后一个随从,走过瘦瘦的廊桥。站在那一排前几任县知事德政碑前,马宗彝对着县城作揖说:“对不住了,我就要逃亡深山老林,铜县子民,暂别了。”
身后随从掩面而泣,此人正是刘四。原来,天亮前,邵师爷骑着马宗彝的黑马飞奔知州大人府上,状告马宗彝私放死囚。马宗彝知道一切都暴露了,趁问罪之师未到,带着刘四亡命山林。
2
马宗彝和刘四一连在山林奔袭五、六天,夜不敢宿店,昼不敢停息,食野果,住山洞,精疲力竭。
这日二人走到山岗上,望着山脚一户人家,屋顶炊烟袅袅,正是午饭时间。马宗彝靠在树上,对刘四说:“刘四你后悔吗?当日我告诉你不要随我亡命天涯,受我牵连,你就是不听,你看,我们不知去哪儿安身!”
刘四说:“大人言重了,能追随您是我福分。想我刘四流浪汉一个,没有亲人,是您马大人将我收在县衙,待如亲人,现在您因为百姓黎民而落难,我应该在您身边效犬马之劳啊。”
马宗彝说:“哎,我半生阅人无数,唯一对邵三这个‘烂杆苕’(华坪方言,坏蛋的意思)看走了眼,收他为师爷二十载,没想到危急时刻竟是他坑了我。”
刘四说:“邵三这种人,只想着自己升官发财,没有大志,是为小人,不会有好报。大人,我们几日没有吃油荤了,我去山脚这户人家看看,能不能做顿饭给我们填肚子。”
马宗彝摆摆手说:“不能去,我们虽然离开铜县县城百多里了,但州里一定在通缉我们,进入民宅,一旦暴露身份,就危险了。”
刘四说:“大人放心,我先去屋外门缝看看虚实,伺机而动。”
马宗彝说:“你小心点。”
刘四一个人遛下山去,轻手轻脚到了屋后,小心探看这户人家的情况。
马宗彝靠在树上休息,等刘四回来。半晌,刘四回来了。马宗彝问:“怎么样? ”
刘四说:“我观察了,这户人家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在家。”
马宗彝说:“那我们去要点吃的?”
刘四说:“大人,现在我要给你化妆,要不然你做官二十年,政声又好,很容易被人认出来。”
马宗彝说:“你要怎么给我化妆?”
刘四说:“我包里还剩一把黄豆,我在火里烧一下,然后你躺下,我把烧烫的黄豆放在您脸上,为您破破相!”
马宗彝说:“这是一种民间古老的办法,最后我会变成一个麻子。哎,想不到啊,我马宗彝堂堂正正读书人,却要变成马大麻子,而土匪贺二麻子却是没有麻子的人,硬是被官府说成是有麻子的人。”
于是,马宗彝就按刘四说的照着做了。滚烫的黄豆放在脸上的时候,马宗彝仿佛闻到了自己的肉香,八九个麻子窝留在脸上。马宗彝脑海里,瞬间浮上老辈诗书传家的教诲,浮上自己金榜题名时的喜悦,以及从政二十载的若干酸甜苦辣,面颊上不觉几滴老泪横溢。
刘四难过地说:“对了,大人还要改一个名字,就叫马大麻子吧,马宗彝这个名字从此就消失在世间了。”
刘四想想又说:“我们就装扮成脚夫,大人今后还要少说话为好,因为你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开口就容易暴露身份。”
二人到了山脚人家门口,叩门喊了几声,一个妇女走出来开门。门打开一条缝,露出妇女惊疑的目光,她看看二人,说:“你们是做什么的?”
刘四说:“大嫂,我们出门找活干,走了多日,身无分文,实在饿得不行,请您行行好给点吃的。”
妇女说:“我男人出去砍柴没有回来,不便请二位进来,你们就在门外等候,我给你们做点吃的。”说完关门进屋去了。
刘四和马大麻子就在门外草垛上斜靠着,等妇女送吃的出来。
一袋烟工夫,就看见一个挑着柴的大汉从小路上走过来,刘四和马大麻子主动上前打招呼。
挑柴大汉看看二人,刘四就把刚才对妇人说的话又说了一遍。大汉放下肩上柴担子,爽快地说:“二位若不嫌弃,就请进屋小憩,吃顿粗茶淡饭,我也是这山中樵夫,粗人一个。”
二人表示感谢,随樵夫进入院子。妇人正在做饭,樵夫就与二人攀谈起来。
樵夫说:“二位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刘四略微看了马大麻子一眼,说:“我们在铜县做杂役,遇到匪乱,待不下去了,就到其他地方去找活儿干,路经这里,身无分文,只得化缘贵舍了。”
樵夫说:“你们应该走大路才是,我家这里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去邻县道路不通啊。”
刘四说:“我们就是不熟路径,误入山中,困顿几日,没有主张。”
屋里妇人做好饭菜,摆到院中,家里还有一个八十老翁,拄着拐杖出来。樵夫说老翁是自家老父,耳聋在家。于是四个男的坐在院中吃饭,妇人和小孩在屋内吃。
樵夫拿出一壶酒来,说:“这是前日到山外卖柴换来的酒,两位尝一口。”
樵夫又指着桌上一盆肉汤说:“这是前日山中打柴,遇到一条十来斤重的毒蛇,被我打死提回家来,与一只山鸡煮成龙凤汤,老父看了鸡头说今天会有客人来。我不信,说家里几年都没人来过,没想到被老父说中了。”
马大麻子和刘四又看看白发老翁,说:“老爷子真行!”
白发老翁低头吃饭,没有听到大家说话,只说:“吃肉,蛇肉补气。”
饭后,二人要道别,樵夫看看天色,说:“夕阳坠山,山林险恶,二位不妨住一宿再走,我家里有柴房一间,二位暂且窘苦而卧。”
马大麻子施礼谢过,说:“一再劳烦主家,实在是过意不去,我们还是赶路算了。”
樵夫说:“出门在外,艰难险阻,二位不必客气,只是屋舍粗鄙,卧榻简陋。”
马大麻子和刘四盛情难却,于是谢过,留宿樵夫家。
夜晚,月上东山,山林松涛拂进柴屋,马大麻子和刘四在柴房柴草铺上,盖着薄被,都没有入睡。墙角虫鸣涌起,马大麻子和刘四开始夜聊。
马大麻子低声问刘四:“今天你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刘四说:“我觉得这家人不那么简单。”
马大麻子说:“对。首先,这个樵夫我见他第一面就看出,是练过武的人,步伐和眼神都稳健灵动,一点都不像久居深山的木讷樵夫。再一个,吃饭的时候,我看见他腰部衣服内层有一个葫芦坠,绘有弓箭,这是蛮王寨兵营的标志。”
刘四说:“蛮王寨是边关千总紫蛮王的领地,看来这里也是他的暗哨。我们处于危险之地,你为何答应留下住宿了呢?”
马大麻子说:“正因为这样,我才决定留下来看看有什么蹊跷。不出意外,邵三现在已经是铜县的知事了,取代了我的位置。在被人通缉的情况下,我们留在这里反而安全一点。”
次日清晨,二人起来,樵夫一家招呼二人吃早饭。饭桌上,马大麻子主动问樵夫:“昨日闻令尊大人会算卦,可否劳烦他老人家为我们二人看看前程?饭后我俩准备上路,不再打扰大兄弟一家了。”
樵夫愣了一下,略微迟疑,说:“其实,你二人可以多住几日。老父算卦举手之劳,稍等。”
樵夫从内屋扶出老翁,凑在老翁耳边大声说明了意思。老翁看看二人,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方促膝而谈。老翁缓缓地说:“我打量二位已有一整日了,二位心神不宁,像是没有确定去路,既然没有决定去哪儿,就留下住几日。”
马大麻子抱拳说:“老人家眼慧,请继续示教。”
老翁继续说:“就说你吧,一脸麻子并不是老痕迹,而是新近所为,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给自己脸上留下永久的遗憾。诸多迹象表明,二位是有难在身啊。”
马大麻子和刘四心悦诚服。
马大麻子说:“老人家能否为我二人指点一个出路?”
老翁说:“二位有两条路可选择,方可避开劫难。一是此地东去五十里,有蛮王寨守关兵营一座,投身边关,为国家马革裹尸,亦不失男儿之志。二是南去三十里有天师观一座,二位出家为道,修身出世,了断凡尘执念,也不算穷途末路。”
二人默默不语。良久,二人向老翁深深作揖,告别樵夫一家,出门上路。一路上,鸟音稀少,天色晦明。
3
话说马、刘二人逃离铜县,邵三因举报有功,被新任为铜县知事,州县发出通缉,抓捕马、刘二人。邵三坐在马宗彝原来坐的太师椅上,望着头顶“明镜高悬”的牌匾,用手在太师椅溜圆而光滑的扶手上撸了几把,长叹一声:“老马啊老马啊,跟随你二十年,我一直望着你的太师椅,妄想有朝一日坐上你的位子,今日终于实现夙愿。老马啊,今夜你亡命何方啊?”
邵三走到马厩,抚摸着黑马,说:“你想念你的老朋友没有?你不跟随他去,也是好事,免得宿露餐风、担惊受怕,留在县衙,随我继续巡视疆域,何其威风!”
黑马咴咴,打着响鼻,继续吃豆子,不理会邵三。
邵三抽着绿玉石烟嘴的烟袋,坐在县衙长廊,望着缥缈的天空,雨雾笼罩着鲤鱼河畔,悠悠吐着烟圈。邵三不仅想写诗,甚至想填词,便命书童捧砚,食指勾起一支细长的狼毫,在兰纹暗底笺上用精致小楷写下一帧:
江湖飘零久,铁砚磨穿何所有?文章嫁帝王,狼奔豕突鲤河柳。二十年来宦海梦,马放南山无觅处,铜县方可游。太师椅上北望,明朝快马轻裘。
邵三呷了一口茶,大快,命衙役抬上滑竿,鸣锣开道,穿过鲤鱼河廊桥。邵三坐在滑竿上,享受着鲤鱼河畔蒙蒙烟雨。退潮的鲤鱼河中,一伙小儿游水嬉戏,像鸭子一样在水里钻来钻去。一个稍大的娃娃见了滑竿上坐着的邵三过来,走过来施礼说:“县太爷大人好!”
邵三面露悦色,问:“小娃懂事,知道我?”
小娃竖起大拇指说:“邵大人文章风流,升任县太爷,鲤鱼河烟柳明媚,我们给大人出个节目。”
邵三大喜,示意衙役停下滑竿,欣赏小儿们的节目。带头小儿骑上河中镇水铁牛的脖子,指挥水中一群娃儿大声念起童谣:
刀口架在耳朵旁,师爷抽烟莫慌张。三根扁担横官道,一根挑着假仁义,一根挑着腹中剑,一根挑着白眼狼。
念完,娃儿们哗啦啦全部潜进水里,朝下游快速游走了。邵三坐在滑竿上略一沉思,脸色大变,咬牙切齿。旁边一个衙役说:“大人,他们在骂你呢,刀口架在耳朵旁不是邵字吗?三根扁担横官道不是三字吗?”
邵三指着远去的一群娃儿,大骂:“小鬼蛋子些给我滚远些!”
河面只留下一些漩涡,卷些枯枝败叶。
邵三忽然看到桥头多了一块新立的德政碑,原来是老百姓偷偷为马宗彝立的。碑下还有被雨水浇灭的香。碑文正中是:马宗彝老大人德政碑。铭文是:
朗朗乾坤,滔滔河水;铜县有幸,舍你其谁?为官五载,功勋属归;肩挑大义,汗洒帐帷;而今远去,青山泪垂。
邵三内心也感到钦佩马宗彝,面露惭愧之色,说了声:“非我邵三不仗义,是你释放绿林大盗,犯下滔天大罪,上天给我邵三施展大才的机会!”
邵三带人沿河而上,抵达城北葛土司衙署。
葛土司戴着狐狸皮帽,肩上蹲着一只老鹰,出门笑脸相迎。
“邵师爷,哦,不对,邵大人,别来无恙?”葛土司说。
“葛兄呐,不但是地头蛇,更是鲤鱼河边一强龙!”邵三回礼。
“比起邵大人,袖里长风、腹内锦绣,我葛某差得远啊!”
“葛兄家族居鲤鱼河明清两朝,雄风不倒,犬牙护院、鹰爪凌云,不简单啊!”
“哈哈哈哈哈!”两人一番谦让,踏着砖缝绿苔,入得葛府深院。只见得院内北苑春深、南窗帘重,画眉深浅入时无,别有一番婉转。
酒桌上,二人一番推杯换盏,开始把话题回到正题上。
葛土司二指捏着小酒杯,望着杯中酒,正言道:“邵大人,不瞒你说,过去五年马宗彝做铜县知事,软硬不吃,导致土官与流官配合不畅,一县治理呈现二马逆向。现在邵大人执掌县印,有什么打算?”
邵三略一思索,狡黠地说:“葛兄放心,你为地头蛇,我做强龙,龙蛇合流,铜县地界就是你我的了!”
葛土司说:“邵兄堪为俊杰。”
邵三说:“下一步,你我合力要做的事情有两件。”
葛土司说:“明白。一是尽快铲除大土匪贺二麻子这个后患。二是追杀马宗彝。”
邵三说:“贺二麻子现在纠集旧部,占据老鹰山,不及时清剿,恐夜长梦多。至于马宗彝,现在流亡山林,暂时构不成威胁,但有机会必除之而后快!”
葛土司说:“贺二麻子是我多年仇家,屡次清剿,总让他逃脱。老鹰山地形我已经摸清楚,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一举剪除。”
邵三说:“铜县最宜广种大烟,利益丰厚,你我当强制县民广泛种植,富民强军,今后方可图大业。”
“干!你我英雄所见略同。”二人开始放怀畅饮。
葛府上空,月如钩。
邵三离开葛府,回到县衙后,立即行文张榜,推行大烟种植。山区或半山区,原来那些红土上的包谷和大麦换成了罂粟。葛土司所属夷民纷纷效仿,广袤山区到了罂粟花开时节,美丽的罂粟花流淌成河。收获时节,铜县东西南北四方各设赶烟会的市场,外县外省的军部和地主收购烟土的马队,纷沓而至。是年,邵三与葛土司大收烟款烟税,瞬间暴利,肥得流油。第二年春,邵三请风水大师卜居鲤鱼河西岸,建邵家大院,占地十余亩,亭台楼阁,好不威风,与城北葛土司府隔山隔河对峙。邵三又择日与葛土司联姻,将年满十六的女儿嫁给葛土司弱智的小儿子,完成强强联合,铜县完全落入二人掌中。其他乡绅豪族敢怒不敢言,惧怕葛土司卫队与邵三民团的二百多条枪,有的主动巴结、趋炎附势,有的惹不起只好敬而远之,不与邵、葛争利。
话说贺二麻子自打抢了葛土司粮仓之后,奔袭老林,重整旧部,拉起五六百人、两三百条枪,占据鲤鱼河源头的老鹰山,扯大旗、建碉堡、垒营寨,重新做起了山大王。贺二麻子虽是个杀人如麻的绿林大盗、土匪头子,但清楚自己这条命是原县知事马宗彝给的,虽然当夜大牢中二人达成的是一笔买卖,贺二麻子出狱当夜就率人拿下葛土司粮仓,赈济灾民,算是扯平了。但贺二麻子内心还是敬重马宗彝,如果不是马宗彝压着,自己早就行刑问斩了,哪里能够等到重回山林的一天。于是贺二麻子也遣人四处打探马宗彝的下落。这日,一个线人来向贺二麻子报告:马宗彝在天师观出家为道。贺二麻子计上心来,决定会一会这位昔日的铜县知事马大人。
4
马大麻子和刘四在樵夫一家指引下,在蛮王寨与天师观二者之间,最终选择在天师观出家为道。一年多时间,在道观修行,马大麻子从县知事到一个地地道道的麻子流亡山林,再到一个入了道行的修行人,人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常常一把老泪仰望落叶,弃了四书五经,在青灯之下读起《道德经》来。
这天,刘四打柴归来,递给马大麻子一封信。刘四说:“道观外路口遇到一个人,让我把信带给你。我当时大吃一惊,竟然有人知道你的下落,感觉不是一般人物,没有多问,迅速回来了。”
马大麻子打开书信,一张草纸上歪歪斜斜几行字:
行迹萧萧改名姓,炒豆换容入山林。青灯难改士者心,重归人世收太平。申时天师观北路口见,老鹰山贺二顿首。
马大麻子收起信件,走到院心,轻轻说了句:“世事难了,尘世未平,该见的人还得见。”
申时,马大麻子和刘四到了约定地点,三个穿着羊皮褂、蓬头垢面的大汉果然等候在那里。
中间大汉扯开缠在头上的黑布,正是贺二麻子。向马大麻子抱拳施礼道:“马大人一年多来受苦了。”
马大麻子说:“换个活法而已,体验人生另一种况味,不失一种风景。”
贺二麻子说:“青灯之下不是大人的归宿,世道上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你一身才华,难道要带到棺材里去?”
马大麻子说:“你我自铜县一别,就井河有别,各奔前程。”
贺二麻子说:“你士大夫情结太重了。我为匪,脸上清清白白,你曾为官,脸上却留下麻子。这不是天大的讽刺是什么?”
马大麻子说:“命运捉弄,人生如此。”
贺二麻子说:“你在四川老家的家人,去年我已派人及时转移,免遭迫害,现尚且安全,你就不想东山再起,与家人团聚?”
马大麻子面色红光绽放,说:“此话当真?”
贺二麻子说:“一言九鼎。”说完拿出一个铜铃,递给马大麻子。
马大麻子接过铜铃,仔细端详,说:“这是我老父的信物,不错。”说完向贺二麻子施礼答谢。
贺二麻子说:“我在老鹰山尚缺军师,诚聘你赴任。”
马大麻子说:“你保护我家人,恩重如山。赴任阁下军师一职,待我思索一下,酉时回话。”
贺二麻子说:“静候佳音。”说完与两个随从走进树林去了。
马大麻子与刘四回到天师观,在天尊神像前焚香一柱,叩拜三首,说:“神佑我族,今我马氏不肖子孙马宗彝马大麻子就要屈身绿林,匪盗为生,下辈子转世做个孝子。”
说完泪下,再三叩拜,收拾行当,与刘四步出静悄悄的道观,回首窥视,白云锁翠,青鸟寂寂。
老鹰山寨,贺二麻子隆重欢迎马大麻子荣任军师,刘四也成为山寨头目。山寨杀了十多只山羊,抬出几十坛白酒,寨门、山洞口披上红布。两排匪兵站成八字,十二支老火枪朝天一齐轰响,山鸣谷应,山崖上老鸦噗噜噜腾空飞起,黑压压遮了匪寨上空。贺二麻子一声山喝:“兄弟们,在这不浑不浊狗日的年代,大家一起死死生生,今天迎得老马当我们山寨军师,老马是饱读经书、见过世面的人,也是我贺二的恩人,得到这样的人物是山寨有幸,今天开始,喝了这碗酒,老马的话就是我的话,老马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干!”
寨中几百人一起山喝海吃,异常热闹。
马大麻子坐在贺二麻子旁边的太师椅上,居高临下,看着莽莽匪寨,一颗颗攒动的人头,光头的,披头散发的,戴着帽子的,青面獠牙的,胡子拉渣的,仿佛进入一个从未到过的世界,拉开一个提枪耍脑袋的野蛮世界,一时心底苍凉,眼眶一热,滴下一颗泪来。刘四在一旁看见,赶紧凑到马大麻子耳边说:“不可啊,你是山寨二当家了,要给大家一种霸气,今后才能服众。”
马大麻子将碗中酒一饮而尽,将刚才的难堪掩饰过去。高举酒碗,“啪”一声砸得粉碎,高唱山歌,迈着虎步,与匪兵乐到一起去了。
随后,贺二麻子听从马大麻子建议,到邻县绑了刘、何、陈三家大户的票,收获极大,利用几十箱鸦片换得不少枪支,扩充了山寨硬实力。为了瓦解铜县最大的两股势力葛土司和邵三,山寨派人下山挑逗边关土酋紫蛮王和葛土司的矛盾。因葛土司多年来有抢亲习惯,恃强凌弱,每年都会做两次混事,把民间新娘轿子抬到葛府,强行与新娘“过初夜”,第二天才将新娘放还回去。这一恶行使得民愤深重。
这天,贺二麻子部下打探到一个消息:过几天就是紫蛮王大儿子成亲的日子。贺二麻子立即安排部署,定下一计。
到了紫蛮王大儿子成亲的日子,紫蛮王家护卫队与娶亲队伍抬着新娘花轿路过山道,贺二麻子山寨队伍伪装成葛土司的人马,将紫蛮王娶亲队伍拦截,击毙部分护卫队人员,扬言是葛土司要强行纳新娘为妾,放走几个人回蛮王寨报信。山寨匪兵将新娘轿子抬上,往葛土司府悄悄进发,到葛府附近扔下新娘及轿子,迅速撤离。
这一事件导致了蛮王寨与葛土司彻底翻脸,紫蛮王率领边关千总营兵,以及积怨颇深的夷民数百,连夜围攻葛土司府,月黑风高,将柴草团团放置葛府院墙四围,用硫磺布团置于箭羽尖端,万箭齐发,葛府瞬间变成火海,火枪手伏击于葛府大门外,逃出的人纷纷被放翻。葛府主仆及卫士百多人,无一幸免,只有葛土司弱智的小儿子因住在邵三大院,方得幸免于难。
鲤鱼河畔,世袭百年的葛土司府一夜之间葬身火海,成为铜县历史大案。紫蛮王擅诛土官,自知朝廷即将问罪,回到蛮王寨,一把火烧了几百年建立的边关兵营,投靠宁远府去了。
事情发生以后,马大麻子突然发现事情闹得太大,虽然铲除了铜县大恶霸葛土司,但伤及许多无辜,更重要的是紫蛮王丢弃边关投靠外省大员,致使铜县与临省边境失去屏障,今后更多的匪乱和战争会不期而至。为此马大麻子后悔不已,请来几位术士,到山下为死者招魂,念经超度亡灵。
贺二麻子认为马大麻子是妇人之仁,说没有杀戮就没有明天。为此,贺二麻子认为应该趁葛土司被剪除的时机,一举下山全力拿下邵三大院,占领县城,把事业做大。
对于这个决策,马大麻子坚决制止,说:“邵三一介贪吏,为获取暴利,广种罂粟,危害铜县,迟早自有督军问罪,多行不义必自毙。我们倾巢攻打县城,必然生灵涂炭,伤害一县百姓,会导致一县多年不能振作。况且,到时候上头派大军围剿,我老鹰山一干弟兄危矣!”
贺二麻子很是恼火,连连叹气,抱怨军师,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5
这天,贺二麻子告诉马大麻子,黑山绅粮刘大坤出资请山寨为他办一件事情,需要带几个弟兄去商谈,就麻烦军师去走一趟。马大麻子骑着马,叫上刘四,带着十多个喽啰,往黑山去了。到了黑山刘家,刘大坤见了马大麻子等人,一听是老鹰山的人,吓了一跳,感紧恭恭敬敬招待。提起贺二麻子所说的事情,刘大坤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马大麻子才知道是贺二麻子故意将他支开,心里马上明白了:贺二麻子要出兵攻打铜县县城!
马大麻子茶水一放,带着兄弟立即往回赶。刘大坤以为招待不周得罪了老鹰山的人,连忙赶出来留客,马大麻子一骑绝尘,马后十多个人飞沙走石,瞬间没了踪影。
回到老鹰山,不出马大麻子所料,贺二麻子只留下十多个守寨老兵,全部下山攻打县城去了。
稍作安排,马大麻子与刘四二人骑马下山,抱着能制止贺二麻子屠城的愿望,直奔县城。在半路,听闻县城枪声大作,贺二麻子与县城民团已经交上火。原来贺二麻子早有安排,遣心腹混入县衙,做了内应,攻打县城时内应打开城门,贺二麻子一枪洞穿民团团首鄢老大的喉咙,北门告破。贺二麻子牺牲了二十来个弟兄,就一举拿下县衙,民团守兵纷纷投降,被贺二麻子缴了枪支,全部关进大牢。贺二麻子另外派了一支人马攻打邵三家新修不久的邵家大院,家丁卫队守不住,邵三肩部中枪,骑着黑马从后门夺得一条生路,单枪匹马往山上奔来。黑马驮着邵三,惊魂未定,转过一片树林,正好遇到纵马赶到的马大麻子和刘四。马大麻子一眼看到熟悉的黑马,自己曾经的坐骑,再看看马背上狼狈不堪的邵三,大喊一声:“邵师爷哪里走?”
邵三勒住马,定睛看到一脸麻子窝的马大麻子,一脸疑惑,再看另一人,认出是刘四,再看看马大麻子,不觉大惊。邵三见二人也不掏枪,稍微安定,双手整整衣冠,故作镇定地说:“二位老朋友别来无恙?”
马大麻子说:“邵师爷啊,你我二十年交情,就不如你头顶的一顶乌纱帽。你也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东西,今欲往何处去?”
邵三说:“荣华富贵一场梦,鲤鱼河边的太师椅,今天再次易主。求二位不计前嫌,宽恕于我,让我逃出去,后会有期。”
马大麻子说:“我可以不计前嫌,但我的坐骑可能不会随你去了。”说完将二指放进嘴里,一声口哨吹响,黑马听到老主人熟悉的声音,前足高高腾起,一声天朗气清的嘶鸣,差点把邵三颠下马背。
任凭邵三挥缰绳、打马背,黑马就是原地打转,举足不前。邵三一急,拔出腰刀,往黑马背上扎了一刀,黑马一声厉叫,向小路上亡命奔去。
刘四拔出手枪,要开枪,马大麻子止住他,说:“随他去吧,秋后寒蝉而已。”
马大麻子和刘四到县城,贺二麻子已经控制了县城,将一县几十家绅粮集中到县衙,控制了人质,收缴了枪支。贺二麻子派人将马大麻子迎接到县衙内,马大麻子看到,贺二麻子坐在自己曾经坐了五年的太师椅上,自己斟上一碗酒,舌头舔咂着嘴唇,长长叹了一口气,对马大麻子说:“军师啊,一切是那么的熟悉,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师爷,我要昭告全城父老,我贺二麻子就是一县父母官!我老贺亡命山林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贺二麻子坐在太师椅上,用双手撸了几把太师椅光滑如玉的扶手,很是享受,望着头顶上空布满灰尘的“明镜高悬”的牌匾,高喊一声:“老子等这天等了三十年啊!”
马大麻子说:“恭喜贺大人荣登宝座!我到城外去转转。”
鲤鱼河畔,又下起了一年中最后的秋雨,空空濛濛,没有边际。马大麻子一个人穿过河上瘦瘦的廊桥,走到了那一排历届县太爷的德政碑前,看到了最新的一块碑,碑中一排大字:马宗彝老大人德政碑。接着看到左下方铭文:
朗朗乾坤,滔滔河水;铜县有幸,舍你其谁?为官五载,功勋属归;肩挑大义,汗洒帐帷;而今远去,青山泪垂。
晚上,贺二麻子在县衙酗酒,醉醺醺之际,刘四上来禀报:“贺大人,城北崖下寻到邵三尸首,旁边还有一匹黑马,是坠崖而死。”
“哦,罪有应得。”贺二麻子醉眼朦胧,一脸得意。
“另外,军师一个人不辞而别,不知去向。”刘四又说。
“娘的,看不起我!现在铜县是老子一个人的,看还有谁能灭我?”贺二麻子沉着脸说道。
夜色已深,鲤鱼河边一片死寂,贺二麻子一个人在县衙太师椅上睡着了。鼾声雷动,头顶上方高挂的“明镜高悬”横匾上,落下许多灰尘,洋洋洒洒,在贺二麻子酒杯里和脸上蒙上一层土灰,如霜如雪。
三个月后,贺二麻子因压榨乡绅,将囤积的鸦片卖往外地,致使铜县民不聊生。省督军派军队对铜县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围剿。铜县县城上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流民四散。贺二麻子神勇,守着最重要的南门,一连三天恶斗,枪管都打红了。夜色即将破晓,战斗停息,一片死寂。迎着曙色,城门大开,刘四用盘子端着贺二麻子的人头,向官军团长献上。
一县战乱平息,由省府委任的新一任县知事如期而至。太师椅上,又有人撸着更加光滑的椅子扶手,仰头享受地望着头顶上方的牌匾。刘四因除恶立功,封为铜县民团大队长,奉命守卫铜县。
鲤鱼河畔,又响起衙门办案的声音。至于那个不辞而别的马大麻子,不,前任县知事马宗彝,他的故事还在铜县县城茶馆与坊间流传,有人说他回到天师观继续做他的道士,有人说他到广州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在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中还立了战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