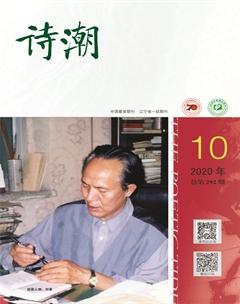暮色四合之地
张执浩
很难再见暮色四合之地了
晚风徐徐,晚霞淡去
亲人们在鸡飞狗跳声中归来
父亲蹲在水边先擦拭农具,再将
洗净的脚塞进湿滑的鞋帮里
母亲把干透的衣服拢成一堆
扔进姐姐们的怀中
很难再见我那么肮脏的脸上
浮现出来的干净和轻盈
只有黑暗在无声无息中包围住我们
却不知房间里的光从哪里亮起
[林忠成赏评] 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这首诗投射出一股“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温暖,田野牧歌从来是一位伟大的心理医生,治疗现代人心力交瘁的“现代症候”。迫于生存,现代人不得不生活在别处,疏离故乡,将精神放逐于钢筋水泥之丛林。“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岌从宦之徒,不远千里”(《聊斋志异》),“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荫,动逾千数”(《北史列傳》)。青少年时期的孜孜以求,以离开故土为终极目的,实现被现代化改写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目标。
在缺乏宗教皈依的悠远传统里,故土、家园、宗族就成了中国人的宗教替代品,它们代替上帝,把人心聚拢在一起。问题是,随着现代化的演绎和全球化推进,故土、家园的精神空间日益受到挤压,被消解,助长了我们失魂落魄、进退失据的窘迫。海德格尔早就深刻洞察了这个危机,“这是一个旧的神■纷纷离去,而新上帝尚未到来的时代。这是一个需求的时代,因为它陷入了双重的空乏,双重的困境。”(《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
田野与大地,是人类原初的出发地,最早的诗歌、音乐、绘画,就是对大地与家园的呼唤,“我们心灵的所有勇气,是对存在第一声呼唤的回声”(《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家园、大地为天下之母,人类以及万物,不过是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的结果。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海德格尔对此持相似看法,“大地是一切敞开者向其敞开之地,并作为敞开者的回归之地,在敞开者中大地作为庇护者而现身”(《诗·语言·思》)。不管世界如何变化,都离不开大地这个母题,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大地通过世界凸现,世界以大地为基础”(《艺术作品的起源》)。里尔克在1925年的一封信里有相似的感慨:“对我们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都具有无穷意味,无限亲切——几乎每一件事物,都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性的东西与加入人性东西的容器。”
大都市见不到晚霞、鸣蝉、炊烟,诗中说“很难再见暮色四合之地了”。对精神放逐敏感的诗人,很容易产生“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