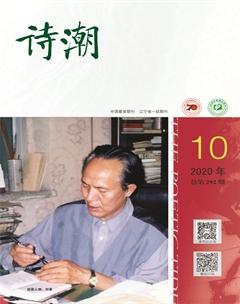都是毛绒绒的东西
坐在船尾的欢喜。
看着旁边几个人拍照的欢喜。
河水干涸由波涛转为涓涓细流的伤感。
某个人不在场的伤感。竞技场上
看到一个大个子被击倒的欢喜。凝视
地图上去过的某个城市的伤感。
电视里一群长相古怪的人一边
跳舞一边打闹的欢喜。走动在不知
其名的什么树的阴影里的欢喜。
站台出口四散的方向感的伤感。
一个早起的女人睁着睡眼倚着
阳台抱着自己望着你的伤感和欢喜。
都是毛绒绒的东西。雪中企鹅齐声叫唤。
[林忠成赏评] 余怒是中国诗坛的卡夫卡,其诗歌图像的差异、断裂造成的荒诞感,与卡夫卡作品异质同构。其诗歌通过扭断语法的脖子,达到非理性的眩惑,发出本雅明式的“光晕”。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认为“我们不能把它(非理性)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扭曲,丧失或错乱,而应简单地将它理解为理性的眩惑。眩惑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夜晚,是笼罩着任何光照过于强烈的地方的核心部分的黑暗。”余怒诗歌图像中的黑暗,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黑暗。逻各斯之眼看到的是理性的太阳,解构主义之眼看到的是虚无和混沌。“眩惑的理性睁眼看太阳,看到的是虚无……笛卡尔闭上眼睛,堵住耳朵,是为了更好地看到本质性日光的伟大光亮……疯人睁大眼睛,看到的只是黑夜,自以为看到了想象的东西,在被某种其实是黑暗的光亮所陶醉的疯人眼前,浮现和繁衍的是各种心象,这些心象没有自我批判能力,却又无可补救地脱离现实存在。”(《疯癫与文明》)
余怒堵住逻各斯的眼睛和耳朵,看到的尽是毛绒绒的心象,是反结构、反语法的“欢喜”,这些“欢喜”是存在主义式的,在逻辑眼里恰恰是悲怆。眼前的一切,船、河水、競技场、电视节目、树影、女人,统统都是荒诞的存在物,相互间无意义链接。作者在写作时,面对的是隐身于墙壁中的隐身人,不是市场的引车卖浆者流。语言从通用的世界中撤退,作品沉默之处,就已在言说。
解构主义目之所及,全是毛绒绒的价值体系,它主动拆除语言的清晰性、单向性,把常规语言上下文之间的逻辑梯子撤掉,让前后句形成落差,延异、复调等反结构效果由此显现,整首诗呈耗散状,每个词都是一个颤抖不已的神经器官。“它增强我们对于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同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让·弗·利奥塔)谬误推理是语言扩容增值的最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