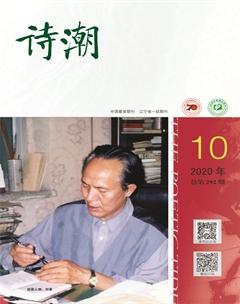人间杂事 [组章]
章德益
鼾 声
那晚,一个女子坐在她丈夫波涛滚滚的鼾声边,垂钓梦境。
她丈夫的鼾声水面宽阔,暗潮起伏,里面有若干神秘之鱼。
垂钓了半夜,果然钓出一尾,啊,风情万种、斑斓炫目之美人鱼!
女子一声呵斥,有泪滴出,遂迅速把那美人鱼一把摁住,拎起,趁鱼儿新鲜赶紧往厨房里跑。一番深加工处理后,次日,烹制成一道美味的川式美人鱼火锅。
晚饭用餐时,她问丈夫,这尾美人鱼味道如何?啊啊,她丈夫瞥了一眼太太,赶紧埋下头吃饭。又抬头,打着哈哈,哈哈……但哈哈声里分明溅出几滴可疑的水沫。细看,是昨夜鼾声里残存的暗流。
是夜,她丈夫鼾声诡谲莫测,旋涡暗涌,不知深浅。那女子沿着鼾声向遥远的上游走去。漫天月色,不知所终。
野生动物美食家
凡美食家,身体里必有一群野生动物出没。
打鼾时,他鼻息里的狮吼与狼吟。走路时,他脚步下的猎豹影子。思考时,他头脑里猴子的灵敏与尖叫。沐浴时,他身体上脱落的穿山甲鳞片。与人拥抱时,他姿态里虎腰熊背的发力。欢唱时,他舌头里闪耀的大眼镜王蛇的火红蛇信!
他消化不良!必须吃消化药助消化。当药片进入他胃囊里,那药片就觉得,啊,四周简直是一片莽野风光。胃液里孔雀开屏,胃酸里眼镜蛇发情,胃壁上金丝猴成群。大象迈步。犀牛漫游。河马蹒跚。如果你有幸观摩到他的排泄物,那真是一片微型的古大陆遗址与待开发的废墟公园。身体的断层已成为动物进化史的一个物证。他那胃的切片早已成为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乃至病毒学家的最爱。你可以从他的排泄物里预见到人类,啊,一种与兽合体的新新种群之降临。
戴帽子的人
戴帽子的人,帽子和头颅不断争吵,争夺肩膀的所有权。
帽子训斥脑袋。什么脑袋?如此荒芜,乱草丛生,毫无章法。
头颅不服气,什么帽子?没我脑袋,要你帽子何用?
而我,介于帽子与脑袋之间,既不敢得罪原生之脑袋,也不敢得罪后天赐予之帽子。
只能写诗歌时,求帽子暂时离开,只留一只孤零零脑袋浪游世界,天马行空。
不写诗歌时,就顺手把脑袋摘下,塞进抽屉里,让它闭目思故,或者闭目养神。在空无的肩膀中央,恭恭敬敬地放上那顶别人的大帽子。
中年人
一个中年人被孩子与老人强行掰成两半,一半生命建造成了幼稚园,另一半生命建造成了养老院。幼稚园里有他一个永远不肯长大的孩子。养老院里有他一对永远拒绝死亡的父母。他在这两者之间日夜奔走,心力交瘁。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老与幼、生与死之间的动态平衡。啊,终于有一天,他变成了他儿子的儿子,又同时变成了他父母的父母。他解脱了。因为在更老与更幼之间他发现自己只是一座中转站。他老在更老里,幼在更幼里。天真烂漫在老与幼、生与死的夹缝间。他现在对着三岁儿子喊爸爸。对着八十岁父母唤宝宝。在生与死之间来回奔走,其乐无穷。
牙齿祭
七十五岁。牙齿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门牙早就叛变。臼齿跟着起哄。牙龈越界造反。舌头顶着口腔像一面造反大旗。
我现在嚼任何东西都是嚼一团混沌,嚼一团虚无。混沌与虚无在我嘴里滚动,嘴是生命的黑洞。
最后的几颗残牙已把我逼到死角,已把我抵押给牙医作人质。
我只能投降。
筷子是我挂白旗的旗杆。我埋头吃饭时飘垂的白发,低垂成無与伦比的投降者的白旗。
读后感
一本书一只鸟笼。一只貌似很小其实广阔无垠的鸟笼。每个字都是一只鸟。每行句子都是一朵云。每个惊叹号都是一棵树。每颗逗号都是一只松鼠。每个问号都是一弯月。它小而不小,确定而不确定。你打开笼门阅读,发现里面真的无边无际。有森林、草原、河流、山峦、卵石滩、桃花水、野生动物群落与天空。你进去,早忘了它的鸟笼本质。在里面爬山、涉水、狩猎、野营,观赏日出日落,感叹月盈月亏,忘了是在书里,笼子里。因为你感觉不到那笼栅与笼门的存在。因为那笼栅与笼门已完全与四周的风物与风景融为一体。多少年过去。你已全然忘了书,忘了笼子。你只认为世界本来就是如此,世界应该如此,世界必须如此。啊,章兄,你是在议论一本书吗?还是在议论你的心灵或者思维方式?不。我仅仅是在议论一只鸟笼。一只用书本搭成的鸟笼。我进去后再没有出来。我的血肉已渐渐融化进笼栅并成为这笼子秩序的一部分。出笼的道路早已绝迹。前方是飞舞的死鸟。身后是飞舞的死鸟。头上是高悬的大地。脚下是塌裂的天空。
在书架找书
在书架找书,右角落传出博尔赫斯的手杖声。左角落传出陶渊明的吟哦声。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上,一朵不穿裤子的云正高一脚低一脚地下楼。书架顶端,幽州台上古远的长吟声,回荡着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唏嘘。
马丘比丘峰的巅峰上,我正攀登着去寻找聂鲁达,却一不小心拐进了卡尔维诺的隐形城市,迷失在隐形城市那无边无际、错综复杂的罗网般墙缝里……
书架最下端,夜夜传出卡夫卡因肺病而挣扎的咳嗽声。那么撕心裂肺,那么彻夜辗转。我真想去看望他一次。但我没有捷径可走。要找到他,必须千回万转,穿越无数城堡与老鼠洞,穿越无数城门与地道,但最后抵达的也许只是一个蛛网构成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