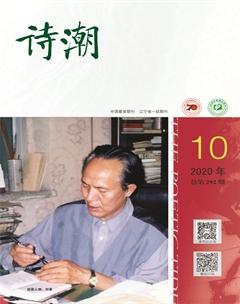比较学 [组诗]
钱松子
比较学
雨来得有点晚,
等待的益处,是让
春天语无伦次,
也让世界衍生无数虚线。
而我,在虚线之间
辨识自己的位置,
仿佛鸟鸣深处的高塔
不示结构,月光收敛为浓汁,
这么说,其实并不准确。
当我从站台归来,
在别人的屋子唱歌,
火车驶过隧道,
把比较学的理论部分
修饰得更深。
夜宿记
遁世有术,乘地铁过鸡鸣寺,
做一个即将开悟的少年,
裸出后背的硬道理。
我不怀疑,为寒夜寻找的解释,
南京用的是一场细雨;
以导航求证生活,
无解,只能是徒劳的思索。
雪意不复存在,
自江宁织造府到小旅馆,
纯属转喻,符合冬日一贯的逻辑。
整个晚上无法确定的含义,
像文化,最终通过
“精神的窄门”,
成为身体可信的一部分。
夏 夜
梦到荷开,波澜当枕头,
梦到窗外事,
今夏并非浪得虚名。
一个人在云端,
前半夜舉杯,后半夜拔罐,
屡屡从盛世借路,
弃车步行,凭空捏造无限开阔意。
你来,明月扶柳挖沟渠,
你不来,横岭侧峰。
灯火引更多夜色,
我有近视眼,所以心安,
有打算,就用蛙鸣输入法。
蹊 径
——与胡畔
“喜鹊喝水,洗羽毛。”
这春天的湖畔,最适宜遇知音,
听水底的喃喃细语,
今生已别无他想,一枝,
一隅,一立场。
而我们像两块镜子,
挤进喧嚣的世界,把寂寞照得雪亮,
很多年后,等自己解释。
那时,天空隐晦得无迹可寻,
神的眼神垂向一滴水,
看不出对立面。
蝴 蝶
像未来一样缄默,
像坏事越干越熟练,从心里认可。
她的生活“一直在表决”,
随时,自反省中掏出手铐。
上 山
从山脚去云顶,人间越来越薄,
几乎透明。峰峦深陷,
草木摸出钥匙,成为它们中的一员,
我拿错了,至今仍在纠结。
“寂静照亮隔音。”
风换了一茬茬,才把穹顶还给我,
带着抚不平的皱褶;
你俯首,才从底片脱身,
先一步回到明天。
知味帖
对屋脊发愣的视觉,
必然已历经风雨的传承,
跟在年华背后,我不止一次消失。
仲夏了,雷继续握紧天空,
挖坑,我手中的绳子,
就是巨大的错误。
“大地上响起椅子拖动的声音”,
亲人们按需回到身体,
脸涨得通红,影子布满老茧,
以至于没有心疼。
山水越走越偏,
白茫茫一片,突围出去的,
都是少年,他们闪烁,
像衬衣上的盐粒,
一夜间,打包此生况味。
小 暑
雷打滚,鹰不着地,
大梦贴窗花,正面红,反面绿。
雨投奔于草尖,像一种愧疚有头无尾,
人间听不出回响。
隐
当星空发出卯榫松动的声音,
季节已枯,人和事没有反驳的余地。
芦荻头顶钢丝,孤灯含水,
那些出于谨慎而停下来的摇曳,
多少有些不甘心,
那就约摆渡者去机会里撑篙,
景色有限,一眼如同永远。
打开百叶窗,放出玻璃,
我们对视的沉默是最高贵的尊严,
与天空平衡,大于飞行,
滋生久违的存在感。
夜太短,穿墙而过的背影难以更正,
给他晚礼服?不如给睡眠,
让疾驰也具备床单一样的褶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