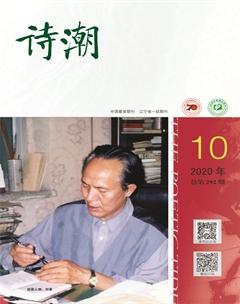刘一君的诗 [组诗]
刘一君
高 处
好险
雾霾爬到了影谷的脚面
被流水
带下山去
看图想起一个人
欧阳文睿
图一左一的那个人
是我的徒弟
也是跟我拍过三部电影的美术师
突然在2016年7月的某天
消失了
踪迹皆无
音信皆无
有人跟我说你死了
有人说你疯了
有人说你入狱了
我宁愿相信
你大玩了一场
历时N年的行为艺术
看到这段文字后联系我
师父想你了
回来咱们再一起唱
《海阔天空》
遥望南方的诗行
进入八月
我和南方的那群
青年
一样焦躁不安
诗意被海风
吹乱
捋不成诗行
尽管我的思想
会在分行和断句的
缝隙间站立
但是 是的
那海峡断得太深
隔望的两岸
正
彼此远去
也有好鸡汤
改变自己是神
改变别人是神经病
所谓争
无非是要别人
活成你要的样子
文宣街的夏天
暴热的伏天中
总有一辆喷水车
绕着文宣街洒水
或向空中
挂出雨雾中的彩虹
在尘光鼎沸的
高峰时刻
街两旁的喷头
会一起喷雨
使得古城的一角
偷得一线清凉
我很疑惑文宣街的
特优待遇
路人说
这儿正好有一座
pm2.5的
检测站
元宝山
树叶掉光了以后
从我的窗子看过去
那座山完整地露出来
形似元宝
沐浴着河流
我没有细算
我想我至少
在两百个房间内洗过澡
被流水覆盖 就像
窗外那裸露的灯
被黑夜覆盖
也扩散着光
也许我身体上的流水
早已汇进大海
早已蒸发成云
早已凝成雨水
再次降落人间
它们从我少年时的房间
流走
在我中年时的房间
回来
那我将无比幸运
此刻
我沐浴在多年以前的
同一条河流
我对贾丰先生有意见
新写字台到货以后
我認识了 家具装配工
贾丰先生
他背着很重的台板
正上台阶
我试图去 帮一把手
但是一个头发很硬的老者
是的 他稀疏的白发
根根竖立
像塑料头上的钢丝刷
接手抬过台板
在知道他年已七十的时候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
还干这么重的活儿
老头笑指着贾丰先生说
帮儿子的忙
这时我犹豫了一下
递给贾丰一根烟
贾丰先生 我说
我对你有意见
你好意思让你爸
干这么重的活儿
贾丰先生抽着烟说
现在人工太贵
找 狗
我要养一条
好看的
真实的
土狗
学名中华田园犬
但是
几乎在我看过的
每一张狗脸上
都多少带着
德牧 腊肠 松狮
拉布拉多 二哈 金毛的
影子
甚至在我影谷的后山
土坯房里
蔡老头家朝我龇牙的丑狗
也长着一副斗牛犬的脸
斑点的毛色
京巴的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