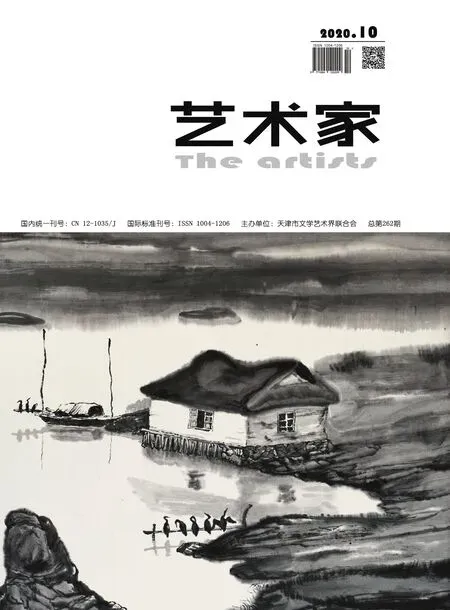王学仲新文人画的特点—以人物画为例
□苗 镇 淄博书画院
文人画的出现可上溯至唐朝,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所能为也”这一观点,文人画早期的发展根源上就奠定了其发展基调。至北宋,苏轼又提出了“士夫画”一词,来区别于院体画及民间绘画。元明清三朝是文人画发展的蓬勃时期,尤其是在元朝的时代背景下,大部分文人对现世的无奈使得田园隐逸之风盛行,本来的“作画聊以自娱”之态却对文人画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引导作用。
新文人画一词虽在20 世纪80 年代才被提出,但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相对于传统文人画,新文人画在创作题材、技法、时代意义等方面有很大变化,两者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境下一衣带水却又迥异的两种艺术形式。王学仲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进行新文人画的探索,尤其是在人物画方面,将传统文人画的“士气”“雅谑”“超形”“机趣”等因素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人物画作品。本文以王学仲新文人画创作中的人物画作品为出发点,着重探寻其新文人画的特点。
在王学仲早期的艺术生涯中,对传统文人画的继承是非常全面的。其父研究碑帖诗词,每日督促其严格练习书法,绘画上从传统的梅、兰、竹、菊入手,诗词古籍的诵读与抄录在其少年时期更是从未间断,这些都对他整个艺术生涯起到了深深的滋养作用。从根本上讲,王学仲的文人画在于根基深、涵养厚,从1944 年创作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画可看出其绘画风格颇受陈洪绶、任伯年的影响,笔精墨妙,画面文人气十足。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王学仲对新时代下文人画的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可视为其新文人画的开端,其绘画的形式、内容与同时期的画家相比风格迥异。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旅日讲学的经历加上“85 新潮”以后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量涌入,使王学仲的人物画作品有向传统回溯与反思的倾向。回溯传统并不是程式化地描摹古人画法,而是把传统题材引到现实中来,为“我”所用。
文人画在发展过程中被部分人贴上了“重意不重技”的标签,把文人画的“天真不雕”当作不重造型和技巧的笔墨游戏,这自然是个误解。王学仲的新文人画中具有传统文人画的艺术精髓,诗、书、画、印的结合与“以书入画”的“写”的精神,同时体现着现代画家的审美意识和思想。
王学仲的新文人画既“新”在笔墨技法上,又“新”在画面意境上,他既掌握古典文艺中的精髓,又对现代艺术史和美学知识涉猎广泛,其作品具备传统文人画中“士气”“超形”等因素,又具有很强的现代意识。王学仲在《钟馗卖瓜》这幅作品中将传统题材引入现实,传统画钟馗多是以除鬼降魔题材居多,在这幅画中,钟馗放着宝刀不用,却坐在一旁卖瓜,看后让人不禁一笑。画中传达出的人才浪费、缺乏赏识人才的伯乐等问题是王学仲对当下现状的思考。王学仲的新文人画去繁就简,在传统与现实中游走,其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还兼具亦庄亦谐的文人精神,令人思索、回味无穷。
文人画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有的审美体系,其特有的东方美学精神与架构中无不体现出超然的哲理性,传统儒、释、道的融合与互补使文人画充满了哲学思考。新时代下的文人画需要新精神、新思想的注入,不仅要外在的形式上有所创新,更要有现代意识。新文人画应具有超形的意味及人生哲理、风趣感、内涵,如果失去这些因素,那就失去了画的本质美,剩下的只能是解说图式的功能。王学仲在《我与我的现代文人画》一文中说道:“我总感到我所探索的现代文人人物画,是一杯苦茶。我在创作中极追求超形意味,在亦庄亦谐的形式中托物兴怀。我不断地试图用我的画笔拓宽文人人物画之内涵性和蕴藉性。”他的新文人画作品将众人熟知的“常理”的表现,通过自身的理解和认识得到升华,将“哲理”表现得更加现实化与生活化。在《采菊东篱下》中,人物形象舍精求拙、舍繁求简,笔墨运用大块、自然,将佛家的“禅”、道家的“朴”、儒家的“诚”融于画中,画面传达出一种“超然”“淡薄”“无欲”的意境。王学仲的新文人画虽师法自然,却不是生硬的搬移自然,是用“内我而外物”的自然观去观察自然,是以他自身的精神情怀作为主体,借助自然之物,形成了其新文人画哲理高于形质的特殊的艺术特质。
王学仲在《论文人画》一文中提出新文人画的三大要素:“现代人类思想的高度、美化陶冶众生之心灵的使命感、以人民忧乐为忧乐的情感意识。”这是其新文人画注重现实生活表现、随时代、求风骨的最好诠释。在新文人画的历史进程中,王学仲立足传统,勇于创新,还民族魂魄,握时代脉搏,为新文人画的发展、开拓、创新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