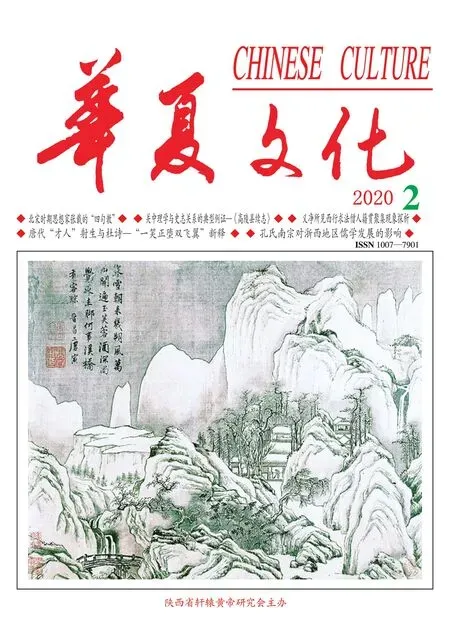读《武梁祠
——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
□缑宇平
巫鸿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是融合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一种尝试,是艺术史、历史、考古各学科相结合的一种尝试。这本书成为武梁祠研究领域中的重要专著,于1989年获得了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被列为20世纪90年代最有意义的艺术学著作之一。
《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是巫鸿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论文,也是他被引起广泛关注的第一部著作。虽然巫鸿在后来的著作《礼仪中的美术》中讲到,这本书的方法论及研究视野有不成熟之处,我们也看到在其之后的著作《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中的研究方法变得更为成熟,但这本书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的研究是对以往武梁祠研究四个主要方面的回应:一,对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进行清点和著录;二,对以往武梁祠研究做一系统回顾;三,在“图像志”(iconography)层次上重新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四,考察武梁祠整个图像程序而展开的思想观念。全书也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的。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及附录。这三个部分可以说是三个研究层次,即学术传统、主题研究、基础性研究。
上编检验武氏家族墓地的遗存和以往的研究,是建构汉代艺术史学史的一次尝试。从这里可以看出巫鸿本人对学术史和方法论的重视,巫鸿对史学史的研究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重视与他在哈佛大学接受的西方史学训练分不开。从他对武梁祠研究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对该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的把握来看,巫鸿作了扎实的学术史梳理。他对学术史的处理方式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在文中并未停留在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上,而是尝试在学术史中梳理出一种自在的历史,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甄别和学习。巫鸿对武梁祠的研究无疑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这使得整本书的研究有一个较高的起点。
上编为学术史研究,分为两章:第一章,收集有关资料,围绕几个世纪以来武梁祠材料的发现、断代、祠堂从属、建筑形式以及墓地整体的情况进行讨论;第二章,勾画出围绕武梁祠所展开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希望呈现出该研究领域里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趋势。附录二三是对上编的补充。附录二是武氏祠研究中重要事件的年表,附录三列出墓地中发现石刻的详细资料,包括尺寸、原始位置、目前所在,以及对它们的著录。
下编,探讨武梁祠画像的图像设计程序及其思想内涵。这是全书的中心,以附录一为基础。附录一是对武梁祠画像的主题和铭文逐一进行图像志的研究。下编则是把单个母题作为一个总体图像程序的组成部分加以解释,表述了东汉人心目中宇宙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天界、仙界和人间。下编三章的划分,正是根据这个图像程序的内在结构及祠堂建筑的形式来决定的,分别讨论刻于屋顶的图谶、左右山墙锐顶上的神仙世界以及三面墙壁上表现人类历史的图像,全书结论部分以反思祠堂的礼仪“原境”而结束。在这里,作者关注了武梁祠与整个汉代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围绕武梁祠的图像程序展开思想观念的探讨。
下编的论述尤为精妙。首先,屋顶图谶象征上天征兆,山墙顶部象征神仙世界,山墙部分代表人类世界,这三个部分相呼应,构成垂直的宇宙。而山墙画像的表述却为水平结构,故垂直结构的宇宙又与水平存在的人间构成互动。这一微妙的关系很有趣。其次,作者把对各部分的论述放到了儒家美术这一大的特征之下展开,儒家思想、儒学人生与祠堂发生微妙的联系。另外,全书还注重阐述武梁祠在礼仪中的多重功能,并关注到祠堂的设计者和当时的社会风尚等问题。
在“屋顶:上天征兆”中,巫鸿对武梁祠中出现的各种“祥瑞”和“灾异”图像进行考据。通过分析祥瑞形象及图录风格、征兆图像的流行、武梁和征兆图像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巫鸿在论述时采用了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文献考据。如他在对“祥瑞”和“灾异”两种图像的考据中认为,“祥瑞源自《瑞图》,而灾异图像则来自《山海经》”。另一种方法便是对同一时期的石刻图像进行比较研究。利用其他地方考古发现的石刻与武梁祠石刻进行比较,从而甄别和判断这些图像的来源和类别。在这两种方法中,文献考据为主,比较研究为辅。在确定了石刻图像的来源之后,巫鸿便开始对这些图像进行“图像学”的阐释,将图像放在汉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情景中进行深入分析并得出结论。在对这些图像进行图像学的阐释中,巫鸿不仅为读者理解武梁祠的征兆图像提供了大量的背景知识,而且还将这些图像产生的时代语境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在“山墙:神仙的世界”中,巫鸿集中讨论了西王母地位在汉代神仙体系中前后不同阶段的变化。巫鸿认为:“西王母、东王公及其仙境的形象是以‘偶像型’的构图设计的,而表现孝子列女、忠臣刺客的图画用的则是‘情节型’构图方式。”巫鸿认为,“区分这两种构图类型对研究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极为关键,因为它们隐含着不同的创作观念以及观看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在本章的论述中,巫鸿将图像学和其内在的文化发展脉络之间搭建起一个便捷的通道,让“图像学”的阐释更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墙壁:人类的历史”一章中,巫鸿将历史学的方法用于自己的研究中。在图像的解读上,他认为武梁祠墙壁上的画像石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阅读方式,从右向左、从上到下排列的。石刻上的三组图像也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的,第一组的古代帝王像从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和女娲开始,最后是夏朝末代君王桀。紧接着的七位列女都生活在周代。第三组以东周曾参的故事开始。在巫鸿看来,这种观看方式和图像的叙事方法、排列方式并不是巧合,而是构图者或者说武梁个人有意安排的结果。同样,巫鸿在对这些“三皇五帝”、“列女、孝子”等图像进行图像志的描述后,在本章的下半部分展开了图像学的阐释。他一开始就将图像的产生与汉代的史学观联系了起来,并对两种历史学家治史的方法进行了深入讨论,一种是编年的方法,强调历史学家那种客观的,以时间为线索的著史原则;一种是司马迁那种史观——即书写历史的基本功能和探索历史范式及提供道德训诫的著史原则。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巫鸿将武梁祠的图像叙事与司马迁的史观联系起来。他得出的结论是:“首先,武梁祠墙壁上的画像描绘了从人类产生一直到汉代的中国‘通史’。其次,就像《史记》一样,它通过精心挑选的个体人物来浓缩历史。再者,这些个体人物根据他们的政治关系、生平德行以及他们的志向而分为几个系列或类别。最后,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同时极为可能是这个祠堂的设计者,武梁的肖像出现在后部历史的结尾处。不论是在整个叙事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还是在暗示作者‘史家身份’的作用上,这个‘自画像’都和司马迁在《史记》的结尾章《太史公自叙》相对应。他将这种历史史观和中国汉代整个儒家学术传统与汉代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巫鸿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对附录部分的处理也很明智。一般的论文附录都会有索引、参考文献、年表之类,而这本书的附录还包含了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基础资料的梳理和阐述,即榜题、图像志、文本等部分。这些材料是书中深入研究不可或缺的支撑,若放到文中必会显得凌乱。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资料与理论、基础与阐释的关系问题。
巫鸿的这本著作不仅深化了对武梁祠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使我们从书中看到了巫鸿重构中国美术史的努力,他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