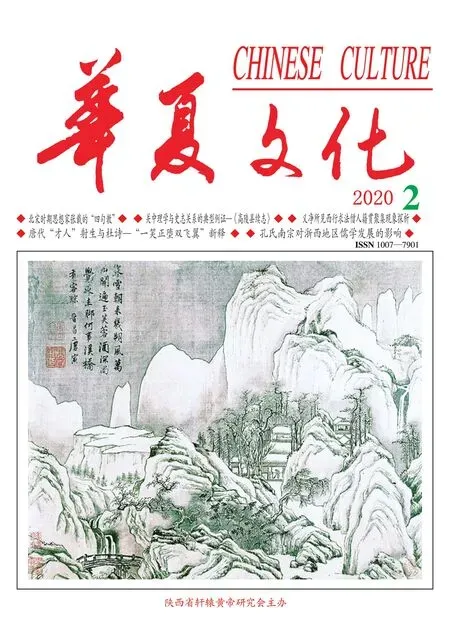李柏儒道并尊的意义与启示
□程灵生
关学不朽。传至清初,“关中三李”者出,于为有力矣。其中李柏著《吾老洞碑记》一文,启迪良多。首先,是儒道并尊的观点,他鲜明地提出:“孔子为天下万世师,以余观老子,则亦天下万世师也。”其次,是区分道家老子的学术与道教唯心论的不同本质,他指出:“道流徒以长生清虚学老子,见其一节,而遗其全体也。”许多读书人常以“严绝佛老”为学术原则,有意回避老子,造成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观念。李柏此文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李柏儒道并尊、孔老并圣的命题,并非妙手偶得,而是有感而发。他实际上想着手解决包括关学在内传统文化长期缺失的“有机的自然主义”即大道思维问题。(参见〔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上,作者的话:“对读者来说,首要之点是应该懂得,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很根深蒂固的有机的非机械的性质。这首先表现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道家、墨家和阴阳家身上。”)他所痛心的是两千年儒术独尊却忘了道家根本;唐以后,以儒典为考纲,这固然凝聚了民族人心,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但又在巩固官僚主义封建统治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阻塞了民族灵性,僵化了思维个性。李柏终生甘当农民,以实际行动拒绝 “章句名利之学”。人们看到明代以后,读书人除钦定《性理大全》,几乎一书不读(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楔子第三页)。这种空疏的学风,造成一大偏颇,两个盲区(详见后文)。直至清末,关学界依然确认“严绝二氏”为家法,排斥老子。即使目光锐敏,已经觉察到李柏价值的学者,如三原贺瑞麟等,也仍用“一时应酬之作,不足为先生累”来“谅解”他的崇老尊道思想。这当然不能怪李柏思虑不周、论证不密,只能怪传统思维习惯中缺失了大道即有机的自然主义观照。
这一偏颇与孔子不无关系。他确实轻视过社会主要生产力即农民的价值,而与老子无关。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道德经·二十三章》,此后凡引此书,只注章)没有说生产实践中农业之道就不是道。认识论上的两个盲区,一是不能看出广大劳动者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联系。即使如张载这样的教育家、哲学家,虽承认“存众人则知万物之神”,也没有将感性与理性(所谓德性之知)相联系。他们都不能说明理性认识是无数感性认识“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认识论上的第二个盲区是,不能看出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除创造物质财富而外,还创造了精神财富——审美价值。因为道家的第二位代表人物庄子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初步论证了它,认为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人类会体验“得道之乐”,即审美价值。而一般认为儒家读书人长期忽略了这一点,以为这只是在排斥道家庄子,其实他们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排斥了。作为儒典的《诗经》,就是孔子整理并作为教材的。“诗三百”的主要篇章,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歌唱,“两南”,《七月》、《生民》等名篇,就是他们的心声。孔子答子夏说:“关睢之事大矣哉!……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这里的王道之原,既含物质生产,又含人自身生产。这就是中国文化“人本论”而非“神本论”的证据。孔子首先肯定了文艺“兴观群怨”四大功能;再追一步就是老子。他在六十七章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慈者,人类之爱也;孔子把它谓为“王道之原”。孔孟接着老子讲:“仁者爱人。”“慈故勇”,说明慈爱是老子揭示历史上人性异化及哲学理论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的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或称核心,离不开老子这个学派的贡献;在最根本的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儒学和道家都是自觉不自觉,全部或部分地同道而行的。他们的主要论点,或内在联系,或外在呼应,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老子的“慈”和“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被孔孟之道发展成“仁政王道”;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章)被孔子领悟为“人道”非常道,“爱人”非常名,那么,人道即可道,“爱人”即可名。于是他便继承并发展了老子大道常道中的一脉——成为孔孟式的人道主义,作为他们游说诸侯的主要说辞。又如孔子“学而时习之”,是老子“为学日益”(四十八章)所派生。孔子在思维品质上讲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是遵从了老子二十四章所警示的:“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就连孔子常以水德来启发教育学生,也源自老子“上善若水”(八章)的启示。更不必说他游说诸候失败之后,回乡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之举,完全是在执行老子“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教导了。
以上所举,不过是我的管窥之见。然而至少可以说明,仅就流传文本考察分析,孔子在继承老子思想上,是恭敬勤劳的。他是老子最好的学生,这是历史的真实。张岂之主编、武占江著《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形成及特点》一书第201页说:“笔者认为《史记》对老子的记载是正确的,他为春秋末期人,《老子》的作者,长于孔子。”
从司马迁对孔、老见面的三次论述看,各有侧重。但他写《老子韩非列传》,必须对道家思想及其传承做仔细疏理,所以记录老子对孔子的教导之言,简约而深刻,透出这位由史而哲的老人善于相人的本领;微妙而幽默的风格,又表现了他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的导师心肠。真是道家之言。他说: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这是第一层。可见孔子东周问道,所及礼法,乃是政治历史问题。孔子盛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古圣人。老子没有当面夸这位学生“好古敏求”,大概怕年轻人飘飘然。但他心里明白,“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便预料到这位学生具有“执古之道,御今之有”的气派,有希望成为“从事于道”“勤而行之”的上士(二十三章)。但年轻人在实践中碰了钉子,又容易灰心;所以老子又讲了第二层:
“且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教他持道有恒,行己无愧,好自为之,不要虚度此生。第三层才向他勾画了理想的人格:
“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边打个比方,要他对自身长处守若珍宝,待价而沽,不可轻易许人。后边说要用大智若愚的行为展示自己的盛德与实力。大概老子又从孔子的谈吐中,看出了他的骄气淫志才这样说。但他明白,青年人的骄气淫志又何尝不是动力。为了在将来看到一位能超越自己的良史良哲,他最后的叮嘱至关重要:
“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大概老子从孔子的“骄气”看出了自信,从“多欲”看出了远迈的志向,所以这“态色”便是自信远迈的神态,而“淫志”则是放之四海的大志。为了鼓励他守护好这些品质,老子才警示说,不要因庸人的指责而丢掉了它们,而保持这些品质才是有益的。而庸人的指责,特别是来自统治者的无礼(无理)指责,是常有之事。例如老子本人就曾遇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四十一章)的情况。
但当时年轻气盛的孔子,要把这些曲曲折折的教诲一时融会贯通,谈何容易。所以他向学生介绍老子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其犹龙也”。龙在东周时代,乃是一个自由、有力、神圣、神密的称谓。可见孔子对老子奉为终生导师的动机,全在于此,即决心详尽地占有这些龙德。
老子见孔子有此良史良哲之才,所以才有意将大道——人道,托孔子以传。所以才说了那些话。《史记》载:“老子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他身后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自己的学说将分支分道地去传承发展,这也是他所不难预料的。他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六十三章)果然,“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极其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老子韩非列传》)我们也看到,农家顺天之时,相地之宜,执著于当时最主要的产业——为农之道。战争频仍,以其“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二十九章)。兵家不厌其诈,来源于老子“以奇治兵”的方略(五十七章)。阴阳家则应用着他的辩证之法。
李柏关于儒道看法的意义与启示,是在老、孔师生关系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得道之乐的历史演进中,看出了儒道并尊的内在逻辑。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特色是无神论(即“人本论”或“情本论”)。其文明结构是以孔子儒学为主干,以老子“从事于道”的实践理性为其认识论,以庄子生产劳动者的“得道之乐”为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