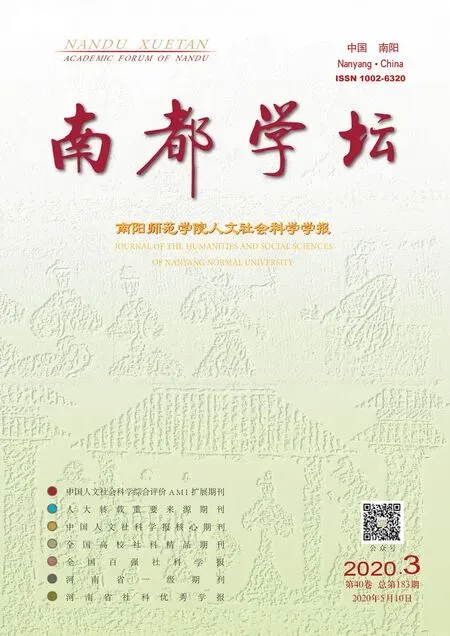论杜甫古体诗的内容新变
吴淑玲,韩成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参照学界唐代文学文体学的研究成果和前人的分类方法,如《昭明文选》的分类方法、《唐诗评论类编》的分类方法,我们确定的杜甫古体诗抛开了骚体诗、乐府诗、歌行体诗等拥有特别名称的诗歌外,统计得出杜甫共有277首古体诗歌,其中五言古体245首,七言古体32首。
《昭明文选》对所收古体诗的分类大致以献诗、咏史、招隐、咏怀、赠答、行旅等进行分类,这基本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体诗歌所反映的内容,作品中有对现实的反映,有表达自己人生志向的作品,但数量较少。作品中咏怀较多而真正触及社会政治本质的相对较少,真正以一种情怀关心国计民生的也少,给诗人所在时代的良将英贤作传记的作品则基本不见。杜甫的古体诗虽然主要用来记录个人的行踪、遭际和交游,是相对私人化的内容,但杜甫是一个胸怀人民、胸怀天下的士人,遭遇又非同寻常地富有时代性特征,故其相对私人化的内容仍然包含了丰富的社会信息。与魏晋南北朝、初唐、盛唐早期的古体诗相比,杜甫古体诗题材更加广阔,内容更加深刻:记时变、述志向、讽时政、哀民生、赞英良、呼唤普世爱心等多方面囊括其中,这是杜甫古体诗对前代古体诗内容的重要突破。
一、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杜甫除在以记时事为主的乐府诗中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事、用心规讽君王外,在私人化的记录个人行踪、遭际和交游的古体诗中,也是时时不忘家国天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诗人与京都诗人圈的一次交游,时与薛据、储光羲、岑参、高适等同游。储光羲的诗作,没有太多个人情感,只是记录登塔的时令、风光及想象中的风云变幻。岑参的诗作,只是登塔的景物描写,没有实质性内容。高适的诗作亦只是登塔的个人感受,只是在结尾部分表示欲效力国家。而杜甫的诗作,则把对国家命运的隐忧注入其间。在诗的开头部分,杜甫就已经说出了“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可见其忧国之心。后面作者又借助景物暗喻时局的混乱:“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进而又写道“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把对国家未来的担忧写在明面。钱谦益曰:“高标烈风,登兹百忧,岌岌乎有漂摇崩析之恐,正起兴也。‘泾渭不可求’,长安不可辨,所以回首而思叫虞舜。‘苍梧云正愁’,犹太白云‘长安不见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贵妃。瑶池日晏,言天下将乱,而宴乐不可以为常也。”[1]钱氏之说,虽太过指实,却也道出了杜甫诗歌高于其他诗人同题之作之处。
我们再来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京赴奉先县,是杜甫得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之后,去奉先县接取自己的家眷,但诗人在“咏怀”二字上做足了文章,将自己的人生理想、报国志愿,融合在这次出行的路途中,将路途所见与国家的治理紧密联系,将归家所见与千万百姓的命运联系,写出了一篇忧国忧民的大作。吴瞻泰曰:“长诗须有大主脑,无主脑则绪乱如麻。此诗身与国与家,为一篇之主脑。布衣终老,不能遂稷、契之志,其为身之主脑也;廊庙无任事之人,致使君臣荒宴,其为国之主脑也。前由身事入国事,转入家事。后即由家事勘进一层,缴到国事,绪分而联,体散而整,由其主脑之明故也。”[2]684《唐宋诗醇》曰:“甫以布衣之士,乃心帝室,而是时明皇失政,大乱已成。方且君臣荒宴,若罔闻知。甫从局外,蒿目时艰,欲言不可,盖有日矣,而一于此诗发之。前述平日之衷曲,后写当前之酸楚,至于中幅,以所经为纲,所见为目,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板》《荡》之后,未有能及此者,此甫之所以度越千古,而上继《三百篇》者乎?”[2]685-686
《北征》诗,写于杜甫疏救房琯遭到审查后“墨制”放还时,此诗以真实的笔墨记录了诗人离开朝廷时的恋阙情怀、路途所见的农村凋敝景象、家庭的艰难困苦之状,同时写出了诗人对国事的忧虑和建议,如对借兵回纥的担心、建议官军深入剿敌等,这说明,杜甫虽身处逆境仍然心忧天下、不忘国事,这是杜甫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唐汝询曰:“《北征》本为省家而作,其间踌躇恋君,訏谟君国,入目必载,关情必书,纪及除邪,转丑为美。虑深陵阙,终以太宗。立意高,包罗广。就诗而论,中兴之业在此老胸中矣!”[2]960
再如《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写诗人冒死逃离叛军盘踞的长安,到达肃宗朝廷所在地凤翔,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此诗最能表现杜甫的爱国热忱。黄生说:
按:当时陷贼者无数,而奔赴行在者,惟子美一人,其为此计,实出万死一生,得达行在者幸尔。由此观之,诸人之不敢轻窜者,非畏死乎?推子美拼死之心,设贼污以伪官,知必以死相拒,不若王、郑辈隐忍苟活也。然而伪命不及者,以布衣初膺末秩,名位甚微,故得免于物色。为公计者,潜身晦迹,以待王师之至,亦何不可?而必履危蹈险,以归命朝廷,岂非匡时报主之志,素存于中,不等诸人之碌碌,故虽履虎涉冰而不恤乎,不幸遭猜忌之主,立朝无几,辄蒙放弃,一腔热血,竟洒于屏匽之内,肃之少恩,岂顾问哉![3]
回归的喜悦生动地表达了诗人对朝廷的一片赤诚,不幸的是,杜甫任左拾遗不久,就因违逆肃宗而被三司推问,险些丧命,深刻印证了肃宗的刻薄寡恩。
《赠卫八处士》是杜甫因疏救房琯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回乡探亲路上所写。诗人见到了少年时的朋友卫八(名不详),艰难之际受到热情接待,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本文作者之一吴淑玲在《杜诗详注研究》中认为:“儿女情、夫妻情、兄弟情、朋友情,这些亲情皆因战乱毁灭,亦因战乱而显得弥足珍贵,家仇国恨互为生发,国恨使家仇愈显深重,家仇则将国恨具化为点点滴滴,深入内心深处。”[4]
《忆昔二首》是杜甫晚年的重要作品,带有总结性质,是诗人陈述自己所闻、所见、所感。《忆昔》其二是对大唐王朝开元以来历史发展的总结,仇兆鳌在段意分析中注意到了杜甫对国家命运的关注:“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自开元至此,洊经兵革,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孤臣洒泪,仍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耳。”[5]1163仇氏的分析,从杜甫写诗目的入手,将杜甫的今昔对比手法所达到的表意效果分析得非常透彻,并于全诗之末再次强化了这一观点:“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开元盛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致开元变为天宝,流祸两朝,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5]1165《九家集注杜诗》《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黄氏补注杜诗》均从《忆昔》所涉及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等史实入手,内容虽详尽,但都没有点出治乱兴亡之理,也没有揭示杜甫作诗用意。仇氏的解说是基于对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的政治理想和杜甫关心国家民族兴亡的崇高人格的认识上,故能得其深旨。
二、陈述平生之志
杜甫的古体诗更多关注个人,他的很多古体诗都不遗余力地陈述个人的人生理想,希望施展才华为国家尽力。杜甫在京城困居的十多年,其实也是多方奔走、希望施展才华为国家尽力的十多年。其间,他尽自己的能力结交可能推荐自己的人,写过不少干谒诗,他明知道“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但为君为国的心不变:“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杜甫为了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写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不仅陈述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治理国家的远大政治抱负“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且不惜掉价地讲述了自己在长安过的屈辱生活:“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但他写这些,绝不仅仅是为了博得对方的同情,更主要是对“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社会现实做出猛烈的抨击,希望对方了解自己这个“儒冠”的窘境,让对方尽快向朝廷举荐自己,以实现“致君尧舜”的愿望。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自己自认为“窃比稷与契”,把远古的能臣干将作为比喻自己的标杆,这种自负也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可见杜甫对自己的期许之高。在这首诗里,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他所关心的都是治世能臣才关心的问题。杜甫责无旁贷地思考着这些,他是真的把自己的治世理念和盘托出了。在《忆昔二首》中,他表示“愿见北地傅介子”,“周宣中兴望我皇”,希望这个国家能够重现“开元全盛日”,回归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开元盛世!这种理想和志向不仅在杜甫的古体诗歌里出现,也在他的一些其他体类的诗作中频频出现。
三、抨击时政弊端
虽然杜甫的古体诗主要用于记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像乐府诗那样直击国家重大事件,但杜甫心系家国天下的情怀时有表露,遇到能够对时政有所谏讽的时候,杜甫会毫不客气表达自己的想法。他的古体诗作里,对所历三代君王都有批判。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开首便愤怒揭露玄宗朝“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社会现实,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揭露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将社会的两极分化揭示得触目惊心,并且抨击统治者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安史之乱前还在大肆挥霍、尽情享受。杜甫指出肃宗的失政:一是重用宦官李辅国,二是宠信张良娣。他在《忆昔》其一中写道“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就是为此而发。杜甫批判代宗失政:重用宦官程元振,导致京都被吐蕃攻陷。他在《忆昔》其一中描写了代宗君臣狼狈逃窜的情景“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这就是失政的恶果。杜甫还在《释闷》诗中写道“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嬖孽,指受君主宠爱的小人,如庶妾、宦官之类,这里即指宦官程元振。安史之乱中,吐蕃趁乱攻占河陇地区,程元振竟然知情不报,以致吐蕃一度攻近长安。此人论罪当斩,代宗却宽恕了他。
《忆昔》作为杜甫晚年古体诗歌的代表作品,全面反映了杜甫对所历朝代由盛转衰的历史事实,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杜甫对唐肃宗和唐代宗的严厉批评,仇兆鳌对《忆昔》诗做出细致剖析:
《忆昔》其一第一段:“此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起灵武,复西京,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其才足以有为,乃任李辅国,宠张良娣,祸及父子,而身亦不免焉。故中兴之业,尚待继世也。后不乐,状其骄恣。上为忙,状其局蹐。此分明写出惧内意。”第二段:“此伤代宗不能振起也。帝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及程元振用事,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车驾蒙尘,一时御边无策,故慨然思傅介子焉。老儒句,自叹不能靖乱而尸位也。”[5]1161-1162
仇兆鳌在分析之后,还援引钱谦益语:“《忆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肃宗朝之祸乱,成于张后、辅国。代宗在东朝,已身履其难。少属乱离,长于军旅,即位以来,劳心焦思,祸犹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复信任程元振,解郭子仪兵柄,以召匈奴之祸,此不亦童昏之尤乎。公不敢斥言,而以‘忆昔’为词,其意婉而切矣。”[5]1163杜甫此诗虽然使用了委婉之语,但仍清楚地告诉读者,现实中存在着骄兵纵恶、宦官专权、后宫乱政等非常严重、难以回避的尖锐矛盾,尽管还属于旁敲侧击,但仍然达到了讽评现实的目的。
又如《往在》一诗,几乎是唐朝安史之乱及其之后的吐蕃侵入长安的回忆录。本文作者之一的韩成武在《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中对此诗有详细分析,引述于此:
《往在》一诗记录叛军攻陷长安后的暴行,十分详尽。杜甫曾被叛军拘禁在长安达数月之久,亲眼目睹了这些暴行,故写来颇为具体。“往在西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云汉为之红。解瓦飞十里,穗帷纷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风。”这是记叛军焚烧唐室宗庙的情景。时当半夜,叛军把九庙点着了,冲腾的火焰把天河映红,烧裂的瓦片崩出十里远,庙里的灵帐带着火苗纷纷飞向高空。先帝们的木制牌位,一一化作灰烬,被风吹散了。这种焚庙的具体场面,是史书中所没有的。诗中又记叛军杀戮嫔妃,捣毁御座,抢掠京都财物运往洛阳等事。安史之乱平息后仅9个月,长安又被吐蕃攻陷,刚刚复修的宗庙又遭践踏,杜甫在诗中记录此辱:“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神圣的祭器被吐蕃腥膻的臭气所污染,庙宇帷屏之间行走着身带角弓的蕃兵。京都两次遭到异族的蹂躏,杜甫深感痛心,他总结教训,把问题挖到君主老根上,认为:一、君主没有向国人作自我批评,所以民心不坚;二、君主不尚节俭,未能取得民众的拥护;三、君主不纳谏诤,刚愎自用。应该说这三条很中肯,击中了要害。唐王朝由盛而衰,原因虽多,但君主应负主要责任;君主的失误之处也很多,但主要就是这三条。杜甫确实具备政治家的才识。[6]240-241
四、哀痛民生疾苦
杜甫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在乐府诗中最集中,古体诗次之。杜甫古体诗写民生疾苦,往往通过亲身经历的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具有实证性。例如他行走在骊山脚下看到冻饿而死的尸骨,便将其写入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奔往羌村的路上,他看到被叛军残害的百姓,便将其写入诗中——“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在四川居住的日子,他看到百姓被旱情和赋税所苦,在烈日下恸哭,便将其写入诗中——“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喜雨》)。在南行的路途中,他看到百姓为赋税所苦,举家逃亡,以致田园荒废,便写下《宿花石戍》以记其事:“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残逆气,吴楚守王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此处罢同“疲”。罢人,即指疲惫的农民。仇兆鳌对《忆昔》其二作段意分析:“此痛乱离而思兴复也。自开元至此,洊经兵革,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乱后景象,真有不忍言者。孤臣洒泪,仍以中兴事业望诸代宗耳。”[5]1165仇氏的分析,从安史之乱给社会民生带来的灾难史实入手,分析精辟,深得杜诗之旨。
五、赞美良将英贤
杜甫的古体诗中还有不少赞美良将英贤的诗作,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品就是《八哀诗》。《八哀诗》涉及杜甫所认可的八位英贤俊才——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他们有的是济世良臣,有的是救世忠勇,有的是文学才俊。本文作者之一的韩成武在《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中有详细论述,引述于此:
为国家英烈立传的作品,集中在组诗《八哀诗》中。诗中哀悼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八人。[6]241
……
对于王思礼,杜甫着重表彰他当年在哥舒翰幕下从军时与吐蕃作战的英勇精神,“未甚拔行间,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敌。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马鞍悬将首,甲外控鸣镝。洗剑青海水,刻铭天山石”。这一段记叙战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时吐蕃已成为唐王朝的主要边患,朝廷所缺乏的正是王思礼这样的敢于与吐蕃对垒的将军。王思礼于上元二年(761)病死太原军中,国难未靖而英雄身亡,杜甫沉痛写道:“不得见清时,呜呼就窀穸。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并说,他的事迹千秋万代都将与汾晋之地的云水同在。(见《赠司空王公思礼》)
对于李光弼,重点记录他在安史之乱初期守卫太原的战功。守卫太原具有战略意义,这等于截断了叛军的右胁,而使肃宗设在灵武的临时政府有了安全保障,使百姓觉得大唐的帝业可期:“司徒天宝末,北收晋阳甲。胡骑攻吾城,愁寂意不惬。人安若泰山,蓟北断右胁。朔方气乃苏,黎首见帝业。”但是,广德二年(763)十月,吐蕃逼近京都时,代宗诏诸道入援,当时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弄权,正在陷害武臣,李光弼恐诏书有诈,未敢率部入京。其后,愧耻成疾,终于广德二年(764)七月死在徐州。对于这件难以辩白的冤情,杜甫亦能站在公正立场予以澄清:“青蝇纷营营,风雨秋一叶。内省未入朝,死泪终映睫。”忠臣形象得以鲜明,宦官丑态得以揭露。杜甫为他的不幸早逝大放悲声,认为是国家的大厦失去了栋梁,御敌的长城倒塌了箭垛。并坚信将来必有正直的史官秉笔直书,把他的冤屈和耻辱加以洗雪。(见《故司徒李公光弼》)杜甫的预言没有落空,两《唐书》本传和《资治通鉴》都披露了此事的真相,这或许与杜甫的申辩不无关系。杜甫抨击宦官当权,同样具有现实意义,肃宗、代宗两朝政局混乱,制敌不力,皆因宦官把持朝政,前有李辅国,后有程元振,这两人虽已身败名裂,而鱼朝恩仍在统领禁军,权力很重,这是杜甫深感忧虑的。
严武与杜甫为至交,二人曾同朝为官,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时,颇得严武的关照,但诗中无一字涉及私交,完全是站在国家利益的高点上评其一生功绩,而又以镇蜀为重点。“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是评其在抗击吐蕃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又赞美他注重推行教化,过问民生情况。“意待犬戎灭,人藏红粟盈。”说他一生志向是把吐蕃彻底消灭,并使百姓的仓库储满粮食。(见《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至于《新唐书·严武传》所称严武“峻掊亟敛,闾里为空”云云,诚难与杜甫对严武的评价相合,其不可信,犹如同文所说严武“欲杀甫数矣”之类,是荒诞无稽的。《新唐书》“列传”的编者宋祁,号称“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他的想象力是惊人的。
李琎是让皇帝李宪的儿子,性谨洁,有文才,与贺知章等为诗酒之友。杜甫初到长安时,与他有交游,曾作《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赞美他多才而忠厚,重友情而讲信用。杜甫在这首悼诗中,记录了李琎曾拦住君主的坐骑,上疏谏阻君主打猎,而且取得了成果。杜甫认为,身为王子而能倡导节俭,实属难得;而天下之所以混乱,与君臣不知节俭密切关联。(见《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这应该看作是杜甫把李琎作为哀悼对象的主要原因。
李邕与杜甫是旧交,作为诗坛前辈,他十分看重青年杜甫的文才,二人结下忘年之交。杜甫在悼诗中除了高度评价他的诗文和书法的造诣,尤赞其敢于直言廷诤,堂堂正气足以振拔颓俗,然而屡遭贬斥,终被李林甫陷害而死。尤其让杜甫悲愤的是,李邕冤死20年,朝廷竟不为其昭雪,“哀赠竟萧条”,不知到何时才能洗雪冤情,则此时朝廷无正直敢言之士可以想见。国无直士,而外患猖獗,国家的前途实堪忧虑!(见《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苏源明是杜甫的老友。杜甫早在年轻时漫游齐赵就与他结识,困居长安时经常得到他的济助。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托病不接受伪职,两京收复后提拔为考功郎中知制诰。杜甫在悼诗中对他的抗贼大节倍加称扬,说他像一棵碧色苍苍的参天松树,他的向阙之心像日月一样光明。对于他遭遇荒年饥疫而死的不幸结局,遥致沉痛的哀悼。(见《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
郑虔是杜甫困居长安时结识的穷朋友。据杜甫悼诗可知,郑虔为人孤高,天资聪颖,通晓天文、地理、兵法、医药、绘画、书法、诗艺,言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不饰华服,形同土木,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安史乱中,郑虔被叛军所俘,伪授水部郎中,称病不受,求摄市令(主管市场交易)。笔者猜度郑虔求此官职,目的是便于向肃宗的临时政府沟通消息,他也确曾把洛阳的敌情写成密件传给肃宗政府。但两京收复后,他仍被定为三等罪,贬为台州司户,死在那里。杜甫对他的生不逢时、蒙冤而死表示了莫大的同情。(见《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
张九龄,曾官至宰相,开元二十四年(736),被李林甫排挤,罢相,后为荆州长史,开元二十八年(740)病逝。从杜甫悼诗中所称“向时礼数隔,制作难上请”来看,他与张九龄并无诗文来往,算不上“叹旧”,是所谓“怀贤”。杜甫之所以怀悼这位贤臣,是由于张九龄是唐朝开国以来最后一位贤明宰相,“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说他冥思苦想,一心想实现致君尧舜的宏伟志向,无暇去追随箕颍隐士的足迹。“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故右仆射相国曲江张公九龄》)他唯恐比不上古代的圣哲,老死无功而有负于苍生。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意味着有唐以来开明政治的终结和一个黑暗时代的开始。杜甫悼念张九龄,是处身于黑暗的混乱的年代,痛惜和追怀那业已消失的盛唐时代的最后一抹余晖。
《八哀诗》确定了杜甫的立身高度,从选择人物到行文角度,无不显示着他是为国失英才而动情,显示着他的国家至上的观念。[6]241-244
杜甫还写过《别张十三建封》,诗中追忆张建封的外曾祖刘文静的开国功勋,以刘文静的业绩勉励张建封积极进取,希望他在国家大厦行将倾覆之际,应时而动、为国建功。这是诗人为国家呼唤贤才。而张建封果然没有辜负杜甫的希望,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为官有道、治理有方,还在反对藩镇叛乱中建立功勋,对唐朝的文化事业也有积极的推动(韩愈、孟郊、李翱等均在其幕府效力,为形成韩孟诗派奠定了人员基础)。杜甫还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中写苏涣的才气,并希望他和道州刺史裴虬都能够“早据要路”,为国尽忠:“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总而言之,只要有机会赞美或鼓励英贤俊才,杜甫总是不遗余力。
六、为自己人生立传
杜甫的古体诗,基本上都是与诗人的家庭生活、朋友交往等关系紧密的,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杜甫的古体诗具有私人化写作倾向,后人可以根据杜甫的诗作,大体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思想脉络、行踪去向、喜怒哀乐,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杜甫的几部有名的传记如陈贻焮、莫砺锋等所写的杜甫评传,莫不以杜诗为主要依据,而杜甫的古体诗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以看作是杜甫自幼年至困顿长安十年的生活写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勾勒出杜甫的人生理想、志向和他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之后的人生经历。《北征》记述了杜甫在房琯事件后被肃宗冷漠、“墨制”放还羌村的经历,他沿途见到战争惨象,到家后见到妻儿苦况,并对肃宗朝政提出弥足珍贵的建议。《羌村三首》写杜甫北征归家的见闻和感慨。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昔游》《遣怀》等,更是诗人对自我的长篇总结。关于后三篇,本文作者之一的韩成武在《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中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兹录于此:
《壮游》一诗从7岁写起:“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一直写到晚年寓居夔州:“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其中包括少年时的诗文活动、年轻时的三次长途漫游、旅居长安的困窘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任左拾遗因廷诤迕旨被黜以及流落巴蜀。值得重视的是,他在回顾个人行迹时,总是与国家的时局联系在一起。例如,他对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危机就看得很清楚:“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皆粟豆,官鸡输稻粱。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豪门贵族相互倾轧,失败者每每被灭族。玄宗的舞马耗尽了百姓的口粮,百姓们忍饥挨饿为宫廷的斗鸡交纳稻粱。杜甫说,仅举以上一二事例,就可以知道朝廷是何等的奢侈靡费,想到古代因奢亡国的旧事,不禁内心惶恐。接下来便是“河朔风尘起”,战乱果然爆发了。不斤斤于个人的遭际,注目于国家的兴亡教训,是杜甫自传诗的超凡之处和价值所在。《壮游》是如此,《昔游》和《遣怀》同样表现了这一特点。
《昔游》诗记录早年与高适、李白游历梁宋之事。但记叙行迹仅用八句,绝大部分篇幅是写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玄宗大事开边战争,宠任安禄山讨伐契丹,终成养虎之患。“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玄宗自傲于天下承平,遂鼓动将帅进行开边,从吴越一带远送粟帛到幽燕,充实军力,安禄山由此变得强悍,萌生了反叛的野心。杜甫说,那时我隔着黄河远眺河北安禄山的辖区,感到情况严重,年轻的心就已充满了忧愁。杜甫是敏感的,他对安史之乱的原因看得很透。
《遣怀》一诗回忆年轻时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在记录“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的同时,再次把目光引向国家的时局:“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当时海内尚未凋枯,玄宗正在崇尚武力扩大领土,猛将哥舒翰等举兵征讨吐蕃,安禄山等率军攻伐契丹。以百万之众攻敌一城一镇,诸将只献捷报不传败绩。军队的装备丢弃如泥,无所顾惜;为了尺寸之土,而牺牲上百人的性命。如此不惜物力和人力的开边战争连绵不断,结果是国家耗尽了力量,太平和乐之气完全丧失,战魔安禄山乘机而起。[6]244-246
《壮游》《昔游》和《遣怀》三首诗,都是勾勒诗人以往的生活,是诗人在晚年为自己的人生所作的总结式描述。虽然很私人化,但杜甫所经历的时代实在太特殊了,他的经历与时代紧密相连,而他的思想又时时不离家国天下,所以这也是几篇自传性作品涉及国家动乱的原因。诗人在对国家命运进行深刻思索后得到的结论是:国家的动乱之源就在于君主执政失误。这体现了杜诗批判现实的深度,这种深度不是一般诗人所能达到的,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也是罕见的。
七、记录亲朋交往
杜甫的古体诗里,有很多与亲戚、朋友交往的诗歌,如《寄薛三郎中》写自己和薛据“子尚客荆州,我亦滞江滨”俱流落江湘的困境;《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记述和王砯的关系及安史乱中逃难时王砯对诗人的救助:“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除了写友人“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的紧密关系,还殷殷嘱托对方要把民生疾苦记在心上,不忘为黎民百姓做事,并保持国士本色:“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请哀疮痍深,告诉皇华使。使臣精所择,进德知历试。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烈士恶苟得,俊杰思自致。”这类诗歌,为我们梳理诗人行踪、交游方面提供了重要信息。
还有一些古体诗歌作品里,诗人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的小人物写入诗中,令人耳目一新,如《园人送瓜》《信行远修水筒》《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催宗文树鸡栅》《园官送菜》《上后园山脚》《驱竖子摘苍耳》《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等,将普通人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写入诗中,让这些园人、仆人、行官、女奴、竖子甚至杜甫并不聪明的儿子宗文都出现在诗中,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八、描绘山川景物
杜甫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写过很多有关山川风物的诗歌,各种风格都有。其古体诗中的山川景物,与其他诗歌体式中的山川景物有所不同。这里主要是指杜甫在走向成都的路途中所写下的那些行旅诗。杜甫到达秦州,并没有找到理想的居所,从此开始了奔向西南的旅程。他先是由秦州到同谷,一路上所经过的山水,都成为他写作的素材,而这些山水文字,与王维、孟浩然笔下的山水迥然不同。如《铁堂峡》:
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
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
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
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5]677
峡谷空寂、峡壁似铁、巨刃摩天、地石俱裂、竹林如海、山巅积雪。奇异瘆人的物象中,显然渗入了作者的乱世惊魂。又如《青阳峡》: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
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
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
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
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
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5]683
南行的路途是这样艰险,冈峦交错、云水相杂,山岩挺出怪异的棱角,石壁如同斧劈刀削,山上的崩石砸向行人,恐怖的寒风和滑溜的霜雪令人寸步难行。又如《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
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
不畏道途永,乃将汩没同。
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
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
寄语北来人,后来莫匆匆。[5]690
这泥功山真是名副其实,漫山遍岭布满泥泞,竟然让白马变成黑色、小儿变成老翁,猿猴和麋鹿都被泥泞缠得力气用尽,或摔或死,环境之恶劣、路途之艰难,可以想见。
杜甫抵达同谷以后,邀请杜甫前来的同谷县令并没有给杜甫应有的帮助,致使杜甫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同谷七歌》成为杜甫悲惨人生的写照。故此,他只在同谷逗留了一个月左右便离开了,开始了携儿带女奔赴成都的艰难旅程。从同谷到成都,沿途山水险恶,杜甫又写了12首记行诗反映旅途的艰辛,如《木皮岭》所写群峰奔涌、岩石崩裂、云雾缭绕、虎豹出没、深渊万丈、栈道崩危,直令诗人感到“艰险不易论”;《水会渡》写夜黑浪高、悬崖外倾、霜重石滑、手寒脚冷;《飞仙阁》写栈道横绝、浊浪奔涛、日寒气惨、长风怒号;《龙门阁》写“绝壁无尺土”“长风驾高浪”“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剑门》写“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入蜀之路,真是像李白所说的,是“畏途巉岩不可攀”。
可以说,杜甫笔下的山川景物,有了与以往山水诗迥然不同的景象。如果说,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自然纯朴是其用以映衬社会的黑暗,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其治疗心灵创伤的灵丹妙药,孟浩然、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是用静美构建他们心中的乐园,杜甫的山水诗尤其是由秦入蜀的山水诗则是杜甫所处动乱时代的影像,是杜甫乱离生活的心中投影。杜甫改变了中国山水诗的写作倾向,对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写作倾向有重要影响。
除以上诸方面,杜甫的古体诗还涉及家庭琐事、风雨阴晴、民间风俗等,数量不多,且少经典,对解说杜甫的人生轨迹和杜诗的艺术风貌都没有特别紧要的关系,不再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