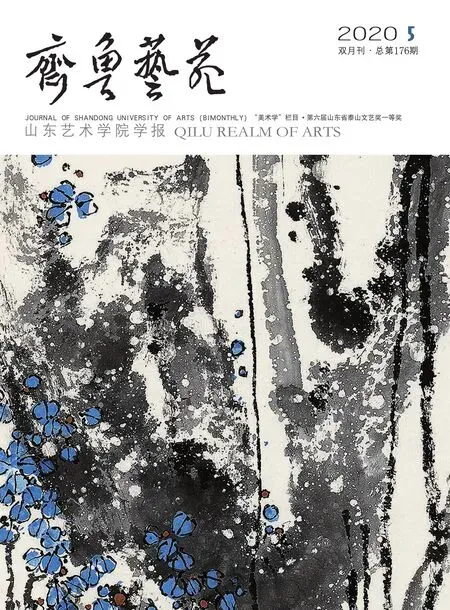《流浪地球》:硬科幻电影的中国道路
高 原,薛精华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由郭帆执导的电影《流浪地球》于2019年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上映。影片上映初期排片不佳,但凭借良好口碑,在上映第三天,便成功登顶单日票房冠军,最终取得了46亿元人民币的优秀成绩。《流浪地球》以好莱坞式的剧作结构,塑造出以中国军人为代表的群体英雄形象,在科幻片的类型下,实现了中国故事的世界表达。影片在剧作、美学、想象力呈现、工业化尝试等方面,都为中国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一、人物分析:群像式的英雄形象
在漫威和DC的连续轰炸下,似乎超级英雄电影已经成为了科幻片中的主流。当世界面临危难的时候,超级英雄作为一种异于大众的存在,以被默许的“暴力、个人主义”等手段解决危机,并与社会和谐共存。[1](P74-78)这些超级英雄的形象如此之典型,以至于我们在其它科幻电影中依旧能够看到这些代表大众、崇尚个人主义及自由精神的“英雄”形象,比如《明日边缘》中的凯吉、《阿凡达》中的杰克等,他们在关键时刻依靠个人行动逆转了局势造就了历史。
然而在《流浪地球》中,这些好莱坞式的超级英雄却被瓦解了。比起好莱坞的经典团队设计,《流浪地球》的救援小队存在一个显著的特点:频繁变动的人员组成。队员牺牲之后又不断有新的人物加进来,救援队的领导力量也几次变动:救援队队长王磊在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后期点燃木星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李一一,在影片的第60分钟才出现。在最后的点燃木星行动中,救援队的人呈现一种分工合作的状态,这与好莱坞影片中队友辅助,主角完成主线任务的设定不同,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不同于好莱坞的“个人英雄主义”,《流浪地球》救援队员身上体现的,是“前赴后继”的群体英雄主义精神。郭帆导演在采访中提到,150万人参与救援的设定,来自于汶川地震的照片。“既然我们没有超级英雄,也不要去建立超级英雄……我始终觉得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达到可以拍超级英雄电影的程度,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类型的文化土壤”[2](P27-32)。
相比地面救援队的英雄群像设定,空间站中刘培强的形象有着一定的个人英雄色彩。他克服重重阻碍,违背联合政府“火种计划”的成规,以一人的牺牲成功点燃木星,拯救了地球上的35亿人。但是刘培强的个人英雄与好莱坞中的孤胆英雄也存在着不同。刘培强在最终撞击之前,并没有对救援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他的英雄成就是建立在地面救援队众人的牺牲和努力之下的,而好莱坞电影中成就的英雄需要经历一路的调查、努力和战斗,虽然有导师、伙伴等人的帮助,但英雄本人是战胜对手的关键力量。对比之下,刘培强在主线任务的完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足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好莱坞个人英雄功能进行设置。
刘培强及其一众战友承载了中国军人的群体形象。他们富有牺牲精神,会为了保护火石将自己防护服的电源耗尽,会为了试图拯救同行的平民而牺牲自己,会为了地球的命运开着空间站撞向火焰。这些在机械外骨骼下坚毅又不失温情的中国军人,是以往好莱坞科幻电影中不曾出现过的形象,为《流浪地球》在西方科幻电影模式思维的限制下,寻找到了“新主流大片”的生存空间。但是这种群像式的展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观众无法分清人物。《流浪地球》试图采用《红海行动》的多专精、多分工、有机整合的特战小队,来进行群像英雄的塑造。但是碍于影片长度,救援队成员的表现远不如主要角色丰富。锤子、刚子、溜子、黄明等次要陪衬角色性格特点不突出,外貌展示也不够,缺乏辨识度,这就导致他们的牺牲很难引起观众共情,也显得毫无意义。“前赴后继”的人民英雄策略,也有无法推进剧情,而随时增加人物的嫌疑,这与影片突出人和人物关系、展现人类情感的整体策略是相违背的。
群像式的英雄策略不失为探索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尝试,但是在突出集体主义的同时,如何保证个体人物的质量,是一个仍需探索的领域。
二、美学分析:硬科幻电影的想象力美学呈现
(一)“硬科幻电影”意识下的类型融合创作
科幻电影以已有的科学元素为背景,在此基础上进行演绎,有时也表现出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作为一种类型电影,它的程式化规律并不体现为具体的题材、时间、地点、叙事规律、表现手法等。科幻电影诉求于一种对于未来科技的体现,并在此次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这使得科幻电影的类型程式更多地体现在故事背景中,而对具体的人物、场景、时间、叙事、基本主题、艺术风格等无强制要求。这种与其它类型电影迥然不同的特征,赋予了科幻片极强的可塑性,让它可以自由地与其它类型片进行混合杂糅,从而延伸出不同的子类型电影,如科幻惊悚片、科幻恐怖片、科幻冒险片、科幻爱情片等。所以,在考察科幻电影时,多类型杂糅是不可忽视的。
在《流浪地球》中,当我们剥离了影片的科学幻想背景,去掉太阳即将熄灭、流浪地球计划、行星发动机、木星的洛希极限、MOSS AI等科幻元素后,所保留下的是一个在灾难前如何拯救全人类的生存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灾难片结构。整部电影依靠这不同层级的灾难表现,一步步地逼迫主角走上求生之路,并最终完成了人类的自我救赎。从这个角度来看,《流浪地球》正是延续了西方《2012》《后天》等科幻灾难片的传统。正如导演郭帆所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把迈克尔·贝1998年拍摄的《世界末日》作为蓝本参考,只不过他们的问题是集中在一个点(陨石)上,而《流浪地球》的问题是全球的”[3](P27-32)。
尽管面临的灾难是全球性的,但《流浪地球》中重点表现的主体却是中国。主角刘启和他所遇到的救援队都是中国人,甚至外国长相的狱友Tim都要用京片子说一句“正儿八百儿的中国心”。前期救援队所奔赴的主要目标是杭州,引导主角从北京一路来到上海,展现了近未来末世中国的地理奇观。最后,影片又通过中国式的过饱和救援以及刘培强颇具献身精神的自我牺牲换来了地球的新生。《流浪地球》虽然在类型创作上大量借鉴了好莱坞同类型影片,但是最终所表现的是中国主流价值观,是典型的“新主流”大片。
这种崭新的国家想象,与之前所面临的灾难片中的危机,一同被统括在科幻电影类型下,完成了奇观展现与价值观表达。而这一切可以实现的基础,是《流浪地球》对于国产硬科幻电影的类型突破。科幻电影的类型程式要求从现有科学出发进行幻想式描述,而对于未来科学技术的想象精细程度,则构成了科幻电影内部的两种分支——科学性较强、注重于细节及合理性的硬科幻和幻想性较弱、相对灵活的软科幻。
对于科幻电影制作经验较为匮乏的我国电影业来说,软科幻不苛求于科技表现,剧本与制作难度较低,是较为容易实现的科幻电影类型。此前中国的科幻片也大多属于此类,如《长江七号》《催眠大师》等。但同时,由于世界观设定较为松散,软科幻无法承担起宏大叙事的任务,大多表现为以科幻元素推动的科幻喜剧片或是将视角集中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来探讨人物内心。对于软科幻电影来说,去表现一个全球性的灾难或是表现宏大的国族想象,都是超越其世界观设定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正是硬科幻电影所擅长的领域。
由于具有完善的科学设定和世界观背书,硬科幻电影可以将世界范围内的变动,以一条清晰的科学脉络进行叙述表达。比如在《流浪地球》中,由于太阳衰老膨胀导致人类必须将地球推离太阳系,这就需要通过木星的引力弹弓进行加速,而在经过木星时受其引力影响导致发动机失火,进而产生地球推力下降的情形,而使其面临坠落木星的危险,这一系列危机的发生,具有明确的因果链条。详尽的科学设定为影片的故事发展、人物活动、美术表现等,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艺术指导意见,这些又共同支撑起了影片的宏大叙事,在一个未来灾难故事中,实现了中国价值表达。
从类型角度来说,电影《流浪地球》的最大意义,正是实现了中国硬科幻由0到1的突破,为中国科幻电影打开了长期以来被封闭的另一扇窗户,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丰富了中国类型片创作维度,预示着未来中国市场也可接受科幻冒险片、科幻动作片等更多细分类型的某种可能。但同时,我们仍需要正视中国科幻电影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现实,而如果盲目追求类型杂糅、类型细分,去放开创作限制,必然会导致一时间良莠不齐的科幻电影作品泥沙俱下,从而对市场造成深度损害。
(二)想象力美学的呈现
作为广义“幻想电影”[4](P1-7,110)的一员,科幻电影诉诸于“想象力消费”。“电影对想象力的弘扬和创造,不仅为人们开拓了想象世界的无限空间,也是对人的某种精神需求——一种‘想象力消费’和‘虚拟性消费’的心理需求的满足……科幻、玄幻、魔幻电影大片等幻想类电影正是因为符合青年受众群体的趣味而需求极大”[5](P126-132)。这些奇观的本质是对幻想事物的表现,是一种假定性美学,是不同于常识的表现。
在影片《流浪地球》中,随着旁白介绍太阳衰竭,“流浪地球”计划逐步展开的情节背景叙述,观众一步步地从现实世界进入到了影片所营造的未来时空中。《流浪地球》既展现了天体级别的危机与应对措施,又充满着对地下城、宇宙航行机械、未来载具、辅助外骨骼等社会环境、生活道具的想象表现。在大的幻想下辅以小幻想,《流浪地球》就这样构筑起了不同层级结构的奇观想象,从天体级别的尺度到普通人的日常吃穿,这部作品构筑的虚拟世界,做到了同时满足多种想象需求,符合当下“想象力消费”的大趋势。
另一方面,科幻电影中的想象力表现也不是天马行空的幻想。电影中的奇观越符合科学原理及其合理假说与推论,就越接近现实世界可能发生的情况,其表现就越真实,观众就越容易接受。反之,如果电影在真实性上有所欠缺,观众就会对影片所展现的奇观产生怀疑,从而拒绝接受作品。不具有真实性的科学幻想只能是空想,这种真实性的欠缺,正是以往国产科幻电影的普遍缺陷,而这一问题在《流浪地球》中正在被一步步改进。在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三个层面的真实性。
首先是逻辑真实。作为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对于科学理论的细节和准确有很高的要求。在谈到理论设定时,郭帆说到,“2007年,我就开始着手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的基础上,做宇宙原则、维度等世界观的撰写……确定要拍摄这部电影之后,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全方位做了一百多年的编年史,非常复杂和庞大,为的就是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和精神做这部电影……我们邀请了四位中科院专家,共同研讨设计,解决包括天体物理和力学上的知识”[6]。这种由专业科学家介入的科学设定,保证了影片逻辑上的严谨性,也为影片故事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科幻电影需要有表现真实。即呈现于银幕上的画面要具有现实世界的质感。这主要针对的是科幻电影中的奇观表现。当观众在欣赏电影时,他对影像的真实性假设是与摄像机直接拍摄到的对象相一致的。所以一切出现在镜头中的幻想物品都需要具有和现实事物相同的真实质感。表现真实对摄影、灯光等部门提出了要求,更是对传统服化道及物理特效、数字特效部门的挑战。对此,《流浪地球》选择了一条稳妥的道路——避开了较为复杂的生物动画,选择了更为容易实现的落石、崩塌等灾难动画。同时,影片更为注重对于物理特效的制作与使用,电影中的物理特效与人物、环境融为一体,带来了真实的观感。可见,《流浪地球》在特效表现上,并没有一味地追求高难度、大场面,而是优先保证画面的真实感,最终实现了表现真实。
最后,影片需要有接受真实。中国观众是缺乏科幻电影经验的,中国文化对于科幻电影也是陌生的。长期以来,中国观众的科幻片经验都来自于好莱坞,而这种由西方文化主导的科学幻想一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就会构成一种错位感。“如果美式钢铁侠摘掉面具后,出现一个中国式的面孔,人们会出现强烈的违和感”[7](P90-96)。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科幻电影不只是需要将假定性的奇观,以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进行表现,而是要以中国观众可以接受的真实性加以塑造。
导演郭帆在《流浪地球》中最主要的美学拓展,便是探寻了中国人的科幻审美标准。这首先要找到中国本身的科技记忆,再在其中寻找到与西方不同的本土化风格。最终,在新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道路中,郭帆选择了苏联工业风作为影片的美学指导风格。“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依据苏联的重工业的那些视觉、听觉,因为中国人对那个是有一定情感的”[8](P90-96)。
在这种美学风格的指导下,影片一转好莱坞科幻片富有未来感和科技感的美术风格,而呈现出一种粗糙、厚重、带有一些年代感的未来重工业画面质感:设计风格更为硬朗,动力结构外露,操作界面为机械按钮和工业化UI。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认同,影片又在视觉表现上融合了大量的中国特征。以电影中的冰封大陆为例,为了保证特效镜头所呈现的视觉感受是中国化的,特效团队就从中国城市建筑、中国自然和地域视觉风格,以及中国绘画的视点这三个方面入手去构建影片场景[9](P139-144),从而保证从客观风景到主观视点的选择,都是具有中国质感符合中国人接受习惯的。
在这三层真实性的保障下,《流浪地球》以硬科幻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奇观表现,完成了中国科幻片的美学突破。如果说想象力是科幻电影的上限,那么保障影片顺利制作的电影工业水平就是科幻电影的下限。如今,科幻电影已经于中国起步,只有保障了电影工业可以为电影艺术创作进行合理支撑之时,科幻电影创作者的想象力才能真正得以解放,才可以去探索中国科幻电影未来的方向。
三、文化分析:中国文化的未来表达
我们说《流浪地球》是一部属于中国人的科幻电影,不仅仅是因为其原著、资金、主创、主演及制作团队来自中国,更因为它在科学幻想的奇观中表达了中国文化价值观,展现了一种不同于好莱坞的中国化未来景象。郭帆认为,“对于中国科幻电影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观念和精神指向层面,如何定义中国科幻片的问题……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包含中国文化内核的科幻片才能被称为中国科幻片”[10](P90-96)。
寻找能够代表中国并与观众产生共鸣的文化内核一度是制作团队在前期的主要工作。而对此方向的确认,则来自于和美国特效团队的交流之中。“去‘工业光魔’的时候……他们认为‘带着地球去流浪’这件事情很奇特,有些不合逻辑”[11](P27-32)。此时导演意识到,由于中美文化的差异,美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对于房子、土地的情感,他们同样无法理解同时出动150万人的救援队。而这些“美国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恰好就是中国文化最具独特性的部分,而这份独特性就是《流浪地球》所表现的文化内核”[12](P90-96)。
“为什么连逃离都要带着地球?”这是2016年交流时美国同行向郭帆提出的疑问。“我当时凭借朴素的第一反映就是,买房子贵,我们还得还房贷……但是细想一下,这恰好就是中国人对房子、对土地的情感”[13](P90-96)。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陆型国家,中华文明的基础长期以来是农业文明。对于土地的依赖形成了人对于土地的感情,从而构成了“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乡土记忆。这种安土重迁的观念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宗族认同。这种价值观与西方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放弃地球、移居外星的殖民式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作为一部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以科学的方式,幻想了未来中国文化如何提供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方案。然而,一部优秀的科幻电影,不仅需要科学的幻想,更需要去幻想科学,去思考科学的未来和它的本质。科技的过度发展所带来的是人文领域的不足,如果人的心智跟不上力量的发展,那么科学所带来的就不是希望而是毁灭。基于此,西方形成了对于科技的反思传统,即对科技发展报以批判性态度。如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就以怪物的形象,实质性地展现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恐惧。这最终形成了科幻题材中长期以来的理性与感性的冲突——科学的理性和人类情感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在中国,这种由于科技发展导致的信仰体系崩溃并没有出现,反而是由于科技落后而被列强轰开国门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具有一种普遍的科技乐观主义。在这种乐观主义下,科技的发展应当带来的是人文的解放,理性是保证感性的基础而不是对抗的力量。《流浪地球》中的人工智能MOSS更应当像手机里的小E、小爱等语音助手一样,在关键时刻提供帮助,而不是阻碍主角。在MOSS与刘培强的对立中,可以看到HAL 9000与鲍曼的影子,但是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理性与感性的冲突这种西方化的科学反思,是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科幻创作的。
如同中国科幻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表现、文化表达一样,中国科幻电影对于科学的思考,也应当从本土出发,去提供独特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的指导下,当代中国是积极拥抱科学技术的,但同时也要求这种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相信,中国独有的科技思考将打开西方理性与感性斗争的死结。《流浪地球》为中国科幻电影打开了大门,而它将和它的继任者一起共同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想象,为世界带来另一种不同的科技反思。
四、产业和市场运作:“重工业美学的实证”
电影工业美学认为,从生产者层面来看,“电影生产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不是个人凭天才完成的……电影生产不仅止于导演、编剧,任何个人、环节都是电影生产系统或产业链条上的有机一环,必须互相制约、配合、协同才能保证系统运作的最优化,系统功能发挥的最大化”[14](P32-43)。
“有潜力的导演、商业演员、优质国企与民企资本”的多方协作,是《流浪地球》生产与制作过程中的一大亮点。[15](P127-128)2012年,中影购买了三部刘慈欣小说的版权,《流浪地球》就是其中一个。2015年,确定郭帆担任影片导演。[16]重工业科幻片的预算非常大,在郭帆的牵线下,2017年北京文化加入项目,对影片出品承制并主控宣发。喇培康在采访中表示,中影致力于推动国产科幻片诞生,一部分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市场责任。电影开拍前,喇培康组织团队带领导演郭帆前往美国、新西兰寻找特效公司、开研讨会,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影片铺路。[17]项目拍摄的4年里,中影方面经常去探班,仅喇培康本人就至少去过两次剧组,及时沟通,排解问题。[18]爆款频出的北京文化主控营销,组织了传统媒体执行团队、新媒体执行团队、口碑执行团队三个外部营销执行团队,[19]从出品、营销、发行等多个方面为《流浪地球》保驾护航。《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表示,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剧组、中影、北京文化三方“相互制衡,各有优势……但是各自发挥了优势”。
对于《流浪地球》的电影工业化尝试,喇培康曾说道,《流浪地球》冲刺的不是中国科幻电影的终点线,而是起跑线。《流浪地球》的制作团队多达7000余人,如此复杂的人员构成,各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意见处理,不同部门的素材兼容,管理组的管理压力都成倍增长。作为重视效电影,《流浪地球》后期的视效工作量巨大,剧组将视效分配给多家公司,平衡风险,也能在进度上掌握主动权,但是多家公司带来的沟通成本和素材统一问题,又成为横亘在视效组面前的难题。对此,后期制作总监孙敏组建了专门的视效管理部门,在命名方式、存储格式等方面统一处理、及时跟进,细化填写体现全片镜头管理表格工作,根据各个公司的进度调整方案,用好莱坞通用的Shotgun软件打包阶段性完成的镜头,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沟通体制,在分工极细的情况下,将多方的制作标准化。
“电影生产中必须弱化感性、私人、自我的体验,代之以理性、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方式”[20](P32-43)。相比一些注重现场灵感的剧组,《流浪地球》的创作都集中在前端,现场只执行,不创作,这就避免了创意变更带来的意见不统一、效率低下问题。影片的重场戏使用PreViz动态分镜预演,将演员走位、拍摄角度、摄影机运动等因素提前规划好。过场戏、文戏等重量程度稍弱的戏份,用动态故事板剪出来,影片开机之前已经剪满了160分钟的故事板,为现场拍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如此,现场要做的只剩下流程化的执行。[21](P48)
导演郭帆曾在访谈中提到:“工业化是我们画画的纸和笔,是让电影完成真正视觉化呈现的重要工具……只有中国电影真正建立起工业化的体系,中国科幻电影所构建的世界观才能实现影像化的视觉呈现……摸索工业化的体系标准和运作流程,目的是为了找到创作的那支笔……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22](P90-96)。在成功产业经验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流浪地球》开创了众多的“第一次”, 探索出了一套标准化生产流程,使剧本研发、现场拍摄、后期制作等各个环节都能够按计划进行、责任到人,有效规避了个体差异导致的沟通成本,这些工业流程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中国电影工业发展所缺少的内容。而中国电影工业也将伴随着一部部《流浪地球》这样的“重工业”电影作品创作,继续发展完善。
结语
《流浪地球》的出现,终结了中国硬科幻电影的空白,打开了科幻电影创作的新篇章,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但我们不能仅因为它的出现,就乐观地认为“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已经到来。在形成规模效应前,观众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的概念将仍旧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甚至部分电影创作者也拿捏不到科幻电影创作的脉门,西方中心主义、反智主义在国产科幻作品中不时出现,消解了刚建立起的中国科幻概念。现在需要的,是在《流浪地球》之后的第二部、第三部科幻电影作品,是成系列的科幻电影集成,是充分体现电影工业美学原则,在高视觉完成度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中国科幻美学风格、中国科学观念的科幻电影创作。只有这样,中国化的未来想象才能真正照入观众心中,中国科幻电影才可以真正迎来它的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