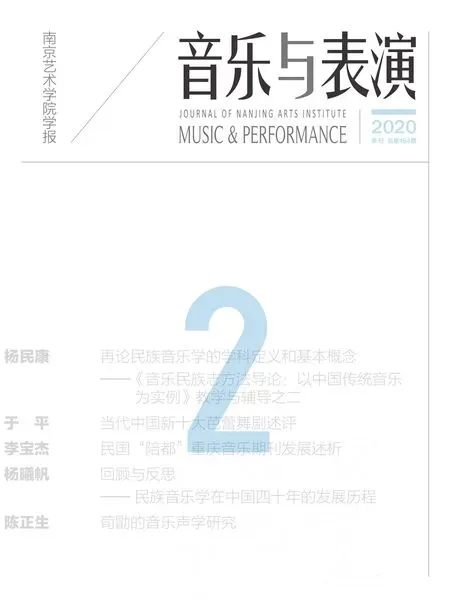被认定的“标准”:新中国民族乐器标准化的实践与内涵①
高 舒(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编辑部,北京 100029)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民族乐器工业注入了“现代化”的科技元素,在制作、规范等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民族乐器的应用和推广开辟了不同以往的新路。二十五品的琵琶、二十三弦的筝、不再匀孔的定调插口笛、六角筒的二胡……这些在今天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标准照”出现的乐器,隐去了它们在20 世纪前的旧貌,构建了中国民族乐器独立个体的标准印象。2019 年12 月7 日至8 日,在2019 全国乐器学研讨会上②本届会议由云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主题围绕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乐器的历史、音乐形态、制作工艺、音响特性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展开。,笔者以《领奏:国家标准的“入场”和中国少数民族乐器改革》谈到了我国民族乐器在制作、演奏和研究等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标准化”问题,引起了吴学源、韩宝强、付晓东等与会学者的共议,闭幕式上,将“标准”的讨论列为明年乐器学研讨会的议题。学者们对乐器“标准”的关注和思考,开启了对21 世纪中国民族乐器发展现状的新一轮审视。
“标准”二字如约定俗成的本意,一直在乐器领域出现,轻工业系统从乐器生产角度,一般将“标准化”视为“工业化”。考虑到“标准”难以完全绝对,进一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前者包容性强,涉及文化背景与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与个体经验和审美喜好层面有关,允许千人千面,各表一枝,如演奏领域;后者则指在特定领域内专门制定的、并社会化流通的规范性准则,例如我国乐器行业必须执行的国家标准(GB 或GB/T)和轻工行业标准(QB 或QB/T),如违反,即不合格,定位次品,不能投放市场。我国的乐器制作行业实际就是这种客观标准的长期实践者,由于生产出的标准器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乐器的性能边界,所以会对乐器制作的目标——演奏,产生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影响。
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人”的自主能动性,关注作品演奏过程中的表现力和创造力。毕竟任何基于“标准化”乐器的演奏,都存在各人对乐器的触发动作、力度、演奏法、指法的差异性,上升到作品演奏层面,即成为不同演奏者演绎的个性,再结合不同的喜好标准,所以外界对演奏风格、水平、效果的评价也往往是“个性”的,有时还会引发对“流派”问题的讨论,难有统一标准。而后者关注的是“物”的规范性,以及这样的规范准则产生的社会化影响问题,如国家和轻工业标准造成的新中国民族乐器器物的“标准化”。本文中主要讨论的,就是这套客观标准执行生产之后,乐器器物本身反映到多个领域中的社会化实践问题。诚然,“标准”的建立过程中难免主观,乐器在“标准”之外也留有个性空间,后文中将一并讨论此类问题。
一、“标准化”观念的提出与落实
我国疆土广袤,地缘复杂,乐器众多,但乐器器物上的“标准”问题一直是薄弱之处。各地乐器发展动辄上千年历史,同类乐器看似一致、实则有异、语汇不通,连基础配件叫法都各执一名。以民间常用的吹管乐器哨片为例,京东哨鼻儿、天津嘴子、山西咪子、东北响儿、河北引子(大引、小引)、河南叫子(叫叫、咪、吹咪儿)、安徽口密子……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如果缺了通用语言“哨片”两字的统纳,理解起来着实不便。
如果说称谓标准缺位,造成了表述和理解的困难,那么,形制和音响标准的缺位,则严重影响乐器的基本性能。笔者在2013-2015 年间多次拜访琵琶知名制作师满瑞兴,他14 岁起就在北京义和斋乐器行,后进入北京民族乐器厂当工人,直至成立自己的乐器作坊,几乎与我国的乐器行业共同成长。提到当年中国乐器“不标准”是全国普遍现象,乐器受各种条件局限,每一批的质料都不同,形制都不一致,性能自然也差强人意。相较于世界乐器工业的规范性,上述民族乐器名称、物质和音响等的“标准化”程度提醒我们,乐器的“无标准”与社会的“现代化”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落差。地方乐器的个性和语汇自然值得珍惜,但从行业发展和应用研究上,也需要辅以“标准化”的共同语言。
新中国成立后,乐器“标准化”观念是以器物为中心的,在国家引导民族乐器发展历程中逐渐落实,再逐渐由器物典范演变为乐器标准,并进一步社会化的。事件起点是1954 年开始的“民族乐器改革”,也被业界称为“乐改”。1954 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成立当年,受第一任全国音协主席吕骥交托,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李元庆在所里成立“乐改小组”,亲任组长,杨荫浏、王湘、毛继增、陈自明等人作为组员先后参与其中,后来进一步成立乐改陈列室,展示改革乐器典范,领导、组织、践行并推广全国民族乐器改革。
这场新中国“乐改”一方面承继了20 世纪初郑觐文等音乐家在大同乐会改革创制164 件乐器、组建“国乐大乐”的大胆构想,也对刘天华等音乐家们在“国乐改进社”的理论讨论等进行了延伸,李元庆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等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引导全国乐器发展理念的文章①这一系列文章包括《谈乐器改良问题》《谈乐器改革的原则》《继续开展乐器改良工作》《进一步地开展民族乐器改良工作》等,后集中收录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李元庆纪念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首篇《谈乐器改良问题》就专门提出“乐器规格标准化问题”:“要使分散经营的乐器作坊所制造出来的乐器达到规格的一致,在目前还很困难。但是现存应该做一些准备工作,为将来乐器制造规格的标准化,创设必要的条件。……确定标准音,建立乐器检定制度,是乐器走向标准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介绍和推荐较优良的乐器设计。例如低胡,它的尺寸、琴弦、定弦法迄今漫无标准,如果由公营乐器工厂和二胡专家们共同研究试验,设计一两种式样,由公营工厂首先推行,逐步改进(每种设计标明号码),就会使私营乐器工厂逐渐有标准可遵循了。”[1]
20 世纪50 年代末,国家轻工业系统②2000年前,此类标准由轻工业部组织编写,机构更名,由国家轻工业局颁布。2001年2月28日,国家轻工业部、轻工业局完成机构转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接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率先向乐器规格发力。1959 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等生产单位提供珍贵数据,参与轻工业部“社会常用的五种民族乐器第一次制作规格标准化试点工作”,历经“文革”期间,直至1977 年7 月,民族乐器第一个部级标准“京胡、二胡、笛子、大三弦、琵琶五种民族乐器轻工业部部颁标准”在上海正式审定,到1980 年10 月,虎音锣等五种常用铜响乐器部级标准草案在武汉审定,民族乐器行业标准终于在20 世纪80 年代覆盖了吹奏、拉弦、弹拨、打击四大类乐器对象,这也意味着标准工作走上正轨。截至现今,我国轻工系统和相关部门已陆续提出并发布民族乐器国家标准(GB 或GB/T)和轻工行业标准(QB 或QB/T)共计30 项③其中3项是国家标准,即十二平均律的频率与音分的计算、乐器产品使用说明的编制原则、乐器分类等;27项是轻工行业标准:即民族弦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琴弦通用技术条件、民族气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十二平均律音名标注方法、响铜体鸣乐器通用技术条件、乐器音准装置准确度等级判定、琵琶、筝、阮、三弦、月琴、京胡、二胡、笛子、笙、箫、唢呐、柳琴、扬琴、虎音锣、武锣、苏锣、手锣、抄锣、水镲、吊镲、军镲。,而其他民族乐器的生产方也争着效仿,建立了省市或者工厂级别的生产标准。[2]上述民族乐器“标准化”,率先实现了服务于民族乐器制造的工业生产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音乐学家在这一过程中成了“乐器规格标准化”要求的提出者,但实际落实情况却要复杂得多。究其原因,“标准化”观念来自文化部的研究力量,但涉及乐器材料、制造、投放、普及、教学等实践环节的业务一直划归农业部、冶金部、轻工业部、中国供销总社、教育部等部委主管,可以预知,“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得不服从于后者所把握的国民经济生产的现实条件。
二、“标准乐器”的普及与应用范围
乐器功能的实现系统,按照时间先后,先制造,经销售,后演奏。其中“制造”环节,是标准化观念从书面转化出实物的第一环节,也是社会化的基础。伴随着国家和部颁标准的确定,通过了专门机构鉴定合格的“标准乐器”,得到了国家颁发的“身份证”,借助知名演奏家和乐团作品在电台、乐器博览会、商品交易会等推广和传播,进入流通市场,带动相应的代表曲目和更丰富的演奏法出现,在演奏、参赛、教学领域得到社会化推广。
(一)表演实践
改革乐器从1952 年开始,就在刚成立的中央广播乐团民族乐团里使用,引发了彭修文对乐队建制的一系列探索,此后,乐器改革品形制、性能以及组合性质更趋稳定,系列乐器等进一步作用于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以及原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等各地各类乐团,成为此后中国交响化民族管弦乐队的基本面貌。就如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阎恵昌所说:
关于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规模的标准化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有争议,各地也有不同的实践。……尽管对标准化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许多作曲家和指挥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但相对固定,相对标准化(不是绝对的)也是有必要的,我们的民族管弦乐队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其实是很标准化的,吹、拉、弹、打这四个声部被大家所共识。[3]
国家级民族管弦乐队之中的知名演奏者对标准乐器的选用,也成就了特殊的榜样意义。中央民族乐团笛子演奏家王铁锤就曾告诉笔者,当年他从定县子位村进入乐团,才使用上了加铜套口的定调笛创作、改编《庆丰收》《赶路》《油田的早晨》,没想到在电台播放大受欢迎,老百姓们争相模仿①见笔者在2011年探访王铁锤先生的采访笔记,王铁锤作为从河北定县子位村走入中央民族乐团的笛子演奏家,有着从民间乐手到国家职业院团演奏员的经历,也对乐器的发展应用有自己的理解。。名家选用的广告效应,无形中烘托了“典范”意味。就这样,在名家、作品、演奏法研讨会、汇报音乐会,加之行政力量的倾斜和推动下,各式主流媒体的积极宣传,使这种标准乐器的影响不仅覆盖国内,还辐射到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
这一时期,在国家内部对民族乐器的应用需求巨大,工厂按照行业标准进行规模生产,大量标准成品正蓬勃而出。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全面实行政府指导,“乐器作为文体用品的一个类别,实行的是‘统购包销’,……乐器商业体制也基本上是一种政府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的乐器交易平台是政府所提供的三个综合性贸易的平台:全国文化用品交易会、全国教育用品设备采购交易会、广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4]。这些每年定期举办的商品交易会,包括后期发展出的各地乐器博览会、大规模吸引大量业内生产商、经销商、原料供货商,也满足着文化、轻工等各系统职业和非职业乐器爱好者的乐器需要。如今上海、北京的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等均已形成品牌,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北京民族乐器厂等知名民族乐器厂作为常驻方,不只常年参加国内外展销会,各厂本身也还积极举办种类丰富的年度乐器订货会。[5]159标准乐器大批量进入了市场,开始着眼未来,也意味着它的主战场,从表演实践扩展到了教学推广、考级评奖。
(二)教学推广
通过院校专业教师教授学生,实现乐器“标准”的普及推广,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早有先例,源头可以追溯到早期刘天华编写教材,培养学生,使民间二胡进入音乐院校,实现了当时二胡结构改革、定弦音高、音域、转调手法的推广[6]。乐器“标准形制”的确定、应用、创作,进一步带来了教学推广的可能性。从1950 年起,民族乐器专业伴随着新一轮的乐器发展和形制稳定,在全国院校中逐步开花。以扬琴为例,长期致力于改革的郑宝恒就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启了扬琴专业,同一时期在国内其他省份,李广才、陈照华等人也分别在开创扬琴专业课,生生不息,传承不止,后来多排码扬琴作为标准型通行至今,离不开他们共同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扬琴教师[7]。
少数民族乐器地区对“标准乐器”样式的确定,同样积极,甚至更加热情。当地艺术院校在许多课程设置并不完善的条件下,争相开设本民族乐器的专业和相关课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艺术学校设立伽倻琴专业,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学校设立马头琴、四胡专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艺术学校设立艾捷克、胡西塔尔、弹布尔专业,西藏自治区艺术学校设立扎木年专业等[8]。在同类乐器样式更显个性的少数民族地区,乐器载体出现标准,使院校专业教学成为可能,也使本民族文化的传习得到了更充分的保障,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样的推广还多了一层系统完善少数民族音乐教学体系的意味。
教学双方的参与带动,使非职业人士也对乐器标准的贯彻有所助力。随着非职业院校、单位、团体积极组织兴趣小组,进行常用民族乐器教学,甚至邀请高水平职业演奏家进行长期、正规培训,也对推广和传承具有长远意义。目前,仅北京就有“金帆民乐团”中小学乐队、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民乐团等数万名学生加入民乐行列。[9]不仅在国内,随着中外交流的日渐常态化,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对中国常用拉弦、弹拨、吹管和打击乐器的介绍,在东西方世界不胜枚举,现如今,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等更是都开设了中国乐器教学。
(三)考级评奖
20 世纪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初期起,全国社会艺术水平民乐考级从乐器、乐曲、演奏法,甚至教材向社会大众公布了一整套常用民族乐器的实践规范,考级大军也成为普及乐器的重要群体。自上海、广州1989 年前后开始举办乐器(业余)考级活动,中国音乐家协会于1991 年寒假也举办乐器(业余)考级活动,如今不同系统和单位乐器组织的考级活动每年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和地区频繁开展,响应者以百万计,仅北京地区的民族乐器考级就有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中国歌剧舞剧院等多家组织机构。其中,中国音乐学院的考级针对民族管弦乐器,还要求一律使用该院考级委员会编选的《中国音乐学院校外音乐考级全国通用教材》《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通用教材》《中国音乐学院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精品教材》,对社会演奏者做进一步规范。
除了面向广大社会民众的业余,常态化的大小“金钟奖”“敦煌杯”“虎丘杯”民族乐器演奏比赛,以及2019 年刚刚结束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民族器乐大赛等民乐定期赛事进一步实现了对职业乐器演奏者和所使用的乐器的规范。这并非小题大做,由于民族乐器存在各种音位排列、音域音量上各不相同的器物形式,既有原生的,也有改革的,如果在公开赛事之中不做限定,就容易重蹈1987 年2 月下旬的“广东音乐演奏邀请赛”中的情形:23 支参赛队演奏指定曲目《雨打芭蕉》都必须更换自己的扬琴。这一更换就是23 组,不免让人对赛事、乐曲和乐器的稳定发展产生疑问。“参赛乐器符合基本形制标准”,一方面满足了赛事的一致性、公平性原则,也从另一方面肯定了标准乐器相对稳定可靠的性能。此外,乐器制作赛事更进一步追求将现行标准乐器的性能典范发挥到极致, 据统计,“‘敦煌杯’民族乐器制作比赛”,从20 世纪80 年代初开创以来,已涉及二胡、琵琶、柳琴、笛、扬琴、筝,及各类自制工具、刀具等二十余项。[5]156
三、海内外对“标准乐器”的认同
经过上述表演实践、教学推广、考级评奖等实打实的应用,以二胡、古筝、琵琶等一系列常用乐器的标准形制在社会上普及,上海、苏州、北京等地民族乐器厂推出的自有品牌乐器甚至还在业内获得了特定乐器拳头产品的口碑。张子锐创制“二胡专用金属弦”和“带挂钩的调节式琴弓”在二胡上通用;二十一弦、二十三弦、二十五弦等成为古筝的常见弦式;扬琴发展为三排码、四排码、五排码,琴竹基本普及;而最普遍的应用是钢丝弦、钢丝尼龙弦、尼龙缠弦。它们由于张力大、不易断弦、质量更稳定,从20 世纪70 年代起,已成为海内外民族乐器使用的弦质。同样,在民族管弦乐队里,定调插口笛、加管加键的扩音抱(排)笙、革胡在内的胡琴系列、阮族系列、民族定音鼓、云锣等都依照特定的规格标准,得到专业演奏者的运用。
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其他国家的民族乐器应用,不仅深受大陆的影响,更直接以大陆乐器为典范。无论大陆推广哪一种改革乐器,港澳台都会很快跟随定购,是1949 年后民乐交流的常态,比如在台湾地区,民乐从业者来大陆求师曲目和技术,大陆音乐家赴台演出和教学十分普遍,大陆民族乐器已实现了用商货柜发货台湾,逐步建立的台北市立国乐团、高雄市立国乐团等专业团体,以及数十个半专业和民间业余乐团所用乐器也都基本来自大陆。[10]从具体乐团个体上说,在香港地区,20 世纪70、80年代,香港中乐团就购入中央歌剧舞剧院方浦东、北京民族乐器厂孙汝桂创制的3 把加键扩音笙使用[11],还长时间订购、使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58 型大革胡,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仿生皮的低音革胡,并大力开展对阮族、唢呐等吹管乐器的系列化改革。[5]145不仅如此,香港中乐团乐改研究室主任、柳琴演奏家阮仕春甚至还向笔者强调,以标准乐器构建的民族乐队形式尚未发挥出应有的潜力,他认为:“比之大陆的众家民族管弦乐团,香港中乐团的音响效果显然要更为让人满意,”究其原因,不是演奏人员,而是乐器器物上花了很多工夫,追求用料、规格、部件、尺寸等的更大程度、更为精细的标准化,使用了比一般通用规格更为严苛的乐器标准。当然,这样的标准乐器,已经在国家、部颁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香港中乐团的自有知识产权内容。①见笔者在2013年6月采访香港中乐团阮仕春先生的采访笔记, 他作为香港中乐团乐器改革业务负责人,主导了乐团的柳琴、革胡等许多民族乐器的改革。
随着“标准乐器”音乐实践性能上的稳定和民乐“交响化”建制的推行,武汉锣厂的云锣、大抄锣愈加受到认可,德国柏林交响乐团、日本名古屋市日中友好协会等长期订购,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国乐团也都引进中国民族乐器,海内外华人民族乐团建制趋于统一。[12]到了21 世纪初,在指挥家朴东生先生的印象里,台湾以及港、澳,还有新、马等国,……都有一个极为鲜明的共同点——乐器统统是大陆制造,做法、座次、编制及训练模式几乎完全一样。……不仅乐器、乐队编成一致,就连所演奏的曲目也大多源于大陆作曲家。[13]
中国大陆的民族乐器经过改革,经过标准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激起人们对中国民族乐器的重视,跨越国界在非华人、华族国度生存发展。语言、乐器、作品、排练习惯和专业用语如出一辙,甚至乐团指挥都是同一位,民族乐器在海内外几乎通用。而民族器乐领域的海内外交流深入到难解难分的程度,这一方面说明华人们对这些乐器自发自觉的欣赏和推崇,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些“标准乐器”适应了乐器发展的国际环境。
四、器物“标准”负载的三层内涵
当我们谈论“标准”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历数新中国成立后,原有乐器改革成型,经过许多轮的试制、试用、淘汰、定型与传播,一步步实现了当下大众认同的民族乐器形象,第一道桥梁正是李元庆提出“规格标准化”。在这个过程中,谁在发力?谁在接棒?谁在实现?谁在认同?是一个涉及国家机构、音乐学者、各大部委专门机构乃至广大民众的大问题。
“标准乐器”出现的首要目的,是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乐器规模化生产面临的问题。因此,国家率先推动“乐改”,选出理想化的乐器个体——标准器,推动生产、实践、销售的互认。但这一系列有轻工业系统出台、得到客观承认的乐器标准,归根结底,只是适用于工厂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标准”,就其器物结果——“标准乐器”还只是形态标准的基本乐器。但是,它们依然负载着丰富的功能性内涵。
标准从无到有,使传统中国实现了与现代世界的连接。标准乐器这一载体,不可避免地对接现代工业文明,显示了传统手工业生产与现代工业标准相结合,达到了超越技术层面的文化融合。“标准乐器”的实践意义,是通过多重功能性来体现的。不论是映射人们脑中的民族乐器“标准照”,或是演奏出的“标准化”声音,一路走来的乐器“标准”实际承载着三层含义:
一是多重意义上的性能典范。
当国家推动的“标准”出现时,我们知道单一一方的建议,很难成为评判的唯一标准。相反,需要乐改的指导者、乐器的实践者以及各部委协调方,共同参与判断乐器在音乐性能、民族个性和使用稳定性上堪当“典范”,方能将这件乐器个体,树立为业内公认的该类乐器的“标准器”。在多重意义之中,“典范”在演奏上的实现,主要依靠以文化系统的艺术院团,尤其是演奏员、研究者为代表的业界领军人士,因为在一般民众看来,名家犹具“性能标准”的判断力,经名家选用的“标准乐器”往往是民族器乐优异性能的象征,在现今各乐器厂(作坊)极力找民乐名家代言、使用乐器也是如此,具有“引导”意味。
二是服务于行业量产的强制性原则。
针对乐器所制定的国家、部颁,包括各个省市甚至工厂自定的标准,主要作用于从事商业性乐器生产的厂家。当轻工业系统从工业生产的角度出发,制订发布具体乐器的行业标准,意味着乐器具有了产品的身份,必须经过国家轻工业乐器监督检测中心等相关监管部门的管理,不符合工业生产标准的乐器,就属于不合格产品,不能投放市场。生产标准,必须是强制性的。
而以工厂为代表的生产力量,按照行业标准规模生产,投入市场,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会反馈相应的数据信息作用于生产标准的应用和更新。前述的我国轻工系统和相关部门提出并发布的各类民族乐器国家标准和轻工行业标准,都在21世纪里进行了多次修订,目前还在持续更新,但是此类强制标准始终是服务生产规格的客观标准,而不涉及界定“好坏”与“优劣”的主观标准。
三是大众应用中的社会化。
身为“典范”的乐器形制,通过强制性原则批量生产为产品,面向市场推广普及,在大众应用中逐渐实现社会化。一般大众,将这一常见的通用形制视为“普遍标准”。实现这层含义,需要依靠教育系统、专业社团、社会组织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以及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是乐器真正走向大规模实践的重要过程,广大民众心中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中国民族乐器的群体印象,很大程度就得益于此。
总的说来,上述三层含义在乐器领域,既可以共同作用,也具备各自独立实现的可能性。成为“典范”的改革形制可能在小范围内得到应用,却并不一定都适用于“大众化”和“行业量产”的标准含义。比如,应用在交响化民族乐团编制里的革胡等乐器,在20 世纪70 年代起,一度被视为低音拉弦民族乐器的典范,但是由于存在争议,适用范围窄,始终在院团和乐器研究机构的实验和改进过程中,因此不具备大批量生产的需要,也不需要建立相对应的官方行业生产标准,仍达不到 “社会化”和“行业量产”意义上的“标准”。而民乐名家爱用的“性能典范”,如果没有同类型的产品投入市场,实现不了城市生活的社会化;旅游景点上常见的“葫芦丝”“拨浪鼓”玩具,虽然大量地社会化,但是没有人会认为它们能作为乐器的经典,也不会以乐器生产标准的形式出现在国家、轻工业强制性标准中(以玩具标准出现另当别论)。
作为乐器的标准,三层含义可以独立、自由组合,然而,一旦体现在“标准乐器”上,这三层含义往往相互关系,互为可能。集中表现在,获得认可,成为业内“典范”往往成为“行业量产”和“社会化”的基础。首先,音不准、律不正、实践性能不好、不适应独奏特性、合奏融合性需求的乐器,无法通过熟知中西乐器的李元庆、杨荫浏等新中国老一辈音乐学家群体的认可,也达不到国家专业艺术院团职业演奏员群体的试练要求。在笔者所统计的新中国乐改期间的双千斤二胡、大琶琴、律吕扬琴等近六百件试制品中,绝大多数的乐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成不了“典范”,也难赢得大众的长期认可,则无法够上“行业量产”的门槛。但值得注意的是,后期我国公布的国家行业标准(GB 或GB/T)和轻工行业标准(QB 或QB/T)中的标准数据,基本都来自1954 年“乐改”确定的典范乐器,如琵琶、筝、阮、三弦、月琴、京胡、二胡、笛子、笙、箫、唢呐、柳琴、扬琴、虎音锣、武锣等各式响器适应了专门的乐器生产标准,也已经在院校教学、考级评奖得到大众化应用,尽管仍需改善,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同时满足了“标准”的三层含义。
结 语
“标准”,对于几千年来道法自然的中国音乐理念来说,实际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当前苏联完成了对巴拉莱卡(三角琴)的系列化,音乐家查哈罗夫等访问中国推荐经验;哈萨克斯坦也完成了传统乐器组建的库尔曼哈孜国立管弦乐团、萨孜根民俗民族志乐团①根据笔者在2018年9、10月采访哈萨克斯坦萨孜根民族乐团(SazgenSaz)成员,现TURAN乐团(Ensemble TURAN)成员的采访记录。等;朝鲜投入力量学习,着手准备本民族大乐团建制②根据笔者在2016年4月采访乐改小组成员陈自明老师的采访记录。……当时的中国乐器虽然不至于陷入全球化的语境,却实实在在地作为国际视域下的“民族乐器”存在。在国家力量下,缺失了几千年的“标准”迅速实现,通行在20 世纪70、80 年代,并作用于全国乐器实践,在现代社会中更新了那沓被称为“中国乐器”的照片,同时还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无条件关注和追随。
笔者认为,自1954 年李元庆提出“乐器规格标准化”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标准乐器”浮出水面,但其所引发的多个系统的合作应用、多个领域的社会化实践是值得进一步权衡的。围绕“标准”的主客观因素太多,在目前条件下,集中讨论工业标准下制造出的“标准乐器”如何在发展、面世的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得到相对普遍的“社会化”认同,是较为可行的。20 世纪民族乐器“标准化”行为的本质,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出于音乐界对乐器的要求,相反,一个百废待兴、亟待发展的新中国,在一片高歌前进的喧哗声场里,专注致力于传统乐器的保存和发展,有一种“时代错置”的为难。恰好历史选择了吕骥、李元庆、杨荫浏等熟知中外的音乐家群体投身于此,在充满强烈感情的传统与性能结构不稳的乐器之间,迈出了标准生产的第一步。是他们能将希望寄托于“标准乐器”之后的应用,也把“标准化”的未完之题留给了今天。
“标准”本身,是现代也是历史的,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共性的也是个性的。20 世纪,民族乐器制作行业的通用语言被作为“标准”,树立了新一代人对中国器乐的“传统”印象;21 世纪,再度审视“标准乐器”,可以折射出我们对于“标准”应用的观念问题。一方面,行业量产的强制性原则主要针对需要大批量生产的一般常用乐器。对于民间地方性乐器的一个选项,当地人有权决定自己群体是否建立强制性标准,因此将强制性原则强加于地方性乐器上,让乐器“千器一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得到,即便是行业标准,也在强制性基本形制之外,为不同品牌的民族乐器保留了个性空间,甚至可以说,如今云南少数民族的葫芦丝、广西壮族地区的铜鼓等都具备了省市或者厂级工业标准,也强调着自身的民族个性,这样的乐器在当地民众的审视下,至今担当着当地人心中的“标准乐器”。
认定“标准乐器”的主体,始终是人。人基于认定的客观标准来进一步探索主观认识,寻求多元化认知,更新和发展民族乐器“方言”体系,使“标准化”道路的探索,不致框死在“个性”的对立面。“标准乐器”并不排他,正视院校、赛事上的常规乐器标准、交响化民族管弦乐队里成系列的乐器阵列,也能尊重田野村头不向工厂标准靠齐的民间乐器和在老乐器音品指缝里的中立音程,为乐器对象的不同“标准化”需求,寻求不同意义上的“标准”。基于“标准乐器”的客观标准来探索主观认识,寻求多元化认知。“标准乐器”走向成熟,不是强调“非此即彼”的唯一标准,而是找到灵活开放的适应性标准。过去的一步太久,如今这一步当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