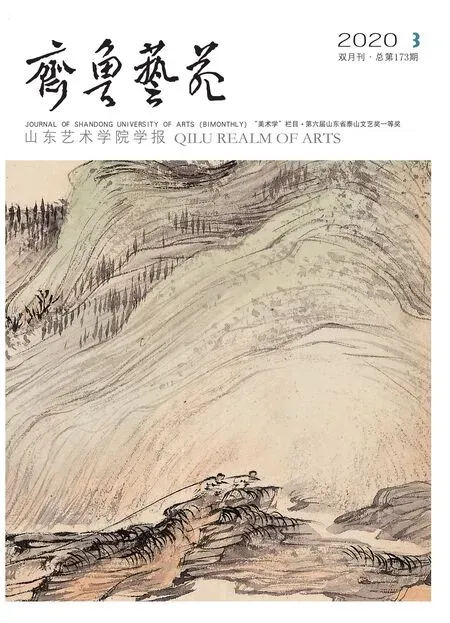中国电影的“想象力消费”问题
——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第48期实录
陈旭光,张明浩,李 立,李雨谏等
(1.2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3.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4.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想象力消费”——缘起与思考
谢谢各位朋友光临“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今天我们作为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第48期,点评对话的力量比较强大。欢迎四川大学青年新锐批评家李立,也是我早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有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李雨谏,他们都非常乐意常回家看看。我们也会经常创造机会请他们回来为我们贡献他们的才智。中国电影“想象力消费”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探讨价值,刚好张明浩的课程结业报告是这个话题,另外就是李立与李雨谏他们最近也都写过关于“想象力消费”的文章,做过一些很深入的思考。
我先简要阐释一下“想象力消费”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表达我的一些理解和想法。其实我对“想象力消费”的思考,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2012年写的一篇文章《关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思考》[1](P98-101),我当时痛感于“中国电影缺乏想象力”。当然,我也注意到了“随着市场受众主体和生产主体的不断年轻化”,同样需要想象力的玄幻、魔幻类电影在近年的崛起。因此我希望并呼吁想象力充沛的科幻电影、“高智商”的惊悚电影、心理恐怖电影的崛起,这些电影那几年是比较稀缺的。我认为这些类型的电影都应该崛起,而且也必然会崛起。而事实上这几年的电影实践中已经开始崛起了。
毫无疑问,中国长期来很缺科幻电影,很多科幻电影虽然名义上是科幻,但其实里面科幻的“核”非常“小儿科”。那么,中国电影为什么缺科幻电影,缺科幻电影所需要的想象力呢?美国电影为什么想象力那么丰富?我当时把想象力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外向型的,就是向外太空开拓,宇航大片、太空片这种。还有一类内向型的,就是向人的潜意识心理深入,比如说类似《盗梦空间》《黑天鹅》那样的电影。中国电影为什么缺想象力呢?恐怕与孔孟儒家之道有一定的关系。孔子不是一直提倡“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吗?幻想世界正是他不愿意讨论的彼岸世界。再另外,就是道家不求甚解的模糊哲学,对科学精神的发展和生产也可能有影响。总之,中国的世俗伦理和务实、经验型的现实性国民精神等都不太喜欢去考虑未来人类社会的结局、命运、“末日审判”等等宏大、未知的问题。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例如“杞人”,当然就被大家嘲笑了,“杞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归根到底,当下中国电影中想象力的缺失某些程度上说,源自整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制约,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规范都可能与之有关系。
后来我就设想,既然科幻电影,尤其是“硬科幻”大片我们做不了,因为文化观念不鼓励表现灾难,没有末世意识,工业化程度可能不够,那能不能先发展一些玄幻、魔幻类电影呢?中国毕竟有《山海经》《搜神记》《聊斋志异》等等一些优秀的神话传说、民间传说作品。所以我当时就呼吁和呼唤玄幻、魔幻电影。事实上这几年玄幻、魔幻电影从创作实践来看确实也比较发达。近几年,不仅有久盛不衰的《西游记》改编,还有像票房很好的原创作品《捉妖记》。2016年,我在北大做了一个“批评家周末”的学术沙龙活动,就是邀请一些学者与陆川导演对话,讨论正在上映的《九层妖塔》。《九层妖搭》改编自盗墓小说。盗墓小说曾经被著名的文化学家陶东风先生批评为“不说人话”。意思可能是说它里面的历史、现实、故事,很玄乎,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缺少现实依据,所以陶东风说它“不说人话”。我觉得这样说也是挺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能不能说,“不说人话”恰恰是玄幻、魔幻,包括科幻类电影的重要特征呢?这不正是现代的“杞人”们所做的吗?不也正是适合于“网生代”,在游戏类、在网络小说、盗墓小说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的欣赏特点吗?这一代很多人喜欢看各种盗墓小说,但是你要从盗墓小说里学历史、地理、文物知识,那却可能是误导,学不到正规的,属于“正史”的历史知识。但是它好玩儿、好看,年轻人喜欢,充满各种玄虚超现实的想象力。
所以,我在《想象力的挑战与中国奇幻类电影的探索》中提到:“中国奇幻、玄幻类电影本身是一种新的文化症候,它顺应的是互联网哺育的一代青年人的消费需求,是在玄幻类、奇幻类电影缺失,以及在儒家传统文化……现实主义创作制约下的背景中产生的。这有其独特而重大的意义。现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引进,并催生了一代人想象与消费,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跟现实没有任何关联的,要转很多弯的影像消费,这种想象力空前强大的消费力,与以前我们说的艺术的满足,情感的消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想象力消费’”[2](P123-128)。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几年,在中国,玄幻、魔幻类电影还是一直处于发展中的,包括以《西游记》为IP的大量改编,还有《画皮》系列、《捉妖记》系列,包括徐克的《狄仁杰》系列,都是这样一些有着明显玄幻、虚幻美学特点的电影。
当然,当时我痛感的缺少科幻电影的感慨,还是在2019年年初《流浪地球》的爆款,以一种“科幻电影元年”的众所期待而打破了这样一个魔咒。
实际上,科幻、玄幻,以及“影游融合”类电影等,都是非常需要想象力。而且我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想象力”不同于以往文艺创作中论述的那种一般不能脱离现实的、细节化的想象力,而是一种超现实的、后假定性的、“拟像”性的想象力。鲁迅先生曾经所说的其艺术创作的手法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这也需要一种想象力,他又说到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先生在这里说的创作特点,我们认为是一种现实主义想象力的创作方式。而在今天我们说想象力可能是一种“后想象力”,不是现实主义的想象力,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媒介、虚拟“拟像”的世界里,符合这一代人特点的想象力方式。我把“想象力”与“消费”这两个术语合在一起,于是生成了“想象力消费”这样一个术语。消费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想象力可能主要还是一个文学艺术、美学的术语。所以“想象力消费”是一个跨学科的术语。
当然,想象力本来就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是人的一种重要能力、天赋,刘慈欣说当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智能人、机器人都普及以后,可能想象力是人区分于动物或者其他一切高能之物的素质。我想,智能机器人也有想象力,但那种想象力可能是锁定的、预见的、被预先编码的。但是人的想象力完全是未知的,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而互联网时代的想象力更是可以无中生有的,它不必以现实、真实为标准,只要遵守“相信”的默契,任何夸张、幻想、虚拟、“拟像”、历史穿越、“不说人话”都可以存在。
所以我把“想象力”与“消费”组合起来。在我看来,“想象力消费”这一术语具有跨界、跨学科性,并具有文化经济学、艺术经济学的复合性,而且可能具有强大的意义再生产功能。
但我们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的术语能不能成立,它成立的依据如何?然后应该接受怎么样的检验?还能够往哪些领域去开拓、拓展,去进行“意义再生产”?比如说我区分的“影游融合”类电影,玄幻魔幻电影,科幻类电影等等,在这类电影当中想象力到底如何表现?“想象力消费”到底如何消费,是符号的消费还是物的消费等等?作为一种艺术或文化的消费,它的功能为何?它的使用价值和意识形态功能又如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能够凝聚很多学科热点,能够聚焦当下文化热点现象的术语。
所以,今天的“批评家周末”沙龙专门围绕着这样的一个话题,进行多方面地深入探讨。大家一会儿可以有阐释,可以有质疑,可以有补充。看看这个从问题导出的思路延展,也是有现实依据和理论建构空间的学术范畴,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和高度。
张明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想象力”消费的功能及策略——以中国魔幻类电影为例
我主要从“想象力消费”的功能以及它的策略来进行论述,然后梳理近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魔幻电影的“现代性”转化过程。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互联网新媒介时代呼吁想象力消费;第二,中国魔幻类电影——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形态之一;第三,想象力消费的内外策略,我把想象力消费的策略分为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第四,想象力消费的三种功能或曰三个阶段;第五,将上述论述加以总结提升。
(一)互联网新媒介时代呼吁“想象力消费”
关于“消费”,产生了诸多影响颇大的理论或观点,无论何种观念,何种主张,都似乎在强调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仿佛在表明收入会影响个体消费的方式与观念。
回眸新中国建国70年消费观念、消费需求的变化,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中国正逐步由旧式生存型消费过渡到新式享受型消费、发展型消费。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已经基本步入小康社会,消费者已经不限于生存资料的消费需求,更多消费的是具有体验、享受感的服务型产品。正如2017年国家发改委所判断的,“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正在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与此同时,随着网络覆盖范围的逐渐全面化,我们也似乎随之进入了一个以青少年受众为主体的互联网新媒介时代。正是在媒介之变与青少年受众之变的溯源下,因为想象力消费的增长才使得我们称这个时代为“新消费时代”。而“想象力消费”显然在新消费主义时代下具有至关重要的位置与作用,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强调的是,互联网新媒介时代下的“想象力”,已经不同于以往文学、艺术理论中所强调的一般不能脱离现实原型的想象了,而是一种虚拟性、超现实的想象。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下,“所谓的想象力消费,就是指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的巨大需求。显然,这种消费不同于人们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消费需求,我们也不能以类似于‘认识社会’这样的相当于‘电影是窗户’的功能来衡量此类作品。在互联网时代,狭义的想象力消费则主要指青少年受众对于超现实、后假定美学类、玄幻、科幻、魔幻类作品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
(二)中国魔幻类电影是电影“想象力消费”的重要形态
关于“魔幻电影”与“魔幻现实主义”中的“魔幻”具有相似性也有所不同。文学中魔幻偏向外壳,电影中的魔幻是内在。文学与宗教学者菩提尔曾在《神话与故事》中提出,构成魔幻的要素有“过去”“魔法”“神话传说”“超科学”等元素。诚然,中国魔幻类电影中也有着此类异于西方的元素。
拥有商业气息、类型特质的中国魔幻类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最早或许可以追溯到具有魔幻、玄幻元素的《火烧红莲寺》(1928)。新世纪以前,由于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限制、国家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倡导等原因,魔幻类电影因题材涉及牛鬼蛇神、妖魔鬼怪等封建迷信、“文化糟粕”而一直不被重视,没有形成一种清晰明确、系统可观的类型。新世纪以来,随着《无极》(2005)、《画皮》(2008)等魔幻类电影的崭露头角,让导演看到了魔幻类电影巨大的票房感召力与经济效益,也让受众感受到了虚拟想象下奇异景观的光怪陆离与波谲云诡,魔幻类型以往的边缘身份在此背景下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观。自2015年起,中国魔幻电影更是在想象力的加持下势如破竹,屡创佳绩,而2019年上映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以49.72亿票房的战绩,位居中国历史票房的榜眼。
毋庸讳言,票房成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受众的审美趋好,魔幻类电影的长足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想象力消费”类电影的锦绣前程
那么,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中国魔幻类电影利用何种策略才得以不断发展,走上康庄大道的呢?窃认为,在电影工业技术与体系不断完善的当下,魔幻类电影完成了现代性转化,一种是外在的、满足受众奇观审美之需的转化:工业体系下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奇幻镜像”式美学呈现与想象力表达;一种是内在的、满足受众情感想象之需的转化:温情世界的呈现、人文诉求的表达与“泛情化”叙事的运用。
(三)想象力消费的两种策略
1.想象力消费的外在策略是工业支撑下的想象力美学表达与梦幻奇观呈现
在电影生产、制作过程中,电影工业美学主张“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文化品格基准,也尊重电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工业性’要求,彰显‘理性至上原则’,在电影生产过程中弱化感性的、私人的、自我的体验,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标准化的、协同的、规范化的工作方式,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张力平衡而追求美学的统一”[3](P18-22)。借助高科技手段呈现视觉奇观、通过系统、协作、规范化进行制作、通过专业团队进行制作支撑……种种特征下的魔幻类电影,无疑是“电影工业美学”视域下颇具重工业美学特质的现实样式实例:“时至今日,在数字特效的支持与体验经济的驱动下,国产魔幻大片不仅学习西方电影制作技术及商业模式,而且也着眼于培养恪守电影工业标准、科学流程的产业品性……以《大圣归来》《寻龙诀》《捉妖记》《美人鱼》《大鱼海棠》等为代表的国产魔幻大片屡创票房奇迹,它们凭借国际化的特效技术、工业化流程范式、专业化制作团队,不断擢升中国电影工业水准,促进国产电影有效海外传播,推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电影市场体系及电影文化体系的协调发展”[4](P138-139)。至此,我们不妨说,近年来中国魔幻类电影在工业体系支撑下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中国电影工业水平,体系化、系统性、规范化的工业式生产,为中国魔幻类电影实施“想象力消费”策略,进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牢固地基。
与此同时,放眼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在美国电影产业中的《指环王》系列、《哈利波特》系列、《爱丽丝梦游仙境》系列、《沉睡魔咒》系列等魔幻类电影大片也是于工业化支撑下完成的:它们依托完善、精细、系统、协作的工业化生产及先进的技术特效支撑进行创作、发展,工业化运营、后产品开发的《哈利波特》甚至曾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似乎在强调工业化制作于魔幻电影的重要性,也仿佛在表明魔幻大片是天然适合于做工业大片的。
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导演以开阔的大远景、远景及富有灵韵的长镜头,营造了一幅幅“虚实相生”“天人合一”似“中国山水画”式的奇观异景,以此满足受众艺术审美消费之需。在片名之后,便是一幅山水飘逸之景,大远景、开放式构图、暖色调等偏于静态的视听造型语言下,我们看到了海水环绕、云雾缭绕、青山绿水似世外桃源的“钱塘江”,在此,雾气、山水、光色、绿茵勾勒出一幅飘逸灵动的奇观之景,虚实相映,别有一番“天地大美”之韵味。
《妖猫传》整体影调表现为一种松弛、舒缓、悠扬、温和的软调,画面光线对比度小,影像亮度也较为均称,大量中近景、跟镜头、推镜头、摇镜头的运用,也给影片营造出一种别具韵味的灵气动感。诚然,中国魔幻类电影所代表的“想象力消费”类电影的外在策略具有共通之处,比如《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
但值得强调的是,中国魔幻类电影“想象力消费”的策略,不仅于“视觉奇观的营造”,还有一种策略是设置具有奇幻、怪诞、夸张、超现实、超历史、无中生有、出人意料等想象力特质的情节、妖魔形象与夸张细节等。《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与太乙一起“入画”修炼,充满着想象力。影片的夸张、怪诞的人物造型,也致使受众出乎意料,如“鞋拔子”脸、患有口吃的申公豹等。
2.想象力消费的内在策略则是视觉奇观下温情世界呈现与人文诉求表达
影片视觉奇观下温情世界的呈现与人文诉求的表达则是促使受众长驻的关键,《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作为一个出身魔丸的异类,在尝试多次融入社会无果后,变为了一个“小魔头”,似乎也是当下无数受众的代表。哪吒由“被边缘”到“被英雄”的弧度性人物设置,也无疑颇为符合受众想要成为“平民英雄”的未来之想象。
《白蛇:缘起》中,捕蛇村民风淳朴、村民性格热情善良、生活和谐融洽,影片在呈现山清水秀、郁郁葱葱、湖光山色的村落奇观的同时,也别有一番“美美大同”之意,满足了受众内在情感、身份想象之需。
《妖猫传》不止于表达人们借助幻术发泄自己情绪,更借助杨玉环等人对待幻术的态度或曰所追寻的“无上密”,为受众呈现了一个“假亦真时真亦假”的温情世界。
毋庸讳言,中国魔幻类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内在策略,具有“想象力消费”类电影内在策略的共性:《流浪地球》式的愚公移山;《微微一笑很倾城》中对爱情故事的温情呈现……这是“想象力消费”类电影的鲜活生命力所在,也是其引人入胜、令人长久驻足、流连忘返的关键所在。
(四)想象力消费的三种功能
想象力消费既是艺术消费,也是经济消费。约翰·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曾提出“两种经济”理论,他认为文化产品可以在并不相同的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中流通,两种经济运载着两种不同的内容: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则流通着意义、快感和社会认同。在文化经济中,受众可以成为意义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借用这一理论,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想象力消费”或“虚拟消费”既是一种艺术审美消费,又是一种经济消费。与此同时,作为想象力消费主体的青少年受众群体,在进行个体社群认同与身份编码(通过消费想象力来进入自我身份场域、彰显网络种群身份,进行重新部落化)的同时,还生产、流通属于他们的青年亚文化、青年意识形态。
(五)结语
诚然,“中国具有丰富的神话资源和长久的文化积淀。我们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三皇五帝,还有《封神榜》《西游记》中的神话系统。另外还有道士修仙、达摩顿悟这样凡人间的故事。我们还有《聊斋志异》这样的民间志怪传说。在《穆天子传》《山海经》等非主流文化典籍中,此类志怪传说也有大量遗存。这些是我国观众自幼耳濡目染的故事,也同时是国外电影制作者不好把控的题材”[5](P41-44)。所以,我们对于中国魔幻类电影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相信,未来中国魔幻类电影将在取材神话资源、立足传统艺术精神、融合多元电影类型、兼容中外价值观念、表达人文关怀诉求、发挥想象力,完善工业/美学融合的先进电影创作和生产理念下继续前行,并进一步以其独特的东方韵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李立(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想象力消费”的现实依据、美学特质与未来路径
大家好!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到一句话——“事不孤起,必有其邻”。陈老师提出这个想象力消费的术语,与他一直以来对想象力问题的思考是密切相关的。与他当年思考“后假定性”美学,对想象力缺失的文化思考,对玄幻魔幻电影的支持等,都是有关系的,是一种顺理成章的逻辑性发展。我在这里接着思考。
《流浪地球》当时号称给中国电影开了一扇门,中国科幻电影的春天来了,但是到了《上海堡垒》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它把打开的门关闭了,于是就会想它怎么会被关闭的?关闭是怎么来的?这实际上是耐人寻味的个案,这个个案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一)现实依据
我觉得现实依据的问题就是“想象力消费”跟电影工业美学的关系,“想象力消费”是对科幻电影提供的思想火花,更是丰富了工业美学实践的厚度。我把它从三个方面论证。
第一,论证了作为方法的可能,因为我们说电影工业美学是来自于问题、经验、“中观”立场的,是以问题为核心展开的角度。
第二,即便是第六代导演,即便是《上海堡垒》的导演滕华涛,也是第六代中极为优秀的导演,但是他同样面临着跟新生代导演郭帆一样的问题,即他同样对科幻电影是不熟悉的,科幻电影的难度要匹配想象力的挑战和电影工业美学所实现的问题,同样是经验不够,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
第三,从国内来说,科幻电影尚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全面向好莱坞学习的过程。如果说陈老师他们谈到的想象力是痛感中国想象力缺失,那要承认,我们面临一个长期补课的过程。
(二)美学特征
首先,以虚拟性为特征,本质是虚拟消费。虽然是在2016年陈老师就提出“想象力消费”的观念,我们发现它是在陈老师更早时候思想的“接着写”,是对“后假定性美学”的扩展,是后假定性美学的“接着写”。
第二,我认为是以新媒介为手段,因为现在客观来讲,现实对电影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了,今天的电影被叫作扩展的电影、媒介化的电影。陈老师在谈论“新力量”导演议题时,总结出来的关于新媒介美学特色的表述,我觉得不如说是电影生存的美学变革元问题。包括跨媒介的奇观化、景观化、拼贴混合,甚至通过对媒介的改造,使其变成真正有创意性的文化产品。
第三,孙绍谊老师提出的“体验力”的定理。最近我有一个新的思考所得,亦在反复思考来北京电影学院发表演讲的电影理论学家汤姆·甘宁对于“吸引力电影”观念的阐述,他在原话中讲到,“吸引力”非常短,就好像中国的烟火一样。其实我当时就想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的作品《烟火》。在“想象力”塑造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以“体验力”为诉求,不断释放想象力,强调启发观众想象力的过程。
(三)未来路径
第一,“影游融合”成为现实。
第二,“科幻电影”跟文化产业的结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何在中国文化产业中去激活它,实现传统文化观念向现代共享价值的转换以及跨媒介趋势的认同与重塑。
最后,促使“想象力”和“体验力”的结合。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发现“后假定性”美学与电影工业美学结合,构成“想象力消费”的整体。其根本价值在于,想象力不仅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手段,更是一种明确的消费目的。“想象力消费”会逐步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影游融合”艺术形态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因此“想象力消费”绝不仅是中国电影涌动的热潮,而是中国电影在“全球化”时代必然要面对的现实挑战。“想象力消费”不仅针对电影内部,而且针对电影外部,不仅针对电影的现在,而且针对电影的未来,只有如此理解与认知,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白,“电影是什么”这样一个永恒的元问题。
李雨谏(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影游融合”与“想象力消费”
今天,我主要想从“影游融合”的角度来思考“想象力美学”和“想象力消费”的议题,论述的途径跟之前明浩做的一样,想从现代消费状态视角来谈论“想象力消费”为什么可能。我用的理论好像跟明浩不太一样,明浩也可以关注一下某位日本学者的专著《第四消费时代》,在其中该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想法,说“第四消费时代”是共享型、内心归属这些话语为主要诉求的消费理念。就是说在消费升级观念的经济驱动之下,人们开始不再仅仅想这个产品做什么,而且思考我可以用这个产品做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等于产生了一个消费认知的转变,这是对三浦展就当下消费时代认知的补充。他提到的就是人们在当下的消费是以唤起自己主观能动性的方式去实现,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在唤起主观能动性的状态之下,然后再完成跟别人链接,他是这样阐述消费升级。
以此为切入来思考,在“影游融合”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怎么探讨“想象力消费”和想象力美学?我们或许可以说,计算机技术是整个“影游融合”的基础,数字是自我指涉和相互指涉,不涉及到任何现实层面的问题。
在代码之间,就是0跟1,在这样一个相互指涉的基础上,它生成的所有创造性影像跟想象的画面,于这个意义上来看是一个想象的、或者再造的现实。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虚拟现实”这样一个术语来表达,因为它是“想象力消费”的技术基础?另一个就是分析层面,在“影游融合”的故事层面上,电影关于虚拟现实的想象其实是比较多元的。再者,“影游融合”类电影塑造了许多基于虚拟空间的网络世界,像《头号玩家》中的“绿洲”等,都是直接用数字技术做出来的纯粹虚构空间。最后,它是以现实世界为一个假定性的游戏空间,就是通过现实空间展示现实本身,但是在虚实层面上给你区别出游戏空间和现实空间,这是内容方面的展示。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影游融合”的背景。我在整理当年毕业论文的时候,发现游戏以及“影游融合”产业最发达的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进而溯源追问,美国人为什么喜欢虚构形象。美国人大部分是通过《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电影来了解“二战”的,斯皮尔伯格说《拯救大兵瑞恩》是给美国人看的“二战片”,不是给全世界观众看的。他的所有逻辑和企图表达的文化理念,是给那个国家创造出的关于欧洲的历史印象,以及处于欧洲战场的“二战”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至于日本,其为什么游戏产业发达、而内容包含着丰富想象力驱动?或者它为什么要用游戏、用“影游融合”的方式,来释放他的想象力?从文化视角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大泡沫、阪神大地震、沙林毒气事件的社会现实影响下,开始形成治愈系文学的发展脉络,村上春树的作品,就是属于治愈系文学的高级系列。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游戏是作为其另一个产业存在的,它提供的文本,提供的关于跟美少女谈恋爱,怎么通过分支选择来拯救世界的设定,为参与者提供的所有想象性呈现,是为了祛除社会的创痛,从而与日本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转折与困境拉开差距。这就是让参与者真正进入一个所谓的梦境,去做超越现实的梦,借以回避现实。
另一点,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想象力”在这个时代流行,它跟主流文化的整体推动力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是需要观察视角的。因为日本从整体上推广其“二次元”文化的时候,是以国家体系化的力量去实践的,它身上凝聚有国家使命,也表明其国家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是跟虚拟、想象的元素并行的。
美国也是如此,当下这种存在于美国电影中的文化态势,包含“影游融合”的观念实践,实际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是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科幻电影或者“漫改电影”作为一个非常强大的产业力量进行全球推广的现实,也是其以举国之力试图推进的运作,甚至可能是一种文化战略。
我不是想做一个什么暗示,暗示现在国家在推进什么。比如说像李立老师提到的《上海堡垒》,让大家所有关于科幻片的期待跌到谷底,这如何去看?我目前没有答案,但可能跟主流文化的某些诉求是相关的。它或者与国家要推进的价值观念层面诉求有关,或者是产业要推进其整体运营策略的要求使然。尤其就当下而言,中国电影生产是紧密跟国家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的。
在中国,想象力电影提供的是几重虚构,这种虚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中实现,我自己想试图对其探究与回应,不然很多观点说起来还是有点虚浮,这也是最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想象力美学”终究要跟我们当下的文化实践发生关系,也是陈老师在相关文章中提到的“后假定性美学”所认知的部分,陈老师的论述亦是结合当下电影创作以及文化创作的具体实践来谈的。
最后,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想象力美学、“想象力消费”等概念,都暂且停流于技术层面,比如说作品内容呈现,当然也包括其产业意义。但是,它如何通过想象来实现故事讲述,其涉及的主题,无论是关乎“中国梦”还是中国“主体性”,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李雨谏刚才的一些想法很有创意,很有创新性,有些想法虽然一下子并未完全想清楚,但是思路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日本电影的想象力是起着治愈系作用的,然后美国电影的想象力,则是一种娱乐?这个思考我比较赞同,美国是美利坚合众国,是新大陆,跟古老古典的欧洲不一样。美国也许是最适合做电影的,因为电影天然具有商品性、工业性、娱乐性,与美国人的性格、美国精神是最为符合的。欧洲电影有艺术电影的传统,一直继承欧洲大陆艺术传统。但是电影在法国发明之后一到了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娱乐品,变成了梦幻工厂。我觉得美国人的性格的确是一个大男孩式的性格,虚构无罪,娱乐无罪,在电影中犯罪无罪,他的逻辑,它的文化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人一开始就不讳言甚至有意夸大电影的虚构性、假定性、想象力等特点,所以美国电影想象力就特别丰富了。
同时,我觉得像《上海堡垒》《流浪地球》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想象,而且都是因为中国现在要走向世界,走向宇宙了,现在国力越来越强大,信心越来越强或者说雄心越来越强,跟这个肯定有关系。
李雨谏(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
《流浪地球》最后有官方资本介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国家资本注入以后,一定会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会为这个文本提供很多额外的东西。但是《流浪地球》里面有一个逻辑我始终认为是不合理的,就是在西方的科幻电影之中,提供一个伦理选择,吴京要烧毁人类文明的数据库,这样的矛盾设置永远不会在西方电影中出现的,这是一个伦理困境。我不能因为当下的需求,就要烧毁全人类积攒起来的成果,这个矛盾的设计或者叙事的设置,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在科幻电影中我没有见过,西方不会设置个人面临这么大的对立面。
《流浪地球》在这里的逻辑有点像香港的电影,要打倒列强,我要击溃某一种霸权,是一种民族情绪的东西,所以他最后烧那个东西。那么,为什么中国人看懂了?但是有个韩国同学就看不懂,为什么要烧那个东西呢?他烧的那个东西我们接受起来能够理解吗?他跟国家资本的注入,包括整个片子最终要完善文化的表达,应该是有关系的。韩国同学说这样相当于“焚书坑儒”,他说那个机器人保存人类文明所有的成果,这个伦理困境我们怎么选择?
李典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就此而言,对他们来说,文化相当于灵魂,生命只是他们的肉体。当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的时候,他们认为会像没有灵魂。还有一个问题,意识形态用孔子的话说是一个春风化雨的东西,就是美国人对意识形态的注入是全年龄段,举一个例子,他们会在所有电视剧和电影里讲一个故事,男孩子会去冒险,但是最后回归家庭,如果回归家庭出现问题的话,就是一个悲剧。为什么“打响指”的时候会引人催泪,因为钢铁侠家没有了,他在一个小家或者大家选择一个东西,所有人都面对你要不要回归家庭?比如说他们之间结婚有孩子,回归家庭。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意识形态,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的思想,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全年龄段、全谱系讲这个故事。我们也有自己的故事,比如说很多年前《哪吒》剔骨还父,但现在我们看这个电影最激动的地方是“他是我儿”,父亲的形象跃然而起,这是我们的意识形态。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对。就是现在提倡和谐社会,家庭和谐、父子恩爱、父慈子孝、浪子回头,改邪归正、回归社会、经过生死之后长大成人,《哪吒》表达的这样的主题肯定是符合我们的文化共识,也是符合当下意识形态需求的。
李典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与此同时,我觉得咱们当下想象力消费最大的困境就是,我们学了很多西方的叙事结构,但是学叙事结构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他们的叙事结构是专门为他们叙事的情景服务的,我们总喜欢20分钟就唱一首歌的迪士尼,我们怎么从这个节奏中找一个讲中国故事的模式,这个框架怎么往里填中国自己的东西,这个非常复杂。还有我们正在期待的《姜子牙》该怎么拍?能不能成功成为一个封神宇宙或者封神宇宙有没有必要?我们有故事,但是完了以后怎么表现这个形式,这涉及整个产业链,也涉及我们如何认识自己等问题。
李雨谏(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
我再补充扩展一下,我们现在说的“想象力美学”“想象力消费”都是技术层面,比如说呈现方面,包括产业意义上的,它怎么想象这种故事,这种故事无论中国梦还是中国主体性也好,这个方面是需要被探讨的。日本提供的是可以跟不同少女恋爱,通过这个恋爱完成一种想象,这是仍然在故事层面去想象的。美国创作了一种牛仔的叙事,这个牛仔怎么结合他的行为,包括他怎么拓宽宇宙,这都是他叙事上的想象。
李典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
“想象力消费”如何升级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当我们消化这个术语或理论之后,我们自己还要成为下一代作者。每一代作者都是看着上一代人的影片长大的。如何通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特点的提炼、概括,形成新的观念和新的生产方式以反哺这个文化产业链?这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工作特别重要的问题。
陈旭光(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通过这次沙龙的学术碰撞,我感觉很有收获。在听的过程中我想到了很多值得继续探讨的课题,值得继续探讨的方向。我总结一下,一是想象力并不仅仅是想象力,想象力有它自己独特的方式,想象力背后可能是有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也有国家的,国家梦想的,例如美国的想象力跟欧洲的就不一样,咱们中国的想象力跟美国的就不一样。还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通过弘扬传统文化,哪怕是边缘文化的想象力,让它再一次激发中国电影产业,这个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也许我作为一个学者的提倡,我们作为青年学者提倡,恰恰符合了一种国民意志甚至是国家意志。第三,到底有没有就是中国特色的想象力?有没有纯粹的中国特色的想象力?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时代,很多想象力很可能是拼贴式的,里面既有中又有西,很多是超越现实,架空历史的。我们如何去艺术创作和生产的层面上对待想象力的问题,是固守于中国?不能在里面看到美国式想象的影子?还是可以包容?例如《捉妖记》里很多形象设置就是不中不西的,徐克的《狄仁杰》里面也有,表面上看有中国古代的亚文化,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很怪奇的东西,但是有很多想象很西方化,比如说中了蛊之后,变成了一个怪物,那不是西方的基因突变现象吗?不就是“绿巨人”这些怪异的想象,恐怕导演自己都分不清楚是中国的想象还是西方的想象了。
我觉得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从我们今天的“想象力消费”继续往下延展的话题。大家还可以继续“接着讲”。这个术语是有它的学术生产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