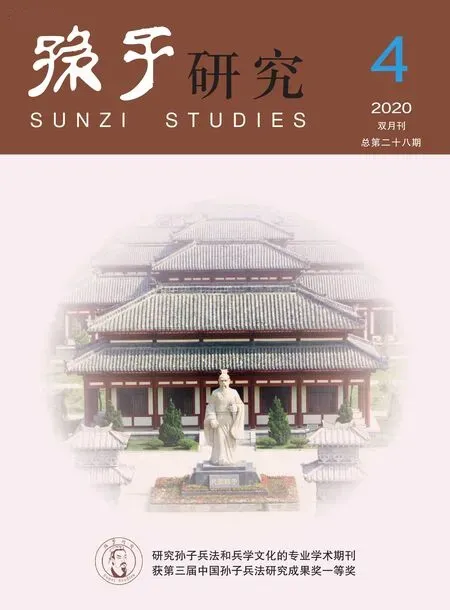论《孙子》“包四种”评价的失当
熊剑平
长期以来,我们都习惯于赞美《孙子》兵学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作为一部兵学经典,六千言的《孙子》确有其无可否认的自身价值,存在不少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良药,或者是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那就是过犹不及的失当评价了。比如,前人就曾对《孙子》有过“包四种”之类的评价,将其视为有关古典兵学的百科全书。这评价,显然失之允当,存在很大问题。对于这些失当评价,今人多有盲从,故不容不辨。
一、兵家四种
所谓“兵家四种”,也称“兵四家”,是汉代人对先秦兵学流派的总结之辞。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末期到战国末世,连绵起伏的战争,给兵学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汉代初年,张良、韩信奉命整理前朝兵书,共得182 家。[1]到了汉成帝时,朝廷下令第二次整理兵书,所得之数已有萎缩。当时,任宏受命校理兵书,共得兵书63 家,1191 篇(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兵家为53 家,790 篇,进一步呈微缩之势。虽说各个时期统计数字不一,但都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兵学发展的繁荣境况。[2]
汉代人曾对先秦时期精彩纷呈的兵学著作进行过系统整理,并按各自特点归纳为“兵四家”,也即四个兵学流派,分别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据《汉书》,四家之特点分别如下: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志》)
上述“兵四家”中,“兵权谋”被列为首位,一般视其为“将帅之学”,约略相当于今日所言之战略学。当然,汉代所言“兵权谋”尚有“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的特点,那么它在汉代人眼中,实则为军事百科全书,因为其具备了无所不包的特点。“兵形势”似侧重于作战指挥,注重阵法的运用,讲究兵力的机动,主张使用精兵锐卒快速制敌。“兵阴阳”关注更多的则为天时、地利,这其中固然包含有自然科学知识,但同时也含有大量的阴阳五行思想和神鬼论,由此而具有“假鬼神而为助”的特点。这在今天看来,不免带有唯心的成分。人们经常批评我国古典兵学掺杂封建迷信,甚至“恒与术数相出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与“兵阴阳”大量充斥其中不无关系,古典兵学思想因此而沾染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内容——比如望气、遁甲等。这显然是因为兵阴阳理论的糟粕一面得以长期恶性发展的结果。“兵技巧”则非常注重士卒层面的实用之学,关注部队的军事训练、士兵的军事素质、装备的维护保养及战阵的布列操练等。
需要赘述一句的是,“兵四家”的分类,如果按照今日逻辑学标准,其实是存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四个并列的子类,前一个可以包含后面三个,这也许是因为分类标准不统一,也许是因为兵书林林总总,情况复杂,很难明晰地进行简单分类。
《汉书·艺文志》所列“兵权谋”共计13 家,259 篇,其中大多已失传。其中,“《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分列前两位,学术界一般认定为孙武和孙膑的兵法。今日所见兵书,无论是《孙子》十三篇或新出土的《孙膑兵法》,仅就篇目数来看,也存在很大的出入。另一本著名兵书《吴子》,人们也认为其著录于“兵权谋”。当然,《汉书》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有《列传》”,今本《吴子》实则只有六篇,篇目数同样存在很大的出入,历史上散佚太多。《公孙鞅》《范蠡》《大夫种》等其他兵书,《汉书》著录篇数不多,基本都已失传,详情已不可考。除这些兵书之外,班固注语中还提及一些:“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从班固的注语可以看出,他在采录《七略》时,于此处有不少改动。其中所提及的兵书,大多早已失传。《司马法》在历史上被公认为兵书,同样散佚严重,因为书中大量论及古军礼,故而被班固编入礼部。当然,由于散佚较多,这本兵书是否也能“包四种”,我们也无从知晓。至于《管子》等书,其中确有大量论兵内容,也在很长时间之内被视为兵书,似乎可当成“包四种”。
对照《汉书》中“兵权谋”的定义,除了需要探讨战略学这样的权谋之术外,尚需“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但今天可见诸书都大致与之吻合。无论是新出土的《孙膑兵法》,还是被班固所省减的《管子》《鹖冠子》等,其内容大多较为芜杂,有关古典兵学的各方面内容,在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论及。今本《吴子》《司马法》都存在较多残缺,仅从现存部分篇目来看,似乎也已具备“兵权谋”之特征。
“兵权谋”既然被列为四家之首,想必其地位最高。从今天所见兵书来看,这些书确实应该代表了当时兵学研究的最高水准。至于《孙子》,传统视为《吴孙子》,被列为兵权谋之首,地位自然更高(不过,在笔者看来,《孙子》和《吴孙子》很可能不是一本书,前面在讨论著录问题时已有讨论)。在历史上,人们早已习惯了堆在《孙子》身上的各种好评,并且从来都不惜溢美之词。其中评价最高的莫过于宋人郑友贤和明人茅元仪。茅元仪曾评价《孙子》“前后不遗”[3],给予充分肯定。宋代郑友贤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中,他曾将《孙子》与群经之首的《周易》进行了对比,并对《孙子》作出如下评价:
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以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
这段话中,郑友贤将《孙子》誉为“包四种,笼百家”的军事著作,显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郑氏所谓“百家”,显然系泛指,到底指哪百家,我们也不得而知。此语无外乎是对《孙子》兵学思想的广袤深邃所给予的一种赞美之词。郑友贤所谓“四种”,当为《汉书·艺文志》所云“兵四家”:“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在郑友贤看来,别的兵书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孙子》十三篇都有。《孙子》在他眼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高大全”的形象,所以才会有“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的效果,甚至是“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
二、不实之辞
在笔者看来,对《孙子》做出“包四种”这类评价,并不恰当,完全是一种夸大之辞。这可能应由一场误会产生,即来自《孙子》著录的一场误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误以为《孙子》即《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其实这两本书书名就有很大不同,篇目数更是相差太多,二者也许没有关系。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包含“《孙子》十三篇”。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了八十二篇的《孙子兵法》或《吴孙子兵法》,只留下十三篇的《孙子》,他们相信是因为曹操的删减之功。其实,这其中疑问更大。在笔者看来,传本《孙子》应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为“《孙子》十六篇”[4]。由于八十二篇的《吴孙子兵法》久已亡佚,我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从该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兵权谋”之首的情况来看,《吴孙子兵法》当符合“兵权谋”所谓“包四种”之定义。换句话说,《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可以“包四种”,而非《孙子》十三篇。
李零认可《吴孙子兵法》为《孙子》十三篇之前身,故此他曾判断:“汉代《吴孙子兵法》除十三篇之外还有许多杂篇,他们在内容上除权谋、形势家言,也包括阴阳、技巧家言。”[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零认为《孙子》只有在加上了十三篇之外的许多杂篇之后,才可能看到兵阴阳和兵技巧这些内容,这才能符合“包四种”。也就是说,今本十三篇并不能“包四种”。
其次,《孙子》“包四种”之评价,多少也和对《孙子》的盲目崇拜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寻找《孙子》,所以就很自然地找到了《吴孙子兵法》。由《汉书》分类可知,在“兵四家”中,“兵权谋”地位最高。《孙子》既然是影响深远的一部兵学经典,那就理所当然地占据这个最高之位。在他们的心目中,《孙子》代表了古代兵学的最高成就,是无所不能之利器,也是无所不包之圣典。因此它既具备“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特点,同时也可“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
通观《孙子》可以发现,其中确实高度强调“上下同欲”对战争的影响力,同时格外关注军事战略问题,非常重视战前的战略分析和情报预测,也对以“诡道”为中心的战争之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总结。如果按照《汉书·艺文志》有关定义,诸如“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等特征,都可以和“兵权谋”求得吻合。我们也可以认可《孙子》具备“兼形势”的特征,因为仅从十三篇的篇题,就可以看到《形》和《势》,故书中应当包含“形势”这方面内容。至于兵形势“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等特点,我们也可以在十三篇中寻常看到。孙子对虚实和奇正为核心内容的战争变术进行了深入探讨,也积极主张“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军争篇》)等用兵方略,非常好地体现了兵形势中“变化无常”这一特征。
问题就在于《孙子》是否同时“包阴阳,用技巧”。在笔者看来,孙子的兵学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这两方面内容。
古代“兵阴阳”理论虽不能全盘否定,但其最大特点就是“假鬼神以为助”,所构建的“神鬼论”中充斥着不少封建迷信思想。冯友兰称其为“有关古代军事中的迷信禁忌”[6]。我国古代兵书之所以“恒与术数相出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与古代军事家一直非常重视“兵阴阳”理论有着直接联系。兵阴阳的过度泛滥,导致有些将领即便明知阴阳术数为迷信,也建议不可偏废。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中一个颇为有趣的话题。类似主张,我们在《投笔肤谈》《草庐经略》等兵书中都可以看到。这从以下一段对话也可见一斑: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名将不法,闻者拘之,废亦宜然。”
靖曰:“……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不管孙子是否知道这种“反其道而用之”的策略,十三篇兵法始终与“假鬼神以为助”的兵阴阳严格划清界限。孙子不仅不谈兵阴阳,而且坚决反对军事将领被“鬼神论”所误。在《九地篇》中,孙子主张“禁祥去疑”。这里的“祥”,是阴阳家术语:“古者吉凶之兆皆谓之祥。”[7]《汉书·五行志》曰:“妖孽自外来者谓之祥。”故“禁祥去疑”的精神实质,就是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鬼神论。对于“禁祥去疑”,明人郑二阳有很好的诠释:“惟患军中或有妄托鬼神怪梦占卜之术,倡为妖异之言,以煽惑惊动人心耳。”[8]由此可知,“禁祥去疑”充分体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兵阴阳的精神。孙子担心那些荒诞不经的神鬼思想动摇军心,进而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用间篇》中的一段文字,同样是孙子反对鬼神论和兵阴阳的明证。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上述这段话是讨论情报和用间时提出的,充分体现了孙子的认识论。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它是完全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9]孙子认为,要想在战争中获胜,就一定要很好地掌握敌情,即做到“先知”;如果想做到“先知”,就需要“必取于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可简单总结为“三不可”,对于古典兵学而言可谓意义深远。在孙子眼中,情报和决策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不能依靠求鬼问神,也不能依靠简单类推得出结论,也不可只看到事物表面,只凭主观臆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的目标。在这段话中,作者与“假鬼神以为助”的兵阴阳理论旗帜鲜明地彻底划清了界限,为的是告诫将帅“力辟奇门遁甲、孤虚旺相、风云占验之种种谬妄”[10]。
《孙子》不谈兵阴阳,已成为众多研究专家的共识,但历史上仍然有李筌这样热衷于遁甲术的注解,试图在注《孙子》时添加兵阴阳色彩。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李筌)以魏武所见多误,约历代史,以遁甲注成三卷。”[11]李筌不仅陷入兵阴阳之中不能自拔,反倒还认为曹操所见多误,以奇门遁甲术注《孙子》。当然,李筌并非始作俑者。考察银雀山出土简文《黄帝伐赤帝》便可知道,早在阴阳五行思想极度泛滥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人试图将《孙子》与兵阴阳建立起联系。此风长期绵延,历朝历代都有,四库存目的《孙子汇考》大概可算作是此类作品的一个极致。只是这类书籍大多已化作桃花流水,我们今天已不容易看到。这一方面说明兵阴阳在岁月的长河中经不起时光的检验,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孙子之伟大。
至于《孙子》十三篇中有无兵技巧,这也很容易看出。与兵阴阳一样,兵技巧也是古代兵书中亡佚数量很多的一类。前者可能是因为其荒诞不经,后者则可能与“古今异宜”有关。吕思勉说:“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古今异宜,故不传于后;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几无今古之异。”[12]孙子重视谋略胜人,对于作战器械的研究似乎缺乏热情,其注意力和研究重心均偏重于谋略,《孙子》由此而成为“坐而论道”之作。十三篇中,固然提及若干兵器名称,却没有花什么篇幅来探讨“兵技巧”,缺少有关“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的内容。所以,如果说十三篇“用技巧”,显然也说不通。
总之,在笔者看来,把《孙子》当成“包四种”的军事百科全书,其实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首先可能是来自著录,其次则可能源于我们对该书研究不够深入,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习惯于“求全”,故而才会将“包四种”作为一种赞美之词用来夸赞《孙子》。但是,《孙子》只是一部坐而论道式的军事谋略学著作,它不可能对军事领域各方面问题都有涉及,对有关战争的所有论题都展开讨论。平心而论,如果《孙子》是一部无所不包的军事百科全书,那么其影响力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久远,这正是孙子所批评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孙子·虚实篇》)。其实,当我们把荒诞不经的“兵阴阳”理论与《孙子》攀上亲戚关系后,显然更像是抹黑,而非赞美。
三、兵家四种何处寻
“包四种”的赞誉,系《孙子》无法承受之重,但并不影响“兵阴阳”和“兵技巧”在先秦时期的流传和发展。通观先秦时期的论兵之作,《管子》《六韬》《孙膑兵法》等,都堪称“包四种”的代表作品,思想相对庞杂。如果与这些论兵之作进行对比,则更能看出《孙子》之纯粹。
《管子》托名管仲而成书,其成书年代,学术界现基本确定为战国时代。[13]1972年,《管子》部分篇章连同其他兵书一起,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这充分证明《管子》曾长期被视为兵书的史实,也与《汉书·艺文志》关于“兵权谋”的注语形成验证。
《管子》书中确有大量论兵篇章。关于作战境界,《管子》追求“至善不战”,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相仿佛。《管子》奉行实力至上原则,一直图谋“兵强”“国富”,与孙子不无契合之处。《管子》倡导“有义胜无义”,主张通过互赢来实现“义于名而利于实”的战略目的,这种争利思想与《孙子》的利益原则不无关联。与此同时,该书也富含“计必先定”(《管子·七法》)、“量力而知攻”(《管子·霸言》)、“释实而攻虚”(《管子·霸言》)等战略战术思想,也可与《孙子》呼应。《管子》书中富含“兵技巧”的论述,非常重视武器装备建设,强调“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管子·参患》)。这与《孙子》明显有别。此外,《管子》书中有不少“兵阴阳”和“兵技巧”的内容,也与《孙子》有别。《幼官》《幼官图》《五行》《四时》等篇早已被公认为阴阳家理论,其中不少论兵内容,但同样充斥阴阳五行思想。尤其是《幼官》和《幼官图》等篇,作者将治军和作战等与五方附图及五行思想等结合起来。总之,《管子》论兵篇章,对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都有较为深入的讨论,所以《七略》将其列入“兵权谋”并不意外。
《墨子》同样富含论兵内容,《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对其只字不提,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在先秦诸子中,儒、墨并称“显学”,可知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一度与孔子相差无多。
对于战争,墨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张。墨子学派所研究的大量的防御之法,深入探讨了“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墨子·备城门》)等方略。尤其是《备城门》《备梯》《备蛾傅》《备水》《备突》等篇所论守御之法,与其“非攻”的战争观及“兼爱”的政治主张等保持一致,也极大地丰富了古代防御作战理论。这一点,恰与推崇进攻的《孙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俞樾所言:“(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墨子间诂·序》)此外,在军事技术,尤其是守备器械上,墨子学派也有大量论述。这些是《墨子》对于“兵技巧”一派的贡献。《墨子》的鬼神思想也值得关注。《天志》《明鬼》等篇公然鼓吹天命思想,认为天会考察人类行为,并给予相应的赏罚,甚至认为战争行为也会受到“天志”的影响,鬼神因素更为重要,以至于说:“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墨子·明鬼》)此外,该书大量论及攻防理论。所以,《墨子》书中的论兵之章,未尝不可列入兵权谋。
通观先秦兵书,《六韬》也堪称符合“兵权谋”的代表。从该书文体及书中表现的儒、法、道杂糅等现象,明显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学术兼容的特征。此外,《六韬》书中还大量论及骑兵战术,包括书中透露的诸如“百万之众”( 《六韬·豹韬·教战》)等信息,都可以大致判断其著作年代为战国晚期。[14]
根据班固注语,兵权谋中曾省减“《太公》”编入“道家”,疑为今传《六韬》。今本《六韬》是一部系统探讨军事问题的兵学著作,儒家、道家、法家等重要学派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述及。《六韬》主张通过积极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等手段,来实现“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六韬·武韬·发启》)的全胜,忠实继承了孙子的“全胜”战略。书中还探讨了遭遇战、运动战、袭击战、突围战等多种战法,阐述了四武冲阵、鸟云之阵等多种作战阵形,对部队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宿营和作战的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对步兵、骑兵、车兵等各兵种的作战方式进行了讨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六韬》对于如何反败为胜进行了很多论述,探讨了在兵力处于劣势或军队处于困境的情况下,防止军队溃败和败中求胜的方法。这是对古代战争理论的重要补充,也为《孙子》等其他兵书所不及。在《军用》等篇,还有关于兵器的探讨,《阴符》《阴书》中则对如何秘密传递情报提供了方案。这些对古代“兵技巧”的发展不无助益。《六韬》的缺陷也非常明显,书中流露出浓厚的“兵阴阳”色彩,比如《龙韬·五音》《龙韬·兵征》中的“观云”“望气”理论,这无疑极大降低了该书的理论水准。由于《六韬》对“兵四种”都有论及,故而有学者指出,对比《孙子》,《武经七书》中最符合兵权谋定义的,“不是《孙子兵法》,而是六韬”[15]。从某种程度上看,《六韬》确为兵权谋著作的杰出代表。
《汉书·艺文志》在兵权谋中著录有《齐孙子》,学界一般认为是《孙膑兵法》。此书大概在汉代末年失传,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其军事学术价值重新为人们所知晓。
竹简记述了孙膑与齐威王的对话,孙膑陈述了“乐兵者亡”的道理。强调“富国”( 《孙膑兵法·强兵》),则展示了孙膑高远的大战略思想。通过与齐威王、田忌的对话,孙膑阐明了“必攻不守”“料敌计险”(《孙膑兵法·威王问》)等战术原则;同时通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阐明的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思想,明显是对孙子的继承。《孙膑兵法》的缺点,也是对兵阴阳理论有大量纠缠。在《月战》篇,作者突出强调了人对于战争的重要作用,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但同时也认为战争与日月星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孙子》相似,《孙膑兵法》也充分重视地形的作用,但也与阴阳五行理论简单比附,“兵阴阳”理论由此掺入较多。此外,《五教法》讨论了治军之法和训练之法,如“教耳”“教足”等内容,比较符合“兵技巧”所谓“习手足”的范畴。既然如此,《孙膑兵法》显然也可被视为“包四种”之代表。
先秦时期还有一部著名兵书《尉缭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列杂家,同时也注明“入兵法”。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成于战国的说法可信。这部兵书思想非常驳杂,将其归于“杂家”也属正常。该书有不少内容与法家较为接近,体现出法家对兵家的渗透与影响。与此同时,书中也保存了大量战国军事制度的原始资料,显得弥足珍贵。除此之外,诸如“挟义而战”( 《尉缭子·攻权》)的战争观,“权敌审将”( 《尉缭子·攻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以及“明法审令”( 《尉缭子·战威》)的治军思想等,也都别具特色。《尉缭子》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作者尤其反对当时流行的“兵阴阳”理论,明确指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尉缭子·天官》)这种唯物精神与《孙子》非常接近。由此可知,《尉缭子》并不符合“包四种”的特征,没被列入“兵权谋”倒也情有可原。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兵权谋还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一般认为《吴起》即《吴子》,又称《吴起兵法》《吴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吴子》一书有不少内容佚失,今本仅为六篇,与《汉书》著录存有很大差距。世人论兵,往往并称“孙、吴”,其实二书存有不少差异。比如《吴子》对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是“争名、夺利”或内乱、积贫等引发大大小小的冲突。[16]这类挖掘战争爆发原因的讨论,《孙子》不曾提及。《吴子》同时认为“强国之君,必料其民”( 《吴子·图国》),因此格外注重对周边国家战略环境、民心向背包括军队作战特点等进行对比分析。作者总结了发起进攻的各种时机[17],强调“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吴子·料敌》),探讨了各种战术方法。这些出色的作战指导思想,与《孙子》互相映照。此外,作者对于将帅的地位和作用等,辟有专篇深入探讨,重视程度超过《孙子》。当然,由于缺失篇什太多,我们无法判断《汉书》著录的“《吴起》四十八篇”是否还有专论“兵阴阳”和“兵技巧”的篇章。
不谈“兵阴阳”和“兵技巧”,无法“包四种”,并不妨碍《吴子》作为一部和《孙子》齐名的著名兵书而长久流传,就像不能“包四种”也无法妨碍《孙子》作为兵学经典供人长久膜拜一样。《孙子》如果是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一定会影响到全书的思想水准,由此而沦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虚实篇》)之类的平庸之作。《孙子》正是因为对以“诡道”为中心的战略战术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才能就此奠定其在兵学史上的不朽地位。而这也是先秦乃至历史长河中其他兵书所无法企及的。通过对比先秦其他兵书,更能清楚看出这层道理。
【注释】
[1]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9 页。
[2]《汉书·艺文志》著录兵家53 家,对于少出之10 家,班固曾出注说明。如果考虑到秦火等因素,汉人所得到数字,即便取其最大值,也一定还有不少遗漏。
[3]茅元仪曾对《孙子》作过如下评价:“先秦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 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在这一段话中,茅元仪将包括《司马法》《六韬》在内的其他五种先秦兵书,都当成《孙子》的注疏文字,早于《孙子》的,《孙子》充分进行了吸收,晚于《孙子》的,则都是照着《孙子》来的。这种评价无疑比前面所述郑友贤的评价还要高,同样给了《孙子》一个非常“高大全”的形象。当然,茅元仪的这些评语是就先秦兵六家说的,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有意思的是,不少人干脆掐头去尾,只记下茅元仪中间的这段话“前《孙子》者,《孙子》不遗, 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从而将《孙子》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的地位,一举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
[4]有关论题,本书第四章已有若干讨论。
[5]李零:《吴孙子发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5 页。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 页。
[7]陆懋德:《孙子兵法集释·九地篇》,民国四年商务印书馆刊本。
[8]郑二阳:《孙子明解·九地篇》,明崇祯辛未刊本。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 页。
[10]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用间篇》,民国四年房西民抄本。
[11]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 页。
[1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85年版,第133 页。
[13]在历史上,《管子》学派属性并不确定,要么被归为法家,要么归被为道家,也有少数学者曾将《管子》列为杂家。
[14]张烈:《〈六韬〉的成书及内容》,《历史研究》1981年第3 期。
[15]高润浩:《〈六韬〉对中国传统兵学的贡献——对〈 六韬〉 历史地位的再评价》,《滨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5 期。
[16]《吴子·图国》: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17]《吴子》总结为十三种: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