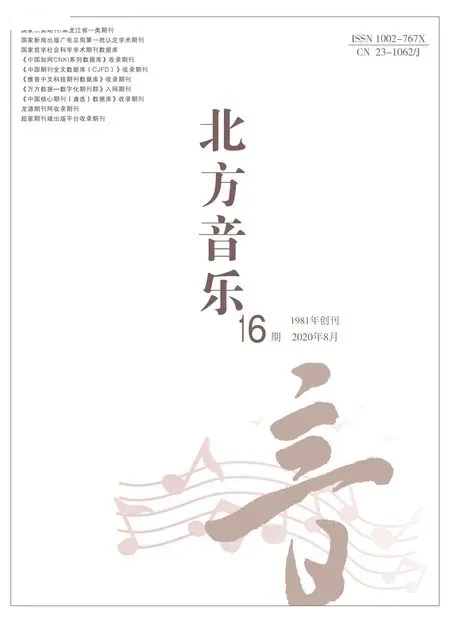阿坝州羌族情歌相关研究
李晓梅
(阿坝职业学院,四川 阿坝州 623200)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已发掘的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着羌人的记载,羌族历史为我国民族史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老的阿坝州羌族情歌是伴随阿坝州羌族婚姻制度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经当地羌民世代传唱与传承,受到了羌族青年男女的热烈追捧,常用于谈情说爱、休闲娱乐,这也反映了阿坝州羌族对爱情生活的美好追求,为羌族情歌注入了灵魂。
一、阿坝州羌族情歌形成的主要原因
情歌在人类音乐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里就能找到很多风情连绵的情歌,《乐府诗集》中也有不少流传至今的爱情诗 ,如《孔雀东南飞》《罗敷》 等,均反映了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爱情观和生活观。情歌的形成正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民风民俗、审美意识等。阿坝州羌族情歌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特殊的地理环境
地形地貌、水流、山川和气候等自然条件无不影响着当地政治、经济和诸多文化内容的发展。放眼古时羌族的发展,主要有四个核心地区,即羌塘、昌都东北的察宁多盐泉、通天河区的哈姜盐湖及柴达木至若尔盖之间的察卡盐湖区域。由于游牧生活的长期影响,其社会文化停滞不前,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许多羌族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逐步开始向南迁徙,寻求新的居住地,从此演化为在西南地区生活的一支少数民族。羌族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地势偏狭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四川省西北高原上东南部地区岷江上游地带的高山狭谷之处,此处地形十分险峻,山峰起伏坡度极大,生活在该地区的羌族人与外界沟通十分不便,因此对民族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久而久之,使羌族形成了特有的封闭型社会文化机构,同时,因为长期生活与此处,受生活不便的影响,造就了羌族人民坚韧不拔的个性,环境对民族的影响使该民族地区的许多音乐保持了原始风貌。
(二)独特的民族语言
人类用于交流情感、传递文化思想的工具有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工具是人类的语言。民族音乐与其本身所具有的语言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联系。羌族语言不仅仅用于本民族的沟通和日常记录交流,而且展现出了本族人的思想文化。该语言属于汉藏语系中的下属藏缅语族羌语支,主要还有南方和北方两大方言,同时,该语言还受到生活区域与之相连的藏族、回族和汉族语言风格的影响,在多种因素综合之下使该民族的语言在声调韵律上充满了变化,语言和音乐开始相融时,语言本身原有的语音、语义、词格、韵律等多个要素都会因原有的语言动态,对音乐的表现产生或深或浅的影响。就本质上而言,语言对于本民族情歌的产生、发展,直至形成一定形态的特殊艺术风格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语言的形态也影响了本民族特有的情歌在音乐具体形态上表现出的旋法、音律等。
(三)特有的民俗文化
从古至今,羌族被大众认为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该民族天然的活泼、坚韧的个性以及本民族朴实的文化传统都是先辈们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羌族人天生爱歌唱,常常用歌唱来记录生活和文化,歌声中记载了羌族人民的历史,他们也用这种方式将本民族的文化传播给后代。除了记录生活文化,羌族人在辛勤劳作之时,经常用音乐抒发自己对自然的感叹,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他们常常热爱饮酒,一边饮酒,一边唱歌舞蹈,通过这些方式来娱乐生活,借酒助兴。只要进入羌寨的区域,马上可以发现羌族的歌声无处不在,人们用欢歌笑语来表现对生活的感恩与快乐。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在一代又一代的羌族生活中不断地传承和发展。正因为其天然的民族本性以及对音乐发自肺腑的热爱,为羌族产生本民族特有的情歌,并推动其发展、流传及后续演变奠定了十分厚重的文化生活环境。
此外,羌族没有自成一派的文字体系,所有的民间故事、传说、历史及民族艺术都是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一代传一代。羌族情歌绝大多数的内容多为男女恋爱感受,而且这些情歌大都是即兴发出,表现的文化细节与本民族民俗特点紧密相关。所以,羌族情歌可以代代流传,很大程度上为保留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艺术提供了传承的工具。
二、阿坝州羌族情歌的音乐形态特征
基于歌曲题材的分类,阿坝州羌族情歌可分为情窦歌、夸赞歌、试情歌、定情歌、相爱歌、盟誓歌、相思歌、丢情歌、挖苦歌、应变歌、劝郎歌、抗争歌、怪山歌等,基于表演形式分类,包括独唱、对唱、齐唱。调式主要采用徵调式、羽调式和商调式。
(一)调式特征
传统民族调式主要是宫、商、角、徵、羽,但就笔者研究阿坝州羌族的情歌中,以徵调式、羽调式和商调式为主。在笔者所研究的四十余首羌族情歌中,大部分采用五声调式, 较少出现六声或七声调式。徵调式占总谱例的49.7%,其次是商调式和羽调式,分别占总谱例的32.4%和17.9%。可见,在阿坝州羌族情歌中使用最频繁的是徵调式,因徵调式色彩比较明亮,多用于表现活泼、明快、调侃等情绪,十分符合羌族人民乐天知命、积极生活的人生观。商调式则具有混合色彩,次之,而羽调式色彩比较暗淡,多用于表现温柔、哀怨、凄婉等情绪,用得较少,宫调式更是极少使用。
(二)曲式结构
通过研究收集、整理的四十多首阿坝州羌族情歌发现,这类情歌在曲式结构上多为短小精简的结构,主要包括几种类型:首先,这类情歌中最常见的是两句体结构,这种结构展现出的情歌可以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表现出呼应的功能,整体结构上保持一上一下的平衡状态,并能一一对应,而且情歌表现出来的状态通常是一动一静相结合的稳定结构。这种结构通常包括两种,分别是对称式和对比式:aa1/、ab。上句通常采用调式主音外的音作结尾,与之相对的下一句则以调式主音作为结尾。第二,还有一种常见的乐段是三句体结构。因为比前者多出来一句,因此就打破了完美的对称性结构,在旋律发展变化上有了更多创新,可以展现出情意连绵的状态。第三,还有一种常见的四句体结构。因为句子又多了一个,在表现的内容方面要远远大于第一种,其旋律与表现力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态。第四,还有一种则是五句体结构的乐段,这种形式出现得较少。
(三)旋律特征
羌族情歌的旋律形态十分丰富、优美,既透露出韵律之美,又包含着空间和时间,其特点主要集中于两个因素:(1)旋律进行上,大多数采用级进上下行和三度、四度小跳相结合的形式。部分羌族情歌偶尔出现五度或六度以上的大跳;(2)旋律线较为多样,既有抛物形式又有波浪式的曲折形式,还有两者相结合的形式。
在羌族情歌中,五律、七律出现较多。如《郎想妹来妹想郎》中的歌词:“郎想妹来妹想郎,把人想得面皮黄;白果开花难相见,污水烧水不得尝。六月里来三伏天,小哥要上贝母山,没得撒子相送的,苦荞馍馍兰花烟。”此情歌的歌词完全依据七律的格式创编,虽在第七句未押韵,但不影响整体性,却将情歌的生活化和口语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四)节奏节拍特征
阿坝州羌族情歌的节奏欢快、灵活多变,多以混合拍子为主,可根据演唱者的演唱风格进行自由调整,其特点包括:首先,从基本节奏形态来看,羌族情歌以非均分的节奏为主,以前短后长XX·、XXX、XX·、XX-和前长后短 X·X、X XX 、X·X 、X- X的节奏型最典型。
其次,就形态和结构而言,前短后长的节奏型与前长后短的节奏型差异不小,但也有不少相似点:(1)两种节奏型均与羌语的语音节奏韵律习惯极其吻合,与自然润腔相贴近;(2)附点音出现是为了强调和拉长强音时值;(3)两种节奏型均属于羌族情歌音调中最典型的节奏型,其在羌族酒歌旋律的发展中互相依赖,对音调特色的形成十分关键。此外,就节奏的使用而言,基本呈现出节奏密字也密、节奏疏字也疏的特点。
(五)歌词特征
羌族情歌主要表现的是本民族的生活状况,其表现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所用词汇极其简洁,在这种简洁的词句中展现出确实扣人心扉的情感。通常,情歌以“纳吉纳那,纳由西,尤西惹那,惹那杂沙”这几句作为总起头的句子,唱完了才开始讲述其他内容。他们认为,“纳吉纳那的歌必须唱出来,如果不唱这些等于遗忘了本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正因为他们长久以来固守自己的观念,其特有的民歌才能流传和保存得这么完善。
如阿坝州茂县白溪乡的《奇布小妹》,歌词为:“纳吉纳拉(哟),拉玛由西啦(呃哟),由西日阿拉(哟),日阿拉鸟珠丝(哟)。”此句歌词可分成两句:第一句是通常的纳吉纳拉起始,然后从尤西惹那提正文,歌曲的音律极其多情、婉转,无不印证了羌族情歌那条不成文的规定。情歌中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唱出现古代文学中才有的对仗等修辞,如天—地、蓝天—白云、花—树、山—水、红花—绿叶等。
三、结语
羌族情歌具有多样性、民族性、诗歌性、口头化等特点,阿坝州情歌的特殊体裁与众不同,其情感包含内容甚广,常能以情感人,文化及特有的音乐价值十分厚重。羌族人民不仅用歌声表达爱情,用歌声歌唱自然,歌颂生活,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研究羌族情歌,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羌族文化,对推动羌族情歌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