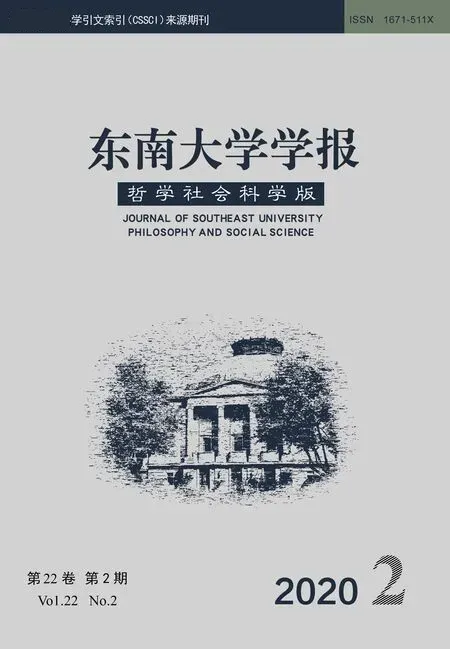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
高广旭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6)
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容涵正义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学界要么主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理解正义,要么主张基于正义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形成了“容涵”与“不容涵”两种观点争执不下的局面。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的焦点课题,不仅在于学界关于马克思正义观的探讨大都以对该问题的解答为基础,更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探讨正义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蕴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批判,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真实彰显。鉴于此,本文提出,重新理解和深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必须跳出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相互阐释的研究路径,而以超越性的视域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深入阐释马克思正义观的规范性,澄清马克思正义观革命的理论内涵,将为破解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容涵正义的谜题开辟新的思考空间。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重释
历史唯物主义能否容涵正义是深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正义观的基础性问题。近年来,学界在有针对性地反思和批判英美马克思主义关于该问题理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揭示,是一种价值无涉的“实证科学”。而正义是一种与事实无涉的价值规范。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互不否定”“互不相干”(1)段忠桥:《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哲学研究》2015年第7期。。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对“事物”进行直接总结和概括的“自然科学”,而是关于经由人的实践活动对事物加以改造的“现实”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涵盖包括正义在内的价值判断。(2)马拥军:《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证”性质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不难看出,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的“实证科学”,那么其科学性就表现在是一种价值无涉的理论,自然与正义是不能相互容涵的。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是蕴含人的主观目的的“历史科学”,那么其科学性就不仅关涉事实,而且关涉价值,进而也就能够容涵正义理念。可见,破解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关系谜题的关键在于明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
一般认为,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实证科学”代替了“独立的哲学”,而“真正的实证科学”也就是恩格斯所强调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体现在以“历史科学”取代了“历史哲学”,从而完成了历史观的伟大变革。这种理解固然不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科学”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是否蕴含着对事物的价值评价,或者说,在这种科学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否相互容涵?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学界存在争议,进而也成为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关键。
马克思指出,思辨的历史哲学终结后,“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概括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6页。显然,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取代历史哲学的是只知道抽象地概括历史事实的实证主义历史科学,这种实证主义历史科学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比历史哲学高明,因为它与历史哲学共同的理论困难在于,没有真正触及“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而排除这一理论困难的前提,马克思认为,“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②
因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我们既不能单纯从哲学的思辨角度加以理解,也不能单纯从科学的实证角度加以理解。因为二者都缺乏对“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实际上,站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高度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科学”,也就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新哲学”。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既拒斥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也拒斥唯心主义的抽象思辨的思维方式,而是将科学的事实性与哲学的价值性统一起来的总体性思维方式。这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作为“真正的知识”的真实意义所在,也才是为什么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科学”的真实理由所在。
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总体性思维方式对“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这种研究所指向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构筑的社会关系。因此,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需要回到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本质的批判中指出,由于蒲鲁东把经济范畴看作是脱离具体生产关系的“无人身理性的自我运动”,所以他把现实的生产关系只看作是抽象的经济原理和经济范畴。实际上,“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在《资本论》的商品形式分析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这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经济规律的描述,而是对政治经济学范畴蕴含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批判。尽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批判的靶子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过程,但是其关注的实质却是这些经济范畴和生产过程背后所隐藏着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
因此,只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我们才能看清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把握到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基础。这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品格的现实彰显,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真实诠释。
如果说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正义关系问题的前提是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那么澄清这一前提的关键在于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关于一般性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更是以商品、货币、价值和资本等经济范畴反思“人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通过对经济范畴背后所隐含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剖析,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限度的总体性批判。
这种总体性批判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性把握,所把握到的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事实之真,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的固有矛盾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超越的本质之真。本质之真,就是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道义谴责内化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性本质的揭示。正是在这种本质之真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何以实现了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真理性考察,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而非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重新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
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既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也不是毫无相干的隔绝关系。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的揭示,推动正义从抽象的价值观念沉降为具体的社会规范。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正义的考察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正义的形而上学基础和人性论前提,而是把对正义的考察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结合起来。通过这种结合,我们看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变革,正义实际上是由它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变革所决定,尤其是由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决定。
由此可见,只有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历史唯物主义之于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意义才能充分彰显出来。因为马克思的正义理解正是通过揭示和批判资产阶级正义观念诞生的物质生活基础,把正义这一古老的价值追求重新拉回到物质生活世界,正义成为内在于物质生产方式中的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总体性观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赋予正义新的内涵,而且为我们重新理解正义的规范性开辟了新的思想道路。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正义规范性的重构
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域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资本为媒介的财富增殖的“事实性”逻辑,正义是财富分配过程中所遵循的“得其所应得”的“价值性”逻辑。正义的规范性只在分配领域有效,在生产领域无效。换言之,在实证主义看来,正义规范性只能在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价值层面展开,而不能在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事实层面展开。
正是囿于上述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论原则,西方学界对于马克思正义观规范性的理解通常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马克思的正义理解只具有描述性而不具有规范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建立在规范性基础上,在讨论马克思正义观的过程中应当避免“规范性标准”的思维套路(7)艾伦·伍德:《马克思反对从正义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对段忠桥教授的回应》,李义天译,《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另一种观点强调马克思探讨的分配正义是以无产阶级利益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评价主要是在道德上进行的,作为一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没有做到按劳分配(8)李惠斌、李义天:《马克思与正义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6页。。结果,马克思正义观的规范性要么被消解,要么变成与事实无关的道德规范。深入阐释马克思对正义规范性的重构,必须超越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方法论桎梏,重新理解马克思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
纵观西方正义观念的形态演变,正义的规范性经历了从德性规范向法权规范的转变。在古代希腊,正义是“四德”(正义、节制、勇敢、智慧)之首,其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德性规范。自启蒙以来,个体权利取代公共善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正义的规范性也随之从德性规范转变为法权规范。正义的法权规范旨在维护个体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判断政治制度是否正义的标准在于政治制度是保护还是损害人的权利。在霍布斯和洛克开创的契约论政治传统中,正义总是在关涉个人财产权是否得到维护的语境下被谈及,“得其所应得”的基本价值预设,准确概括了现代政治哲学所树立的正义的法权规范作用。当我们以正义为尺度去判断一种制度和一种行为时,也就是在以法权为标尺对该制度和行为做出相应的价值评判。凡是与法权标尺相符合即为正义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
正义规范性的古今之变表明,分配正义取代德性正义成为现代正义观念的基本议题。进而,当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中探讨正义的规范性时,就需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因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更是对包括分配正义和法权正义在内的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总体性批判,这种总体性批判构成我们透视马克思重构正义规范性的切入点。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这种方法既没有停留于对象的直接性,只把握对象的整体的混沌的表象,也没有对对象加以间接的抽象,形成关于对象的观念集合,而是在对象所处的历史总体中把握对象的内在结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关系,这就是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和叙述方法的思辨性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统一就蕴含在《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中。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的根本区别所在。不同于实证主义将经济事实与道德价值对立起来加以理解,唯物辩证法对于事物的把握既不是客观的事实呈现,也不是抽象的概念思辨,而是在对事物具体总体的考察中把握事物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
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在直接性上对于正义的理解具有批判意义,即批判资产阶级正义观念所内蕴的财富分配层面的法权应得和意识说教层面的道德应当;但是在间接性上也具有建构意义,这就是,透过唯物辩证法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方法论原则的超越,揭示资产阶级正义观脱离资本生产的事实基础而变成抽象形式的同时,为建构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正义规范开创了新的思想进路。
理解这种建构意义需要结合黑格尔以总体性辩证法对法权正义的批判。在黑格尔看来,当生命由于财产权而遭到威胁时,财产权的狭隘性就突显出来,对生命的尊重应当高于对财产权的尊重。换言之,对人的自由的理解不能仅仅奠基于财产权,而应奠基于对于财产权的扬弃,通过这一扬弃,人的生命自由的整全性活动才得到总体性的确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总体性视角,黑格尔看到,法权规范只有通过对自身的否定才能达到具体的规范,而具体的规范实质是一个总体的辩证发展过程。因此,黑格尔认为,法权规范是停留于意志自由的抽象形式的外在规范,而内在规范是从实体性原则出发的历史性的和目的性的规范。
尽管黑格尔准确把握到现代性法权正义的自否定本质,但由于他把规范的内在性局限在伦理精神的自我运动这一抽象形态中,因此,他在消解市民社会法权规范的“权杖”的同时,把正义的规范性来源述诸作为伦理实体的民族国家。对此,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既然是法权正义问题出现的场域,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应当立足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进而,不同于黑格尔把正义的规范从抽象法权过渡到市民社会再过渡到民族国家,马克思牢牢立足市民社会本身的批判,把正义批判的论域落实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价值规范只有沉降在人的现实生产方式及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真正实现。
因此,马克思正义观的独特之处在于,把黑格尔对抽象法权及其正义观念的思辨批判,沉降到对于抽象法权及其正义观念所立足的物质生活基础的批判,从而把唯物辩证法的规范性具象化为对资本逻辑的总体批判中。正是基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差异及其规范性特征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把握到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更是这一事实所构筑的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社会现实总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内蕴的规范性不是抽象的价值规范,而是事实批判中蕴含着价值批判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规范。这种社会历史规范意味着,马克思始终是从社会生产及其创造的社会现实总体出发理解正义的规范作用,强调包括正义在内的价值规范所遵循的根本逻辑是社会现实的总体发展逻辑,这构成马克思正义观的规范性与现代资产阶级法权正义规范性的本质差别。
综上,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秉持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具体总体的辩证法是理解马克思正义观规范性的一把钥匙。只有从具体总体性的辩证视角出发,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何以容涵马克思正义观的规范性。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正义不是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抽象法权,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性的社会现实。作为社会现实的正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不是外在的形而上学规范,而是内在的辩证规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非正义性就蕴含在其正义性之中,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批判也不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外,而在对资本逻辑及其拜物教本质的揭示和批判之中。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揭示出的资本与正义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正义观规范性的理论特质。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的正义观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马克思拒绝脱离“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空谈正义,而是把对正义的理解诉诸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对正义规范性的重构表明,马克思所理解的正义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不仅具有批判性,而且具有建构性。在资本批判中实现正义批判,这体现了马克思正义观批判与建构辩证统一的独特思想进路。深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革命需要剖析资本与正义的关系。
剖析资本与正义的关系,首先涉及的是如何理解剩余价值与正义的关系,因为剩余价值最直接地突显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劳动力买卖关系所蕴含的正义问题,即劳动力的使用与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值,“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表面来看,这一论断不仅没有批判无偿占有的不正义,反而强调了这是“特别的幸运”和“不是不公平”。换言之,马克思似乎在强调剩余价值占有的正义性。然而,细加分析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交换情境是在货币与劳动力之间,而不是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
在前一种交换情境中,货币占有者购买劳动力的过程,只是货币与劳动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过程,这个交换所体现的仅仅是货币与劳动力商品之间的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在形式上确证了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平等,或者说公平的交换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剩余价值并不是发生在作为交换的货币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交换过程中,而是发生在资本对劳动力的具体使用即劳动生产过程中。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所购买的是劳动的交换价值即劳动力,交换过程发生在“流通领域”,后者所购买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能力,使用过程在“生产领域”。
正是由于这一差别,马克思接着指出:“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①那么,资本家“发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答案是,资本家早就看到了资本在生产领域剥削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这一不正义的机制总是在流通领域以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一商品交换机制的方式被掩盖起来,也就是以正义的方式干着不正义的勾当。所谓“特别的幸运”,正是马克思通过描述货币与劳动力的买卖关系,揭露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伪善性和非正义性。
如果说对剩余价值是否正义的剖析必须超越雇佣劳动作为商品的流通层面,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那么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生产方式语境中则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与正义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法权观念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这里,马克思明确强调不存在独立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绝对正义,正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总是与相应的生产方式相一致。既然正义总是与相应的生产方式相一致,那么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时候,与生产方式相一致的正义也必然发生变革。资产阶级正义观变革的动力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固有的矛盾,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
透过《资本论》关于资本与正义辩证关系的探讨,我们看到,对于马克思而言,正义问题的产生并不是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在流通领域,交换价值所塑造的自由平等符合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正义;在生产领域,交换价值的形式合理性必然随着资本控制下的交换价值的发展而瓦解,劳动以及劳动对象的资本化控制,最终将促使交换关系中的形式正义被生产关系中的实质不正义所瓦解。
资本批判视域中的正义批判体现了马克思理解正义的独特思路。透过这一思路,我们看到,在人类关于正义这一古老问题理解的意义上,尤其是在对比近代以来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观念的意义上,马克思实现了正义观的伟大变革。
在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财富分配的基本原则问题始终是正义理论研究的重心。分配的正义性究竟是基于平等原则还是自由原则,不仅成为现代政治哲学诞生之初关心的核心问题,而且构成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焦点问题。与之不同,马克思正义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决定了正义只有结合具体的生产方式正义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更是强调分配问题只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一个次要的衍生问题。“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由此,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现代性正义脱离具体社会现实的根本批判,而且实现了正义论域的根本转变,即从分配方式转向生产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以理解,马克思对正义的探讨为什么拒绝从交换价值和资本的流通层面展开,而总是将正义和具体劳动结合起来,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总体出发。因为对于马克思而言,是否正义并不是一个形式合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实质合理性问题。作为实质合理性问题,关键不在于如何定义正义,而在于如何实现正义。所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并没有直接借助正义原则,而是通过解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发展过程,揭示它与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耦合关系,从而从内部揭穿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伪善性。
在以资本逻辑所构建的交换价值体系为支撑的正义观念体系中,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等观念被看作是可以独立于经济基础的“永恒真理”。马克思对于交换价值的资本化发展逻辑的描述,深刻揭示了这一发展逻辑的内在矛盾。这就是,交换价值的资本化发展必然把劳动纳入到“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体系中,劳动成为交换价值,这既是资本产生的前提,更是资本发展的动力。结果,本来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的劳动,在资本面前其使用价值被剥离,只剩下抽象的交换价值。
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货币与商品的关系,货币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资本从不关注劳动的具体使用,只关注劳动的交换价值。因此,劳动资本化运作的生产方式及其构筑的经济关系,实质是一种以牺牲具体劳动特殊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化体系,而这恰恰为资产阶级正义的“永恒真理性”奠定物质基础。
与资本正义的资本本位不同,马克思既强调以劳动本位的生产方式瓦解资本本位的生产方式,从而颠覆资产阶级正义观的物质基础,同时在这一瓦解和颠覆的同时,构建了现代社会正义的合理形态,这就是劳动正义。劳动正义是以劳动为价值本位的正义形态。它并不抽象地强调对劳动以及劳动成果所有权的保障,而是关注社会制度及其所植根之上的生产方式对劳动具体的和总体的尊重。由于这种尊重内在超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价值原则,所以劳动正义的实现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体现了马克思推动政治哲学从“好制度”的理论追问转向“好生活”的现实追求的重大思想革命。
总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正义的规范性,为深入阐释马克思的正义观革命开辟新的思考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正义的物质生活基础的剖析,既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性的思想高度,也体现了马克思重构正义规范性的思想深度。马克思正义观所触及的社会现实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塑造的社会支配形式和社会统治体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对资本正当性中所蕴含的不正当性的内在批判,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瓦解资产阶级正义观念的合法性,从而实现了从分配方式到生产方式的正义论域革命,从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的正义形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