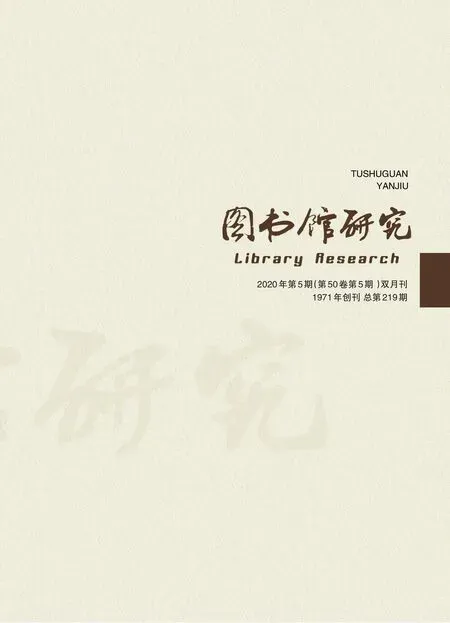民族地区高校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研究*
——以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为例
蔺继红,孔 彬,刘久帅
(1. 内蒙古农业大学图书馆,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2. 抚州市图书馆,江西 抚州 344000)
双语阅读推广人是阅读推广人的组成部分,双语阅读推广人既有阅读推广人的共性,又具有民族个性。在大数据背景下,少数民族的阅读载体、阅读内容和阅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移动阅读替代传统阅读,少数民族阅读文化受到了极大冲击。面对这一现象,文献调研显示,关于少数民族阅读推广模式和阅读推广人培育相关的研究极少,对于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方面的研究更是鲜少有学者涉足。
1 双语阅读推广人
2012 年颁布的《深圳市阅读推广人管理办法》规定: 阅读推广人是指市民个人或组织阅读机构,通过多种渠道、形式和载体向公众传播阅读理念、开展阅读指导、提升市民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业和业余人士[1]。中国图书馆学会也在2014年“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中对阅读推广人予以定义:阅读推广人是指具备一定资质,能够开展阅读指导、提升读者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专职或业余人员,包括各级各类图书馆和科研、教学、生产等相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及有志参与阅读推广事业的其他社会人员[2]。目前,在文献调研显示,没有双语阅读推广人和少数民族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定义,研究甚少,几乎是空白状态。
本文利用CNKI 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数据来源,选择高级检索,以“双语阅读”为检索词进行主题精确检索,检索时间到2019年12月31 日,以核心期刊为检索范围,共检索到11 条相关文献。有部分学者从发文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2年开始关注双语阅读,到2012年4篇,到目前为止双语阅读研究论文呈下降趋势。从检索主题分布呈现,论述英汉双语阅读方面的论文6篇,少数民族双语阅读相关研究的论文是3篇,有学者从民族学生阅读障碍角度出发,研究了阅读培育保障机制的建立。以“双语阅读推广”和“双语阅读推广人”为检索词进行主题精确检索,检索时间到2019年12月31日,没有检索到相关文献。文献表明有关双语阅读概念论述目前没有较规范的定义,结合相关文献中中国图书馆学会对“阅读推广人”的阐述,及多年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经验和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双语推广人既有阅读推广人的共性,又有其民族个性;双语阅读推广人是在阅读推广人定义基础上的补充,双语阅读推广人指的是具备一定阅读推广人的资质,能够用本民族语言、汉语或英语兼同且较流利地交流,为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双语阅读指导、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的蒙汉兼同专职人员或业余人员。以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为例,蒙古族是既有文字又有语言的民族,蒙古族阅读文化有别于中华民族的阅读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阅读文化[3]。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是我们研究的新课题,亦是填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阅读推广人培育的空白。
2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调查情况
2.1 调研对象与调研方法
为了使调研尽可能客观,全面反映真实状况,课题组以内蒙古地区五所高校(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内蒙农业大学)的蒙汉双语授课的蒙古族大学生以及这5 所高校的图书馆馆员为调查对象进行调研,他们分别来自畜牧兽医、草业科学、蒙医药、经济管理、蒙古学和法学等不同专业。调研方法主要包括:问卷调查法,当面访谈和电话访谈。问卷调研通过发放纸质问卷和投放网络问卷的形式结合进行;本次调研共发放纸质问卷100份,收回98份,电子问卷共收回208 份,共计有效问卷306份。访谈调研采用电话访谈与当面访谈相结合,访谈对象包括五所高校的蒙汉双语授课大学生,图书馆馆员,蒙古族老师以及少部分汉族老师。
2.2 调研数据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相结合,我们对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蒙汉双语阅读推广现状有较为深入了解。调研内容主要包括5个方面:调研对象的民族及年级、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现状、对图书馆的使用现状、对于图书馆服务的建议、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设置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下分别从这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2.2.1 调研对象的民族及年级
调研首先分析了蒙古族大学生的民族及年级情况。就民族而言,306人(97.72%)来自蒙古族,0(0%)人来自其他民族;就年级分布来看,大一学生有26 人(8.50%),大二学生有100 人(32.68%),大三学生有95 人(31.05%),大四学生有85 人(27.78%)。可见调研对象主要是蒙古族学生且其年级分布基本均匀,调研样本具有较强合理性。
2.2.2 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现状
对大学生的阅读喜爱情况调研得知,在306名学生中,有25 人(8.17%)表示非常喜欢阅读,有210 人(68.63%)表示喜欢阅读,有46 人(15.03%)表示不喜欢阅读,有25 人(8.17%)表示不清楚。可见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对阅读有兴趣,喜欢去阅读。
调研通过多选题“您喜欢的阅读类型”了解蒙古族大学生喜欢的阅读类型,有147 人(48.04%)选择蒙古族现代文学,有153人(50%)选择蒙古族历史,有102人(33.33%)选择蒙古族期刊,有77人(25.16%)选择蒙汉双语读物,有25 人(8.17%)选择蒙文数字资源,有140 人(45.75%)选择其他类型。结合当面访谈可见蒙古族学生的阅读类型整体上有局限,主要集中在蒙语版出版物中的文学作品。访谈中有不少蒙古族大学生表示蒙语版出版物科普类读物有限,这些局限性也限制了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范围。
调研通过多选题“您的阅读方式”了解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方式,有242 人(79.08%)选择看纸质版书籍,有77 人(25.16%)选择看电子书籍,有57人(18.63%)选择听书,有38人(12.42%)选择使用数据库资源,有58 人(18.95%)选择其他。可见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方式以纸质版书籍为主。在与图书馆馆员及蒙古族大学生的电话访谈中,他们表示书籍类型和内容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的阅读,他们阅读的大部分书籍都是老师,同学或者朋友推荐的。可见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对于蒙古族大学生的迫切性。
调研通过单选题“您每周的阅读时长”来了解蒙古族大学生的每周的阅读时长,有64 人(20.92%)选择1小时以下,有134人(43.80%)选择1~3小时,有83人(27.12%)选择3~7小时,有13人(4.25%)选择7~12 小时,有12 人(3.92%)选择12小时以上。可见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的每周阅读时长为1~3 小时,说明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量不够。
2.2.3 蒙古族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使用情况
调研通过单选题“您经常去所在高校的图书馆么”了解蒙古族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使用情况,有51 人(16.67%)选择经常去图书馆,有99 人(32.35%)选择偶尔去图书馆,有108 人(35.29%)选择有需要才去图书馆,有13 人(4.25%)选择几乎不去图书馆,有35 人(11.44%)选择没去过图书馆。可见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是有需要才去图书馆或者偶尔去图书馆,这也导致他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较低。在访谈中,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表示在学校他们偶尔会去蒙文阅览室,甚至有的蒙古族大学生根本没去过蒙文阅览室,他们不知道蒙文阅览室的存在。
调研通过单选题“您对于图书馆的各类数据库了解么”了解蒙古族大学生对数据库的了解状况,有13 人(4.25%)选择非常了解,有172 人(56.21%)选择一般了解,有121 人(39.54%)选择不了解。可见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对于图书馆的各类数据库资源不了解。在访谈中了解到,对于数据库非常了解的蒙古族大学生是因为选修了信息检索与利用课,在课上了解了数据库的功能和作用。
调研通过填空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使用图书馆的资源,增加自己的阅读量,您希望蒙汉双语阅读老师(或其他语言老师)为您提供怎样的服务”了解蒙古族大学生对于图书馆服务的建议,有的同学希望做好图书馆资源分类,增加蒙文书籍,有的同学希望可以每天推送有意义的书籍,有的同学希望增加蒙文书籍类型,多些新出的书籍,比如蒙文版励志书和专业书籍,通过观点分析,大部分同学表示希望可以多多举办活动,提升阅读兴趣,多多推荐书籍,提升涉猎范围。
3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建设及存在问题
3.1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建设
上述数据表明,蒙古族大学生阅读兴趣培养和阅读能力提升是急需要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通过蒙汉双语推广阅读活动加以引导和培养。调研的内蒙古地区五所高校图书馆是否设有兼职或全职专业蒙汉双语兼同的阅读推广人,详见表1。

表1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建设现状
3.2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建设问题
图书馆机构的问题:调研了解到,内蒙古地区高校图书馆没有把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提到图书馆人才建设的日程上,也没有纳入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培训中。阅读推广活动跟随每年4·23阅读日开展,没有系统性、长期性、特色性和层次性,图书馆蒙古族馆员,在双语阅读推广过程中仅具有语言优势,没有阅读推广理论知识和图书、情报学专业背景,因此不能开展专业、系统和长期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由于图书馆存在服务欠缺的问题,导致图书馆宣传不到位,访谈中了解到,大部分蒙古族大学生大学4年期间,从不光顾图书馆。
教学机构的问题:图书馆教务处、学生处和团委相关管理部门联系不密切。在业务开展方面:对阅读推广活动和阅读推广人没有顶层设计,导致没有把阅读推广活动嵌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致使阅读推广活动没有体现出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和制度化。
教学中的问题:蒙汉双语授课的蒙古族大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牧区,基础教育是蒙古语教学。进入大学后,专业课学习是蒙汉双语授课,学习过程中,可利用的信息和阅读的文献资源有限,数字资源更是有限,老师们在教学中没有把专业文献的阅读嵌入到教学中。因此,使其缺乏跨文化阅读意识。
4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路径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推行阅读推广人培育行动的一部分。在多元文化视域下,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是蒙古族民族文化传承的需要。对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培育既要借鉴全民阅读推广人的共性,又要体现蒙古族文化的特性。根据内蒙古地区高校蒙古族大学生蒙汉双语阅读现状和图书馆蒙汉双语推广人岗位设置情况,从不同层面开展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
4.1 培育机构的设置
首先要建立统一的组织领导,即高校教务处、团委、学生处和图书馆机构。由这些管理部门统领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培训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统筹规划、评审评价、过程指导等培训工作。制定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和建设方案,培育课程由优秀阅读推广人、阅读推广专家和蒙古学文献专家讲授。
4.2 培育课程专业化和特色化
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是在培育全面阅读推广人的基础上开展具有特色的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培育。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课程需要图书馆、学校教务处共同设置和组织,对蒙古族老师阅读推广人培训课程可以嵌入到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中,阅读培育课程开设图书馆学基础、文献学、阅读史、蒙古文文献学、阅读推广系列教材、蒙汉双语阅读活动策划与组织、蒙汉双语阅读载体与方式的研究、蒙古族大学生阅读心理与行为。学习成绩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对蒙古族大学生阅读推广人的培育课程,学校教务处把信息检索与利用、阅读史两门课程纳入学校的选修课,每门课程的学分是2学分,其他课程和老师培训一样,通过图书馆定时、定期培训、学习和考试,成绩合格者给颁发结业证书。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才培育课程内容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和教务处开展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训过程中与专业课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蒙古族教师和蒙古族大学生阅读推广人能力培育,使他们熟知阅读推广的核心知识与技能,了解自己的阅读现状与问题,关注本民族出版物的发行状态,研究蒙汉阅读推广案例,掌握阅读推广理论、活动流程,具备组织与宣传能力。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利用图书馆数据库资源安排线上线下蒙汉双语实践的方式,组织蒙古族大学生参加系列阅读推广活动[4-5]。
4.3 开展蒙汉双语阅读推广活动
调研中了解到高校图书馆几乎没有开展长期、系统的特色阅读推广活动。致使图书馆的蒙古文文献资源成为“死文献”98%的蒙古族大学生不知道蒙古文期刊全文数据库。移动阅读代替传统阅读的环境下,对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有更高的挑战,首先,学会利用新媒体社交工具的公开性、参与性和社交性的特点进行数字阅读推广,文献资源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服务进行数字阅读推广。其次,在跨文化视角下整合阅读推广活动,使得阅读推广活动有特色、有层次。例如:“蒙汉民族的纪念日”阅读推广、蒙古族名家讲坛模式、读者阅读座谈模式、资源开放管理模式、获取知识技术的普及模式、网络及多媒体的推广活动。使蒙古族教师、馆员和学生以角色的身份积极参与到阅读推广活动中,使图书馆文献资源、阅读环境对民族文化传承发挥价值和作用。
5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对策
5.1 把控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质量
在多元文化冲击下,培育蒙古族馆员、教师和学生成为蒙汉双语兼通阅读推广人,把控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当下是极其重要的。深刻理解公共图书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具备信息安全意识,读者阅读的个人信息、网页浏览、阅读数据等信息行为已是大数据的一部分,如果缺乏安全管理可能导致读者隐私的泄露。另外,蒙古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的阅读信息管理和保护是有区别的。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育质量的高低,关系到阅读生态环境的安全。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馆员在参与阅读推广课程培育过程中,通过嵌入式教学方式,结合专业和就业引起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树立蒙古族大学生良好道德与责任,全面、系统接受阅读推广理论知识,制定周密的阅读计划作为教学方法,以本专业文献和专业经典读物为阅读方向,通过课堂训练蒙古族大学生文献的阅读能力,及蒙古文网络资源的收集及阅读能力[6]。
5.2 完善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评价与资格认证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培育机构处于“零”状态。这就需要民族地区高校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和图书馆共同建设和完善好阅读推广人培训,对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培养结果分级段进行评价和考核,并对考评合格的蒙汉双语合格的教师和学生给予学校结业证。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评价是指蒙古族大学生思想品德、专业知识和蒙汉双语阅读素养、蒙汉双语阅读技能、蒙汉双语沟通能力。通过培训和学习使越来越多合格的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才加入阅读推广队伍中,为民族地区的文化繁荣发展发挥作用。
5.3 提升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信息素养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具备的信息素养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阅读能力和阅读推广活动的组织。在多元文化教育环境下,信息素养能力是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应对信息生态环境的综合能力。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更加注重对知识信息的挖掘,关注知识组织、区块链技术、数据挖掘、数据融合和信息技术。(1)提升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信息意识。信息通过阅读获得,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信息意识,使得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认识到双语阅读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重要性。牢固地确立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融合多民族文化,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对蒙汉双语阅读有积极的内在需求,善于将阅读与学习、生活和就业迅速密切联系,有效地进行拓展阅读。(2)提升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信息知识。处于跨文化背景下的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在阅读推广中,更加需要知识的挖掘,通过阅读获得知识,有效利用信息技术知识,开展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例如开展蒙汉双语兼同的名家讲座、微信公众号、蒙汉双语阅读推广活动等。(3)提升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信息能力。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在推广阅读的过程中,依照需要熟练地用蒙汉双语去捕捉、评价、选择、整合、吸收、处理、利用文献中的信息,并对文献中的信息进行创新。使得蒙古族师生将潜在的阅读需求不断强化,增强阅读的分析和表达能力。(4)提升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信息道德。信息道德是指个体在信息活动中所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规范;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处于跨文化背景下推广阅读,奠定正确的阅读道德和阅读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蒙汉双语推广人具备正确的阅读价值观,在阅读推广过程中会促进蒙古族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健康发展。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具备正确的阅读价值观,在阅读推广过程中彼此营造一种良好的班风、校风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书香社会的发展。
5.4 强化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阅读素养
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具有阅读推广专业素养,包括学习探究能力、蒙汉双语组织管理能力、蒙汉双语社交沟通能力、创新创意能力、宣传营销能力、学习写作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等。强化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阅读素养,既有全民阅读推广人阅读素养的共性,又有少数民族阅读推广人阅读素养的特性。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阅读素养的培育需要民族地区高校、家庭、社会文化机构三位一体共同体。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各级图书馆、草原书屋、流动书车等阅读服务保障体系的主观能动性,保证三位一体的互动。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和教学管理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蒙汉双语阅读活动和阅读指导,如特色专栏、讲座、真人图书馆等[7]。三位一体共同联合,共同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书香家庭、书香校园、书香社会。
强化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循序渐进的阅读素养。阅读素养包括获取与检索、整合与解释、反思与评价三方面内容,含六要素:认读、理解、鉴赏、评价、活用、技巧。培育和提升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阅读素养,前提是要有阅读的习惯、兴趣和积累。针对专业、学历层次的阅读差异,在阅读培养和阅读指导上,进行分层次指导和培育阅读。阅读指导教学分层次由高校教务处开设蒙汉双语阅读课,在图书馆和课堂完成。课外阅读指导分层次,在高校图书馆、学校管理部门(团委、学生处、教务处)、文化部门进行联合完成这项工作。
5.5 突出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传承特色文化的角色
内蒙古地区由于文化、宗教、跨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影响,阅读推广活动缺乏民族特色,没有专业的蒙汉双语兼通阅读推广人做这方面的服务工作。2019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内蒙古大学参观,翻阅了我校出版社组织翻译的《摆脱贫困》蒙文版、《契丹小字研究》等成果。总书记认真听讲解,不时驻足端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蒙古文古籍的搜集、整理、保护,挖掘弘扬蕴含其中的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内涵,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优秀的民族作品、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需要发扬光大,需要专业阅读推广人和蒙汉双语兼通的阅读推广人去推送和传播,在民族地区培育蒙汉兼通的阅读推广人是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素养。
5.6 根系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需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谈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崇,更多次提到“文化自信”。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促进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用蒙汉双语推广经典阅读(包括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的经典读物)使得蒙古族师生克服语言障碍,增强多元文化的认同心理,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之根。根系民族地区人才发展。民族地区高校为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人才,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培育有助于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丰富阅读资源,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蒙古族大学生适应学习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是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和特色阅读文化发展的需要。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有区域性和民族性特点,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的职责是通过推广阅读,传递阅读价值的正能量,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形成良好的阅读环境,培育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其阅读能力[8]。
6 结语
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是对阅读推广人理论和实践丰富和补充。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不仅可以提高蒙古族大学生的阅读能力,解决其专业学习和就业的阅读障碍,还可以提升蒙古族大学生的人文情怀,构建和谐校园。培育蒙汉双语阅读推广人使民族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资源由“死”文献变成“活”文献,对蒙古族学生对其民族文化的理解,传承和弘扬都有莫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