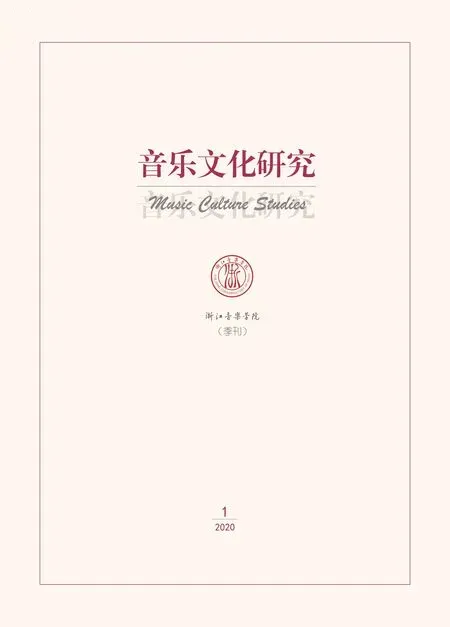当前民族歌剧若干问题之我见
居其宏
内容提要:中国歌剧是中西合璧的产儿,而民族歌剧则是中国歌剧家族的光荣一员,并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历史地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魅力和特色。文旅部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根本目的,是改变新时期以来民族歌剧“一脉单传”的现状,使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和艺术光彩。然而,当下歌剧同行对民族歌剧的理论认知和创制实践,仍存在一系列误解和偏向,若不及时予以廓清,则势必影响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自民族歌剧经典《白毛女》2015版全国巡演、2017年原文化部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并成立由二十多位著名艺术家组成指导委员会以来,“民族歌剧”一词在我国音乐界、戏剧界、歌剧界一时成了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歌剧院团对创作、演出民族歌剧给予高度重视,推出了一系列扶持举措,三年来各地献演的新创剧目呈现出井喷之势。与此同时,何谓“民族歌剧”?它有什么样的特色?与其他中国歌剧、中国戏曲和西方歌剧是什么关系?民族歌剧该怎样传承与发展?它面临的命题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如何去改进它,使它能够健康发展?
上述这一系列问题,在歌剧业界原本多属常识,我本人也在各种不同场合公开阐发过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令人不解的是,这些基本常识居然会在一些同行和相关领导之间触发激烈争论,并对当前民族歌剧的创作、演出和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消极影响。
有鉴于此,对这些问题再作一番普及性廓清或学术性阐发,看来仍有必要。
中国歌剧是中西合璧的产儿
这是第一个常识性命题。难道竟有人否认这个事实?不仅有,且大有人在;如认为中国歌剧就是中国戏曲、中国戏曲即为中国歌剧即为一例;如认为我国当代民族歌剧无须向西方歌剧学习又是一例。为此,当需话说从头、简溯历史。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音乐最具代表性的品种是戏曲艺术。王国维将戏曲定义为“以歌舞演故事”,瓦格纳认为“歌剧是用音乐展开的戏剧”,两者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戏曲是不同于西方戏剧的独特舞台戏剧,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美学原则和表现体系,既博大精深,又雅俗共赏,在我国繁衍了近千年,拥有最广大的受众群体和广袤市场。
但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传入,以及一批先进文化人的大力提倡,我国音乐戏剧生态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一)近代西方歌剧在中国的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包括话剧、歌剧在内的西方戏剧传入中国。上海作为“东方巴黎”,曾有很多西方歌剧院团、艺术家到上海演出过经典歌剧作品。这些经典剧目影响了中国第一代歌剧作曲家,如创制12部儿童歌舞剧(被公认为是中国歌剧的滥觞)的黎锦晖及创作我国第一部正歌剧《王昭君》的作曲家张曙。其他如为《白毛女》创作音乐的李焕之、瞿维和向隅等,都曾在上海看过西方歌剧。
另一个重要的地方是具有浓郁俄罗斯建筑风格的城市哈尔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白俄”歌剧家流亡到哈尔滨,给中国观众带来了很多俄罗斯歌剧和西方歌剧,同样也影响了第一代中国歌剧艺术家。
第一代中国歌剧家,一方面长期受中国戏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接触了西方歌剧,开阔了艺术视野,萌发了将中西音乐戏剧融合起来、创作中国歌剧的强烈冲动,就此奠定了中国歌剧创作中西合璧的基础。
(二)蔡元培的“中西合璧”思想
除了明末清初西方歌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流带来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蔡元培“中西合璧”的办学思想。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学术开自由之风,提出弘扬民族文化,融合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办学宗旨,为当时歌剧艺术家的理论与实践引导了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
(三)萧友梅等人的“中国民族乐派”理想
具有留洋学习西方专业作曲经历的萧友梅、黄自等人,回国后提出“改造旧乐、借鉴西乐、创造新乐”的“中西合璧”方针,对俄罗斯民族乐派非常推崇,希望借鉴欧美专业音乐和俄罗斯民族乐派的成功经验,明确打出创建“中国民族乐派”的旗帜。为此,蔡元培和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专,延聘黄自等人为教授,培养出大批兼通中西音乐文化的现代型、专业化音乐家,其中作曲家便有贺绿汀、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以及前述的李焕之、瞿维、向隅等人,为中国专业音乐和歌剧创作储备了一批“中西合璧”人才。
(四)中国早期歌舞剧实践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促使一部分艺术家想借鉴西方歌剧,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用“中西合璧”形式创造中国歌剧的想法。于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黎锦晖创作的《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等12部儿童歌舞剧,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由此标志着中国歌剧的诞生。这一点已经成为歌剧界一致的共识。
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曾有些人认为中国歌剧是从延安秧歌剧开始的,否认20世纪20—40年代黎锦晖等人作出的开创性贡献。改革开放后,这种思想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歌剧界普遍达成共识,认为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是中国歌剧的源头。
儿童歌舞剧培育了张庚等一大批歌剧艺术家。张庚在其回忆录里写到,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对第一代歌剧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五)中国早期正歌剧实践
由于儿童歌舞剧容量小、时间短,大人看起来不满足,于是早期的歌剧家产生了借鉴西方正歌剧的美学原则和表现体系,创作中国正歌剧的创意和实践。此间,先后创作了《王昭君》《上海之歌》等我国最早的一批正歌剧。
1941年,由臧云远、李嘉作词,黄源洛作曲,创演了一部抗战正歌剧《秋子》,1942年1月31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首演后,不仅国民党要员纷纷赞扬,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郭沫若和《新华日报》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秋子》是第一部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中国正歌剧,在当时文化界引起极大轰动,首演后在全国巡演数十场。2015年,南京艺术学院复排《秋子》,将其重新搬上舞台。
(六)中国早期歌曲剧实践
歌曲剧,即话剧加唱式歌剧。话剧以语言来表现戏剧,在话剧结构里加进若干唱段。最具代表性的是聂耳于1934年创作并首演的《扬子江暴风雨》。首演时,聂耳将其定位为“歌剧”,剧中包含《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等歌曲唱段。
街头剧是在街头演出的话剧加唱式结构的歌曲剧。较为典型的是吕骥等人于1935年创作的《放下你的鞭子》,剧中有一首著名唱段《新编“九一八”小调》,流传很广。
歌曲剧的创作较为简单便捷,创制、演出速度最快,但其艺术质量在我国歌剧家族中也是最差的,很难产生能够流传于世的经典剧目。
(七)民族歌剧奠基之作《白毛女》的实践
194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时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于是孕育了延安秧歌剧的诞生,其代表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起先在陕甘宁、继而在其他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
由于秧歌剧形式短小、内容单薄、戏剧性不强,不能表现宏大的主题和复杂的戏剧内容,于是,开始要求秧歌剧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其代表性剧目是《惯匪周子山》。
早期歌舞剧发展的高峰就是延安的秧歌剧。民族歌剧《白毛女》正是在延安秧歌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时,恰逢河北“白毛仙姑”的故事传到陕北,时任延安鲁艺戏剧系主任的张庚组织了一批音乐戏剧家将它改编成歌剧《白毛女》,并将第一稿交给时任延安鲁艺院长的周扬审查。周扬认为第一稿仍然没有脱离秧歌剧的形式,依旧由小曲、眉户调、秦腔构成,没有创新,要求推倒重来。随后,由当时20岁左右的贺敬之担任第一编剧,丁毅担任第二编剧,对《白毛女》剧本进行重新创作;在音乐创作团队中,除马可、刘炽等人外,又吸收了向隅、李焕之、瞿维等曾在国立音专接受过专业作曲教育和西方歌剧熏陶的作曲家加入创作队伍,努力向陕西、河北、山西的民歌和民间戏曲学习,使《白毛女》面貌为之一改。
中国戏曲的音乐戏剧性展开思维,分为曲牌联缀体(曲牌体)和板式连套体(板腔体)两大表现体系。在《白毛女》的创作中,除了借鉴西洋歌剧的有益经验和表现手段外,最重要的是继承发展了戏曲板腔体思维,为喜儿和杨白劳创作了一系列具有板腔体特征的唱段。
当然也吸收民歌的营养。例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其音调走句一律下行,整体性格是悲切的。马可将其旋律增高大二度,加入两个偏音,在落句时变下行为回环,就产生了《北风吹》的旋律,调整后的旋律音调变得明朗、清澈,整体音乐性格为之一变。
《白毛女》的经验告诉我们:民族音乐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好东西,照搬与无视都是不对的。从民歌和戏曲中吸取养料,加以创造发展,才是最正确的创作思路。
民族歌剧音乐创作要做到“既熟悉,又新鲜”,只有这样才容易被中国观众接受。如果全熟悉的话,会让人觉得是老调;如果全是陌生曲调,观众审美积淀少,不易接受。
《白毛女》的主题思想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延安首演后引起极大轰动。中共中央领导,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都对它评价极高。
此后,所有的中国歌剧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个谁也无法否认的铁的事实:中国歌剧是中西合璧的产儿。中西合璧、兼收并蓄才是所有中国歌剧的发展方向。
(八)两个结论
基于“中国歌剧是‘中西合璧’的产儿”这个事实,必然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其一,从纵向(历史)的维度看,中国歌剧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品种,是中国艺术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由民间型向专业型战略转轨的产物。否认这一点,就必然否认中国歌剧的新文化特质,从而将中国戏曲艺术也误认作中国歌剧的源头和主流,从而导致中国歌剧概念的极度泛化,反而稀释乃至取消了中国歌剧的独立品格和价值。
其二,从横向(世界范围)的维度看,中国歌剧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歌剧艺术一样,都是人类歌剧艺术的一个分支。否认这一点,就割断了中国歌剧与世界歌剧之间客观存在的血肉联系,从而导致中国歌剧界孤立主义的产生,关闭了本已敞开着的向西方歌剧学习借鉴有益经验的门户,中国歌剧的国际化便无从谈起。
因此,在强调中国歌剧本土化、民族化的同时,也要强调中国歌剧的国际化,要为人类歌剧艺术提供中国作品、中国风格、中国创造,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文化使命。
当然,中国歌剧家的某些作品,先国际上获奖再走回国内,也不失为一条中国歌剧走向国际化的可行途径;但我认为,就中国歌剧的整体而言,尤其是民族歌剧,我们若想真的走向世界,首先要必须走进中国观众的心里,首先在中国站稳脚跟。
因此,要有勇气和胆识承认,中国歌剧是人类歌剧艺术的一个分支。当我们在谈论中国歌剧尤其是民族歌剧在一度创作中的某些弱点和不足并以西方经典歌剧举例时,心里不必紧张。因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其目的正是为中国歌剧实现“三精”统一标准、攀登中国乃至世界歌剧高峰提供强大助力和坚实支撑。
中国歌剧既然作为中西合璧的产儿,在中国广大观众的歌剧生活中繁衍发展了将近一百年的今天,看不到我们与西方经典歌剧客观存在的差距,非但歌剧审美视野日趋开阔的中国观众不答应,更无从谈攀登世界歌剧之巅,又遑论文化自信?
中国歌剧必须联系实际,立足本土,将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多风格的原创歌剧的追求,作为当代歌剧家的创作导向和努力目标。在此基础上,还要使中国歌剧为人类歌剧艺术在21世纪的发展增添中国气派、中国经验和经典剧目,让各国同行和观众为中国歌剧由衷喝彩,才是中国歌剧真正走向世界之日,也是中国歌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所做的一大贡献。
民族歌剧是中国歌剧家族的光荣一员
眼下一些同行对文旅部扶持民族歌剧颇有微词,甚至对“民族歌剧”这一概念提出根本性质疑,其说林林总总,恕不详列。何谓“民族歌剧”?它与其他中国歌剧是何关系?又有哪些独特和别致之处,需要单列门户给予特殊关照?
回答这些多属常识性的问题,恰是本文这一部分所承担的任务。
(一)中国歌剧家族及其分类
前已说过,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过数十年的不懈探索和创演实践,不同审美追求和歌剧观念的歌剧家,根据其对歌剧综合元素、创作技法的不同运用,以及在体裁、风格和语言等方面客观形成的差别,历史地造就了由歌舞剧、歌曲剧、正歌剧、民族歌剧、新潮歌剧(按出现的年代先后排列)这样一个风格多样、和谐并存的中国歌剧家族——
歌舞剧,以20年代黎锦晖儿童歌舞剧、延安秧歌剧、60年代的《刘三姐》、改革开放后的《米脂婆姨绥德汉》为代表。
歌曲剧,以30年代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抗战时期的《放下你的鞭子》、改革开放后的音乐话剧为代表。
正歌剧,以40年代的《秋子》、50年代的《草原之歌》、60年代的《望夫云》、改革开放后的《伤逝》《原野》《苍原》《钓鱼城》《骆驼祥子》为代表。
民族歌剧,以40年代的《白毛女》、50年代的《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60年代的《红珊瑚》《江姐》、改革开放后的《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为代表。
新潮歌剧当然也是中国歌剧家族的平等一员。它是自勋伯格以来,调性逐渐瓦解,泛调性和无调性、十二音、序列主义、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等各种现代作曲流派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剧界的产物,以郭文景的《狂人日记》和温德青的《赌命》为代表。
所有这些不同风格或类别,只要有人创作、演出,有人看,就有存在的价值,就为中国歌剧添加了新的东西,都是中国歌剧家族中平等的一员,不应受到排斥。
然而,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民族歌剧一直是中国歌剧的主脉,它有众多优秀剧目、高度艺术成就和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在中国歌剧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的歌剧类别。
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
从20世纪80年代直至2017年,在我国歌剧家族中,正歌剧占据主流,新潮歌剧、歌舞剧和音乐话剧也有长足发展,唯独曾经光荣无限的民族歌剧却遭到冷落——改革开放以来,仅有总政歌剧团一家创演了《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两部优秀民族歌剧,这就是我常说的民族歌剧“一脉单传”。
正歌剧、新潮歌剧、歌舞剧、音乐话剧及音乐剧的兴盛令人欣喜,应予充分肯定;然而请问: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民族歌剧在当下“一脉单传”的窘境,就能熟视无睹么?
(二)民族歌剧艺术特点的界定
民族歌剧这个概念,以及民族歌剧这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歌剧类型,是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应运而生的,是中国歌剧家植根于中国大地、中国国情、中国文艺传统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审美需要,在科学扬弃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基础上的独特创造;自20世纪40年代《白毛女》诞生以来,直至2005年《野火春风斗古城》首演,其间经过60年创演实践的不倦探索和历史积淀,客观地、历史地形成了自身的艺术特征和概念内涵。
我们所谓之“民族歌剧”,是中外音乐戏剧艺术有机嫁接、高度融合的产物,既有人类歌剧艺术都具备的戏剧音乐性和音乐戏剧性这一共同特征,又具备其他优秀中国歌剧都应具备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而它之大有别于西方歌剧和其他中国歌剧类型的鲜明特征和创新之处就在于:
1.剧本创作
自觉学习戏曲文学的舞台叙事法则,不懈追求情节的丰富性和戏剧冲突的生动曲折;不懈追求歌剧文学的音乐性,按照音乐戏剧性展开的需要设置结构、场面和唱段;不懈追求人物形象塑造的立体化;不懈追求剧诗创作的音乐性、诗意和个性化;不懈追求板腔体剧诗丰富的心理层次和结构铺排。
2.音乐创作
自觉向中国传统音乐和戏曲音乐学习,坚持以声乐和歌唱性为主、优美旋律至上,追求音乐语言和风格浓烈的中国神韵和气质;对民间音乐素材的使用更靠近音调原型,并运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变奏、加花、缩减、展衍等方式加以贯穿与展开,以达到“既熟悉,又新鲜”的审美效果;尤为重要的是,运用戏曲板腔体思维和结构及专业作曲技法创作主要人物的核心咏叹调,以揭示人物复杂情感层次和内心冲突,刻画主人公的音乐形象。我认为,恰是这个用板腔体思维和板腔体结构创作咏叹调,与西方歌剧运用主题贯穿发展手法和戏剧性思维既异曲同工,又大异其趣,是中国作曲家对人类歌剧艺术的一大创造和贡献。
3.表导演艺术
歌唱以民族唱法为主;即便是其他唱法,必须自觉向民间歌手和戏曲演员学习,切实掌握歌唱中的吐字、声韵、润腔等复杂技巧,以彰显浓烈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韵;自觉向戏曲表演的虚拟美学学习,切实地掌握“四功五法”技巧,并根据作品内容需要和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调演员与所演角色在外在形象和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用以表现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
回顾我国民族歌剧60年全部历史以及从《白毛女》到《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所有代表剧目,都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上述艺术特征和概念内涵,客观存在于七十多年来所有经典剧目的本体形态之中而无一例外。尤其是咏叹调创作中的板腔体思维和结构这一条,是中国作曲家对于人类歌剧音乐戏剧性展开的一个重大贡献。
这是历代民族歌剧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新时代歌剧家必须承认、必须尊重的历史存在。在当代艺术观念多元的语境下,你可以批评它的种种不足,更可坚守自己的艺术观和歌剧理想,另开通向世界歌剧金字塔的登顶之路,但你却无权否定它的存在。
(三)民族歌剧概念的历史演变
“民族歌剧”这个概念,并非生来就有,而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1.20世纪40年代的“新歌剧”
1942年5月,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延安艺术家经过秧歌剧的成功实践,终于孕育了《白毛女》的横空出世。此后,延安文艺家将这一时期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歌剧类型统称为“新歌剧”。
“新歌剧”之所以“新”,当时延安艺术家们是这样解释的:
其一,与中国传统戏曲(当时也称之为“旧歌剧”)相比,是新内容和新形式。
其二,与20世纪20年代黎锦晖儿童歌舞剧、30—40年代国统区艺术家创作的各种歌剧(如40年代重庆首演的正歌剧《秋子》等)相比,是新内容。
其三,是左翼新音乐运动(如以聂耳创作的《扬子江暴风雨》为代表)、延安革命音乐运动(如秧歌剧)的一个新创造和新发展。
2.“新歌剧”在20世纪50年代
在整个50年代,中国歌剧界一直沿用“新歌剧”概念来称呼《白毛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相继出现的《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霞》《洪湖赤卫队》这些歌剧作品,使之与同时期出现的中国歌剧其他类型相区别,并以一系列经典剧目使“新歌剧”成为中国歌剧的主脉。
但“新歌剧”概念也在歌剧界引起了争论。如张庚同志就说:“‘新歌剧’的‘新’,一方面给我们以光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少麻烦。”当时,对“新歌剧”及其概念的质疑并未深入展开。其学术成果集中体现在《新歌剧问题讨论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里。
3.“民族歌剧”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
到了20世纪60年代,作曲家胡士平发展了马可“新歌剧应向戏曲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歌剧戏曲化”理念,并将这个理念贯彻于歌剧《红珊瑚》的创作和表演艺术中;同样也是胡士平,提出以“民族歌剧”概念代替“新歌剧”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马可、贺敬之、陈紫、张锐、张敬安等很多同行的赞同。
此后,我国歌剧界均以“民族歌剧”这个概念来为《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红霞》《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剧目作类型定位;至于其他类型的中国歌剧,则分别以“歌剧”(如《草原之歌》)、“歌舞剧”(如《刘三姐》)为之定位。
4.“民族歌剧”概念在改革开放最初30年
从1978年到21世纪最初十余年,由于发生了中西音乐观念的大碰撞、大融合,思想解放、观念多元,正歌剧、音乐剧、歌舞剧乃至新潮歌剧很快成为中国歌剧创作的主流,相比之下,“民族歌剧”类型受到了冷落,主动创作民族歌剧的院团和作曲家越来越少;在此期间,真正创作民族歌剧的院团仅总政歌剧团一家,堪称优秀的民族歌剧作品,也仅《党的女儿》和《野火春风斗古城》两部,王祖皆、张卓娅夫妇成为中国民族歌剧血脉在新时期得以接续的代表人物。
对当前几种观点和现象的回应
从2017年至今,因文化主管部门大力提倡、全国各地各级歌剧同行积极响应,民族歌剧得到空前繁荣和发展;新创剧目井喷,也出现了《呦呦鹿鸣》《马向阳下乡记》《尘埃落定》等较好剧目。然而,在这繁荣现象的背后,也引起诸多不同观点的争论,隐伏着一系列令人担忧的倾向和问题。对此,本文择其要者,略加回应。
(一)关于“工程”与中国歌剧生态
文旅部之所以要设立“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其目的是改善中国民族歌剧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歌剧生态中“一脉单传”的现状,使它与其他中国歌剧一起得到平等而充分的发展,营造一个各种歌剧类型平衡发展、多元并存的健康生态。
因此,国家积极扶持民族歌剧,并不意味着只发展民族歌剧,排斥其他歌剧品种。一个重要例证是,在这个“工程”推行的同时,在各地不也涌现出《楚庄王》《檀香刑》《白鹿原》《山海经·奔月》《天地神农》《逐月》等正歌剧吗?其中,郭文景的正歌剧《骆驼祥子》以其出类拔萃的歌剧魅力而受到同行和观众的一致称赞。
(二)关于“工程”的三个“精准”
作为一个体裁分类概念,“民族歌剧”与我国歌舞剧、正歌剧、音乐话剧、新潮歌剧和音乐剧一样,都是中国歌剧家族中的平等一员,都应得到繁荣和发展;新时代党和国家之所以重点扶持民族歌剧,乃是因为此前“一脉单传”现象并不正常,必须扭转。
若将“民族歌剧”普泛化为“中国歌剧”,那么党和国家设立的“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以及一系列重点扶持和滚动举措,也就失去了它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甚至有可能令民族歌剧这一脉陷入彻底消亡的境地。
有鉴于此,我认为必须鲜明亮出“精准传承”“精准扶持”“精准发展”的旗帜,以有利于我国民族歌剧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所谓“精准传承”,即必须解决我们要传承的民族歌剧到底是谁,它在七十余年历史发展中客观形成了哪些不同于中国歌剧其他类型的特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根本无法达成“精准传承”使命,甚至有可能令“扶持发展工程”走偏。
所谓“精准扶持”,即我们将要重点扶持剧目,在其艺术本体内部,是否具有民族歌剧的那些基本质素。2017年,各地参与重点扶持剧目评选的竟高达一百四十余部,其中包括《白鹿原》《檀香刑》《楚庄王》《玛纳斯》这类明显属于正歌剧的剧目。除此之外,我认为2018年的重点扶持剧目《命运》同样如此。这个问题若不解决,也就根本无法达成“精准扶持”的使命,同样有可能令“工程”走偏。
所谓“精准发展”,即在民族歌剧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也就是说,在当代歌剧家对民族歌剧的成功经验和若干不足钻深、吃透之后,根据当代观众审美情趣的变化,才能有针对性地完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就意味着,当代歌剧家的新创民族歌剧,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和创造成果,依然是民族歌剧,是新时代的民族歌剧,而不是将民族歌剧发展到别的方向去(例如正歌剧)。这个问题不解决,“工程”同样也会走偏。
(三)关于题材和样式
目前国内的歌剧创作,存在一个很普遍、很严重的问题,即院团和创作者对歌剧题材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跟风和局限性,长征、抗战、“一带一路”、扶贫、建党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主旋律题材一拥而上,又不严肃认真面对这一光荣而崇高的艺术创造使命,导致违背歌剧艺术创制规律的粗制滥造现象极为严重,多数剧目思想艺术质量低下,最终不得不由“一拥而上”堕入“一哄而散”。
这些主旋律题材、重大题材要不要写?当然要写,也应该写、必须写;但是有一点应当弄明白:这些题材之于当代歌剧家,非但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任务,更是一项严肃而崇高的艺术创造使命,必须在遵循歌剧艺术规律、按照歌剧的音乐戏剧性思维、刻画鲜活动人的歌剧形象等方面下苦功夫、花大气力,精雕细刻,反复打磨,方有出精品的可能。例如2017年宁波市演艺集团的《呦呦鹿鸣》和青岛歌舞剧院在2019年获“文华大奖”的剧目《马向阳下乡记》,它们都是表现现实题材的民族歌剧,且在思想艺术质量上代表了当前我国现实题材歌剧创作的最高水平。
有鉴于此,我反复重申下面这两句话:
其一,题材样式无优劣,“三精”标准见高低。
其二,写什么,怎样写,固然重要;但写得怎样,则更为重要。
(四)关于板腔体咏叹调
历史上,用板腔体思维和结构来创作剧中主要人物咏叹调,是从《白毛女》到《野火春风斗古城》以来所有剧目共同的特征而无一例外。其中都有很多板腔体咏叹调,用以表现抒情主人公复杂的内心层次和丰富的情感冲突;非但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也有深切动人的歌唱性,它们之长期被歌唱家和广大观众喜听乐唱,其根本奥秘正在这个戏剧性和歌唱性兼具的审美品格之中。
板腔由“板”和“腔”两部分组成,“板”是板式,属于曲式概念、结构概念;“腔”是声腔,属于音调和旋律概念;因此,所谓“板腔”,兼具双重内涵。
现今有些作曲家在民族歌剧咏叹调创作中将“板”与“腔”拆分开来,在创作中使用“板”的结构概念,利用具有结构意义的节奏和速度的变化、对比和连接来营造戏剧性;但在旋律创作上,却不用戏曲声腔,而是自创新音调,而同样也很有新意。
时至今日,创作民族歌剧,不用板腔体写当然也可以,只要写得好,老百姓喜欢就行。
(五)关于民族歌剧若干历史局限和当下弊端
民族歌剧、即便是那些经典剧目,在其艺术本体内部也存在若干历史局限;在当下的民族歌剧创制中,也同样暴露出某些严重弊端。
1.女强男弱
民族歌剧中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普遍存在女强男弱现象。《白毛女》中,形象最为突出的是喜儿,最好的男性形象是只活了半场的杨白劳,其次是黄世仁和穆仁志,大春的形象塑造得最弱。《小二黑结婚》中小琴的形象最为丰满,二黑哥的形象弱于二孔明和三仙姑。《洪湖赤卫队》中形象最突出的是韩英,刘闯较弱。《江姐》中江姐的形象非常丰满,而作为男性正面角色的华为,其形象则远远弱于反面人物沈养斋和甫志高。这种现象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有所改变,杨晓冬形象较之前男性歌剧形象突出,但其还是缺少戏剧张力。
2.风格陈旧与音调创新
新鲜感不足,创新不足。民族歌剧中有个重要的“核腔”概念,即核心腔调;核心腔调在全剧音乐中、不同人物的唱腔中过多地运用,就会造成核心唱段音乐风格相似,不容易区分,人物形象不鲜明,个性化不够。
3.重唱创作
重唱是歌剧作曲家绝不应该放过的用音乐承载戏剧的形式,例如《弄臣》里吉尔达、公爵、玛德琳娜、利哥莱托的四重唱。没有任何一种形式比重唱更能表现戏剧冲突。然而从《白毛女》到《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国民族歌剧中的重唱存在严重不足——没有优秀的戏剧性重唱,多为抒情性、和声性重唱,或用简单复调,不同声部之间没有对比和戏剧冲突。
4.合唱和乐队写作
歌剧(当然也包括民族歌剧)中的合唱与乐队创作,是塑造群体形象、推进剧情、展开冲突极为重要的形式和手段。在既往的民族歌剧创作中,合唱大多仅作为渲染气氛、描摹色彩而存在,而庞大编制的乐队音乐,则更流于托腔保调的伴奏。我们批评当今歌剧创作过程中机械化生产问题,在乐队音乐创作中表现得尤为严重——现今作曲家很少自己配器,很多只写一个旋律,就交给助手或学生去配器,造成歌剧器乐与声乐两大部分的疏离,“两张皮”现象甚为普遍。殊不知歌剧的音乐戏剧性展开是立体的,声乐与乐队的思维是同步的,两者是一个严密而有机的整体。
5.歌剧思维与非歌剧思维
“歌剧思维”是金湘提出的概念,歌剧界同行都很赞同这种观点。歌剧音乐创作、剧本创作、表导演艺术、舞台美术,都应当遵循歌剧思维和歌剧独特的表现体系。但是现在我们的歌剧创作中有很多非歌剧思维。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一些晚会策划人、词作家、作曲家和舞蹈编导等开始介入歌剧创作,习惯于用晚会思维、歌曲思维、舞剧思维、歌舞思维乃至拉洋片思维来创作歌剧作品。我们当然欢迎其他门类的艺术家加入到歌剧创演队伍中来,但必须遵循“歌剧思维”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否则,戏剧性品格羸弱的问题便无可避免。
6.关于机械化生产
民族歌剧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弊端是机械化生产。虽然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批评了这个不良倾向,但仍有一些歌剧家对此置若罔闻,某些艺术家和院团领导情绪浮躁,创演机制极为急促,甚至规定必须在短短几个月内便完成全剧创制并举行公演。
这不是典型的“机械化生产”,又是什么?
为此我建议:首先,无论国家艺术基金还是民族歌剧传承发展过程,将剧目创制周期由一年放宽至两年;其次,歌剧创制者一定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认认真真搞艺术、做民族歌剧,切实花苦功夫、下大气力,精心打造出几部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
本文是作者在数十年对中国歌剧、民族歌剧的探究基础上形成的个人看法,自认为经得起时间和当下中国歌剧审美实践的考验;但究竟如何,则不敢自专,还应交给历史,交给广大观众,由中国歌剧今天和未来的审美实践来作出最终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