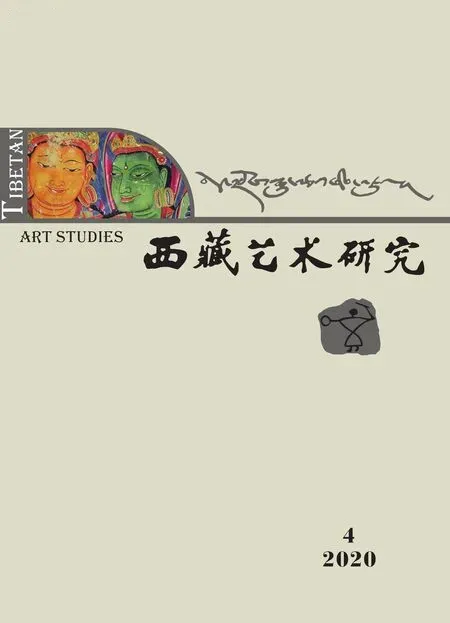口述记忆中的语境与文本①
——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青海卷》的再认识
张歆冉
口述史是“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口述历史访谈指的是一位准备完善的访谈者(interviewer),向受访者(interviewee)提出问题,并以录音或录影的形式记录下彼此的问与答。”②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口述史作为一种田野方法在舞蹈研究中的应用也非常的广泛,但相对成熟的理论研究处于初级阶段。《舞蹈口述史与“口述”舞蹈史——兼论舞蹈人的身体记忆与社会记忆》(车延芬,2016)一文通过列举舞蹈口述史的案例与深入的理论讨论,较为全面的阐释了舞蹈口述史的学术价值。以舞蹈界杰出艺术家为访谈对象,编写的个人自传式的书籍也有很多,例如《中国民族民间舞口述史》(高度,黄奕华主编)、《舞蹈旅程的记忆—— 一位中国民族民间舞教育者的口述史》(邓佑玲主编)、《舞者述说:中国舞蹈人物传记口述史》(中国舞蹈家协会)等著作利用口述史的方式,通过对人的关注使历史呈现更具多样性。在研究长于抒情的舞蹈艺术时对表演者情感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但文本在记录各民族舞蹈的过程中很难准确传达出民族舞蹈艺术鲜活的民族风格及韵律。而在进行口述对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口述者的声、情、貌记录历史,使历史变得更加生动、立体、真实,从而可以弥补被文本所遮盖的民族身体记忆。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青海卷》(以下简称《青海卷》)以文本的形式,通过民间调研将青海省传统舞蹈进行编汇,对保护民间濒危舞蹈艺术起到重要作用。在笔者对《青海卷》进行再学习后发现无论是框架设计或是内容的编写都非常具有前瞻性,即使今天的我们重新去编写舞蹈集成也很难超越。但另一方面文本在记谱过程中弱化了民族舞蹈的韵律感,对舞蹈本体——身体的关注与强调较弱。在多次对文本分析后,笔者选择了舞蹈较为多样、民族文化较为丰富、语言具有特殊性的藏族舞蹈作为研究对象,对当时主持编撰工作的措罗·普华杰老师进行访谈,希望通过口述史这样鲜活的历史研究方法去揭示,在时代影响下老一辈艺术家编撰过程中是如何展开具体实践,当下的文本如何形成并固定,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哪些经验。
一、编写历程:口述记忆中的时代性
为保护中国舞蹈艺术的长久发展,为了将地方舞蹈文化被更多的人了解与学习,1981年9月国家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编辑部,自此无数艺术家与文化学者开始走进民间,去挖掘各民族优秀的舞蹈艺术。在共同努力下各省均完成了《集成》整理出版工作,为民间舞蹈艺术的良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在众多《集成》编撰过程中,《青海卷》的编写是比较艰难的,前后共历时二十余年的时间。
“当时全国有很多地方的《集成》已经出来了,青海则相对落后。之前负责编写集成的人只是把地方上的一些资料收集过来,没有进行详细的编写,一直没有成果。当时他们主要整理的是海东地区的汉族舞蹈,针对藏族舞蹈的整理则非常的少,有的资料就是塔尔寺的羌姆,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对舞蹈进行分类时出现了错误现象。”(2020年8月17日,西宁,对谈人:措罗·普华杰)
《青海卷》前期的编撰之所以相对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团队成员在编写经验、民族语言、田野采风等多方面工作经验较为欠缺,对《集成》整体编写没有较为合理的安排与分工。通过对谈人对编撰过程的回忆、文字资料的整理以及笔者亲身的田野工作,发现科学的文本架构以及深入的田野调查是《青海卷》最终能够出版的重要保障。而文本架构、田野调查又与当时的时代需求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具有时代性的文本架构
在措罗·普华杰负责《青海卷》编写工作前,曾任职青海省海南州文化局局长,因此他对青海省从事舞蹈艺术工作的人非常了解,在掌握现有编写组成员后,他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从外省借调专业人员协助编写《青海卷》。
“我们从陕西和湖南请来了三位专家进行协助,他们的专业能力、文化水平非常的高。我在期间主要负责资料提供与文字翻译工作。大概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充实、丰富,《青海卷》就出版了。”(2020年8月17日,西宁,对谈人:措罗·普华杰)
在《青海卷》编写时两地的负责人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对民间舞蹈艺术的采集、整理、编写有着非常专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文本架构上已经形成按民族对全省舞蹈艺术分类,再针对具体民族舞蹈从民俗文化、舞蹈形态、音乐伴奏、服饰道具、传承人等多方面进行记录的书写方式,可以说这一文本安排非常理论化、科学化。因而在两位专业学者的帮助下,通过对以往工作经验的借鉴加上团队成员明确的分工,《青海卷》 在三个月内保质保量的迅速完成。老师在讲述当年如何安排文本结构时说到《集成》的编写虽然针对的省份不同,但在文本结构的设计中是统一的,包括对动作分析时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各《集成》也进行了较为统一的安排。
作为一本地方舞蹈志,《集成》 代表着当时舞蹈研究者对民间舞蹈艺术的认识,展现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对舞蹈之外民俗、音乐、服装、道具的关注,对舞蹈艺术的文化特征有着较为深入的考虑。《集成》的编写虽然弱化了舞蹈身体中的民族风格,但就文本架构而言非常具有前瞻性,笔者在山南地区进行田野采风时仍旧会参考《集成》的文本架构,足以见得即使在今天《集成》的科学性、全面性仍旧影响着我们的田野工作。
(二)时代需求下的“采风”活动
负责《青海卷》编写工作的措罗·普华杰毕业于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接受过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及舞蹈理论知识。在任职青海省海南州文化局局长时曾主持编写《海南州文化集成》,集成覆盖范围包括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舞蹈等四个方面,对海南州民间文化知之甚深。同时作为舞蹈编导的措罗·普华杰,在编排《格萨尔王》前期,深入青海省藏族地区学习与藏族有关的歌舞艺术、历史民俗、宗教文化。作为一名藏族舞蹈家,同时对藏族文学、藏学,佛学,藏医学和格萨尔研究方面有一定了解的专家,其本身对民族文化就有着非常专业而全面的了解,加上长久以来扎根民间沃土,无论是思想或是身体上对藏族艺术的掌握都非常深刻。专业的舞蹈训练,深厚的民间舞蹈艺术积累对《青海卷》的编写影响非常重大。
因为之前我就对青海省藏族舞蹈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所以在编写的时候马上就知道哪些内容要编写进来。因为我对舞蹈非常了解,汉语和藏语掌握的也非常熟练,所以在编写的过程中他们问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我马上就能告诉他们,也会比较注意舞蹈的风格特征。(2020年8月17日,西宁,对谈人:措罗·普华杰)
在此之前,关于舞蹈艺术的收集整理工作主要是针对汉族部分,藏族舞蹈的挖掘则较为薄弱,一则受语言影响,二则对民间艺人、现存舞蹈种类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编写工作进行的极为缓慢。在措罗·普华杰参与编写之后,无论是语言翻译、民间资料的收集整理或是舞蹈本身的分析和记录在准确性、全面性、工作效率等多方面均有显著成效。
二、文化语境对身体语言及语言的影响
藏族舞蹈艺术具有非常显著的民族特性,根植于丰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在民族文化数百年的沁润中,藏族舞蹈在形成鲜明的民族共性外,在我国三个主要的藏族聚居区中也表现出具有地方风格的区域特殊性。虽同属于藏民族,但在服饰、表演场域、动作风格以及语言描述中存在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在对《青海卷》所记录的舞蹈进行分析时,使我产生了疑问,编写者在内容选择上做出了怎样的取舍?在编写过程中如何准确的将身体语言转化为文本? 如何在编写过程中更好突出区域舞蹈风格的特殊性?
在编写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既能代表整个藏族风貌的舞蹈,又在其中筛选出独具青海省地域特色的藏族舞蹈进行编写。我们既要突出民族性又要强调地域性。(2020年8月17日,西宁,对谈人:措罗·普华杰)
通过访谈与文本分析,笔者发现《青海卷》藏族舞蹈部分除了内容选择上编委会尝试利用具有地域特色的身体语言,来凸显地域文化的独特性,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在翻译过程中,为避免语言翻译破坏原有文字中所蕴涵的民族性,老师们会特意按照安多方言进行翻译,从语言上保证地域风格。根据老师的叙述不难看出无论是舞蹈的选择或是文字的翻译,文化语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地域文化对身体语言的影响
《青海卷》藏族舞蹈部分的编写,主要是通过对民间资料的收集与翻译,通过访谈与文本对比,笔者发现藏语音译后的舞蹈,虽然称谓一致但舞蹈表演形式、社会功能存在有差异性。《青海卷》中所记载的“卓”,是舞蹈、音乐、诗词为一体的古老藏族民间歌舞,在玉树地区,人们把“卓”称为“锅卓”,即围圆而舞的意思。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编辑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青海卷》[M].中国ISBN 中心出版社.2001.p213.青海卓有男子表演和男女同时表演两种形式,无伴奏,舞蹈风格较为粗狂。在男女同时表演的卓中,男女舞者各站半圆,由“卓班”(男性领舞)带领大家按顺时针方向载歌载舞。男唱奇数段,女唱偶数段,轮流演唱。而在西藏山南地区流传的“卓”则是腰间系鼓的道具性歌舞,表演者为男性。表演时伴随着甩发等高难度动作,舞蹈风格时而悠闲自得,时而热情奔放。此外早期的青海“卓”是民间节庆、祭祀仪式、活动庆典等众多场合中艺术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藏的“卓”只有在高僧大德的迎送以及寺院宗教活动中才会出现,两类“卓”的社会功能也存在有差异性。由此可见音译后的舞蹈虽属于同一民族且称谓一致,但因地域不同其舞蹈表演形式、社会功能相去甚远。
由于地域文化对身体形态的形成、社会功能的影响,因而在编入过程中,《青海卷》选择了具有自我地方特色的“卓”舞进行编写,并详细的记录了舞蹈的社会功能、音乐伴奏、服饰道具、舞蹈形式,着重强调了舞蹈身体语言的地域独特性。
(二)语境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采集完民间乐舞之后将活态舞蹈、藏语言文本转换为汉字进行再编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比较麻烦的是如何在保留民族性、文化历史不变的情况下将安多藏语准确的翻译成汉语。通过措罗·普华杰老师的回忆得知,当年在翻译的过程中因各地区藏语发音不同,人们会按照卫藏发音来翻译安多的舞蹈,其结果导致舞蹈含义发生巨大变化。
比如说青海的“白嘎”,拉萨就是“哲嘎”,在翻译的过程中就把“白嘎”翻译成了“哲嘎”,“哲嘎”在青海是“白色大米”的意思,这样意思就完全变了。前面翻译的人,翻译的不准,变成汉语之后不知道原本的藏语是什么了,后面的人根据汉语翻译成藏语结果意思都变了。“白嘎”是持拐杖跳舞的人,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白色大米”的意思。(2020年8月17日,西宁,对谈人:措罗·普华杰)
安多与卫藏两地语言虽同属藏语,但差异性较大,在田野采风或是文献翻译中,语言理解的准确性对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当年在转译过程中会出现只考虑发音和简单直译的现象,对文字产生语境、特定称谓等更专业、更特殊的问题考虑非常欠缺。像《青海卷》这样需要将活态舞蹈与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进行印刷传播的工作来说,语言的准确性非同小可。在进行《青海卷》编撰过程中,措罗·普华杰老师一则对安多与卫藏语言非常了解,二则接受过专业的藏族舞蹈训练与文化学习,所以在编写翻译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将动态转为文本,同时保留了原本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使阅读者拥有更丰满的想象空间。
三、从口述记忆看历史“真实性”
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我们更进一步还原历史“真实性”,弥补了文本之外更为鲜活的,关于记忆的内容。非文本的口述有文字所达不及的优势:身势、表情、语调、场景的“合谋”生动地传达寓意,包括大量直觉。①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6-9.在此其间我们还可以通过对谈人的亲身感受去更深入的认识到文本背后所掩盖的史实。但我也并不否认,在口述过程中会夹杂有对谈人对事件的主观认识以及情绪化的表达,这就需要作为访谈者的我们以更专业和理性的视角对口述材料进行提取。
(一)特定语境中的历史事实
口述史料虽然具有“原始性”与“可靠性”,但搜集口述史的史料并不是寻找逝去舞蹈的真实面貌,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想要呈现一种“互动”关系:这包括采访者和受访者交谈中双向的艺术创作过程,双方的生活经验与社会认同的交流与认知,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高度的有弹性的空间。②车延芬.《舞蹈口述史与“口述”舞蹈史--兼论舞蹈人的身体记忆与社会记忆》[J].民族艺术研究.2016,29 期.通过对措罗·普华杰老师的采访,“语境” 成为文本编写最重要的部分。在时代语境的作用下,《青海卷》形成了科学、规范的文本框架,在固定的框架中较为全面地对民间舞蹈艺术进行了挖掘与保护,保证了青海舞蹈艺术的发展与传播。另一方面在文化语境的作用下,青海藏族舞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身体语言,在编写过程中,正是认识到文化语境的特殊性,措罗·普华杰老师才会非常强调在内容选取上既要突出藏族舞蹈的民族性,更要强调安多藏族的地域独特性。此外,在文字翻译工作中,对文化语境的考虑更是非常全面。虽同属藏族,但由于地域差异性,发音及语言文化也存在有区别,故而《青海卷》的藏族舞蹈部分语言翻译是以安多发音及语言文化为依据进行有针对性的藏汉互译。
(二)如何从文本走回舞台
对舞蹈艺术的认知不能只停留在固态的文本中,对文本的解读只是书写者对舞蹈的认知,对“历史真实性”就要存疑,因为“文献记载中哪些是‘事实’或‘非事实’并非是研究要点,更重要的是文献作者在何种情境(社会情境与叙事文化情景)下作如此书写;而诠释, 并非只是在既有社会与知识体系中弥补其缺漏, 而是反思我们整个社会与知识体系,以及两者间的关系。”③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版, 第29 页, 第37 页.我们通过文本与历史进行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下社会语境,要以动态的眼光对历史进行适用于当下的解读,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认识。
通过口述采访及文本对照笔者发现,《青海卷》以及整个《集成》的编写不是简单转译,而是借用芭蕾与古典舞的专业知识对空间及基本体态进行预先说明,再者主要负责编撰的老师接受过非常专业的舞蹈训练,在编写中利用专业术语将民间生活化身体行为转变为规范的学院身体行为。具有专业性的身体记录对文本走回舞台中,动作的学习与复原非常有帮助,具有一定基础的阅读者可以很快的掌握舞蹈的基本形态。但另一方面,文本中夹杂着编写者非常主观的意识形态,活态中的舞蹈韵律感还是会被减弱,文字在传递作品情感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访谈时老师所提到的情感内容,动作连接间丰富的民族性还是会有所削弱。在对《青海卷》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还是需要我们走进田间地头,深入民族地区用身体去切实的感受民族舞蹈中独有的地域特殊性,在学习《青海卷》的同时还要关注到民族舞蹈发展的时代性,关注当下青海舞蹈艺术发展的审美特征。
结语
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是在于,它可以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历史。①(英)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因而在对谈的过程中才能更深入的挖掘出《集成》背后被时间所掩盖的真相,才能发现《集成》今天形成的文本架构、内容编排是在时代的作用下产生的,极具前瞻性,时至今日对我们的田野采风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及参考价值。在编写过程中,编委成员通过舞蹈种类的选取、文字语言的翻译来突出和保留舞蹈艺术中所蕴含的独特的地域文化。也正是因为口述史可以扩大资料范围,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才使得我们能够掌握更鲜活的历史内容,在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避免陷入个人主义的误区,以一种更客观、更全面的视角去看待舞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