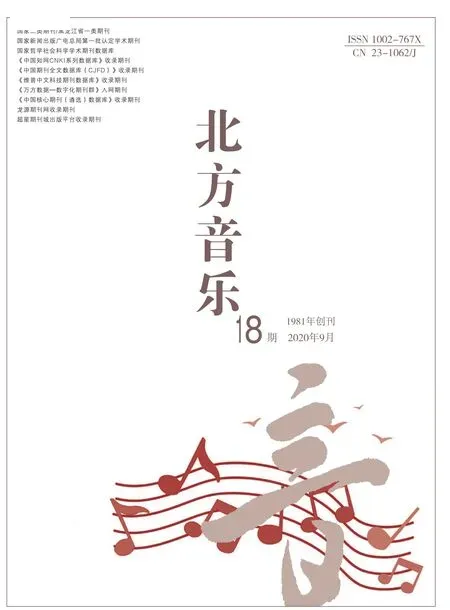浅谈18世纪60
——90年代意大利作曲家对俄罗斯音乐的影响
王洛飞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漯河 462000)
引言
谈及浪漫主义时期的俄罗斯民族乐派,以格林卡作为起点是较为常见且具有标志性的。诚然,从格林卡开始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音乐在当时以西欧音乐为核心的体系中逐渐发展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彼得大帝决定实行欧化政策与俄罗斯早期本土音乐家产生的这一段时间里,外来音乐家在将优秀的作品带入俄罗斯的同时,必然对俄罗斯的整体音乐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外来音乐家更多来自于意大利,这一情况一定程度上表现于18世纪初俄罗斯便出现宫廷意大利歌剧院。且在民间歌剧院建立后,意大利歌剧逐渐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18世纪中叶之后的意大利歌剧正在经历启蒙运动带来的改变,包括百科全书派对传统正歌剧的批判、法国巴黎的“喜歌剧之争”以及最为重要的格鲁克歌剧改革,等等。这时期向外输出的意大利歌剧与传统印象中能够向外输出的音乐存在差异,其风格、体裁都存在争议,但正是这种处在改革之中的“意大利歌剧”却成功传入俄罗斯,并获得了上至皇宫贵族下至普通市民的支持。这种现象与当时俄罗斯的历史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18世纪60年代应邀前往俄罗斯的音乐家们
在西欧的历史上,我们时常能够看到女性在获得一定统制权后着重发展文化艺术音乐的情况。中世纪阿基坦的埃莉诺借由自身权利聘用各地游吟诗人发展“宫廷之恋”体裁便是其中一例。而时间至176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罢黜当时的彼得三世,成为俄罗斯史上唯一一位被冠以“大帝”之名的女王。在此之后,借由原本彼得三世的西欧化政策和已然建立的意大利歌剧院等硬件设施,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向西欧众多音乐家抛出橄榄枝,聘请其前来俄罗斯任职。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意大利音乐家来到了俄罗斯,其中有四位最具代表性:
威尼斯的加卢皮(Galuppi Baldassarei,1706——1785),在其年少时,由于在威尼斯本地剧院中,除却维瓦尔第之外,那不勒斯作曲家的地位远高于威尼斯作曲家的缘故,直到维瓦尔第去世,加卢皮的两部重要歌剧才在1740-1741年前后成功问世。此后的时间里加卢皮开始前往伦敦进行演出和指导歌剧,并逐渐获得名声。1748年5月,他被选为圣马可大教堂的牧师,此期间其专注于创作宗教作品,但实际上日后他的创作重心仍然会转移到歌剧之上。1749年,加卢皮开始与卡洛·戈多尼(Carlo Goldoni)合作进行歌剧创作,并在接下来的九年间大获成功。当1762年加卢皮成为威尼斯唱诗班的导师后,显然他的名声已经远达俄罗斯,因此,1764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下,加卢皮前往俄罗斯。
相比于加卢皮,那不勒斯的帕伊谢罗(Paisiello,Giovanni,1740-1816)前往俄罗斯的时间稍晚。1754——1763年,帕伊谢罗在那不勒斯的奥诺弗里奥音乐学院接受教育。从1766年开始,帕伊谢罗回到那不勒斯作为一名自由作曲家开始喜歌剧创作。我们抛开帕伊谢罗为获取皇室认可而进行的一系列与婚约有关的活动,总而言之,其结果是,1776年帕伊谢罗收到也接受了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邀请,以3000卢布的年薪前往圣彼得堡任职。
但在六年后的1782年,在俄罗斯大公保罗的建议下叶卡捷琳娜二世邀请萨尔蒂(Sarti Giuseppe,1729——1802)来取代帕伊谢罗。很明显,相比于帕伊谢罗,萨尔蒂更富有实践经验。1748——1752年,萨尔蒂担任法恩扎(Faenza)大教堂的风琴师,同时兼任法恩扎剧院的导演职务,并创作了第一部歌剧《亚美尼亚的蓬佩奥(Pompeo in Armenia)》。1752年12月,他成为Pietro Mingotti歌剧团的音乐总监,并在访问哥本哈根期间受到腓特烈五世的钦佩。后担任哥本哈根的意大利剧团导演,继续进行歌剧创作,直至1763年意大利剧团解散,萨尔蒂开始担任宫廷音乐总监。1765年萨尔蒂回到意大利,并创作了几部严肃音乐作品。在此后萨尔蒂持续奔走在宫廷与教堂之间,不断进行创作,同时担任贵族甚至国王的音乐老师。1779年,萨尔蒂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并被整个欧洲所追捧。直至1782年,萨尔蒂收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前往圣彼得堡。
而最后一位奇马罗萨(Cimarosa Domenico,1749——1801)来到俄罗斯的时间最晚,同时也对前三位的音乐成果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奇马罗萨从12岁开始在洛雷托音乐学院(Conservatorio di S Maria di Loreto)接受了11年的专业教育。1770年,奇马罗萨与尼科洛·津加雷利(Nicclo Zingarelli)、朱塞佩·焦尔达尼(Giuseppe Giordani)在同一个无伴奏合唱大师班学习,并从尼可罗·皮钦尼(Niccolo Piccinni)那里学习到了更多作曲技法。1772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那不勒斯喜歌剧(commedia per musica)《Le stravaganze del conte(伯爵的怪癖)》。此后直至1780年7月10日,其代表作《意大利人在伦敦(L’italiana in Londra)》问世,在此前后奇马罗萨也在进行严肃歌剧创作,如《凯奥·马里奥(Caio Mario)》(1780年)和《亚历山大在印度(Alessandro nell’Indie)》等。此后的7年中,奇马罗萨被逐步任命为那不勒斯皇家教堂的编外风琴手(后升为第二风琴手)和奥斯佩达莱托音乐学院(Ospedaletto conservatory)音乐大师。1787年,奇马罗萨接受了凯瑟琳二世给予的圣彼得堡宫廷职位,在途经帕尔马、维也纳和华沙之后,1787年12月3日抵达圣彼得堡。
从这几位音乐家前往俄罗斯前的经历可以看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非常有计划和目的性地去邀请在意大利已有一定成就的音乐家。且从1764年,即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两年后这一行为便已经开始。直至1791年,由于第二次俄土战争导致的诸如经济、社会等问题,致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无力再去邀请音乐家前来俄国。
再看上述音乐家涉及的创作方向,加卢皮创作歌剧和宗教作品;帕伊谢罗接受教育期间任职小型歌剧公司总监后作为自由音乐人主要创作喜歌剧;萨尔蒂担任风琴师、兼任剧院导演、担任过宫廷意大利剧团总监,同时也进行过严肃剧的创作;奇马罗萨同样担任过风琴手并进行喜歌剧和正歌剧的创作。叶卡捷琳娜二世显然并未在“喜歌剧之争”中选择某一方,尽管在1779年以前圣彼得堡的舞台上是不允许上演喜歌剧,但这一时期她仍然广泛接收喜歌剧、正歌剧等各种内容的歌剧,并逐渐将圣彼得堡的舞台向喜歌剧敞开。同时,格鲁克的格局改革也并未左右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选择,广泛的包容性给予了音乐肥沃的土壤,借由意大利歌剧在俄罗斯生根发芽。
二、意大利音乐家在俄主要影响
由于18世纪60——90年代赞助人制度仍然对音乐家群体有重要影响。贵族的雇佣仍是大部分音乐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故根据前文以音乐家为线索的论述方式,从宗教音乐和世俗音乐两个角度来论述意大利音乐家对俄罗斯音乐造成的影响。
在西方音乐的历史上,自中世纪以来音乐与宗教便呈现出密不可分的关系。即使俄罗斯半数以上的领土被划分在亚洲,但在学习和引入西欧音乐的同时,结合自身东正教的宗教基础,宗教音乐仍然是俄罗斯音乐的重要部分。从加卢皮到达圣彼得堡一年后便为东正教礼拜仪式创作了15首俄文无伴奏合唱,便能够看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雇佣加卢皮的用意。且在1769年夏,加卢皮的作品《牧羊王(Il re pastore)》在威尼斯得到承认并被用来纪念约瑟夫二世。此后加卢皮的创作开始更加向宗教音乐倾斜。
在加卢皮之后达到俄罗斯的帕伊谢罗曾在圣彼得堡曾担任帝国教堂的负责人,但是在不久之后这一职位便被俄罗斯大公保罗(Grand Duke Paul)认为萨尔蒂更适合担任此职务。然而,事实亦是如此。在萨尔蒂的指挥下意大利歌剧达到了艺术上的顶峰,无论萨尔蒂和帕伊谢罗孰优孰劣都可以发现俄罗斯当时有意引进优秀的音乐家来发展自己的宗教音乐。帝国教堂的负责人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由外来音乐家担任,直至保罗一世时期才出现了第一位本土斯拉夫裔的帝国教堂负责人,即鲍尔特年斯基(Bortniansky)。由此足见叶卡捷琳娜二世引进音乐家改变国内宗教音乐环境的目的。
在世俗音乐方面,在18世纪60——90年代这个背景下如何对待喜歌剧和严肃歌剧成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问题。如前文所说,加卢皮的到来使得莫斯科的舞台向喜歌剧敞开。甚至有可能早在加卢皮到达俄罗斯之初便已经创作了一首喜歌剧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伊姬尼亚在陶德亚(Ifigenia in Tauride)》。萨尔蒂再来到圣彼得堡后创作出了喜歌剧《假继承人》(1785年)和严肃歌剧《阿米达和里纳尔多》(1786年)。他同时也用法文和德文创作,甚至与帕什凯维奇(Pashkevich)和卡诺比奥(Canobbio)合作制作了俄罗斯歌剧《奥列格早期王朝(Nachal'noye upravleniye Olega)》(1790年)。这部作品非常优秀,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一直在俄罗斯被演出。接着萨尔蒂为女皇的唱诗班创作了几首俄罗斯清唱剧,一首庆祝波将金(Potemkin)夺取奥恰科夫的重唱曲和一首纪念路易十六的安魂曲。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萨尔蒂在俄罗斯期间发明了一种用于计算声音振动的机器,此后他为圣彼得堡管弦乐团建立了音高标准(a'=436)。在奇马罗萨到达俄罗斯后,他所做出的贡献则更多的是去延续加卢皮、萨尔蒂等意大利音乐家所在做的事情。演出方面他对早先创作的严肃歌剧《埃及艳后》,以及两部喜歌剧《敌对的女人(Le donne rivali)》和《洛卡·阿祖拉的两位男爵(I due baroni di Rocca Azzurra)》,都针对俄罗斯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演员调整。
从表现来说,叶卡捷琳娜二世将意大利音乐家邀请到俄罗斯的行为致使喜歌剧在俄罗斯被逐渐接受,各类剧目也在俄罗斯得以上演,甚至部分音乐家为适应俄罗斯的实际情况开始对剧目进行改编。这无疑加深了俄罗斯本土音乐与整个欧洲音乐的联系。接着,虽然俄罗斯早在18世纪初便借由彼得大帝的欧化政策学习西欧音乐,但意大利音乐家的到来将更加系统的音乐理论带入俄罗斯。同时,如前文中提到“萨尔蒂为圣彼得堡管弦乐团建立了音高标准”这类事件,也标志着俄罗斯的音乐更加与整个欧洲相统一。
三、18世纪60——90年代俄罗斯音乐发展启示
至此,不难猜测叶卡捷琳娜二世想通过意大利音乐家获得的东西。一方面是音乐本身,无论是喜歌剧、正歌剧还是清唱剧、宗教仪式音乐,对于音乐本身的渴望驱使叶卡捷琳娜二世动用大笔费用雇佣音乐家们来到俄罗斯。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行为间接给予了俄罗斯极为优渥的音乐环境,使得这个有半数以上土地在亚洲的国家在音乐上切实和欧罗巴接轨,为后世俄罗斯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是为何格林卡能够成为研究俄罗斯音乐时的首要对象——他是第一位被欧洲所承认的俄罗斯作曲家。也许在西方中心论的背景下这种“被承认”显得有些片面,但实际上格林卡为欧洲所承认的同时,将俄罗斯声乐作品特有的形式以及俄罗斯民间歌曲的特点融入其中。他在《云雀》中将祖国的景象借由诗意的画面呈现出来,同时又将斯拉夫民族特有的哀伤赋予作品。《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则在他对作曲技法熟练的掌握下借由旋律的自然发展形成了乐句间规整的对称关系。由此足见,格林卡对欧洲音乐创作技法了然于胸,同时也熟知如何借由这些技法表现本民族文化和情感。
王晡教授在《西方音乐史》绪论中针对历史研究有这样一段话:“‘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经断言这一名句,其核心意义是明确肯定了历史的现实性……在历史研究中,现实性一方面表现为对过去的当代分析,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过去当代存在状况的观察。”在这样的理论支持下再看18世纪60——90年代的俄罗斯音乐发展便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如何面对外来音乐理论、体系的问题。在过去的时间里,西方中心论将欧洲为主的音乐体系凌驾于各地区各民族之上,直至“音乐人类学”等专注于研究欧洲音乐以外音乐学科出现。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仍有大部分国家地区在使用欧洲的十二平均律或某些音乐体系进行音乐创作。在这种前提下如何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特点的同时发展音乐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俄罗斯的这些经验为当前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如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者们一般,着手于减字谱、工尺谱以及旋宫转调系统等传统内容的研究与相关音乐创作。亦可如18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一般大方吸收欧洲的音乐理论体系,并结合本民族独有的文化进行创作——事实上有大量的先辈音乐家已然如此行动,并获得丰厚成果。如俄罗斯音乐在浪漫主义时期逐渐发展最终成为西方音乐史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一般,使用正确方法和态度学习得来的外来文化,最终会化作土壤滋养本民族音乐发展,这种方法可以成为一种确实存在的经验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