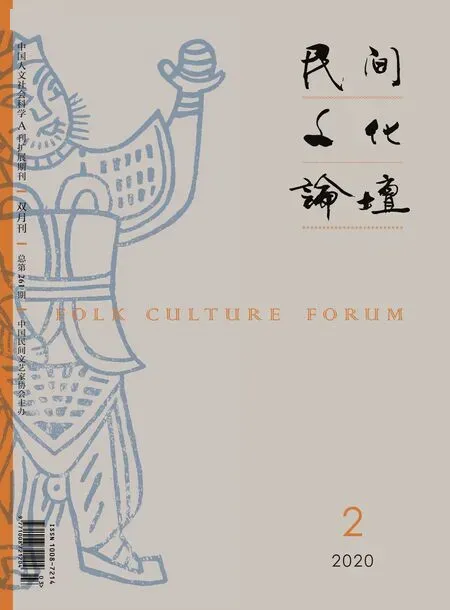实践民俗志与女性民俗研究的一种可能性
王均霞
主持人语
近十年来,学界越来越注意对性别民俗的研究,不仅是女性民俗,男性民俗研究也开始见诸学术刊物,这也暗合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民俗学的当下转型。社会性别制度在不断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民俗之“民”的分化已经是一个显著的社会现实,中国民俗学研究早已开始区分不同群体,比如阶层、年龄、性别、职业等层面的差异。对民俗的观察和讨论既不能忽视个体叙事,也不能离开民俗之“民”的特殊性。本期刊出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女性民俗进行研究。第一篇强调了日常生活实践作为一种路径对女性民俗研究的重要性;第二篇将女性回娘家习俗作为考察对象来探讨日本女性的故乡观;第三篇通过梳理“女性”“女性主义”“女性视角”等研究视角的演变,厘清女性民俗学发展的学术脉络。也即,关注女性民俗的学者在紧紧盯着“无数雷同的水滴当中的一滴水”的同时,会注意女性自身文化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的细节,也会注意这些细节与社会总体的联系。
——主持人 刁统菊
一、从社会制度的性别批判到探究女性民俗的日常生活实践
传统父权制在家庭内部构筑了“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分工秩序,并要求女性处于“从”(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位置。人们深刻地践行着这套“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将女性塑造成男性及其家庭的附属品,将其生活限定于家的围墙之内,与公共事务相隔离,并使之成为“自然而然”“理所当然”。这种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体现在中国古代的礼制典籍、法律与习俗中。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礼记》系统规定了女性作为男性之附属的“礼”。例如,“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妇人者,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古代亦有诸如《女诫》《内训》《女孝经》《女论语》《女范捷录》《女儿经》等强化传统父系家族制的女性之“礼”的典籍。而相应的法律法规则保障了这套强调父权制的社会性别规范的正统性及其顺利实施。例如,在婚姻问题上,古代法律保障了男性的直系尊亲在子辈婚姻问题上绝对的话语权,从而剥夺了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青年男女在该问题上的自主权。①瞿同祖:《中国律法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男性离婚的意愿,却几乎完全不支持女性离婚的诉求。①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在家族财产分配上,儿子理所当然地是父亲的承继人,在法律上有不容侵犯的承继期待权,但女儿却绝不能作为父亲的承继人。②同上。在犯罪处罚上,法律的运作逻辑也遵循着“男尊女卑”的惯例,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例如,在明清时期的法律中,妇人犯罪,除了犯奸罪和死罪收监之外,其他杂犯无论轻重都不收监,而是责令其夫收管。③瞿同祖:《中国律法与中国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民间习俗中同样体现着父系家族制中的社会性别规范。如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中所收录的民间歌谣,便清晰地呈现了在父系家族制度中女性所受到的压迫。④刘经庵:《歌谣与妇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年。
可以说,官方的礼制规范、法律以及民间的习俗实践一体性地构筑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秩序。不过,这套父系家族制度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冲击。例如,1903 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目睹了中国“妇女地位之低微不改”而“心力憔悴”,因而编译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全书按地域介绍了五大洲各国的女俗,并通过比较明晰教化之优劣,强调国家振兴与女性解放的程度密切相关。林乐知寄希望于通过兴女学来释放妇女。⑤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 年,第12—15 页。同样是1903 年,金天翮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女界钟》,指明受制于专制,中国女子更注重个人的私德(如守身如玉、防意如城),而不知公德(如男女平权、女子读书入学、婚姻自由)为何物。因而,他极力主张女性入学的权利、交友的权利、营业的权利、掌握财产的权利、出入自由的权利和婚姻自由的权利等。⑥李又宁主编:《华族女性资料丛编(1):女界钟》,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 年。“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达到一个高潮。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们首先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对文献的考据、实地的田野调查等来揭示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对女性的压迫;进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呼吁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大学生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⑦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
妇女解放运动作为反封建的重要内容,吸引了那些试图推翻封建帝制的个人和组织的广泛参与,形成了一股整体上反对传统父系家族制度对女性的压迫、主张女性权利的社会潮流。从国家制度层面上实现男女平等某种程度上成为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
回顾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实现男女平等的成绩也尤其令人瞩目。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中国妇女逐渐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获得了相应的权利。例如,早在20 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之时,政府便陆续颁布了劝禁缠足的上谕,并对女子留学给予一定的鼓励。1920 年,在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六次年会上,来自全国16 个省区的20 名代表向教育部递交《关于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教育部对该提案采取了默许的态度。⑧顾秀莲:《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 年。1923 年1 月1 日,国民党公开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确认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1 月2 日,国民党发布 《中国国民党党纲》,强调要完成男女平等的全民政治。1927 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国民政府在一系列法律政策如《民法·亲属编》《民法·继承编》中对妇女相应的权利进行了规定,着力推进解决加诸妇女身上的重重压迫。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十分注意妇女解放问题,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先后颁布了许多保障妇女权益、推进妇女解放的法律法规。1931 年,中共中央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并陆续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其中对妇女的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例如,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法律面前不论男女一律平等,十六岁以上的苏维埃公民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徐辰:《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 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 1840—1949 下》,北京:中央编译局,2017 年,第199 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实行男女婚姻自由。”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徐辰:《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 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 1840—1949 下》,北京:中央编译局,2017 年,第454 页。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其中第九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年宪法”), 徐辰:《宪制道路与中国命运 中国近代宪法文献选编 1840—1949 下》,北京:中央编译局,2017 年,第479 页。。另外在相关选举权的规定中,特别强调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后,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经历了历次修订,但在妇女的权益方面都延续了共同纲领以来的相关规定,且内容有所增加,如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1954 年宪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本书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 年,第8 页。等内容。1992 年4 月3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并于2005 年8 月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做了相关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在宪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从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益、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法律责任等方面规定了妇女所享有的相关权利(益)和责任。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男女平等已经基本实现,这体现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各项法律法规当中。男女平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国策。
那么,国家制度层面上性别平等的基本实现,是不是意味着在实践层面上也是如此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今天,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下,借助传播迅捷而影响广泛的大众传媒技术,性别问题似乎重又成为一个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无法回避的显性问题。诸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大龄未婚青年问题、拐卖妇女儿童问题、性骚扰(侵)问题、教育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以及LGBTQ 问题及相关衍生问题,最近几年持续地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引起强烈的舆论纷争。过去被一体性地诉诸礼制典籍、法律与习俗的一套社会性别制度,在今天更多地被诉诸于习俗,并被内化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性别观念,继续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今天的性别纷争更多地出现在接受了新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少数人和仍抱持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冲突,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层面上的性别纷争,它不再明显表现为人与制度之间的对抗,而是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从其现有特点来看,这些性别纷争表现出明显的参与者性别立场标签化的趋势。性别观念对立的各方往往基于对方彼时彼地的言论或行为给予标签化的批判,“直男癌”“直女癌”“(中华)田园女权”等标签应运而生。而性别纷争中对立的各方却缺乏对这些被标签化的性别观念或行为由以产生的根源的追溯,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对话。这显然并不利于性别问题的解决。
同时,正如一些学者所指明的那样,当代活跃的女权运动者与性别研究者并不划等号,二者之间交集甚少,“年轻的、以拉拉为主体的、少数性工作者小组参与的中国新生代女权运动者”并不被大部分主流的女性主义者/性别研究者所接纳①黄盈盈:《反思Gender 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社会学评论》,2013 年第5 期。,活跃的新生代女权运动者与主流的女性主义者/性别研究者之间缺乏必要的对话与合作。一方面,新生代女权运动者往往借助现代传媒技术的内容传输(如西方影视剧、综艺、微博、微信等)以及相应的学校教育吸收来自西方的、具有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倾向的社会性别观念,并依此对传统中国父权制结构之下强调家国而非个体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激烈的批判与直接的对抗,但她(他)们同时又缺乏足够的耐心与路径,探寻普通人的社会性别实践背后的行动逻辑根源,即: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在其日常生活中是如何被生产与再生产出来的?另一方面,有能力去探寻普通人的社会性别实践背后的行动逻辑根源的学院派社会性别研究者,却囿于“学术”本身而对当下日常生活实践中所产生诸多性别问题视而不见,无法有效地、从普通人的立场去回应当前已经(正在)发生的种种性别问题。董丽敏的研究表明,尽管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大潮迅速重新建构起一套新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进一步加固了人们对于既有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文化的刻板印象,妇女群体重新被边缘化甚至弱势化,但此时的女性研究及其机构已经被纳入到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女性研究虽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在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却也在此过程中“日益沦为一种在学院/知识内部循环的影响有限之物”②董丽敏:《“性别”的生产及其政治性危机——对新时期中国妇女研究的一种反思》,《开放时代》,2013 年第2 期。,失去了其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
将研究目标定位于“关于女性”和“为了女性”的女性研究,如果失去了关怀现实的能力,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义。从这个层面上讲,今天学院派的女性研究需要跨越学院的藩篱,重新寻回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度与批判力。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场域中,去探寻那些正在被实践着的、具有模式性的民间习俗如何型塑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这一路径与当下中国民俗学研究的日常生活实践转向相契合,通过实践民俗志的书写,女性民俗研究可以在该方面做出贡献,为当代社会性别问题的解决提供具有指向根源的解决路径。
二、实践民俗志与女性民俗研究的路径探索
实践民俗志为探寻那些正在被实践着的、具有模式性的民间习俗如何型塑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提供了可能性。这里所说的实践民俗志意指一种聚焦于具体的人及其民俗实践的民俗志写作方式。与传统的关注静态的事象的民俗志书写不同,它所书写的民俗既是静止的,又是流动的;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下的。
从宏观的学术背景来看,这种民俗志写作方式与中国民俗学的学科范式,从关注民俗事象到关注语境中的民俗①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 年第2 期。、从对历史民俗的关注转向对当下的关注密切相关②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 年第1 期。。刘铁梁是此种民俗志写作的主要倡导者与实践者。基于对北京各区县民俗文化的调查与民俗文化志书写模式的探索,他在反思传统的类型描述式的民俗志写作方式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在对“‘生活文化’或‘生活层面的文化’的理解上对各地方民众的生活进行整体的观察”③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6 期。和描述的具有“问题意识”④同上。的民俗志写作。他所提倡的民俗志的调查与写作具有如下特点:1.具有特定的时空背景,以地方性为着眼点,能够从地方历史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深厚底蕴。2.主要关注两种民俗:(1)已经基本消失,但仍活在人们的记忆中的民俗,或者是在当下人们的生活中偶有显现,正在淡出日常生活的民俗;(2)当下广大民众正在传承、享用的活态民俗;3. 采取系统的观点,在“生活文化”或“生活层面的文化”的理解上对各地方民众的生活进行整体的观察与描述;4.关注“场域”(field)或“情境”(context),关注人们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上对民俗的运用,将具有主体性的人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包含进写作当中。⑤同上。在此基础上,刘铁梁更关注民俗志中的个人叙事,关注实践者言说自身文化权力的倾向。他将实践者视作有资格叙事历史的独立个体,提倡让实践者按照自己的表达习惯自由地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以此把握实践者对自身生活与文化的理解。这种民俗志写作方式强调“把当地人们日常生活实践历程作为描述的对象”⑥刘铁梁:《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民俗研究》,2019 年第1 期。,也就承认民俗之民的个体实践及在此过程中其所做出的意义建构的研究价值,揭示了民俗之民建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的能力。通过这样的民俗志写作方式,一种日常生活的组织方式、一种观念的实践过程⑦同上。被呈现出来。
而实践的主体是有性别的人,实践者本身的性别观念理所当然地包含于其民俗实践过程之中。在实践民俗志写作中,关注性别的研究者可以借此来揭示性别观念在民俗实践场域中的运作和实践,将其作为理解当下民众的性别观念由以形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突破口。这种以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与布尔迪厄所倡导的性别研究路径不谋而合。在对性别的历史研究中,布尔迪厄提醒研究者不能仅仅描写妇女处境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也不能仅限于描写不同时代的性别关系,而应该致力于确定每个阶段的行动者与制度系统的状况。他强调,一部性别关系史的真正目标是结构机制(比如确保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再生产机制)和策略的连续组合历史⑧[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男性统治》,刘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119 页。。这种研究路径将稳定的制度与灵动的策略通过行动者及其实践连接在一起。一方面,它可以超越以事象为中心的民俗志研究在普遍意义上对女性民俗进行静态描述。这种描述抽离了具体的时空和具体的人,它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传统却无法很好地与当下正在被实践着的日常生活发生关联。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有效地纠偏放大镜般地强调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田野民俗志书写路径,这一书写路径强调女性作为父权制压迫的反抗者的一面,却忽视了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与错综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审视女性的生活状态。同时,它还有助于超越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的对立,将矛头指向隐匿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一套社会性别制度。
尽管在理论上已经有诸多讨论,但在实践上能够并置静态稳固的习俗与动态流转的人的习俗实践的女性民俗志书写尚属稀有。在当下的民俗学领域里,并不以性别视角作为主要研究出发点的《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的民俗志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具有启示性。
刁统菊的《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2016 年出版,该书在亲属制度的研究框架里研究了以往常常被忽略的姻亲关系。借助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及聚焦于实践的民俗志写作方式,作者围绕通婚圈、姻亲关系的相关仪式性表达(婚礼、回门、生育、丧葬仪式等)、婚姻偿付机制、嫁女归属问题、姻亲关系与家族组织、姻亲交往秩序等多个维度,对华北乡村地区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了描述与剖析。作者的关注点聚焦于华北乡村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仍被实践着的、或者尚未远去仍活在当地人的记忆中的姻亲关系的民间习俗。
作者采用了实践民俗志的写作方式来呈现华北乡村地区姻亲关系的民间习俗实践。以华北乡村,尤其是山东枣庄市山亭区红山峪村为田野地点,通过长时段的参与观察与访谈,作者对该区域内正在实践着的或者仍被记忆着的姻亲关系建构与维系习俗进行了剖析。与传统的剥离了具体的人的民俗志写作方式不同,其研究“力图通过本地人的行动和言语去透视隐藏在其身后的动机,尽可能接近当地人的生活实际”①刁统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29 页。。在具体的写作路径上,作者采用了两种策略:第一,基于长时段的田野调查资料,勾勒当代华北乡村地区姻亲关系实践的整体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姻亲关系实践做整体描述时,作者通过以当地人的原话做文章标题,以及适当引用具体的人的观点的方式来凸显当地人的视角。第二,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来呈现华北乡村地区姻亲关系实践过程与细节。在其民俗志写作中,静态稳固的传统习俗与动态流转的当下实践的结合成为可能,当地人所讲述的历史与当下实践有了交汇点。
虽然性别并非作者的关注重点,但我们还是很容易将该书与性别关联在一起。这仰赖于以下三点的微妙结合:首先,姻亲关系本身是由女性作为媒介连接起来的亲属关系网络,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自然地包含着地方社会的性别观念及其实践。性别观念虽然并不被直接言说,却自然而然地体现在当地人的一言一行中。其次,作者是一位关注性别问题的研究者。在其现有的研究中,除了涉及性别的姻亲关系研究之外,她的研究还涉及对女性与民俗宗教、女性民俗学者与社会性别制度的思考。②可以参见作者发表的论文:《女性与龙牌:汉族父系社会文化在民俗宗教上的一种实践》(《民族艺术》,2003 年第4 期)、《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基于对22 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的田野经验》(《民族文学研究》,2017 年第4 期)等。正是她对性别研究的关注使得该书首先是“从嫁女的生活经验出发”③刁统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29 页。的。再次,作为一位出生并成长于华北地区的已婚女性,作者“也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拜访亲戚,也会参加亲戚举办的某些仪式”,因而能够感同身受地理解其受访者,“能够体会许多姻亲关系上的微妙之处”。④同上,第29 页。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也是其所研究的文化的局内人,其作为嫁女的生活经验也成为其研究对象,这保证了作者对嫁女的生活经验的理解深度。正是由于以上三点的融合——姻亲关系本身具有性别属性、作者具有性别意识以及作者是一位有嫁女经验的局内人——使得作者对姻亲关系的描述与探讨中,有意无意地呈现了在过去的亲属制度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的女性在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位置及其中所蕴含的性别观念。
我们举一例来说明。在《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的写作中,当代华北乡村地区成年女性的身份归属与价值清晰地呈现在婚姻缔结与生育仪礼实践中,为我们透视女性与婚姻以及生育的关系、进一步反思当代性别观念提供了一个窗口。
在华北乡村地区未婚青年男女的婚姻缔结过程中,父母承担着为儿女婚配的责任,成为其婚事的重要操持者与决策者。例如,儿女的婚事常常是由父母托人撮合的,父母要为儿子娶亲准备婚房、支付彩礼,为女儿出嫁准备嫁妆。在婚礼仪式中,男方和女方各自的亲属也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通过随礼、帮忙、参加婚礼仪式等方式参与进来。就人际关系的整合而言,“婚礼上的主人公并非一对新人,他们扮演了傀儡的角色,在幕后操纵的却是家庭乃至家族。”①刁统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71 页。山东枣庄红山峪村青年段秋俊的婚事就是父亲段承桂托他的侄女婿介绍的。通过媒人牵线搭桥,男女双方见面相看。见面的时候,女方陈莉是和她的婶子一起来的。两人相处4 年之后,陈莉和婶子到男方家来相家,男方则郑重地招待女方。时隔不久,男女双方一起到女方家下通书,确立了两家的亲戚关系。喜日子定下来之后,男方全家便投入到紧张的准备工作中,准备喜被、装饰新房等。喜日子头一天,“新娘的婶子、叔伯嫂子拾柜,把香烟、饼干、8个馒头以及自家蒸制的两个离娘饼和瓷制痰盂放在柜子里。痰盂内盛一斤点心,还有6个染红的熟鸡蛋、红花生、枣、栗子、两盒香烟”②同上,第75 页。。喜日子当天,新娘在离开娘家去往婆家之时,喝了稀饭“意思是少惦记娘家人,和娘家人走动得少些,多和婆家人相处,不要三天两头回娘家”③同上,第76 页。。等到迎亲的车队接了新娘回到男方家,“新娘一进家门,新郎的大娘就从手中的盘子里抓了一把麸子,混合着枣、栗子、糖和花生,往她头上一扬,说:‘一把栗子一把枣,大的跟着小的跑。’”④同上,第76 页。喜日子第二天一大清早,新娘和新郎将两个离娘饼和四个馍馍交给公婆,并给公婆磕头请安,同时,“两个女迎亲的和一个扛红席的”还要带着新人去拜祖坟、拜家族,回来全家分吃一个离娘饼。上午,新娘的叔叔和哥哥来接新娘回门。传统的回门礼标志着婚礼的结束,也标志着新娘在婆家身份的确立以及新娘和出生家族关系的更新。
婚后还有一系列的相关习俗保证嫁女与娘家的分离,强化其对于娘家而言的“外人”身份。例如,女性婚后回娘家的节日禁忌。在红山峪村,有嫁女不在娘家过节的习俗:“因为春节是‘年’,年要在自己家中过;忌立春,因为‘春’比‘年’还大,否则穷娘家;元宵节不见娘家灯,‘见了娘家灯,一辈子穷坑’,意思是嫁女将成为娘家一辈子填不满的‘穷坑’;清明节、十月一、立冬、腊八、数九都不能在娘家过,比如‘不忌清明,死老公公’‘不忌数九,死两口’‘不忌立冬,死老公公’‘吃她娘家的端午粽,大姑子小姑子都死净’,等等”⑤同上,第200—201 页。。不过,作者同时也揭示了相关习俗的狡黠之处,“为了实现某种平衡,在节日禁忌之外,又产生了一种弥补性的仪式,以此来营造社会的非常秩序。”⑥同上,第204 页。红山峪村有“正月十六好日子,家家都叫亲妮子”的说法。也许,这正是传统的性别观念被很好地接受了的原因所在。
那么,女性经由婚姻成为娘家“出姓”的人之后,女性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婆家的人了呢?并不是。“婚姻给了女性一个合适的社会位置,赋予她生育的资格和权利。但是,只有她生育孩子(或者过继了孩子),才能真正成为这个家的人,否则永远都是个外人。”①刁统菊:《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82—83 页。生育与嫁女的职责连接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婆家和娘家双方的行为与态度内化成嫁女的认知观念的。例如,在婚礼过程中,婆家和娘家都不断用鸡蛋、栗子、枣、花生等来指明对新娘婚后生儿育女的期待。对于婆家而言,“娶来的媳妇必须具有生育能力”;对于娘家而言,给妻集团相比受妻集团具有优越感和优越地位主要是因为“自己给予对方家族一种新鲜的生命和延续下去的动力,使他们能够在死后得享子孙祭祀”②同上,第86 页。。因此,当一个女性不能生育时,受妻集团不满意,“给妻集团的威望也会降低,家族中其他女儿甚至同一村落里未嫁女子的出嫁都有可能受影响”③同上,第85 页。。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嫁出去之后,好几年不怀孕,娘家为此简直操碎了心。各种求子的方法纷纷登场,要是不迷信的都找医院。信迷信的都找拽门头的,就是巫婆”④同上,第85 页。。
从作者对以上相关内容的民俗志描述中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发展迅猛的今天,对于一个乡村女性而言,婚姻和生育仍不是其个人的事,而是深受其背后的家庭/家族所左右的。通过婚姻和生育的相关民俗实践,女性被嵌入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网络中。而正是在这一社会关系网络的互动中,其身份归属与价值得到生产与再生产,父权制的性别观念被潜移默化地内化成当地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认知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尽管作者所呈现的是乡村姻亲制度中所蕴含的父权制性别观念,但我们显然不能将其割裂地理解为与城市相区隔的乡村民众的性别观念。从代际传承的角度来看,当下很多城里人的父辈都是作者所呈现的姻亲制度的践行者,这些人的性别观念显然无法完全摆脱父辈的影响;从空间流动的角度来看,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是从乡村流动到城市里的,他们的性别观念直接带有这种印迹。因而,如果我们要追溯当代许多性别纷争的参与者的性别观念的源头,我们无法绕过这些习俗以及习俗中所蕴含的这些父权制性别观念。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父权制性别观念的内化,左右了当下处在快速流动进程中的人们潜在的性别观念实践。这种诉诸实践的民俗志写作路径为我们剖析当代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突破口。
由于该书并不主要从性别视角出发,《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并没能够在习俗与实践之间充分呈现华北乡村社会的性别观念实践,但《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所呈现的实践民俗志的写作路径,对于从性别视角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场域中呈现当地人的社会性别观念及其实践极具启示性。就应对当前我们所面临的诸多社会性别问题而言,实践民俗志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场域中,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抽丝剥茧地呈现个体(群体)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实践过程。它为超越具体的男性和女性的对立、更深刻地理解当下不同个体(群体)纷繁复杂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与实践过程提供了可能性。
三、实践民俗志与重返有现实关怀的女性研究
女性研究重拾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的路径有许多条,其中一条应当包括通过实践民俗志的写作达到对社会性别观念在日常生活实践层面上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揭示。今天的性别冲突已非改革开放之前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向由礼制典籍、法律和民间习俗三位一体地实践着的父权制社会性别制度开刀。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过去作为一套礼制并由法律做保障的父权制已经不再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中,但它并未消失,它通过具有模式性和重复性的民间习俗实践,继续作为一种被内化为常识的“社会性别观念”,结构性地影响着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今天,性别冲突很大程度上转变成接受了新的社会性别观念的人和仍抱持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的人之间的冲突。要根本地理解这些冲突,我们不能不去理解那些出现在性别冲突漩涡里的人、其所秉持的社会性别观念的由来,以及其所秉持的社会性别观念形成的语境。将拥有不同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实践者及其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场域中的民俗实践作为描述重点的新民俗志的写作,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场域中深度理解那些实践者,并揭示其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以及实践过程,这有助于将现有的贴标签式的性别冲突引向对冲突根源的探寻,并有助于在更宏观的社会结构框架里思考女性的能动性的问题。尽管性别并非其关注的重点,但《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的民俗志书写方式、作者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性别问题研究意识、以及作者的局内人身份的组合所呈现出来的,对于当下的女性研究跨越学院的藩篱,重返有现实关怀的女性研究具有值得借鉴的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