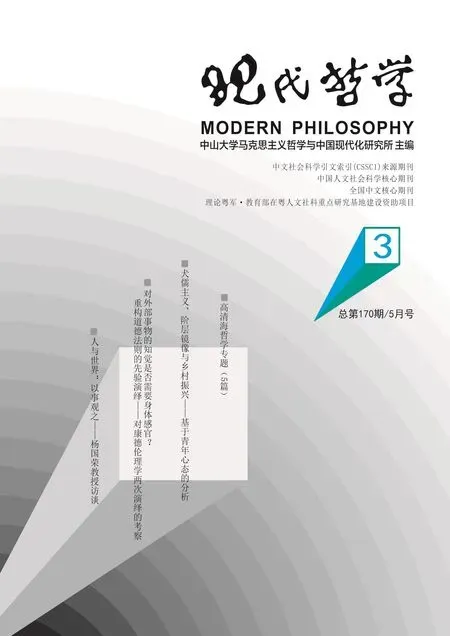类哲学的“种生命”隐喻
魏宗鹏
在高清海的类哲学思想中,人有双重生命即种生命和类生命,类生命是对种生命的超越。类哲学不满足习惯上对“生命”概念的狭隘理解,人在本能生命基础上还应该超越本能生命。而“种生命”指的就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我们对生命概念的一般理解,这种“‘生命’,通常是指具有自组织能力并高度有序的有机体说的”(1)高清海:《高清海哲学文存续编“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按《类哲学的生命隐喻》的理解,类哲学的“类生命”是“宇宙”生命的化身,“宇宙”生命由通常的“生命”隐喻而成。宇宙生命不提供生命的日常饮食,提供的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按照类哲学思想的表达,从生命到宇宙生命的过程展现为一种超越或突破,而从话语形态上展现为一种挪用(隐喻)(2)马天俊:《类哲学的生命隐喻》,《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第57-61页。。本文认为这一理解需要进一步的前提性阐释,也就是说,从客观的话语形态看,不但类哲学的“宇宙”生命由通常的“生命”隐喻而成,通常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即“种生命”也是隐喻而成的。本文将论证,类哲学思想的阐述在话语形态上存在不同领域跨越的三种生命隐喻。如果说由生命概念隐喻而成的“宇宙生命”是类哲学的拱顶石,那么隐喻性质的“种生命”则是类哲学的基石。
一、“种生命”的隐喻性质
达尔文在写作《物种起源》时,曾表明他在阐释关于物种演化的现象时,借鉴了人类社会领域的思想资源,“下一章要讨论的是,全世界所有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这是它们按照几何级数高度增值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就是马尔萨斯(Malthus)学说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应用”(3)[英]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页。。有趣的是,在达尔文的“物种演化”思想闻名世界的时候,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领域,成就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来借用马尔萨斯的学说来帮助他描述物种之间在演化过程中的生存斗争,但他不曾想过,他从社会学说借用来的思想又被重新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催生出新的思潮。从社会到自然,又从自然到社会,看似折腾一番功夫,实则好处显而易见。原本马尔萨斯的学说只是流行的社会学说之一,但达尔文把“生存斗争”学说一经应用到整个动物和植物界,马尔萨斯的学说就超越了人类社会的解释领域,可以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类比或挪用。在这一创造性的类比过程中,原来只在人类社会发挥解释效力的学说,成为生物学史上划时代的达尔文主义。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达尔文的学说从动物和植物界又重新引回人类社会时,原本作为流行的人类社会学说之一的马尔萨斯“生存斗争”学说,“换了身行头”成为解释力大增,涵盖多个领域的“新”学说。从观念的隐喻机制看,可以说达尔文生物学说是马尔萨斯社会学说的次生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又是达尔文生物学说的次生形态,因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是马尔萨斯社会学说的次-次生形态。每个次生形态都从其相应的原生形态继承观念成就,汲取真理力量。在这个隐喻投射和折返的过程中,当达尔文生物学说拥有“自然科学”地位时,社会达尔文主义借此给自己增加了某种客观上的可信度,使自己成为最具真理力量的一门“自然科学”。换句话说,当这种学说将隐喻再度挪用或类比到人类社会,似乎就比单纯的某种人类社会学说更富理论力量,更能说服人。达尔文的这个例子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密切相关。
类哲学思想在阐释本能“生命”或种“生命”概念时,采用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概念:生命通常是指具有自组织能力并高度有序的有机体(organism)(4)参见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8页。。通行的生物学教材认为生命具有以下属性:有序性(order),应激性(sensitivity),生长、发育和繁殖(growth, development, and reproduction),调节(regulation),自稳态(homeostasis)(5)参见[美]拉弗、约翰逊主编:《生物学(第6版)》,谢莉萍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当我们仔细考察生物学这门学科是如何描述生命的特征时,可以惊奇地发现,生物学家们描述生命特征所使用的术语和人们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的一些术语相近或重合。比如,在生物学上的生命有机体(organism)一词,与其词源相近的有社会机构或组织(organization);社会治安或秩序(order)一词,在生物学上专指生命的有序性(order);社会的规章或法规(regulation),一词,在生物学上被用来指生命的自我调节(regulation);在社会领域中,社会增长(growth)、社会发展(development)和社会再生产(reproduction)三个词,在生物学上则指生命的生长(growth)、发育(development)和繁殖(reproduction),等等。这类现象在生物学中并非特例。从词源的考察看,以有机体(organism)一词为例,Organism(有机体)源自Organ。
Organ从13世纪起首先出现在英文里,指的是乐器;14世纪后,指像现代的风琴之类的乐器。最接近的词源为古法文organe、拉丁文organum。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希腊文órganon——意指工具、器械、器具。具有两种衍生意涵:(一)抽象的“instrument”——意指机构;(二)乐器。órganon后来有一个应用意涵,被反复使用在所有的衍生词里,例如在英文里,从15世纪初期,眼睛被视为一个“看的器官”(seeing instrument),耳朵被视为一个“听的器官”(hearing instrument)等等;由此organ被解释为身体的一部分。(6)[英]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38页。
可以注意到,Organ一词最初从工具、器具中衍生出机构(抽象的“instrument”)和乐器的意思,接着在15世纪由工具或机构延伸出与身体相关的器官的意涵。在这个意义上,Organism生命有机体的意涵源于与身体相关的器官,而Organization社会组织或机构的意涵源于机构。从词源上看,生命有机体(Organism)的意涵源自与身体相关的器官,而身体器官的意涵源自从工具、器具中衍生出机构。依前文的铺垫,Organism的词源的变迁和延伸,从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工具和机构的意涵到自然界生命有机体的意涵之间的跨越是靠隐喻达成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生物学上的繁殖(reproduction)源自produce一词,pro指向前(forth),duce指引导(lead),以此延伸出人类社会领域的生产活动(7)Walter W. Skeat,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2005, p.477.,在18世纪 produce特指农业制成品(agricultural productions)以便与工业制成品(manufactured goods)区分(8)参见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produce,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24日。。很明显,produce的生命繁殖的意涵源自农业的生产(种植作物、繁育牲畜)。可以发现,生物学家描述自然领域生命现象的术语总是无法脱离人类社会领域,甚至将人类社会领域的部分术语直接挪用到自然界领域去描述生命现象。比如,生物学上的生命有序性(order),order一词源于古法语的odre(秩序),最早来源于11世纪的宗教释义,意指“生活于宗教戒律下的人的身体”(9)Walter W. Skeat,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p.414.。人类社会领域的秩序(order)在自然的生命现象中体现为生命的有序性(order),此处的挪用现象非常明显。
较诸我们置身其中的人类社会,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对我们来说显得相对遥远和陌生。但人类可以通过言语的方式,借助我们所熟悉的领域去切近相对遥远和陌生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生物学家借助人们熟悉的社会领域的术语来描述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生命现象。但是,这种将一个领域的术语用来描述另一个不同领域现象的方式,实则是一种类比或挪用,一种隐喻活动(10)隐喻(metaphor)。metaphor的朴素意思就是“挪用”,即把词语及其含义从此(习惯的)挪用于彼(陌生的、待定的)。metaphor(隐喻)并没有“隐”的意思,其前缀meta-的意思与metaphysics的前缀意思相近,都是“跨越”“超出”之类的意思。其词根phor所对应的希腊语是“转移”“传送”之类的意思。(马天俊:《类哲学的生命隐喻》,《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第58页)。。这种类比或挪用并非是装饰性质的,它实际上是通过隐喻方式截取并挪用人类社会形态的部分特征,来创制关于自然界生命现象特征的知识。生物学家将描述人类社会的术语用来描述自然生命现象,就像达尔文使用马尔萨斯的社会学说描述自然界物种的演化一样。他们通过类比或挪用,以隐喻的方式让原本作为人类社会领域的术语,在跨越到自然领域之后发挥出新作用,让原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术语成为生物学这门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
二、“类生命”超越性的隐喻机制
通过对西方思想史的考察总结,高清海认为“人是什么”的问题始终无法摆脱一个“两难问题”:“人不能没有生命,不能存在于生命之外,生命意味着人作为实体存在的现实性;人又不能不超越生命,与生物生命又是不完全同一的,只有从生命的超越性才能说明人优越于动物的崇高本性。要么是生命,把人划进动物;要么是超生命,把人并入天使。”(11)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第21页。在他看来,“关于‘人’,历来有着千百种说法,归结起来,其实不外两种基本方式:或者注重人的超越性,于是便把人‘神化’;或者注重于本源性,由此就要把人‘物化’”(12)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第2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页。。那么,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哪?他认为“出路是有的,关键在于头脑。只要我们转换思维方式,打开被封闭的思路,就会出现‘柳暗花明’的景象。为什么不能从走出‘生物生命’的狭隘生命观去考虑出路?”(13)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第21页。这里,他颇为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当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面对活生生的人,从人的历史发展去看人的起源和产生,问题就变得十分清楚而明白了;这里没有丝毫神秘性的东西,人的自身根源、自为本性就在他们生命特有的生存方式之中,这就是人的富有创造性的感性活动——‘生产实践’活动。”(14)同上,第27页。他认为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标志,是人能够摆脱动物式的本能生命而超越本能生命的方式。
人为什么非要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继而划定一种叫做动物式的本能生命,再超越这本能生命呢?“动物(animal)一词源于拉丁语中的‘灵魂’,即赋予生气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animation)。”(15)《西方大观念》第1卷,陈嘉映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790页。与植物相比,动物与人更相近,显得更有“生气”,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人属于动物。但是人类对其它动物进行分类、概括和定义,对其它动物来说是一种特别的不公平。因为没有动物在听到人类对动物的定义会跳出来说“你们人类是错的”,特别是当我们把除人以外的其它动物界定为只依靠生命本能而生存,把人类自己界定为一种超越于本能生命的存在时,已在无形中彰显出人比动物更优越的态度。对此,蒙田评论:“动物其实是人的朋友和伴侣,人却对它们任意支配,还自以为是地分派给它们某种力量和某种特性。他怎样凭借自己的小聪明会知道动物的内心思想和秘密?他对人与动物作了什么样的比较就下结论说动物是愚蠢的呢?”(16)[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2卷,,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1页。蒙田认为人对动物的这种优越的态度源于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高自大,但本文认为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一些人类学著作中,原始人的部族存在着人类把自己称作某种动物的现象。“图腾集团的祖先们根本不是与现存动物完全相象的动物,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却同时神秘地包含了动物和人的本性……‘他们虽然相信他们的远祖是水獭,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是象现在生存的那种水獭。作为他们祖先的水獭是一些水獭人,而不是动物。’”(17)[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8页。这里不难看到,原始人类把自己视为其它动物,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原始人并没有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意识。在一些发达的原始部落,原始人把动物当作图腾,但是图腾已经和人合二为一,已不再是动物,而是“动物—人”的结合。可见,即使原始人在图腾信仰的发展中,开始逐渐地有人与动物的区分意识,但并不认为人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存在优劣之分。在古希腊文明传统中,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关于人优越于动物的论断,但这不是绝对的。譬如,在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形象颇为常见,人类羡慕动物身体蕴含强大力量。德谟克利特曾明确表示人应该向动物学习,但更多的哲人或智者倾向于人优越于动物的观点,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理性灵魂是人优越于动物的明显特征。在基督教神学传统中,上帝创造万物,但根据自身创造了人,人的地位高于其它动物。“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18)《圣经》(和合本)“创世记”(1:26)近代以来,人们对人类理性的宣扬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优越于动物作为既定事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谈到人比动物高明的问题:“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8页。在这点上,高清海的观点同马克思一致,把人比动物优越视为理解“人”的一个非常重要却是默认的前提。类哲学思想对人的双重生命观在话语形态上的表达,也从人的这种优越性开始:正因有一种属人的生命活动比动物本能式的生命活动要高级或优越,才有类生命要超越本能生命的冲动。
借助生物学的“生命”概念,类哲学把本能生命理解为具有自组织能力并高度有序的有机体(20)参见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第28页。。承接前面的讨论,生物学家通过隐喻的方式截取并挪用部分人类社会组织活动的术语,来描述生物学的“生命”特征。人类借助语言以我们熟悉的人类社会形态作为模板描述自然的生命现象,这是一种高度自觉的抽象言语活动。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提升,如人类实验观察工具的精密化等,这种抽象言语认知活动也会不断深入,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会挑战人类已有的认知成果。比如,在微观世界,病毒只具有“生命”的部分特征,因此既不能将病毒理解为“生命”,也不好把病毒理解为“非生命”。从这个角度看,生物学的“生命”概念只是一种暂时的、方便人类进行认知的描述方式,它既不承诺囊括所有的类生命现象,也不承诺可以概括生命现象的所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人只能以人既有的认知方式来理解陌生和未知的现象。人只有把这些通过人既有认知方式而获得的知识作为理解的基础,才得以开展更深层次的认知活动。因而,人比其它动物所谓的优越性地位,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人类盲目自信或人类追求高贵的主观欲求,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人永远无法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式的认知方式。人类因为更熟悉自身的生命活动和社会形态,所以会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尺度来比对所观察到的其它动物的生命活动。这意味着人对其它动物生命现象的描述,只能源于人类自身生命活动形态的截取和挪用,而正因这种截取和挪用的隐喻认知过程,其它动物的生命形态总是部分体现人类的生命形态,人的优越性由此彰显,人的超越性也蕴藏在其中。
在这个意义上,类哲学对本能生命和超本能生命的双重划分,单从本能“生命”或“种生命”的概念看,从话语形态上就已经暗示了本能生命与超本能生命的某种关联,即它们借靠着人类的言语形式而相互区分,也借靠着人类的言语形式而相互关联,而二者之间关联的言语机制是隐喻性质的。
在谈到类哲学人的双重生命之间的关联时,高清海指出,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即“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意味着“生命与环境的天然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来生命的生存必须要依赖环境的天然条件,到了人这里则转变为依赖生命自身的活动;原来的生命本属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个关系现在逆转了过来……也就意味着改变了生命与生物的物种关系……这就表明,人已使生命超脱了生物物种的规定和限制(21)同上,第29、30页。”。在这个意义上,人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改变了其它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受动关系,使之展现出一种独属于人的“超脱生物物种”的特性。问题在于,通常我们理解的生命指的就是一种生物学意义的生命存在,而把人称之为超越生物物种的生命指的是什么?高清海谈到:“人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已经打破了这个词义的禁锢,我们在很多场合都经常使用‘生命’一词,它们的内容并没有局限于生物学的狭隘含义……民族生命、国家生命、政治生命、文化生命……为什么对人的生命就不能有一种属于‘人’而高于动物的内涵?”(22)同上,第22页。在这个意义上,高清海赋予“生命”双重含义:一方面,“生命”可以指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另一方面“生命”还具有超越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容。虽然高清海举了“民族生命”“国家生命”等例子,问题的难点仍然存在:,即到底该如何理解这种超越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
三、类哲学思想的三种生命隐喻
众所周知,上述“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生命”、“社会的生命”、“心理生命”、“政治生命”、“职业生命”、“文化生命”等,相对于生物学的“生命”,显然都是隐喻(metaphor)。metaphor的朴素意思就是“挪用”,即把词语及其含义从此(习惯的)挪用于彼(陌生的、待定的)……在“民族的生命”,“国家的生命”,“社会的生命”等隐喻中,所发生的是那种习惯上的或标准的“生命”概念向“民族”、“国家”或“社会”等议题的跨越性“转移”,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构建了这些议题,造成了非如此则不能达成的特定理解。(23)马天俊:《类哲学的生命隐喻》,《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第58页。
上述引文出自《类哲学的生命隐喻》一文。从客观话语形态上,超越本能生命的“生命”是标准的“生命”概念隐喻而成。遗憾的是,虽然这里从话语层面揭示了超“生命”或类“生命”的隐喻性质,但没有进一步深挖“种生命”,即标准的生物学“生命”概念也是隐喻性质的。如果说本能“生命”或“种生命”概念,以隐喻的方式让原本作为社会领域的术语在跨越到自然领域之后发挥出新作用,让原属于人文科学的术语成为生物学这门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那么超“生命”或类“生命”就是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概念中已变成自然科学术语的“前”人类社会领域的术语,再次引回挪用到人类社会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按该文的理解,超越本能生命的“生命”是标准的“生命”概念隐喻而成,但本文认为其中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就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马尔萨斯的学说从达尔文那里挪用又应用到人类社会学说,虽然看似白折腾,但里面的意味有很大不同。从社会组织(organization)到生命的有机体(organism),再到社会的生命有机体(organism),由“生命”隐喻生成的超“生命”,既拥有与人类社会相似的秩序、法规、增长、发展和再生产等特征,也有与生命有机体相似的有序性,调节、生长、发育和繁殖等特点。二者之间的结合创制了一种新的“社会性”的生命理解。用类哲学的思想表达就是“使无生命世界潜在的能量得以活化”(24)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第37页。。这种新的“社会性”生命与“民族”“文化”等不同议题相结合,就生成不同类型的“社会性”生命。此外,按该文的理解,类生命是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化身,“宇宙”生命点明了“类生命”的终极意义。为此,该文总结了“宇宙”生命的六个特点(25)马天俊:《类哲学的生命隐喻》,《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第59-61页。,但该文认为“宇宙”生命与“民族生命”“国家生命”等同样是隐喻(26)同上,第59页。,却没有觉察到具有终极意义的“宇宙”生命是在“民族生命”“国家生命”等隐喻基础上的再次隐喻。而高清海认为,
生命在进化和发展中生长出了人的生命,人利用自己的生命活动创造了“超生命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生命突破了生命自身的封闭循环,通过“类生命”而把生命引向于更广大的无生命世界。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在它指导下的种生命活动能够沟通生命界与无生命界,使无生命世界潜在的能量得以活化,从而发挥出它们自身难以实现的价值性。这就是人的类生命肩负的天职、“超生命的生命”具有的巨大意义。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说人的“类生命”也就是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化身。(27)高清海:《“人”的哲学悟觉》第3卷,第37页。
从话语形态看,“类生命”之所以能够沟通生命界与无生命界,是因为“生命”概念本来就是由与自然生命界不同的、来自人类社会领域的术语以隐喻的方式达成的。一旦“生命”概念如此达成,就在话语形态上显现为与非自然生命界(人类社会领域)不同的图景。在这个意义上,当借助隐喻而生成的自然生命界,反过来以隐喻的方式跨越到人类社会领域,人类社会领域就被创造出一种类似自然生命界的意义图景。
归结而言,类哲学思想在话语形态上存在不同领域跨越的三种生命隐喻:第一种生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概念,即类哲学的“种”生命,该生命隐喻实现了人类社会领域到自然界生命领域之间的跨越;第二种生成了类哲学的“类”生命,并结合第一种,实现了从人类社会领域到自然界生命领域再到人类社会领域的跨越;第三种生成了类哲学的“宇宙”生命。“宇宙”生命隐喻实现了从人类社会领域到更宽广的宇宙天地的跨越。总之,如果说由生命概念隐喻而成的“宇宙生命”是类哲学的拱顶石,那么借隐喻得以生成的种“生命”则是类哲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