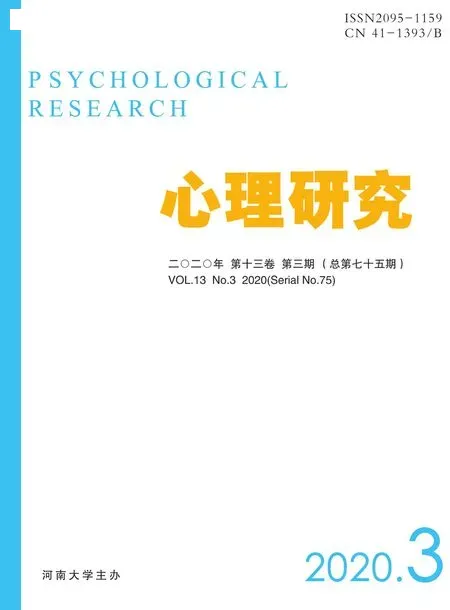后物质主义:理论、测量及相关研究
崔俊杰 李 静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430079)
1 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李静, 杨蕊蕊, 郭永玉, 2017;Chen, Yao, & Yan, 2013; Dittmar, Bond, Hurst,& Kasser, 2014; Jiang, Song, Ke, Wang, & Liu,2016; Kasser, 2016; Richins, 2017; Wang, Liu,Jiang, & Song, 2017)层出不穷,而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民众在生活中除了追求物质财富之外,文化需求与精神寄托也逐渐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林滨, 江虹, 201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在几十年时间里保持稳定增长,不断充裕的物质财富使得出生于20 世纪60 到80 年代的一代人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相对于金钱、物质消费、安全与秩序等,他们更关注自我实现、种族与性别平等、公民政治参与和生态环境等问题,即从关心物质价值转向关心后物质价值(丛日云, 2018)。 1971 年,美国政治学家Inglehart 通过分析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s)调查数据,对引起价值观变迁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理论的两大假设,同时预测了价值观变迁的方向和价值观变迁将会带来的影响(Inglehart, 1971)。 1990 年,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数据的分析,Inglehart 证实了他之前提出的代际价值观变迁假设,正式确立了后物质主义理论。
2 后物质主义的理论假设
2.1 稀缺性假设
稀缺性(scarcity)假设是指“一个人优先考虑的事物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 那些相对来说短缺的事物会被给予最大的主观价值评价”(Inglehart, 1990)。 这体现了经济学理论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在一定时间内消费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个体从该商品的连续消费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 在心理学领域,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 只有当这两种需要获得满足后人们才会考虑如归属、 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要(Maslow,1943)。如果说生理和安全需要更多反映的是个体的物质主义价值观, 那么更高层次的需要则可以归属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有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负相关, 而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呈正相关(Petersen & Lindström, 2010; Wang,2016)。 Novy 等(2017)也发现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后物质主义倾向越强。 这说明了,对于那些物质财富匮乏、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人们来说,他们很难发展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 (Wilson, 2005)。我国学者佟德志和刘琳(2019)通过研究WVS 数据也发现,我国居民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休闲时间、民主权利、 环境保护等后物质主义价值的需求日益增长。
2.2 社会化假设
在社会学中,社会化(socialization)指的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通过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劳动技能、价值规范等来获得一种持续的、终身的体验并适应社会的过程”(Macionis, 2013)。 而由于一个人早期形成的性格特征和人格结构很难会在成年后发生重大改变, 因此早期的社会化经历要比成年期更为重要(Inglehart, 1990)。 这解释了那些出生于二战前后,经历过战争、饥饿等死亡威胁的一代人在得到安全环境及物质财富之后, 仍然会保留着物质主义价值观。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老一辈人与新一代人有关生存问题的价值冲突也会逐渐显现。 在老一辈的人看来,生存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则认为, 生存和生活实质上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这种对于生存问题截然不同的态度使得老一辈人仍然非常看重物质财富, 而新一代人则更加注重自尊意识、自我表达、生活品质、环境保护等非物质性追求。 Wong 和Wan(2009)发现,随着中国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于后物质主义, 并且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多地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魏莉莉(2016)对中国90 后和80 后的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90 后比80 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 一项针对西班牙群体价值观的研究发现,18 到35 岁的青年群体在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未确定这三者间的分布差异不显著, 而在35 到60 岁以及60 岁以上这两个群体中, 选择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个体数量显著高于另外两个选项(Roales-Nieto, O’Neill, Preciado, & Malespín, 2013)。
社会化假设同时也补充说明了稀缺性假设的不足,即经济繁荣和物质安全只是后物质主义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例如,有研究发现,爱沙尼亚人的价值观在后苏联时期并没有任何向后物质主义发展的明确开端,尽管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升,但物质保障和安全问题仍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 这可能与该国历史上屡遭侵略、 政权上反复更迭等因素密切相关(Kheinla & Derman, 2011)。 不同的政治制度也会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Shan,2018)。Yang 和Cho(2018)通过分析WVS 数据探讨了为什么大多数韩国人仍然是物质主义者。 尽管韩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飞速发展,但由于福利制度缺乏、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以及政治改革, 使得韩国人担心实际收入减少以及失业风险, 这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安全感, 也使得大多数人更倾向于物质主义价值观。 教育和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后物质主义,但这些因素并没有超过一个不安稳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后物质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3 后物质主义的测量
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始于1981 年,每隔大约5 年使用一个共同的问卷在近100 个国家进行一轮调查。WVS 旨在帮助科学家和决策者了解世界各地人们的信仰、价值观和动机的变化。Inglehart 关于代际价值观变迁的一些主张便是基于历年的WVS数据。
最初,Inglehart(1971)认为,关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选择需要以牺牲另一种为代价,并且他将这种权衡应用在了测量方法上。 他采用了一道四选项的题目, 让被试选择其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两个选项: 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选项中做出选择,您认为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第二重要?(1)维持国家秩序。(2)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给予人民更多话语权。 (3)对抗物价上涨。 (4)保护言论自由。
选择1 和3 的被试被认为是“物质主义者”,选择2 和4 的被试认为是“后物质主义者”,选择任何其他组合的被试被认为是“混合者”。 这道四选项的题目作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测量指标已被各国研究者广泛使用(Tranter, 2010)。 然而,Inglehart 关于价值观变化的观点在几个方面都受到了批评, 特别是关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概念和测量指标的效度问题。
在概念上, 后物质主义价值范式长期以来就认为, 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单一连续体的两端或两个独立维度的价值观, 而忽视了它们之间交互的可能性。 Giacalone 和Jurkiewicz(2004)使用修订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量表(R-MPMI)评估这些价值观在预测个人和社会认同 (dimensions of personal and social identity, DPSI)时的效用。 结果表明, 两者交互式的概念相比于两者单独时的概念解释了DPSI 的更多差异。 因此,有必要对后物质主义概念进行重组。还有研究者认为,后物质主义指标更像是在测量民主价值(Warwick, 1998)。
在测量上, 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单一题目的测量缺乏信效度(Davis & Davenport, 1999),并且不能充分反映这些选项在被试眼中的重要性程度,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失业也是一种重要的指标(Sacchi,1998)。此外,该测量还存在指标的敏感性问题,即后物质主义指标对短期经济波动(如石油危机、经济危机) 比 较 敏 感 (Kyvelidis, 2001; Yang & Cho,2018),Inglehart 本人也认可了这一点, 因此这种测量的效度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Ippel, Gelissen 和Moors (2013)通过数据分析发现,Inglehart 后物质主义指标存在跨时间一致性和跨文化不一致性。
从1995 年 开 始,Abramson 和Inglehart(1995)将WVS 中的有关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选项数量增加到12 个(原来的4 个选项和8 个新选项)。 这12 个选项中有7 个选项属于物质主义价值观,另外5 个属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它们被分成三道题目:
a.人们有时谈论今后十年我国应该有什么样的目标。请问您认为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第二重要?(1)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2)保证国家强大的国防力量。(3)看到人们在工作和社区中有更多话语权和决定权。 (4)努力让我们的城乡更美丽。
b.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选项中做出选择,您认为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第二重要? (1)维持国家秩序。 (2)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中给予人民更多话语权。(3)对抗物价上涨。 (4)保护言论自由。
选购冰鲜鱼时,重点看三个部位:鱼眼、鱼鳃、鱼的肛门。新鲜的鱼眼球突出,光洁明亮,不新鲜的鱼眼灰暗无光;新鲜的鱼鳃呈鲜红色;新鲜的鱼肛门收紧,不突出。
c.如果您不得不在下列选项中做出选择,您认为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第二重要?(1)稳定的经济。(2)社会变得更博爱而不是缺乏人情味。 (3)社会变得更为看重观念而非金钱。 (4)与犯罪作斗争。
被试的量表计分由他们所选择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选项的个数决定,从0(物质主义者)到5(后物质主义者),分数越高,表示越倾向后物质主义。
有研究者表示,认可一组价值观(无论是物质主义价值观还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都不会自动排除对另一组价值观的认可。 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要求被试按照12 个项目的重要性进行比率分配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选择 (Wilson, 2005)。 此外,Kyvelidis(2001)发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测量存在跨文化比较的问题,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试对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例如,日本被试更倾向于将“努力让我们的城乡更美丽” 这一项归属到后物质主义中去, 因为他们认为这一项意味着环境保护而非城市物质经济发展带来的繁荣。
4 后物质主义的相关研究
自后物质主义理论提出以来, 有不少研究者使用其中的概念进行实证研究, 与心理学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价值观、幸福感、健康和环境保护方面,下面将分别进行介绍。
4.1 后物质主义与其他价值观
Rokeach(1973)认为,人们的各种价值观念是以相互联系的方式共存于一个大的价值观系统中的,因此, 任何单一的价值观只有被置于此系统中来理解才更有意义。 为了清楚地阐明各种类型价值观之间的结构关系,Schwartz(1994)提出了价值观环状模型,他将人类普遍具有的10 种类型的价值观(享乐主义、成就、权力、刺激、自我定向、普遍性、慈善、传统、遵从、安全)分为两个维度(自我提高/自我超越、对变化的开放性/保守)。 有研究者探索了Inglehart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56 个项目的社会价 值 问 卷 (Social Values Inventory; Schwartz,1992)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后物质主义与自我定向和普遍性动机呈正相关, 与安全动机呈负相关(Wilson, 2005)。
Wang(2016)考察了中国消费者社会地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客观社会地位与后物质主义呈正相关, 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被试倾向于更注重商品的情感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还有研究者发现,物质主义者、混合者、后物质主义者在价值观差异、国力和国家秩序、左/右态度,还有国际间的和谐平等这些价值态度上有显著差异 (Braithwaite, Makkai, &Pittelkow, 1996)。
4.2 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和健康
还有研究者对后物质主义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例如,Flouri(2005)发现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心理健康无显著相关,但在加入自我效能感之后发现,物质主义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 而自我效能感又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躯体健康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非常强的正相关, 而心理健康与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都无显著相关 (Petersen & Lindström,2010)。
4.3 后物质主义与环境保护
有研究表明,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能够解释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Dorsch, 2015)。 Mayerl 和Best(2018)分析WVS 数据发现,在富裕国家,民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环保意识显著相关, 而在较贫困国家,这一相关不显著。 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Zhou, Ye, Geng 和Xu(2015)探讨了内隐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环保行为之间的关系。 60名中国学生完成了内隐联想测验和环保行为问卷,随后在情境模拟实验中测量实际的环保行为。 结果显示,内隐后物质主义显著预测了环保行为意向,而内隐物质主义则显著预测了实际环保行为。这表明,对于中国人来说, 物质主义是他们实际环保行为的重要动机。 南非研究者Loubser(2018)也发现,相比人均GDP 水平较高的国家而言,较不富裕国家的后物质主义者更看重物质经济发展而非环境保护。
除了个人层面之外, 政治层面上也有越来越多以保护生态环境、 反对经济无节制增长作为主要政治主张的绿党开始进入政治舞台。 例如,Winkler(2016)考察了日本自民党从1956 年到2013 年竞选宣言的变化, 发现了由关注经济问题和福利政策向后物质主义政策(如环境保护)的转变。
5 小结与展望
已有的研究验证了后物质主义的两个假设。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 人们的生活状况显著改善,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环保、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生存需求和物质财富得到保障之后,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后物质主义价值议题。然而,目前关于后物质主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有待加强。
首先是后物质主义的概念界定及其与物质主义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指出,后物质主义与自由主义还有民主价值非常相似(曾竞, 2018),如何明确地界定后物质主义概念是后续研究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有研究发现,物质主义位于Schwartz 价值观环状模型中接近自我提高(如享乐和权力)的位置(Burroughs & Rindfleisch, 2002),而这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相关的自我定向和普遍性的位置刚好相对。那么,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究竟是一个维度的两端还是两个独立的维度呢?有研究者认为,相对于两者独立的概念来说, 一维的概念能够解释其他变量更多的变异 (Giacalone & Jurkiewicz, 2004),而也有研究者尝试用二维的模型去取代现有的单一维度的概念(Promislo et al., 2017)。 这个问题目前还未有定论。 进一步完善对后物质主义与物质主义这两个概念的辨析, 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人类动机和价值观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 由于后物质主义的测量主要源自WVS中的个别题项,不仅信效度饱受质疑,而且与常用的心理学量表在形式和计分上都大相径庭。 不过,在WVS 数据库中,有很多题项涉及经济增长、城市发展、公民自治、言论自由等有关后物质主义的问题,并且更为丰富和详细。 我们可以采纳WVS 中合适的题项,并参考心理学领域一些成熟的价值观量表,如Richins 和Dawson(1992)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s Scale)、Rokeach(1973)的 价 值 观调查量表(The Value Survey)和Schwartz(1992)的社会价值问卷(Social Values Inventory),在后续研究中编制形式和内容上都更标准更符合心理测量学规范的后物质主义量表。
再次, 已有研究虽然考察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社会地位、幸福感、健康、环保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基于问卷调查的相关研究,对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关系背后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揭示不够。 未来研究可以尝试采用更为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实验法、追踪调查法等,同时, 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变量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更为深入和细化。
最后,Inglehart 的后物质主义理论是基于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提出的, 而本土化的研究应更多地考虑中国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尽管大幅提高但发展很不平衡。 2003 年中国人均GDP 首次突破1000 美元,2007 年则超过了2000美元,根据其他国家以往数据,这是衍生后物质主义的临界点(陶文昭, 2008)。 除了经济发展不平衡之外,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中国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代际巨大差异。 Inglehart(2013)认为,在20 到25 年后,中国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价值观代际变迁, 并且最有可能发生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一代人身上。 他们可能会有着与传统价值观相异的社会诉求, 当这种诉求与现实的社会规范发生冲突时, 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节与疏导是亟需研究的问题。 如今,中国进入了注重质量、追求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有研究者指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中国正在践行的科学发展观在思想理念上具有契合点(如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并且, 衡量一个社会的发展不仅要看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看非物质方面的发展水平(杨玲, 胡连生, 2013)。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之下, 民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产生与发展是否会有不同的趋势?我们可以将受教育程度、政治制度、集体/个人主义倾向、独生子女文化等作为自变量或控制变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