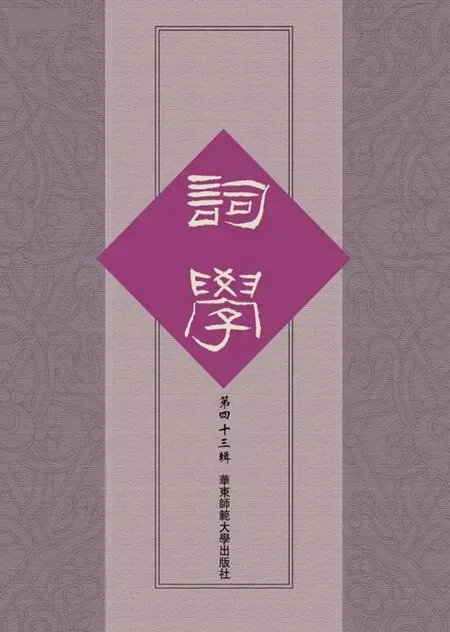凌雲健筆意縱横
——施蟄存詞學研究歷程與成就平議
劉效禮
内容提要 施蟄存先生爲二十世紀詞史最具國際視野、融匯中西學術和突破舊藩籬開創新格局的詞學宗師。本文簡要回顧施蟄存先生研治詞學經歷、主要詞學著作出版過程;《北山樓詞話》所映現的施蟄存研治詞學的主要特點;施蟄存與時俱進的詞學發展觀,他爲詞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和世界所作的堅持不懈的努力。
關鍵詞 施蟄存 詞學 《北山樓詞話》 《詞學名詞釋義》(譯注本)
新加坡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嚴壽澂教授的《〈北山樓詞話>論詞要義》於《詞學》第四十一輯發表後[一],在海内外詞學界頗獲讚譽。近二十年來晚清民國詞人和二十世紀詞史成爲詞學研究的熱點,有關研究文章和專著連篇累牘紛紛揚揚,頗有目不暇接之勢,但似大都没有或語焉不詳地甚少涉筆於施蟄存先生。本世紀初,在施先生百歲壽辰之際,曾有一篇全面論述施先生卓越詞學成就的論文,即臺灣詞學名家林玫儀教授的《施蟄存先生的詞學研究》,此文於二〇〇三年刊於香港《文學世紀》,並收入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慶祝施蟄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但均因發行量過於稀少,因此一般詞學愛好者很難讀到。由於施先生在二十世紀詞學發展中卓有成就,也因創辦《詞學》專刊而在海内外詞學界的廣泛影響籠罩至今,筆者認爲對施先生在近現代詞學發展史上的傑出貢獻做進一步深入研究極爲必要,因此,不揣淺陋,爲推介和宣揚北山樓詞學勉盡微末之力。
一 施蟄存研治詞學暨主要詞學著作出版歷程
施先生八歲甫入松江第三小學時,即從父親藏書中閲讀詞學書籍如《白香詞譜》、《草堂詩餘》等並學習填詞[二]。他三十初度在主持中國現代最有影響的綜合文學刊物《現代》後,又在上海雜誌公司主編「中國文學珍本叢書」,並在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十月完成叢書中明毛晉編《宋六十名家詞》一至六集的點校[三],改正了原本輯刻中的疏略錯誤,使這套現存最早刻印的宋詞總集能普及於世。
我國古代學者關於詞學文體的評論,除少量專著形式外,多見於詞話和各種版本詞籍的序跋。前者有唐圭璋先生編纂的《詞話叢編》,後者有施先生編纂的《詞籍序跋萃編》:
一九六〇年秋收後,我從嘉定學習回來,被安置在中文系資料室工作。我偶然想到在古典文學領域中關於詞的理論和評品,最少現成的參考資料。古人著作如《詩品》、《文心雕龍》、《文鏡秘府論》,都還講不到詞。宋人詞論著作也只有簡短的《詞源》、《樂府指迷》等三四種。元、明以降詞話之類的書也遠不及詩話之多。因此在各種詞集的序跋題記中,可以搜集到不少關於詞的評論的史料,如果把它們輯爲一編對詞學的研究工作不無用處。於是我決心抄録唐、宋以來詞籍的序跋。[四]
這部書稿歷經時局動盪和各種曲折磨難,終於有幸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凡十卷,包涵唐五代詞、宋詞、遼金元詞、明詞、清詞的别集序跋,詞總集、選集的序跋,以及詞話、詞譜、詞律及其他詞學雜著的序跋。全書各篇序引跋記涉及不同傳本的校勘評騭,源流系統的考論溯證,詞人詞作的品賞評定,格律聲韻的辨證校訂,可謂内涵豐贍、菁華畢具,是與《詞話叢編》互相補充,也是詞學研究者案頭必備的重要詞學研究工具書。
抗日戰爭期間,施先生在内遷於福建長汀的厦門大學任教,「盡讀其圖書館所藏宋元人筆記雜著」,鈔出「有關詞學之評論瑣記」編爲《宋元詞話》。[五]此稿久儲篋中四十餘年,經陳如江增補後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在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施先生認爲此書「可以爲唐圭璋《詞話叢編》之補編」[六]。此書問世二十年後仍因其雅俗共賞的特徵,而在互聯網上獲得眾多網民由衷的喜愛:「這本書確實是摘録了很多有趣的材料,看過它之後再去讀詞别有一番風趣。也可以當做筆記小説來讀,小小的軼事中我們發現原來古人和我們一樣喜怒哀樂,小尷尬,會心一笑中擁有了一趟不虚的旅程。」[七]
一九九九年一月,與陳如江合作體現宋詞演進大體走向的《宋詞經典》在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施先生在「前言」中説:「每一首詞都是一個世界,都是詞人開闢的一塊天地。面對這麼一個豐富的世界,美妙的天地,我們在每首詞的『解題』中儘可能地根據作者創作的年月、地點、際遇、心境、意圖及慘澹經營的匠心作一番簡明扼要的闡釋剖析。」[八]
一種文學形式從萌芽到定型,需要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這種已定型的文學形式,還需要另一個過程,才能確定其名稱。施先生認爲詞從詩分化出來,逐漸發展而成爲脱離了詩的領域的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其過程是從盛唐到北宋,幾乎有二三百年的時間,而最後把這種文學形式定名爲「詞」,還得遲到南宋中期。他涉及詞學二十年後,終於在整理研究詞籍序跋的過程中,才將「長短句」、「歌辭」、「曲子詞」、「樂府」、「樂府雅詞」、「近體樂府」、「詩餘」這些千年詞學長河發展初期陸續映現的基本名詞,嚴謹清晰地在詞學學理上界定清楚。曾有學者以爲:「詞,這一文體,在唐宋時期不大爲人所重視,是以『詩餘』而出現的。」[九]施先生指出這句話失於考證:「可知他没有注意到,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始終没有出現『詩餘』這個名詞,再説『詩餘』這個名詞,並不表示宋人不重視詞,恰恰相反,還因爲詞的地位愈來愈被重視,故名之爲『詩餘』,把它們推進了詩的行列。」[一〇]
歷代詞人及詞論對詞學基本名詞頗多歧義,有些現代辭書甚至連長短句的注釋都不夠正確。[一一]有鑒於此,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文史知識》月刊向施先生約稿後,他在該刊一九八四年第五期至一九八六年第二期連載《詞學名詞釋義》。中華書局於一九八八年六月將連載各文薈萃成書,收入「中華文史知識文庫」,常銷至今。
詞本來是流行於民間的通俗歌詞,使用的都是人民大眾的口語。施先生認爲唐五代的《花間集》裏所收的五百首詞就代表了早期士大夫所作曲子詞,「《雲謡集》是民間的俗文學,《花間集》是知識份子的俗文學」[一二]。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間集》曲子詞的規格體制,選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宋花間集》,一九六四年又選了一部《清花間集》,使埋没隱晦已久的「花間」傳統在這兩個選本中再現其風格和傳統。一九八七年始應浙江古籍出版社之請,「同意把這部書稿印出來,爲古典文學愛好者開闢一個視野,爲我自己留下一個文學巡禮的蹤跡」[一三]。嚴壽澂和林玫儀教授都對這本《花間新集》予以崇高評價。嚴壽澂説:「蟄存師以爲《花間》傳統之可貴,正在於發乎情的自然之致。結論是『理學興而賦學絶,貫道之説出而抒情之才盡。此唐五代詞之所以不可復、不可學也』。」這一段話,「不僅是夫子論詞要義,更可視爲對整個文學傳統的看法,即文學當尚情而不尚理」[一四]。林玫儀認爲:此兩書均「别開蹊徑」,兩相比較,《清花間集》益形重要。一般都對清詞較爲生疏,清人詞作又醇駁互見,此書於各家作品後皆有精彩評論,乃是施先生詳閲清詞别集近三百種後,幾經斟酌,復參考前人詞話評論,有的綜論諸家之造詣得失,有的駁斥前人之説,對於清詞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標作用。[一五]林玫儀薈萃施先生主要詞論著作的《北山樓詞話》收入《施蟄存全集》後,獲得第十三届上海圖書獎二等獎。
二 施蟄存研治詞學的主要特點
施先生説:「一九六〇年代,分類編了詞籍的目録,給許多詞集做了校勘,慢慢地感覺到詞的園地裏,也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於是才開始以鑽研學術的方法和感情去讀詞集。」[一六]
「考證」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研究方法,施先生經常運用考證的方法,謹嚴、縝密地辨僞存真,解決了詞學中許多聚訟紛紜或久懸難決的千年之謎。如收入《北山樓詞話》中的《説「詩餘」》、《張志和及其漁父詞》、《船子和尚撥棹歌》、《説〈楊柳枝>、〈賀聖朝>、〈太平時>》、《唐詩宋詞中的六州曲》等,他都對其中的詞學名詞或句法或詞調,對它們在詞學發展過程中的出現、衍變及其確切含義,放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及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了科學的論證,這些文章言簡意賅,有的僅千餘言,但均義藴深厚,考證嚴密,邏輯謹嚴,勾畫映現了中國詞學史發展的鮮明脈絡。又如《説〈憶秦娥>》、《白居易詞辨》二文,前文在考證《憶秦娥》詞調格律演變之跡後指出,《憶秦娥》實爲宋人樂遊原懷古詞,此詞非先有詞而後有題,乃先有題而後有詞;此所謂李白詞者必不能出於張先、馮延巳以前,其爲宋人所撰僞託李白所作已無可懷疑。[一七]後一文則揭示歐陽修《近體樂府》「長相思」即《花庵詞選》所録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施先生在詳盡考證後指出,歐陽修讀白居易詩於「暮雨瀟瀟」句也心賞之,遂取以入小令,因此所謂白作《長相思》三首並非唐詞,均應還諸歐陽修。他還清晰地指出近年問世的《全唐五代詞》收白居易詞三十七首,舊本所無而新增者均爲齊言之詩,或用曲調名爲題,或用唐人一般舞曲題,其詞仍是五七言歌詩,不能視之爲詞。又一字至七字疊句詩,爲六朝時已有之雜體詩,並非白居易創調,此書也誤依《詞譜》題爲《一七令》著爲詞格。[一八]
「比較」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研究方法,而「比較文學」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施先生的詞學研究對這兩種比較都運用得很廣泛。前者如他在《讀温飛卿詞札記》中把温庭筠和李賀、李商隱相比較,在《讀馮延巳詞札記》中把馮延巳和温庭筠、韋莊相比較。[一九]施先生對這種傳統的比較研究方法運用得如行雲流水般洗煉而頗具新意,往往直指古人用心之隱微曲折處,别具法眼,道人之未言。他既爲聲譽卓著的外國文學研究權威和翻譯名家,自然會在詩詞研究中引入與外國文學及異域語言的比較。如他在《唐詩百話》中把李賀同英國天才詩人却透頓(查特頓)和濟慈進行比較研究,把唐王梵志詩和古希臘的「説教詩銘」(又稱「格言詩銘」)進行比較研究。外國文學研究名家倪蕊琴教授在《難忘的教益》中説「施先生自覺地在教學中運用比較文學研究方法」,她引用施先生自己的話説:「當我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的時候,有時引述外國文學的例子。反之,當我講授外國文學時,我也會引用中國文學爲例子(我講過一年歐洲文學史,一年歐美小説史)。」[二〇]施先生在《歷代詞選集敘録》中指出,歐陽炯解釋《花間集》之命名殊不明曉,而他引唐韓愈《進學解》、《説文段注》、《聲類》和古希臘及今歐洲各國稱詩集爲Anthologie,指出古今中外,以花喻詩,不謀而合,「《花間集》之取義,殆亦同然」。[二一]此洵爲學貫中西的博聞通人之解。
施先生的學術研究和他的文學創作一樣均具有極爲鮮明卓越的個性,因而别樹一幟獨具風貌,他的詞論同樣勝義迭出,精湛有力。他尊重傳統,也十分注重發揚傳統,然而却不固守傳統,故步自封,甚至抱殘守缺。最爲難得而又給人啟示的是他的與時俱進的詞學發展觀。他在致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信中説:「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盛極一時,《文心雕龍》因此成爲顯學,我對此現象很不滿意。我覺得,無論對古代文學或對現代的創作文學,都不宜再用舊的批評尺度,應當吸收西方文論,重新評價古代文學,用西方文論來衡量文學創作⋮⋮對外國學者,要求聽聽他們的研究方法,以各種文學批評理論來運用於詞學研究的經驗和實踐。」[二二]他在《樂句與文句》中指出遇到樂句與文句參差的詞,應依文句讀,對平仄更不應站在文本的立場上挑剔歌者:「作曲者、填詞者、唱詞者,都可以發揮各自的創造性,互相截長補短。詞中的『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黄庭堅的寫本作『浪聲沉』。『盡』與『沉』,平仄不同,有人以爲東坡原作應當是『浪聲沉』。這是説東坡没有突破規律,此處仍用平聲字。我以爲『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是一氣呵成的句子,『浪聲沉』三字接不上以下六字句的概念。《容齋隨筆》記録了當時歌女唱的是『浪淘盡』,可知此處用平或仄聲字都可以唱,然則又何必在平仄之間判别是非呢?」[二三]
施先生對詩詞格律與音韻均有精湛的研究,但他却向詞律研究者周玉魁指出:「我以爲詞律不必鑽研,没有意義了。一切文學起源於民間,原來無格律,到文人手裏就會有格律。有了格律,民間就不受束縛,再創造更自由的體式。唐有律詩,而後民間有曲子詞。宋詞有了格律,民間就産生了南戲和北雜劇,這是明顯的例子。不過詞在宋人律還不嚴,萬氏《詞律》所斤斤較量的『又一體』,其實是多一個襯字或減少一個字,宋人並不以爲是二體。有些詞中的『衍文』可能是襯字。我們不必去爲宋詞定語式,所以我説不必研究詞律。」他還進一步揭示説:「我甚至以爲,詞字平仄也不必定死。宋人作詞甫畢即付歌女,她如果覺得不便唱,她會變仄爲平的。去上問題也是如此,她會以上聲唱成去聲的。只要聽今天的歌曲,歌者所唱皆異於我們平時所讀,可見斤斤於平仄,也没意思。所以我不主張今天再考訂詞律。」[二四]施先生認爲「元明以後,詞已不是曲子詞,只能説是古代的白話詩了。」(《致周陶富》)[二五]「詩詞有婉約、豪放二種風格,但此二者不是對立面,尚有既不豪放亦不婉約者在。詩三百以下,各種文學作品都有此二種風格⋮⋮如果寫《詞史》,不宜説宋詞有豪放、婉約二派。」(《致周楞伽》)[二六]施先生洪鐘大吕般的讜論,對那些至今仍酸腐保守地固守以詞之婉約派、格律派爲正宗的詞學研究者和寫作者來説,無異於石破天驚般的棒喝。「筆墨當隨時代」,「唯陳言之務去」,固守婉約、格律千年不變只能促使詞學的發展和詞的創作走向衰落和滅亡。
施先生所創辦和主編的《詞學》爲我國唯一以研究歷代詞學和促使當代詞學發展爲宗旨的學術專刊,也早已經爲廣大詞學研究者所必讀而蜚聲於海内外,被稱譽爲「中國詞學界的一面旗幟」、「我國最具獨特品位和風格的學術專刊」。《詞學》創刊時,施先生殫精竭慮地運用他在學術界和文藝界各方面的良好關係,幾乎將在我國詞學界卓有聲譽的名家都盛情邀請列名於編委會内,爲了進一步擴大《詞學》的影響,又在主編名單中謙讓地位列第三,盛邀懇請詞學宗師夏承燾、唐圭璋列名於前。在施先生的建議、推動和指導下,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舉辦召開了新時期以來第一届詞學討論會。施先生和夏承燾、唐圭璋均在大會開幕式致書面開幕詞,五天盛會將結束時宣告成立中國詞學會籌備委員會,並推舉夏承燾爲名譽主任,唐圭璋爲主任,施蟄存爲副主任,馬興榮爲秘書長,各有關方面和人員也在學會職位上各安其位。[二七]鬱歟盛哉,充分映現了我國詞學界空前大團結的繁盛勝景,也時時處處顯示出施先生的博大胸懷和良苦用心。現在《詞學》第一至十二輯的《編輯後記》,施先生在《詞學》上發表的詞論,以及他的詞學文獻學、版本學、目録學研究,都已薈萃於《北山樓詞話》,爲我們對詞史和詞學理論廣泛深入的研究提供了極大便利。
三 施蟄存與時俱進的詞學發展觀
施先生極具國際胸襟、世界視野,他研究詞學之始即關注詞學匯入於中外文化交流。他是我國百年來詞學家中引領、促使詞學走出國門融入世界文學的第一人。
施先生在中學就讀時的部分課本即爲英國原版教材,他在之江大學攻讀的也是英語專業。其後他在震旦大學的法文特别班曾和戴望舒、杜衡等一起接受過在該校任教的法國天主教神父樊國棟的嚴格講授和訓練,並每周都要完成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法語的作業。[二八]雖然他因接受現代書店之聘擔任了《現代》主編,而不能和戴望舒等一起赴法留學,但當時上海爲最爲開放的遠東第一大城市,英美新出書刊轉瞬即出現於上海,因此也使他能及時瞭解世界。美國哈佛大學李歐梵教授説:「我有時候對我的學生説:我們這一大堆學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現代文學,恐怕還比不上卅年代的一個年輕人——施蟄存先生⋮⋮我問他任何冷門問題,他都對答如流,令我自慚形穢。」[二九]「文革」後中國作協、全國文聯恢復召開大會時,當時尚未對他全面落實政策,因他翻譯西方文學作品的卓越成就,邀他出席的代表身份是「翻譯家」。二〇〇二年二月,中國翻譯家協會正式爲他頒發「中國資深翻譯家」的榮譽稱號。[三〇]
香港《文學世紀》主編辜健編纂整理的《施蟄存海外書簡》,由河南大象出版社收入「大象人物書簡文叢」,於二〇〇八年四月問世。這是中國詞學家的第一本海外書簡集,共收録施先生「文革」後至二十世紀末與海外各界學者的通信約三百封。二〇一二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施蟄存全集》,收録施先生約一千通書信,其中與歐美、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文友學人的通信近五百封。二〇一四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從北山樓到潛學齋》,收録了施先生與美國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主任、《劍橋中國文學史》主編孫康宜的七十二次來往通信,並附録致著名詞人張珍懷、詞論家康正果、書畫家張充和以及錢歌川、吴琦幸、劉慧娟等的有關信件。孫康宜在本書序言《來自北山樓的信件》中説:
在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期間,我就是那些從海外向施先生求教者之一。那時我剛開始研究明清文學和中國女詩人。雖然已在耶魯大學當起「教授」,但我却把自己視爲施老的「研究生」。我經常在信中向他提出有關古籍和研究方法的問題,而他總是每問必答,爲我指點迷津,而且還爲我旁搜各種典籍和文獻,不斷托朋友帶書給我⋮⋮施先生還爲我打開他的「北山樓」的四面窗。施老的「治學四窗」是世界有名的,他會按朋友的需要隨時打開任何一窗。他的四窗包括古典文學研究,西洋文學的翻譯工作,文藝創作和金石碑版之學⋮⋮他還特地爲我手書杜甫的佳句「清辭麗句必爲鄰」,以爲紀念。[三一]施先生致孫康宜的信也極爲坦誠,如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信中説:「你的書名《詞的演進》用E v o l u t i o n,我不知道和『發展』(Development)如何區别?在文學上,一般總用『發展』而不用『演進』,你的中譯本是否還是改用『發展』較好,或者用『演變』如何?」[三二]又如此年十二月十二日信中説:「映然子詞不甚佳,視柳如是、王修微,瞠乎遠矣。又,稱詞爲『詩餘』,曲爲詞,此一觀念大可注意,蓋沿襲元人之觀念也。宋人稱詞爲『詩餘』,當時未立詞名,故以詞爲『詩人之餘事』,卑之也。元明人以曲爲詞,尊曲也。曲即爲詞,則詞爲詩餘,此時之『詩餘』,乃詞之尊稱矣。此意前人所未言,我從《吟紅集》中悟得之,足下以爲可取否?」[三三]
林玫儀教授是中國臺灣地區最負盛名的詞學家之一。她認識施先生以後,每次來滬都直趨施先生書房就教,逐漸由師生親如父女,施先生最後一次在華東醫院住院時,她與其先生整天整夜在病床旁陪侍看護。她在《施蟄存先生的詞學研究》中説:「認識施先生是我的福分。我與先生相識,完全因爲詞學。施先生對我近年來的研究方向影響極大,透過他的著作,以及多年的通信與談話,我從施先生身上學到很多,除了學問方面,還有做人的道理。」[三四]她深感施先生提携後學不遺餘力:「我與先生相識時,先生已是譽滿中外的學術泰斗,我不過是個後生晚輩。先生偶然看到拙作,就托吴興文先生於返臺時帶來《詞學》一册,並且向我邀稿,此種胸襟氣度令我敬佩不已。多年以來,先生對我多所勉勵,對於我的研究工作,亦不時加以指點,且多次惠贈大批珍稀詞籍。贈書大大擴展了我的詞學研究範圍,促使我注意到詞籍版本的問題,從而開展研究詞學之新角度。這份知遇之情我深深銘記在心,但難以爲報。」[三五]
四 融匯中西學術,突破舊藩籬開創新格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施先生創刊《詞學》時的學術視野即遍於海内外,每輯刊物均會盡力刊用海外稿件,並在《編輯體例》中再三申明、邀約,他並親自將每輯刊物目録譯成英文刊出,在「新得詞籍介紹」專欄外,另辟「中國港臺版詞籍經眼録」。在不時報導詞學在日本、韓國、越南、歐美的存在、發展外,原擬編爲「美國詞學研究專號」的第九輯,擴展爲一九九二年一月出版的「海外詞學研究專號」,由此也進一步推動了北美詞學研究成爲「顯學」。施先生在《詞學》除刊出使用考證、校勘、比較、歸納等傳統方法研究的論文外,還注意刊出使用西方現代美學理論如接受美學等研究詞學的論文,從而推動詞學融入二十世紀社會科學現代化的大趨勢。
日本宋詞研究會對施先生《詞學名詞釋義》評價極高,認爲此書極爲清晰地揭示了聚訟千年的詞學名詞的淵源與演變,對詞學研究和創作均極有啟示。二〇〇五年三月該會會刊《風絮》創刊,便自創刊號至二〇〇九年三月第五期分期全部連載此書。該會詞學名家荻原正樹、明本茂夫教授和保苅佳昭博士等分章節將《詞學名詞釋義》譯成日文,對書中提及的人物、典故、筆記、詞集與歷史和文化背景作了極爲詳盡的注釋,又以「參考」爲名提供詳細的文獻資料。在《風絮》全部連載完成後又經整理修訂,於二〇〇九年三月由東京汲古書院推出完整的精裝日文注釋版。施先生是現代詞學家中詞學專著被譯注成外文並在異域連載、出版的第一人。他生前大力促成「詞學西行」,身後他的詞學遺産又爲「詞學東行」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貢獻。
「業師施蟄存夫子,精於詞學,論詞一空依傍。」(嚴壽澂)[三六]「吟壇雄踞最高層。」(吴小如)[三七]「蟄存先生知識修養面極廣,凡所著譯,都站得住,有特點,不做則已,做必有顯著的個性,文詞則清新俊逸,有詩情韻味,一如其人。」(徐中玉)[三八]「施先生屬於二十世紀,二十世紀的現代文學精神也屬於他。他是能够和那個時代的世界文藝潮流同步的人。」(李歐梵)[三九]「先生是不世出的奇才」,「先生是至情至性人,他的才識、風骨,無人不欽佩」。(林玫儀)[四〇]北山樓詞學體系氣象萬千,襟抱氣度,雍容磊落,特有高朗之致。詞學遺産也博大精深,千匯萬狀,意格閎曲,澄澹俊邁,書法清妙,頗有新意啟示於讀者。他親自主編的《現代》綜合文學雜志和《詞學》,早已成爲二十世紀不朽的文林圖籍經典和熱門的學術研究課題。北山樓學術遺産和詞《學辦》刊傳統一定會更加發揚光大。
[一][一四][三四][三六]嚴壽澂《〈北山樓詞話>論詞要義》,《詞學》第四十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第三〇一頁,第三〇四頁,第三〇一頁,第三〇一頁。
[二]黄德志、蕭霞《施蟄存年表》,《淮陰師範學院學報》二〇〇三年第一期。
[三][三〇]趙淩河《施蟄存文學著譯年譜》,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第一二八頁,第三五四頁。
[四]《〈詞籍序跋萃編>序引》,林玫儀編《北山樓詞話》,劉凌、劉效禮編《施蟄存全集》第七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八五頁。
[五][六]《〈宋元詞話>序引》,《北山樓詞話》,第二八七—二八八頁。
[七]國學數典網,h t t p://b b s.g x s d.c o m.c n/f o r u m.p h p?m o d=v i e w t h r e a d&t i d=146721。
[八]《宋詞經典前言》,《北山樓詞話》,第二九四頁。
[九]金啓華、張惠民等《唐宋詞集序跋彙編》,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第一頁。
[一〇]《唐宋詞集序跋彙編》,《北山樓詞話》,第三三四頁。
[一一][一二]施蟄存《詞學名詞釋義》,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第七頁,第四頁。
[一三]施蟄存《〈花間新集>序》,《北山樓詞話》,第二八三頁
[一五]林玫儀《施蟄存先生的詞學研究》,《慶祝施蟄存教授百歲華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七五頁。
[一六]施蟄存《〈詞學名詞釋義>引言》,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版,第一頁。
[一七][一八][一九]《北山樓詞話》,第二六二頁,第二六三頁,第四四五頁,第一八八頁。
[二〇]倪蕊琴《難忘的教益》,《夏日最後一朵玫瑰——記憶施蟄存》,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六九頁。
[二一]《北山樓詞話》,第一三四頁。
[二二][二四][二五][三二][三三]《北山散文集》第四輯,《施蟄存全集》第五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一五六頁,第一九七六頁,第二一三五頁,第二一六八頁,第二一七二頁。
[二三][二六]《北山樓詞話》,第三〇〇頁,第三二三頁。
[二七]參見《詞學》第三輯「詞學討論會」記者報導,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三〇一頁。
[二八]參見《震旦二年》,《北山散文集》第一輯,《施蟄存全集》第二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三二三頁。
[二九][三九]李歐梵《廿世紀的代言人:慶賀施蟄存先生百歲壽辰》,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十三頁,第十二頁。
[三一]孫康宜《〈從北山樓到潛學齋>序言》,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六頁。
[三五][四〇]林玫儀《悼念施蟄存先生》,《詞學》第十五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第二九一頁。
[三七]吴小如《壬午歲暮恭讀北山樓詩俚句敬題》,《慶祝施蟄存教授華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扉頁手蹟。
[三八]徐中玉《回憶蟄存先生》,《慶祝施蟄存教授華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第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