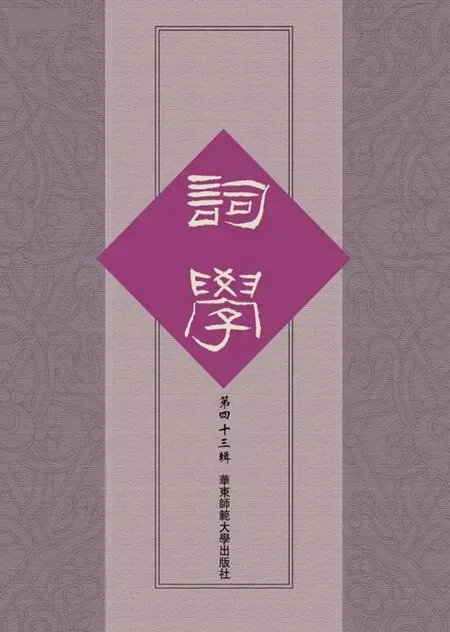詞論中的「魔道」
——金聖歎《唱經堂批
歐陽明亮
内容提要 金聖歎《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雖然撰成於清初,但却是明代「主情近俗」詞學觀念的一次系統的批評實踐。在金聖歎的批點下,歐詞中「言情」、「側艷」以及「淺近」等特徵得到充分揭示,甚至被有意放大。同時,金聖歎還以「論傳奇之法」論詞,探討歐陽修詞的敘事視角,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以及隱含的故事情節。這些理念、方法與清初詞壇逐漸興起的「尊體」、「尚雅」的詞學思潮完全相悖,因此無法得到清代詞論家的認同,乃至被譏爲「魔道」。然而,金聖歎憑藉豐富的批評經驗與獨特的藝術感悟,揭示出歐陽修詞中諸多不爲前人探見的藝術技巧,這些結論又被清代詞論家暗自吸納到自己的批評實踐之中。
關鍵詞 金聖歎 歐陽修 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 詞學批評
清代初年,在批點《西厢記》、《水滸傳》等俗體文學之餘,好以金針度人的金聖歎又以歐陽修的十二首詞作爲範本,對其精心批點,寫成《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一]不過,在歐陽修詞的歷代推崇者中,金聖歎是一位頗爲「尷尬」的人物,這種尷尬表現在:金聖歎對歐詞的批點與推崇不但没有得到清人的認可,甚至還被譏爲「魔道」。事實上,無論是金聖歎對歐詞的批點,還是清代詞論家對金批歐詞的排斥,其背後都有深刻的理論背景。從詞學發展史看,《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是明代「主情近俗」詞學理念的一次系統全面的批評實踐,但正因如此,金批歐詞也必然成爲清代詞論家的清算對象。本文即結合明、清兩代詞學思想的差異、變遷,對《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的批評理念、批評方法以及價值影響略作探討,以祈方家教正。
一 主情近俗:明代的詞學思想與《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的批評理念
在有關詞學史的論著中,金聖歎往往被劃歸清代。[二]然而,無論是從思想觀念、行爲方式或者生活時段上看,金聖歎都更屬於明代,他與明末雲間詞派領袖陳子龍同歲,比清初詞壇巨子陳維崧、王士禛、朱彝尊等年長二十餘歲。以清王朝平定江南的順治二年算起,到「哭廟案」發生,金聖歎在清朝統治下只生活了十六年。此外就金聖歎的思想淵源而言,他深受泰州學派的影響,是在晚明尊崇人性、張揚個性的啟蒙思潮下成長起來的文人。同樣,在詞學理念上,金聖歎的《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也與明代的詞學思想有着更爲密切的聯繫。
明代詞學,尤其是中晚期詞學的總體傾向表現爲兩個方面:一是「主情」,一是「近俗」。所謂「主情」,即將「言情」視爲詞體的基本功能。如王世貞《藝苑卮言》所云:「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爲也。何者?其婉孌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奪嗜。」[三]這一觀念到了明末更爲盛行,如沈際飛在《詩餘四集序》中即表示:「人之情,至男女乃極,未有不篤於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間反有鍾吾情者。」[四]因此,用詞體來表現男女之情成爲最合理、也最正當的創作要求。在「主情」的同時,明代中後期的詞體創作與詞學思想也表現出「俗化」與「曲化」的一面[五],這與明代中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以及文人思想觀念的轉變有密切關係,也是明代散曲的流行、俗文學的發達對詞體創作滲透影響的結果。
這種「主情近俗」的詞學觀念,直接影響到明代詞人對宋詞的接受與評價,其中《草堂詩餘》在明代的持續風靡並不斷翻刻便是最明顯的表現。這部南宋坊間爲應歌之需而編纂的詞選,由於所選之作多以兒女之情爲内容,語言偏於淺近平易,所選詞調也往往屬於聲情舒緩之類,易於表現纏綿之思,因而在明代出現了大量翻刻本和續編本。在翻刻續編的《草堂詩餘》中,明代詞論家留下了諸多批點文字,雖然這些批語往往是隻言片語,且帶有較大的隨意性,因而缺乏深度,不成系統,但却是明代「主情近俗」的詞學觀念最爲直接的反映。
例如明人在評點歐陽修詞時,已不再像南宋曾慥、王灼以及羅大經、羅泌等詞家或學者那樣,或者對歐陽修詞中的側艷之作表示懷疑,或者極力强調歐詞的「風流藴藉」、「温柔寬厚」。相反,對於不再顧忌「言情」的明代詞論家而言,歐詞中的側艷之作不但不需要懷疑或迴護,反而是歐詞最爲動人之處。他們毫不顧忌地推崇歐陽修詞中的此類作品,並對歐詞中的香情艷態予以特别關注,如評《蝶戀花》(越女採蓮秋水畔)「如絲爭亂,吾恐爲蕩婦矣」[六],又評《南歌子》(鳳髻金泥帶)「前段態,後段情」[七],而這些詞作正屬於宋人眼中的「疑以傳疑」之作。
與此相應的是,明人在點評歐詞時,還尤爲重視歐陽修詞的「淺近」,如沈際飛認爲歐陽修《長相思》(花似伊)「真聲不可删」[八]。此處所謂的「真聲」,即指詞作表現出一種類似民歌俗曲的天然之趣。此外,他們還常常將一些曲類作品與歐陽修詞進行對比,或者在歐詞中尋找元明曲家的創作源頭,如將《浣溪沙》(湖上朱橋響畫輪)中「日斜歸去奈何春」一句與湯顯祖《牡丹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予以比較,認爲湯顯祖的句子是本歐詞而出[九],又認爲《生查子》(去年元夜時)一詞與元曲極爲相似,所謂「元曲之稱絶者,不過得此法」[一〇],又認爲「關漢卿詞本此」[一一]。
明代詞論家對歐陽修詞的這些點評角度也正是金聖歎批點歐詞時所秉持的主要理念。在《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中,金聖歎將「主情近俗」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成爲明代「主情近俗」詞學思想的一次系統的批評實踐。
金聖歎的批評理念首先體現在選詞標準上。金聖歎選取作爲範本的十二首歐詞分别爲:《長相思》(深花枝)、《訴衷情》(清晨簾幕卷輕霜)、《踏莎行》(候館梅殘)、《減字木蘭花》(樓臺向曉)、《減字木蘭花》(歌檀斂袂)、《生查子》(去年元夜時)、《生查子》(含羞整翠鬟)、《瑞鷓鴣》(楚王臺上一神仙)、《蝶戀花》(海燕雙來歸畫棟)、《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蝶戀花》(永日環堤乘彩舫)、《蝶戀花》(越女採蓮秋水畔)。其中《瑞鷓鴣》(楚王臺上一神仙)、《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兩詞基本可以判定爲吴融、馮延巳的作品,我們姑且不論。從其他十首作品來看,它們全部屬於歐詞中表現男女情思的側艷之作,而歐陽修詞集中那些境界較爲開闊、抒發個人情志與感慨的作品如《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採桑子》組詞等則一首未選,雖然這些詞作有不少也收録在明人所熟知的《草堂詩餘》之中。此外,金聖歎還分别爲每首作品添加了詞題,以點明它們的創作内容,如「美人」、「春閨」、「寄内」、「艷情」、「歌姬」、「春恨」、「採蓮」、「春睡」、「蕩船」等,由此可見金聖歎對這些詞作的主旨與風格的基本判斷,即純粹表現男女之情、美人之態的側艷之作。總之,金聖歎對歐陽修詞的選擇有著明確的標準,他有意忽略歐陽修詞中其他風格主旨的作品,唯獨鍾情歐詞中的側艷之作、聲色之詞,而這些作品也正是實踐其批評理念、貫徹其詞學思想的最佳範本。
其次,在具體的批點中,金聖歎對歐詞所表現的艷情作了深入的揭示,並有意放大,乃至從中解讀出「妖淫」、「穢褻」的成分。如其批《減字木蘭花》(樓臺向曉):
「樓臺向曉,澹月低雲天氣好」,先説樓臺。「翠幕風微」,漸説到翠幕。「宛轉梁州入破時」,漸説到人。「香生舞袂」,先説舞袂。「楚女腰肢天與細」,漸説到腰肢。「汗粉重匀」,漸説到汗粉。「酒後輕寒不著人」,説到輕寒不妨,則妖淫之極,不可言矣。[一二]
又云:
看他前半闕,從樓臺、翠幕説到人。後半闕,從衣袂、腰肢、汗粉説到説不得處,有步步蓮花之妙。
衣袂、腰肢、汗粉還説得,至末句真不好説得矣。[一三]就詞作本身而言,這首《減字木蘭花》(樓臺向曉)較爲直露地刻畫了一位舞伎的舞姿媚態,的確是歐陽修詞中典型的側艷之作,因此《樂府雅詞》、《花庵詞選》等宋代詞選并未將其選入,然而金聖歎却不但以此爲批點對象,還直接以「艷情」爲題來爲詞作張目,並透過詞作的具體内容揣摩其背後的幽隱情事,力圖將讀者的思路引向所謂的「説不得處」,以證明其「妖淫之極,不可言矣」的評價並非虚語。
這種解詞思路在《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中屢屢可見,如《減字木蘭花》(歌檀斂袂)一詞,描寫的是一位美貌歌姬的動人歌聲,金聖歎對此也做了同樣的解讀。在「櫻唇玉齒,天上仙音心下事」一句的夾批中,金聖歎直白地指出:「更妙於『心下事』,定當私昵穢褻。」[一四]又認爲其中「滿座迷魂酒半醺」句「妖艷」之極。[一五]
除極力揭示艷情外,金聖歎還極爲推崇歐陽修詞中淺俗直白的語言。他對《長相思》(深花枝)詞的上闋「深花枝,淺花枝。深淺花枝相並時。花枝難似伊」評價極高,認爲「四句十八字,一氣注下,中間更讀不斷,真是妙手」,又説「只看前半闋,不用一字,只是一筆寫去,却成異樣絶調」。而對於下闋「玉如肌,柳如眉。愛著鵝黄金縷衣。啼妝更爲誰」,金聖歎則認爲無法與上闋媲美,因爲「後半闋,偏有許多『玉肌』、『柳眉』、『鵝黄』、『金縷』、『啼妝』等字,偏覺醜拙不可耐」[一六]。從用語來看,這首作品的上闋淺露直白,接近口語,極類民歌俗曲,如有論者曾斥之「鄙俚極矣」[一七]。相較之下,詞作下闋則用語稍雅。但金聖歎却以上闋爲「絶調」,以下闋爲「醜拙」,可見他對詞作中淺近類曲的語言不但不排斥,反而情有獨鍾。
總之,在《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中,無論是對詞作内容「妖淫」、「穢褻」的解讀,還是對詞作語言淺近直白的推許,都是明代詞學「主情近俗」理念的全面體現,而金聖歎也正是通過對歐詞的批點,將這一理念推向了極端。
二 以論傳奇之法論詞:《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的批評方法
除了秉持「主情近俗」的詞學理念外,《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還表現出一個鮮明的特色,即金聖歎的批詞之法源自他對戲曲、小説等俗體文學的批評經驗。
具體而言,金聖歎的歐詞批點注重探討詞作的敘述視角,力圖揣摩作品内部的章法結構與詞作情思的關聯脈絡,這一點我們可以在金聖歎的批語中找到諸多實例。如他評點《生查子》(含羞整翠鬟)時稱:「邇來填詞家,亦貪得好句,而苦無其法,遂終成嘔穢。殊不知好句初不在『風雨』、『珠玉』等字餖飣而成,只將目前本色言語,只要結撰照耀得好,便覺此藉彼襯,都成妙艷。」[一八]可見,金聖歎認爲詞句之妙,並不完全在於煉句,而應該注重詞句之間的彼此照應,互相映襯,相互生發。如他稱讚歐陽修《踏莎行》(候館梅殘)一詞「前半是自敘,後半是代家裏敘,章法極奇」[一九]: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熏風暖摇征轡」,「殘」字、「細」字寫蚤春如畫。「摇」字不知是草,不知是風,不知是征轡,却便覺有離愁在内。「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此二句只是敘愁,却已敘出路程;上三句只是敘路程,却都敘出愁。其法妙不可言。「樓高莫近危欄倚」,此七字從客中忽然説到家裏。「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此十四字又反從家裏忽然説到客中,抽思勝陽羨書生矣。[二〇]
雖然前人也曾稱讚《踏莎行》(候館梅殘)的精妙,但往往只著眼於詞句與字眼,尤其是末句「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措辭之妙。如黄昇認爲此句「句意最工」[二一],王世貞評價此句爲「淡語之有情者」[二二],但對於詞作的結構佈局和敘述視角却少有留意,而金聖歎則從詞作的創作思路出發,將詞作中不斷變化的敘述視角揭示出來。
戲曲小説的批評經驗對金聖歎批點歐詞還有另一個影響,即金聖歎非常看重詞作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他不但著力對詞作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心理活動進行細致剖析,同時他還會設想或虚構出詞作内容背後的一些隱含情事,將詞中人物放置其中,以突出人物形象的真實與鮮活。如他批點《減字木蘭花》(樓臺向曉):
前半之末句,只説「梁州入破」,則暗藏一妙人;後半之末句,只説春寒無妨,便暗藏一妙事,真是鏡花水月之文。[二三]
從「藏一妙人」、「藏一妙事」兩句看出,金聖歎顯然認爲詞作並非只是單純地描寫一位女子的舞蹈場面,而是將其看作一場纏綿情事中的一個片段,因而使讀者既能領會其所揭示的「艷情」主題,同時也能調動想象去感受舞者的内心世界。同樣,他對《蝶戀花》(海燕雙來歸畫棟)詞「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一句的批點也是著眼於詞中人物的内心:
「簾影無風,花影頻移動」九個字,看他何等清真,却何等靈幻!蓋人徒知「簾影無風」是靜,「花影頻移」是動,而殊不知花影移動,只是無情,正爲極靜;而「簾影無風」四字,却從女兒芳心中仔細看出,乃是極動也。[二四]
在這段批語中,金聖歎獨出機杼,用内心世界的「情」作爲衡量外部世界動靜的標準:花影雖動,但因爲「無情」,故而是「極靜」的狀態;簾影雖靜,但却是女子用心留意的結果,而她之所以留心簾幕,乃是心有所動,期盼心中所繫之人能夠到來,因此反映出女子内心世界的「極動」。通過此種分析,金聖歎將「簾影無風」這句客觀的景物描寫與詞中女子的心理活動緊密地聯繫起來。簾影之「靜」成爲詞中女子無法平息的相思之情的外化,而詞中女子的情思也由此真實、鮮活起來。
曾有學者指出,金聖歎批《西厢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心理分析之作」[二五]。顯然,金聖歎在批點歐詞時也運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將歐陽修詞藝術世界中的微妙之處勾勒清楚,而詞中的人物形象也在這種解讀下更加鮮活豐滿。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金聖歎的歐詞批點與他批點《西厢》、《水滸》等俗體文學時所採用的手法十分接近。
透過以論傳奇之法論詞的批評方法,我們可以大致了解金聖歎的詞體觀念。金聖歎傾向於將詞與戲曲、小説等俗體文學歸爲一類,即以虚構情事爲内容,以人物刻畫爲重點,而與以抒情言志爲主要表達方式的古近體詩區分開來。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將金聖歎的杜詩點評與歐詞批點進行比較。
金聖歎一生鍾情杜詩,在《唱經堂杜詩解》和《貫華堂評選杜詩》中,金聖歎對杜詩作了系統的點評。在點評中,雖然金聖歎也習慣性地運用了戲曲小説的批評經驗,然而從本質上説,金聖歎對杜詩的點評,依然採用的是傳統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原則,如其評杜甫《發潭州》:
此不知當日先生是何心血做成,亦不知聖歎今日是何眼光看出。總是前人心力不得到處,即後人心力亦決不到;若是後人心力得到之處,早是前人心力已到了也。千秋萬歲之下,錦心繡口之人不少,特地留此一段話,要得哭先生,亦一哭聖歎。[二六]
然而在金聖歎的歐詞批評中,我們看不到這種將作品與作者的思想生平相聯繫的做法。金聖歎雖然對詞作的表現手法和内在情韻作了細緻入微的探究,但他只是就詞論詞,而決不會在作者本人的生平經歷或精神世界中尋找某種來源或根據。簡言之,金聖歎不會在詞作的内容中去尋找作者本人的情感與懷抱,這也就是爲什麼有學者在論及金聖歎的歐詞批點時,會認爲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純文學的形式主義批評」的缺陷。[二七]造成這種「缺陷」的原因之一,就在於金聖歎並不將詞體看成是與詩一樣的抒情言志的工具,而是將描寫虚構的情事情景、塑造虚構的人物形象作爲詞體的主要功能。因此,作品成功的關鍵是詞作中表現的情事是否動人,人物是否鮮活,而與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境界以及生活經歷並無關聯。從這個角度説,在金聖歎眼中,詞體更接近於戲曲小説(只不過在篇幅上詞體更爲短小,因而只能展現一個場景或一個片段),而與詩有着明顯的分别。
或許在金聖歎心中,詞與詩之間的這種差異並不存在高下之分,畢竟金聖歎是一位將俗文學與傳統詩文並置的文學批評者,但他以論傳奇之法論詞,却在無意之中觸及到詞學發展史中最爲敏感的問題,即雅俗之辯。可以這樣説,無論金聖歎如何批點杜詩,都不會引起有關詩歌文體地位的爭論,左右人們對詩體故有地位的看法。然而,當金聖歎以論傳奇之法論詞,並由此將詞體與戲曲、小説等而觀之時,其所牽涉的問題就更爲複雜了。自北宋以來,詞體就一直在雅俗之間徘徊,而「雅俗之辯」也一直是詞學發展史上的一個核心論題。南宋以來詞壇復雅之士就表現出明確的尊體意識,盡量拉近詞體與詩體的距離,而明代詞學之所以被清人稱之爲「中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主情近俗」的詞學觀念之下,詩尊詞卑,判然有别,而金聖歎不但在《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中將「主情近俗」的詞學理念貫徹其中,同時還以論傳奇之法論詞,由此將詞體的功能、性質與戲曲小説等同起來。可以説,雖然金聖歎自己並非有意如此,但他的種種做法實際上是對詞體雅文學地位的徹底否定。
三 魔道與金針:清代詞論家對《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的貶斥與暗
從時間上看,《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成書於順治十年前後,此時雲間詞派的餘韻流響尚未消歇,以王士禛爲首的廣陵派、陳維崧爲首的陽羨派開始活躍於詞壇,而朱彝尊也在此時著手於詞體創作,並最終成爲浙西詞派的宗主。可以説,金聖歎批點歐詞之時,正是清代詞學確立自我面目的發軔期。而從詞史上看,清代詞壇雖然流派眾多,但無論各流派之間在理論觀點和創作實踐上存在何種分歧,都表現出一個共同的傾向,即在詞統上力圖越過「中衰」的明代,以直接五代兩宋。在續統觀的影響下,「尊體」意識成爲清代詞學理論發展歷程中歷變不衰的思想主綫,無論是崇尚「醇雅」、追求「意格」,還是師法「蘇辛」,各個詞派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將詞體納入雅文學的範疇,而明代「主情近俗」的詞學觀念則成爲清人極力清算的對象。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金聖歎的《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雖然作於清代初年,但正如前文所述,它的批評理念却延續了明代「主情近俗」的詞學思想,並將其系統化地運用於批評實踐。在金聖歎的批點下,歐陽修詞中「言情」、「側艷」以及「淺近」等特徵被充分揭示出來。金聖歎不但在解讀歐詞的過程中完全排除了詞體承載主體性情與思想寄託的可能,而且在語言、功能和創作手法上將詞體納入小説、戲曲所屬的俗文學系統,由此將詞體與詩體的距離進一步拉大。可見,金聖歎的歐詞批點與當時詞壇逐漸興起的「尊體」、「尚雅」思想完全相悖,由此也必然被清代詞論家所排斥、批評。
在金聖歎離世之後,清初詞壇陸續出現了一批詞選詞評,其中所表現的選詞標準、評點角度以及詞體觀念都與《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截然不同。例如先著在《詞潔》序言中説:「《詞潔》云者,恐詞之或即於淫鄙穢雜,而因以見宋人之所爲,固自有真耳。」[二八]與金聖歎專門屬意詞中的「妖淫」、「穢褻」相反,先著明確告示讀者當以「淫鄙穢雜」爲戒。他在點評陸游《鵲橋仙》(華燈縱博)一詞時又云:
詞之初起,事不出於閨帷、時序。其後有贈送、有寫懷、有詠物,其途遂寬。即宋人亦各競所長,不主一轍。而今之治詞者,惟以鄙穢褻媟爲極,抑何謬與。[二九]先著所謂「今之治詞,惟以鄙穢褻媟爲極」,很可能就是針對金聖歎專門選取歐陽修的側艷之詞進行批點、並熱衷於其中的「妖淫」、「穢褻」的做法而發。而隨着清代詞學的發展,金批歐詞遭受的批評也越來越猛烈。在《白雨齋詞話》中,陳廷焯將金聖歎的批詞之法斥爲「魔道」,並云:
其評歐陽公詞一卷,穿鑿附會,殊乖大雅。且兩宋詞家甚多,獨推歐公爲絶調,蓋猶是評《水滸》、《西厢》之伎倆耳。[三〇]
在陳廷焯看來,金聖歎以評《水滸》、《西厢》之法論詞,與詞體的地位、性質完全不合,這種「殊乖大雅」之舉是將詞體貶低爲與戲曲小説爲伍的俗體文學,這顯然與清代詞壇導源風騷、推尊詞體的詞學理念截然相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清人對金聖歎的歐詞批點表現出極度的不屑,但當他們對歐陽修詞做具體分析時,却或多或少受到金聖歎的影響,例如關於《生查子》(含羞整翠鬟)中「雁柱十三弦,一一春鶯語」一句的精妙之處,在金聖歎之前雖也有人提及,但只是點到爲止,如卓人月《古今詞統》評道:「『雁柱』二語,摹彈箏之神。」[三一]對於此句如何「摹神」則未作説明,這種大而化之的點評顯然不能令立志以「金針度人」[三二]的金聖歎感到滿意,他從「結撰照耀」的角度對其作了細緻分析:
「雁柱十三弦,一一春鶯語」,此二句之妙,人未必知,予不得不説。蓋從「十三」字,生出「一一」字;從「雁柱」字,生出「鶯語」字也。[三三]金聖歎的這個批語對一些清代詞論家産生了直接影響,如黄蘇評點此詞云:「『一一』字,從『頻』字生來,『春鶯語』,從『得意』字生來。」[三四]雖然對於「一一」、「鶯語」二字意脈勾連的理解有所不同,但黄蘇此處却明顯地襲用了金聖歎的解讀思路。
在這一點上,即便是將金批歐詞斥爲「魔道」的陳廷焯也不例外,在其早年所編選的《雲韶集》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到金批歐詞的「影子」。如陳廷焯對《訴衷情》(清晨簾幕卷輕霜)中「都緣自有離恨,故畫作、遠山長」一句做了如下點評:
結三語姿態横生。「縱畫眉能解離恨否」,明知不能,偏要故畫作遠山之狀,我與眉有仇耶。筆法真妙。真能傳出癡女子心腸。[三五]
陳廷焯的這番評點,無論是角度還是用語,都極爲明顯地受到金聖歎批語「即有恨,亦何與畫眉事?以畫眉作使性事,真是兒女性格也」[三六]的啟發。又如關於《長相思》(深花枝),金聖歎的批語爲:「四句十八字,一氣注下,中間更讀不斷,真是妙手」,「後半闋⋮⋮偏覺醜拙不可耐」。而陳廷焯評曰:「一字一意,筆如轉環,極盡詞中能事。後半闋嫌平。」[三七]二者的承襲關係也十分明顯。再如《漁家傲》(越女採蓮秋水畔)一詞,金聖歎對末句「離愁引著江南岸」中「引著」二字點評道:「此則練句之妙也。」而陳廷焯《雲韶集》中亦評曰:「『引著』二字妙甚。」[三八]
可見,清代詞論家一方面回避、排斥金聖歎的歐詞批點,另一方面又在批評實踐中,尤其是在對歐陽修詞的品鑒解讀時,受到它的潛在影響。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雖然金聖歎對「側艷」、「淺俗」的嗜好以及將詞體與戲曲、小説同等看待的詞體觀念與清代詞學的發展趨勢不符,但他畢竟在戲曲小説的評點實踐中培養了豐富的批評經驗和藝術感悟力,當他借用戲曲、小説的批評手法來對歐陽修詞進行分析解讀時,雖然帶有明代詞學思想的鮮明烙印,但却不能不説是對詞體創作技巧的一次全新觀照。較之前人品評詞作時所採用的概括性、印象性的語言,金聖歎對詞作文本的解讀更爲細膩,批評語言更爲豐富,分析角度也更爲靈活。在這種解讀下,詞作中一些原本不易爲人探見的創作技巧往往纖毫無隱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從而給予清代詞論家頗多啟示。
總之,金聖歎撰寫《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是希望通過對歐詞的細致批點,授人以作詞的「金針」。然而,這部寫於明清詞學思想遞變之際的批點之作不僅在批評理念上完全沿襲了明代「主情近俗」的詞學思想,還變本加厲,將其推向極端。同時,在具體的批評方法上,金聖歎又以論傳奇之法論詞,將戲曲、小説的批點手法運用於詞體。這些做法都與當時逐漸新生的詞學觀念格格不入,乃至截然相反,因此除了偶爾作爲批評對象,被譏爲魔道之外,幾乎很少有人願意提及。不過,金批歐詞對清代詞論家的影響又隱約可見。憑藉豐富的批評經驗與獨特的藝術感悟,金聖歎往往能揭示出前人忽視的藝術技巧,解讀出詞作幽隱的内在情思其,中不少獨得之見如同金針暗度被,清代詞論家吸納到自己的批評實踐之中。
[一]《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一般被認爲是金聖歎的晚年之作,參見傅曉航《金聖歎著述考》,《戲曲研究》第七九輯,文化藝術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第一九〇頁。
[二]如謝桃坊《中國詞學史》在第四章中將金聖歎與先著、許昂霄合爲一節。參見謝桃坊《中國詞學史》,巴蜀書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三一—二三六頁。
[三][二二]王世貞《藝苑卮言·附録》,《弇州山人四部稿》,臺灣偉文圖書公司一九七六年影印版,第六九二〇頁,第六九二五頁。
[四]沈際飛《詩餘四集序》,《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七二八—一七二九册影印明崇禎本《古今詞統》,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五]「俗化」與「曲化」雖是兩個概念,但二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從創作角度説即口語化、大眾化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化,而遠離典雅的格調與書面的特徵。參見萬雲駿《詩詞曲欣賞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一三頁。
[六][七][八][一一]沈際飛《草堂詩餘續集》卷下,《歷代詞話》,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五八七頁,第六一四頁,第五七一頁,第五七一頁。
[九][一〇]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詞統》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七二八—一七二九册影印明崇禎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一二][一三][一四][一五][一六][一八][一九][二〇][二三][二四][三三][三六]金聖歎《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金聖歎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八三四頁,第八三四—八三五頁,第八三五頁,第八三五頁,第八三三頁,第八三六頁,第八三四頁,第八三四頁,第八三四—八三五頁,第八三八頁,第八三六頁,第八三三—八三四頁。
[一七]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八九九頁。
[二一]黄昇《唐宋諸賢絶妙詞選》卷二,《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五九六頁。
[二五]譚帆《金聖歎與中國戲曲批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一二三頁。
[二六]金聖歎《金聖歎評唐詩全編》,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六二〇頁。
[二七]參見謝桃坊《中國詞學史》,巴蜀書社二〇〇二年版,第二三六頁。
[二八][二九]先著、程洪《詞潔輯評》,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一三二七頁,第一三四七—一三四八頁。
[三〇]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八九九頁。
[三一]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詞統》卷二,《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七二八—一七二九册影印明崇禎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三二]金聖歎曾云:「僕幼年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君』之二句⋮⋮今日見《西厢記》,鴛鴦既繡出,金針亦盡度。」見金聖歎《貫華堂批第六才子書〈西厢記>》卷二,《金聖歎全集》,鳳凰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第五八九頁。
[三四]黄蘇《蓼園詞評》,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三〇二五頁。
[三五][三七][三八]陳廷焯撰,孫克强、楊傳慶輯《雲韶集輯評(之一)》,《中國韻文學刊》二〇一〇年第三期,第五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