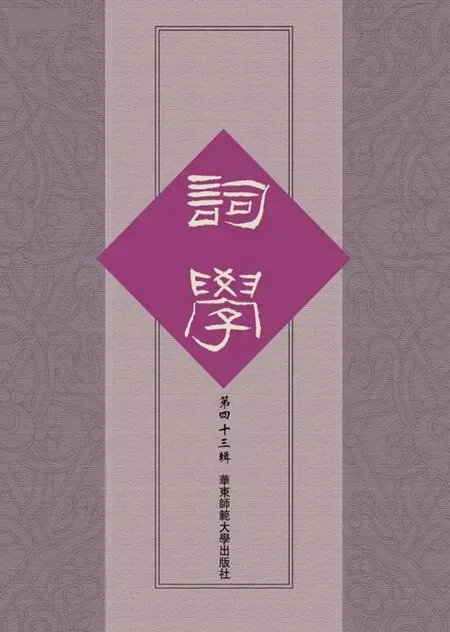兩宋蜀地文化風尚與南宋川陝俗艷詞風
趙惠俊
内容提要 蜀地華侈艷遊的文化風尚是花間範式得以形成的温床,在宋初成都知府張詠開創的「聚之爲樂」政策下,該文化風尚在北宋被保留了下來,豪奢俗艷的詞風也相應延續。只不過與北宋詞壇的京城主流基本一致,在當時也就没有形成地域特殊性。建炎南渡之後,蜀地因未受兵難而經濟持續繁榮,華侈艷遊的文化風尚與豪奢俗艷的詞風得以繼續盛行,並在南宋川陝地區「半獨立」性質的影響下日益穩定。而東部地區不僅在戰時不復艷遊的經濟基礎,還於孝宗中興時期産生了醇厚博雅的風氣,再加之其他地區互有差異的主流詞風,使得豪奢俗艷成爲了南宋川陝地區特有的地域性詞風。這種詞風對於入蜀爲官的外籍詞人影響很大,如陸游等詞人的蜀中詞作便大多順應時俗,暫時性地轉變爲豪奢俗艷之態,進一步加强了川陝詞壇的地域性特徵。
關鍵詞 川陝詞壇 俗艷詞風 蜀地文化 南宋詞
安史之亂後,中國文學的京城文壇向心力大幅減弱,逐漸發展出多元化文學中心的格局。文學不再完全依附於皇權,新興的地方文學中心也越來越不唯京城風尚馬首是瞻,而是顯現出非常鮮明的個性。到了南宋,文學的地域性分佈更加顯著,在兩浙京畿地區以外存在著相當數量的地域文學空間,各自擁有著不同的創作理念與文本樣態,爲明清文壇樣貌導夫先路。詞體文學同樣無法繞過這場文學時代之勢的影響,今日被視爲南宋詞主流形態的姜吴清疏醇雅之詞,在當日其實只是以臨安爲中心的兩浙京畿地區的主流詞風,兩浙之外的詞體寫作則各有偏好。比如江淮—京湖這樣的直面金兵的邊防區,酒宴歌席間響徹的是追求軍事功名的豪氣詞,無論詞人的寫作心態是自慨家國抱負,還是應酬帥臣座主,功名與豪情終究是繞不過的話題。至於閩贛等不與金接壤的地區,自然没有太多高唱慷慨意氣的場合,作爲士大夫熱衷的退居之地,此處的詞風便以書寫士大夫山林閑適的退居日常爲主流,在文本形態上深受稼軒退居詞作的影響,較典麗精工的姜吴之詞要粗疏清癯一些,少了幾分富貴雍容之態。而在南宋一定程度上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川陝地區,其實擁有著更加獨特的詞風個性,與上述三者皆不相同。實際上蜀中與川外的東西差異,是最能體現南宋文學地域性分佈的經典案例。祝尚書在本世紀初便以《論南宋文學的東西部差異》一文將之初步揭示,從愛國主題、文風承傳與詩派文體三個方面對此現象進行了發覆。不過祝尚書的論述以詩文爲核心,提及詞體者惟有「詞家相對較少,尤其鮮有專業詞人(唯程垓可稱其選,有《書舟詞》傳世),雖不乏作者,然皆非專工。而東部地區則詞家林立,流派眾多。此種現象尚待研究,大約是巴蜀遠離政治中心,文人仕多不達,文酒詩會較少之故。」[一]數語而已。儘管其間對於當日巴蜀詞風樣態的描述不盡準確,但依然足以提示川陝詞風當與東部地區流行詞風皆不相同。姚惠蘭在《宋南渡詞人群與多元地域文化》一書中,便結合成都遊樂文化與南渡成都詞人群體詞作之關係,指出四川地區在南渡時期以艷詞、遊冶詞爲主要寫作内容的現象。[二]姚惠蘭初步揭示了川陝詞壇的獨立特異性質,但遺憾的是,由於論著只關注南渡時代,從而未能察見川陝詞風前後相承的脈絡。實際上,作爲花間範式的起源地,艷詞與遊冶詞本就是蜀中最爲熟習與興盛的填詞傳統,南渡之後以艷詞、遊冶詞爲主要寫作内容的現象,實際是北宋蜀中詞風的延續。這番罕見的延續使得南宋川陝詞風具備强烈的排他性,東部地區蔚然興起的雅詞思潮對其影響較小,極大地影響到了當日詞壇分佈的格局以及後世詞體文學走向。由於今日南宋詞史的敘述框架與評價體系是由宋末秉持兩浙立場的詞家所奠定,故而與兩浙醇雅之詞相去甚遠的南宋川陝詞人及其詞作自然無法進入詞史話語而得到有效保留,於是便形成作者稀少、作品不工的表象,祝尚書提出的疑慮其實就源自這場接受史的發酵。本文即擬整體觀照掩埋在接受史中的南宋川陝詞壇,試圖從社會風俗、文化習尚等角度尋找俗艷詞風在此地始終延續且於南宋成爲顯著個性特征的原因,並探究這一現象對於當日詞家的影響及其深遠細微的詞史意義。
一 北宋時代西蜀艷遊華侈的社會風俗
豪奢俗艷的流行歌曲實際上與發達城市經濟相伴隨。一般來説,經濟越爲繁庶的城市,市民群體就越龐大,其地流行的歌詞曲調也就越容易呈現豪奢俗艷的樣貌。畢竟這樣的曲詞滿足的是人類最爲直接的感官享樂,無論聽眾的文化背景、教育層次如何,都能直接從中獲得精神的愉悦與滿足,與雅文學需要接受過相應程度教育之人才能欣賞的特性迥異。由於接受過士大夫文化教育者終究是城市中的少數群體,從而城市人口基數越大,社會階層越豐富,世俗群體的規模也就越大,俗曲艷詞的流行程度也就越高。作爲以成都爲核心城市的蜀中地區,自古就以繁庶著稱,社會風俗也就自然繞不過豪奢冶艷。這樣的城市樣貌在五代十國時期達到高峰,由於前後蜀皆定都成都,從而成都實際上也獲得了京城身份,進一步推動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市民階層的擴大。不僅如此,前後蜀王室還積極主動地實踐甚爲鋪張揚厲的豪奢生活,如後蜀國君孟昶不僅自己以七寶裝飾溺器,而且也鼓勵大臣與市民過著豪奢的生活。[三]在帝王的推動與親身實踐下,豪奢冶艷的生活方式成爲蜀中士民的習尚,到了五代十國末期已經積澱得相當深厚,呈現出如樂史所云之「地沃人驕,奢侈頗異人情,物態别是一方」[四]的風俗面貌,這也是公認之花間範式得以産生於此的重要原因。
蜀中的這種社會風俗在北宋滅蜀之初受到了很大的破壞。由於在北宋滅蜀戰爭中,大量宋軍將士通過掠奪成都而一夜暴富,使得北宋初年四川地區的行政長官也每每欲藉蜀中財富發家。他們通過置博易務、禁私市、不行商賈等手段將蜀中財富輸送至京師,同時也爲自己積聚資産。這種以蜀中百姓爲代價的財富聚斂與外輸,使得習慣侈靡生活的蜀地百姓痛苦不堪,相應地出現了大量的反抗事件,轟動宋初的王小波、李順起義便與此密切相關[五]。於是當蜀事平定之後,新任成都知府張詠有鑒於此,做出了順應民情的爲政改變:
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强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塚之上,立馬張旗望之。後乖崖公帥蜀,迺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爲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彩舫十數只,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名曰遊江。於是都人士女,駢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燕於寺内。寺前剏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倍於往歲,薄暮方回。[六]
可見宋初官員無論是否有心聚斂,治蜀政策皆是以遏制豪奢艷遊爲基礎,從而不僅豪征强掠了蜀地人民的財産,更完全破壞了蜀地的社會風俗,社會治安自然難以安定。故而張詠「聚之爲樂」、「化賊爲民」的政策實際上是以恢復後蜀社會生活習俗的方式來穩定蜀中秩序,使得蜀地豪侈艷遊之風在短暫中斷後重新恢復。張詠的做法很快起到了預想效果,繼任官員也紛紛沿用不改,成爲治川的重要政策傳統。李樸就曾記載下哲宗時代的蜀中樣貌:「西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爲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七]如此北宋的成都知府扮演起了類似前後蜀君王那樣的角色,成爲蜀地豪奢艷遊的鼓勵者與實踐者,使得北宋的蜀中風俗始終延續著鬭富競侈的樣態。
這樣的治蜀政策不僅使得蜀中經濟持續繁榮,更爲此地延續了後蜀時代龐大的倡妓群體,市民也得以在日常生活中依舊狎妓爲樂。黄休復《茅亭客話》即記載道:「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柳條明悟,人多狎之。」[八]極見蜀地私妓暗娼的風行。這樣的風氣也影響到官妓、營妓,本應按律與官員互相保持距離的她們每每跨越雷池之限,使得來此任官的士大夫頗多沾染艷風,爲自己招來私人生活不檢點的隱患。這尤以成都知府一職最難幸免,《邵氏聞見録》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文潞公慶曆中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蜀人也,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自迎見於漢州。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妓之項上帕羅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唤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九]
文彦博儘管是北宋一代名臣,但他於個人生活上其實偏好享樂,先前出守洛陽之時就喜好携妓遊春,以至於遭到司馬光的批評。此番出任成都知府的他本就容易受到當地冶艷風俗的沾染,再加之張詠以來「聚之爲樂」的治川傳統,他也就更會頻繁地携妓燕遊,招致朝中的流言蜚語其實並不奇怪。不過幕士張俞爲文彦博擺脱狎妓過度之名的方式却是用妓下套,足見蜀中使用妓樂的場合非常頻繁,倡妓群體已經深深融入蜀中日常生活之間,以至於本是奉詔暗訪文彦博私生活的何郯並不以這場發生在漢州的宴飲爲意,只是認爲是在做一件蜀地習以爲常的事情,並未想到此後會遇到的尷尬。實際上這個故事的情節在宋人筆記中不止一次地出現,另一位著名的主人公是宋初學士陶穀。他曾代表後周出使南唐,因態度傲慢,遂在驛舍中被韓熙載用妓下套,留下一闋小詞《風光好》。後來南唐中主李璟在宴請他的時候命妓歌此詞,陶穀由是大爲窘迫狼狽。儘管陶穀和文彦博的故事情節非常雷同,但陶穀故事的背景在五代末年的江南,到了北宋中葉的時候,江南地區已經不再産生這種類型的新故事,而同時期的四川却依舊産生了以文彦博爲主人公的故事,至少可以説明北宋新興文化風潮對四川的影響力很弱,從而五代艷遊的習俗風尚在四川得到了近乎原初式地保留與延續,花間範式也就仍然是蜀中歌詞的主流樣態。不過蜀地盛行的私妓暗娼也意味著蜀地歌詞不可能盡如詩客所作的花間諸詞那樣得清艷雅麗,而是以豪侈俗艷爲最主要的面貌。這些詞作當然會在南宋以降的接受史中被漸次删汰,而且就當時來説也不具備多少全國性的流傳度或鮮明個性。畢竟在詞體雅化方興未艾的北宋,俗曲艷詞本就是最主流的歌詞樣態。再者,北宋京城開封才是最大的俗曲艷詞創作中心,更何況洛陽的經濟實力也比成都强大許多。於是乎北宋蜀地的俗曲艷詞在藝術性與流傳度等方面均相對落後,相關歌詞也本就被開封流行樂壇的偉岸身影遮蔽掉了大半。
二 南渡之後川陝地區「半獨立」性質與俗艷詞風的延續
南渡之後,隨著國土面積的鋭減,蜀中與陝南合并成爲川陝獨立攻防區,成爲宋金雙方在西部地區的主戰場。但是除了陝南多有重大戰事之外,其他區域並不受戰火侵擾,而且重要城市也未如東部那樣受到戰爭的直接破壞,成都始終是富庶繁樂的天府。是故豪侈的生活方式在南渡之後的川陝地區得以始終延續,既没有遭致開封的覆滅之災,也不會像江南那樣暫時中斷。不僅如此,南宋政治地理格局由圈層式轉變爲分塊式,中央對於地方的控制力較北宋大爲減弱,這對於相距兩浙京畿地區過於遥遠的川陝地區影響更大,作爲方面要員的成都知府擁有相當大的地方權力,使得由其主政的川陝地區實際上具備了「半獨立」的性質。這種心態其實早已藴藏於蜀中民眾間,范成大於成都知府任上寫過一首《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詩,詩中通過「耳畔逢人無魯語,鬢邊隨我是吴霜」一句表達著異鄉佳節的故園之思。其間「魯語」一詞爲蜀地詞彙,范成大爲其自注道:「蜀人鄉音極難解,其爲京、洛音,輒謂之虜語,或是僭僞時以中國自居,循習至今不改也。既又諱之,改作魯語,尤可笑,姑就用其字。」[一〇]可見北宋時期的蜀地就已經潛藏著特異於中原的半獨立心態,張詠「聚之爲樂」的治蜀政策又將這種源於割據政權的情感悄然延續了下來,在建炎南渡後的時局激烈震動中得以强烈凸顯。
在這樣的政治地理格局與地方文化心態下,東部地區發生的政局、思潮變動對川陝地區通常不會産生多大的影響,該地的政治與文化能夠不斷延續著前代遺風,更多地遵循自我内在的發展趨勢。這種地域性格對於詞體文學的影響在南渡伊始就非常顯著,最明顯的莫過於成書於建炎三年(一一二九)的《梅苑》。是年金兵南侵之勢未減,東西各綫戰事均相當吃緊,而南宋新政權又遭遇苗劉兵變,可謂内憂外患、風雨飄摇。如此政治憂難之際,黄大輿居然在蜀中編選蕭閑風雅的《梅苑》,其生活狀態與個人心態較東部地區的遊離可見一斑。當時局穩定之後,川陝地區的半獨立態勢愈發强烈,有時甚至連中央行政命令也不奉行。宋高宗與宋孝宗皆相當强調簡樸的生活方式,經常用行政命令干預世俗社會尚奢靡的風俗,但這些命令對川陝地區基本没有約束力。李心傳曾記載到南宋帝王御筆嚴申監司互送之禁,但四川官員對此毫不在意,不僅一次贈物送行可達幾萬緡之多,而且又創製壓境錢等新名目,使互相獲得的錢財數量更爲增加[一一]。蜀地之所以能夠如此不改官民共行奢侈的社會風俗,當然是因爲其地並未直接受到靖康兵亂的波及,從而能夠保證經濟的持續繁榮。范成大《離堆行》詩就寫道:「自從分流注石門,西州秔稻如黄雲。刲羊五萬大作社,春秋伐鼓蒼煙根。我昔官稱勸農使,年年來激西江水。成都火米不論錢,絲管相隨看蠶市。款門得得酹清尊,椒漿桂酒删羶葷。」[一二]便是孝宗中興時代蜀中繁庶的寫照,這爲豪侈之風的延續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隨著孝宗中興時代的深入,江南地區也恢復了往日的繁華,行在臨安更成爲重現開封氣象的帝都之所。儘管市民階層還是一如既往地喜好俗艷之曲,但是兩浙地區的士大夫及貴胄群體却不再以競富鬥侈爲尚,而是承襲了徽宗大力推動並親身實踐的新式富貴日常,通過玩弄筆墨丹青、花木雅物、園林奇石等承載文化知識的雅物展現自我的富貴與學識,作於其間的詞體文學也就不再競侈從俗,而是在林泉蕭散式的潤飾下初步形成了醇雅的樣貌,並在姜夔等詞家的創作與范成大、張鎡等重臣貴胄的推動下成爲兩浙詞壇最爲外顯的詞體形態。但是在經濟持續繁榮與官民半獨立心態的共同作用下,川陝地區並没有受到兩浙新興文化風尚與詞體趣味的太多影響,反倒將北宋許多的豪奢風習直接保留了下來。最典型者即牡丹會,如陸游所云:「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即花盛處張飲,帟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一三]這番描述與北宋人對京洛豪冶生活景象的記載别無二致。不僅北宋中原的娱樂活動藉蜀地保存,承平年間的重要文物也賴蜀中傳續。張震《補夔州大晟樂記》云:「自中原遭變,城邑爲虚,雖東南郡縣還定安集之餘,而禮樂器用無一存者。蜀獨以不被兵,僅獲全。而數十年間,吏唯簿書獄訟公食之爲,故謂儒者事特無訾省,甚者竊取資幾案虞玩之用。此其於幸中又得不幸者也。始,夔有賜樂,視諸故府十闕五六。雲安舊爲軍,亦有賜,取而合之不足,則又搜取於它州。鐘磬正聲、中聲凡五十有六,按圖爲簨簴,寘諸學宫,每歲祀陳於庭,雖備而不作,尚庶幾存其意,此夫子不忍去告朔羊之志也。」[一四]代表徽宗宣政承平之象的大晟樂器居然也能在戰亂初定後的四川被復原,更加説明承平習氣在川陝地區得到了比較良好的保存,與之相應,倡妓群體也依然會像北宋那樣,在蜀中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於是趨俗尚艷的文藝趣味在南渡後依然盛行於川陝地區,左右著南宋中興時代川陝詞風的基本面貌。范成大《次韻代答劉文潛司業二絶》(其二)詩云:「迴廊月下短歌行,惟有知音解有情。一曲紅窗聲裏怨,如今分作兩愁城。」[一五]句中的紅窗,即徽宗朝京城極爲盛行的世俗曲子《紅窗迥》,曲調與歌詞都相當俗艷。宣政年間,曹組曾因創製數百解《紅窗迥》而名盛東京,但他也因此在南渡後遭致「滑稽無賴之魁」的罵名而文集毁板。兩浙地區已難再聽聞的《紅窗迥》却在蜀中依舊廣爲流傳,極見川陝地區對於俗艷詞風的偏嗜。而《紅窗迥》的傳唱不息,也説明里巷私妓是川陝地區絶對優勢的音樂傳播群體,范成大「十里珠簾都卷上,少城風物似揚州」[一六]的感慨,便是因川陝群倡雲集的社會風貌而發。如此川陝地區詞體寫作的字面風格同樣也會保留艷俗的特徵,周煇《清波雜志》中就有這樣的記載:「成都富春坊,群倡所聚。一夕遺火。犁明有釘一牌,大書絶句詩於其上:『夜來燒了富春坊,可是天公忒四行?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乃伊洛名德之後,號道山公子者所作。又有小詞一編,皆艷語。」[一七]可見無論作者原先是何身份,來到川陝從事詞體寫作總會不由自主地受其地風氣影響而填出艷俗之詞,雖伊洛名德之後也不能幸免。周煇在下文就此發出了填詞需謹慎的言論,重復了北宋時代對於晏幾道、黄庭堅等士大夫的勸誡。但是其時詞體雅化已經完成,詩詞寫作合流的趨勢在東部地區早已蔚爲大觀,士大夫用詞體書寫自我日常生活已不是奇怪之事,兩浙貴戚及專業詞人甚至將雅詞推至極工極變的階段。於是周煇的這番勸誡就顯得落後時代太多,但反過來却也再次印證了南宋川陝地區詞體寫作的獨立性,俗艷詞風在此地始終具備執著而穩定的寫作傳統,並在京畿詞壇早已日趨典雅的時代背景下,於北宋並不顯個性的豪奢俗艷,成爲了南宋川陝詞壇鮮明的地域特徵。
三 南宋川陝俗艷詞風對外籍士大夫詞人的影響
儘管川陝地區社會風氣與文藝趣味迥異於東部,但圍繞最高主政者成都知府爲中心展開詞體寫作的創作生態則與東部相同,使得來此擔任地方官員的外籍士大夫入川之後,便自動成爲相關地區的宴飲座主與文學活動中心。陸游在《范待制詩集序》中有云: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眾,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盼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農,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一八]
從陸游的敘述中可以明顯看到,作爲川陝獨立攻防區的最高長官,成都知府也具備統兵的軍事身份與責任,但是其人其地却並没有出現京湖—江淮地區那種對於恢復與功名的强烈歌唱。范成大的具體施政内容也反映著他在此地確實不太重視軍事,反倒致力於實現太平無事的政績。這其實是北宋士大夫在出守地方時的普遍心態,他們的使命是保境安民,故而太守的與民同樂就成爲地方大治的承平之象。范成大鎮蜀時其實頻繁地召集幕僚飲酒賦詩,在他自己的詩中便經常出現諸如「九月十九日衙散回,留大將及幕屬,飲清心堂觀晚菊,分韻得譟暮字」[一九]的詩題。這不僅説明范成大對於軍事工作甚至北伐中原無甚興趣,還能看出川陝地區的文期酒會其實並不稀見,舉辦酒筵雅集同樣也是川陝地方主政官員的日常活動,當地市民應也期待著席間士大夫新作的傳出。
儘管像范成大這樣的外籍士大夫可以憑藉官職召集川陝地區的詞體寫作活動,但在該地强烈的豪奢俗艷詞風下,他們並不能自由地按照自我習尚填詞,大多數情况下不得不和那位道山公子一樣遵從川陝文藝風氣,填製風調艷麗趨俗的詞篇,最多只能保證不至於那麼得骫骳。以成都知府爲首的士大夫當然不會公開出現在富春坊這種地方,他們多在公私園林中舉行宴會並即席填詞,後蜀燕王宫故址是他們經常遊賞的地方,如陸游這闋《漢宫春》:
漢宫春 張園賞海棠作,園故蜀燕王宫也
浪跡人間,喜聞猿楚峽,學劍秦川。虚舟汎然不繫,萬里江天。朱顔緑鬢,作紅塵、無事神仙。何妨在,鶯花海裏,行歌閑送流年。 休笑放慵狂眼,看閑坊深院,多少嬋娟。燕宫海棠夜宴,花覆金船。如椽畫燭,酒闌時、百炬吹煙。憑寄語,京華舊侣,幅巾莫换貂蟬。[二〇]
陸游的詞作風格多樣,故後人有「驛寄蘇秦之間」的評語。但仔細究之,其詞風亦與創作地域聯繫緊密。其入蜀前與東歸後的作品基本不出京湖—江淮與閩贛兩地主流詞風,或與統兵文臣抒發恢復豪情與功名感慨,或於林泉漁樵間記録士大夫的退居日常,偶爾也會用詞體表達壯志難酬的憤懣,惟有蜀中九年的詞體創作是以艷詞爲主。這闋《漢宫春》便是典型的蜀中宴會上的富艷之作,雖然表達著疏離政治的日常化主題,但是用了屯田蹊徑的筆法鋪敘燕王宫夜宴之豪艷,並不是陸游的慣常詞筆。詞中出現了退居士大夫詞作中的兩個常見主題:一是上片「紅塵無事神仙」,表達的是遊戲人間不羨飛仙的心態,但是與閩贛地區的士大夫在山寺林泉間杖履遊戲不同,陸游所言是要在妓圍窈窕間度過餘生;一是全詞煞尾處的貂蟬意象,南宋詞人常用之代指功名,陸游此處亦是如此,不過是在唱功名之反調,書寫放下功名的情緒。這種表達其實也常見於退居士大夫的筆下,他們習慣用杖履、幅巾等意象代指山林間的蕭散隱士,以與貂蟬相對。儘管陸游在這闋詞中也使用了幅巾意象與貂蟬對舉,但他很明顯並未以幅巾借代山林野客,而指的是繁庶京華間的冶遊公子。從而這闋《漢宫春》從字面句法到内在意藴,都與南宋已經成熟的士大夫詞相去甚遠,而接近北宋專業詞人筆下的京城恣遊之詞。
這樣的詞中心態於放翁詞中還有其他的案例,《柳梢青·故蜀燕王宫海棠之盛爲成都第一今屬張氏》一闋云:「錦里繁華,環宫故邸,疊萼奇花。俊客妖姬,爭飛金勒,齊駐香車。何須幙障幃遮。寶杯浸、紅雲瑞霞。銀燭光中,清歌聲裏,休恨天涯。」[二一]亦是用鋪敘之筆寫錦城豪艷,陸游甚至在其間消解了其入蜀詩歌裏頻繁吟詠的鄉關之思,出現了願意沉醉於此地温柔富貴之鄉的表達。除了燕王宫之外,陸游《月上海棠·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水龍吟·春日遊摩訶池》、《鷓鴣天·薛公肅家席上作》等詞更能體現以成都知府爲核心的遊宴活動非常頻繁,士大夫充分利用前後蜀的皇家園林遺産進行遊樂,相關詞作也以豪侈俗艷之風爲主。這當然是張詠「聚之爲樂」政策在南宋的延續,也爲外籍士大夫提供了一片填寫富艷之詞的創作空間。曾發出「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之壯語的丘崈,在來到川陝之後也變得和陸游一樣填寫起艷詞來:
祝英臺 成都牡丹會
聚春工,開絶艷,天巧信無比。舊日京華,應也只如此。等閑一尺嬌紅,燕脂微點,宛然印、昭陽玉指。最好是。樂歲臺府官閑,風流剩歡意。痛飲連宵,花也爲人醉。可堪銀燭燒殘,紅妝歸去,任春在、寶釵雲髻。[二二]
丘崈感覺到了成都牡丹會與北宋東京十分相似,但却没有因此勾起他常有的故國之思或恢復壯志,反倒是繼續在花間尊前沉醉下去,甚至還爲美好時光轉瞬即逝而痛感遺憾,不能不説是適應川陝地區豪侈生活與俗艷詞風的入鄉隨俗。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陸游似乎覺得成都知府組織的艷遊活動還不足以盡興,於是也跑去富春坊狎遊一番,其《憶秦娥》一闋云:「玉花驄。晩街金轡聲璁瓏。聲璁瓏。閑欹烏帽,又過城東。 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風。酬春風。笙歌圍裏,錦繡叢中。」[二三]這活脱脱的就是道山公子的再現,至少在這闋詞的文本空間内,陸游並不在乎他入蜀的本意究竟是什麼。如此外籍士大夫入蜀之後無法延續以文章太守、歸耕居士或統兵文臣等東部常規身份來生活與寫作,只能以風流才士的口吻填製著俗艷或富艷的歌詞,而且也並不怎麼使用兩浙詞壇新興的富貴表達方式,進一步加深了南宋川陝詞壇豪奢俗艷的風氣,使之成爲東部詞壇雅化浪潮下獨樹一幟的存在。
餘論
川陝地區在南宋詞壇特異的俗艷詞風在後世被逐漸淡忘,這是受到論家立場、詞作經典性、詞人地位等多方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將此特徵重新於接受史的遮蔽中勾勒出來並非要抬高俗艷之詞的藝術價值,也並非欲藉之否定姜吴雅詞崇高的經典地位,而是希望可以盡量還原南宋詞壇多元地域分佈的創作生態,爲詞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維度。既然川陝的俗艷詞風有著非常强大的生命力,甚至會深刻影響來此任職的外籍士大夫,使得他們的詞作發生暫時性的豪侈俗艷轉變,那麼也就可以察見姜吴雅詞在南宋詞壇當日並非一家獨大,其實與俗艷詞風、稼軒詞風一樣,是南宋詞壇多元面貌的一部分。詞人會因爲行蹤流轉而發生適應當地流行詞風的暫時性改變,亦説明詞體文學在南宋時期尚未産生自覺恪守的填詞家法,也就没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詞人流派,詞之文體生命於此時並未進入成熟完備的狀態。這項工作其實要在清初詞人手中才算真正完成,成爲「清詞中興」的重要因緣之一。因此並不適合用某些特定風格或範疇來限定南宋詞人的創作,他們的詞作面貌雖有相對主流的樣態,但依舊是多元而富於變化的。有時這種因不同地區而呈現出的詞風變動還可以成爲某些詞作寫作時地的重要參考。其實吴熊和先生在判斷陸游《釵頭鳳》一詞寫於蜀中之時,就已經將川陝詞壇的流行詞調與詞風作爲重要旁證。[二四]如若結合本文的分析,則更能看出艷情主題的《釵頭鳳》其實更符合陸游蜀中諸詞的寫作特徵,應該是入蜀時期受蜀地豪奢艷遊文化風尚影響的作品。此外上引陸游、丘崈等詞人的川陝詞作絶大多數是即席應歌之作,不僅詞情詞貌適應川陝俗艷詞風,詞中吟詠的女性人物與恣遊心緒其實也多是逢場作戲,不能當作詞人真實思想的反映。這提示著儘管詞體雅化在南宋已漸趨成熟,詞人也已經習慣用詞體來表達自我真實生活與情感,甚至會將身世之感寄託於男女艷情之中,但是詞體傳統的應歌代言之體依舊有著强大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寫作空間,相關作品的數量也非常可觀,從而在面對一些詞中人物身份模糊的作品時,需要謹慎將其與詞人的真實生平相勾連,它們很可能只是應歌、應酬間的無謂之作,並非確有其事。這對於那些語涉男女相思的詞作來説尤爲重要,在没有明確的内外證據情况下,還是將其視作應歌代言之體要更爲妥當些。其實明代詞壇會出現俚俗輕浮的風尚正也説明俗艷詞風並未因爲姜吴雅詞的出現而凋敝,依然有著深廣的創作基礎。明人選擇俗艷與清代浙西詞人選擇醇雅的内在機理也就相去不遠,皆是從南宋詞壇的多元樣態中擇取一瓢。從這個角度來説,南宋川陝詞壇特異於東部的俗艷詞風也就具備了更爲深遠的詞史影響,其將詞體最原初之縱情於男女情愛的表達主題及方式較爲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爲《花間》、《草堂在》明代的大昌留下了一處門徑。
[一]祝尚書《論南宋文學的東西部差異》,《宋代文學探討集》,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一三四頁。
[二]姚惠蘭《宋南渡詞人群與多元地域文化》,東方出版中心二〇一一年版,第二八八—三百八頁。
[三]李攸《宋朝事實》卷一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二六八—二六九頁。
[四]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第七九頁下。
[五]王闢之撰,吕友仁點校《澠水燕談録》卷八,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一百五頁。
[六]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一,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十一頁。
[七]李樸撰,燕永成整理《豐清敏公遺事》,《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八册,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一三一頁。
[八]黄休復撰,趙維國整理《茅亭客話》卷四,《全宋筆記》第二編第一册,大象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三十二頁。
[九]邵伯温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録》卷十,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第一〇一頁。
[一〇][一二][一五][一六][一九]范成大著,富壽蓀點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第二三二頁,第二四八頁,第二五四頁,第二三三頁,第二三〇頁。
[一一]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第六九五頁。
[一三][一八]陸游《渭南文集》卷四二,《陸游集》,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第二四〇一頁,第二〇九八頁。
[一四]張震《補夔州大晟樂記》,《宋代蜀文輯存》(第五册)卷六〇,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第二四八頁。
[一七]周煇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卷八,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第三三九—三四〇頁。
[二〇][二一][二三]陸游著,夏承燾、吴熊和箋注,陶然訂補《放翁詞編年箋注》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八十五頁,第八十七頁,第一六九頁。
[二二]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版,第二二五四頁。
[二四]吴熊和《陸游〈釵頭鳳>詞本事質疑》,《吴熊和詞學論集》,杭州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第二七一—二七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