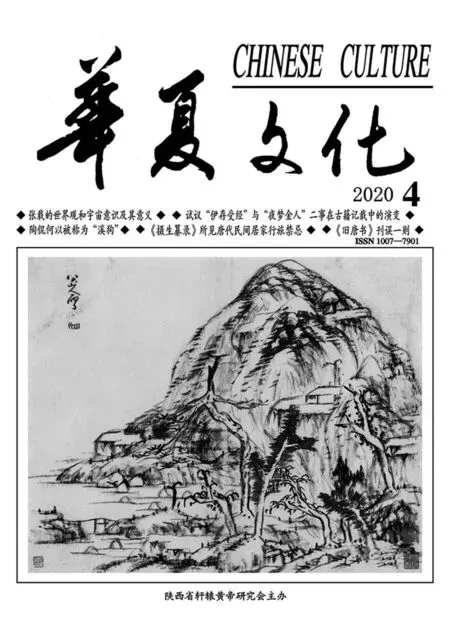史学确立为官学不由石勒始考
□华迪威
《晋书·石勒载记》云赵王二年“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胡宝国先生在其《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中认为这标志着史学在教育中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门类,标志着西晋以后经、史区分在教育上的体现。
此条史料是袭自北魏崔鸿撰写的《十六国春秋》,一向被认为是“史学”二字第一次并称在史籍中,史学似乎已经与经学、律学一样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我们检视史料,发现《晋书》中除此之外再无“史学”二字出现,这里的“史学祭酒”是否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历史学呢?
我们先看看负责担任经学祭酒的裴、傅、杜三人。《晋书·裴宪传》云其“修尚儒学”且在石勒初开创制度、制定朝仪时出力甚多,由其担任经学祭酒自然再合适不过;《晋书·傅畅传》云其“谙识朝仪”也在制定制度等方面出力甚多,其儒学修养也足以让其担任经学祭酒一职;《晋书·石弘载记》云其“受经于杜嘏”。可知三人都有深厚的儒学功底,让他们担任经学祭酒是人尽其才。
再看续、庾二人。《晋书·续咸传》云其:“修陈杜律,明达刑书”,庾景则无其他记载,但可以推知应该也是对律法之事颇为精通之人,可知石勒都是以有相关知识储备的顶尖人才充任祭酒的。
接下来看担任史学祭酒的任播、崔濬。《晋书·石弘载记》云石勒“使刘徵、任播授以兵书”,前文中有石弘“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之记载,而石勒之所以让任播授石弘以兵书是因为他认为“今世非承平,不可专以文业教也”。经学、律学自然为文业,而任播却并不被石勒认为是文人,如果“史学祭酒”是历史学,自然也属于文业,而从石勒的态度又可以明显看出任播并非一般的文人。
按照石勒以个人知识结构与体系划分官职的一贯方式,这里的“史学祭酒”或许并非历史学,而是与兵学直接相关,与任播一起授石弘以兵书的刘徵更是石勒手下的大将。或许刘徵负责传授其行军打仗之具体经验,而任播在兵学理论方面对其进行传授,崔濬则除此之外并未再出现在史籍中。
从整体来看,有关“史学祭酒”的相关材料或无法证明其与我们如今认知的历史学有直接的关联性,从为数不多的史料所呈现出的担任史学祭酒的任播,其知识体系更接近于兵学而非文业。故我认为这条史料并不能证明历史学在石勒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于证明经、史已经分离也未必那么有说服力,更无法确认此时之史学学官是否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与历史学相关的官职。
诚然,大多数文献中出现的“史”、“史学”就是我们认识的历史学,但在好兵的石勒眼中,是否史学含义近似于过往历史中行军打仗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呢?这也是有可能的。如《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刘宇上书求《史记》,被大将军王凤以“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为理由拒绝,可知《史记》中存在战略权谋或关兵学之事,故不许诸侯王阅读,也可从侧面看出史学与兵学确实存在着一定联系。
既然我们无法确认石勒设立的史学祭酒与历史学直接相关,那么之后宋文帝刘义隆以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学并立就尤其值得考察。《宋书·雷次宗传》云元嘉十五年“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何承天负责史学一门。《宋书·何承天传》云其“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元嘉十六年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沈约《宋书》的基础便是由何承天等人陆续修成的南朝宋国史。《宋书·礼志一》提到“史学生山谦之”,应当是何承天门生无疑,《宋书·徐爰传》又有:“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则山谦之继何承天之后继续修史,与上文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山谦之确曾就学于何承天学习史学相关知识,故能继承其学,继续完成修史大业,可知刘义隆所立史学学官培养的确实是史学人才,这应该是史学被立为官学的铁证。
——刘家文
——徐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