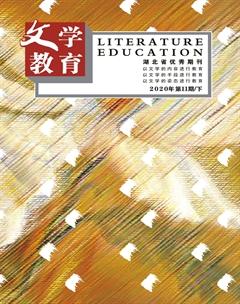《书目答问》与文学批评
余媛
内容摘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清末学界流传甚广的一部目录学著作,该书旨在指导当时的后生学者: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该书目按照四库的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再加上“丛书”一部,一共五个部类来编排书目。在书目的取舍、编排顺序、序言和提要等内容中,无一不流露出张之洞的文学批评观念,同时也是清朝末年文学思想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张之洞 书目答问 目录学 文学批评
一.目录学之于文学批评
“目”,本义是眼睛,眼睛为双数,故后世便以目来表示复数。其引申义用于逐一称述的事物,诸如节目、条目、项目、名目。“录”字,在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释为“凡录之属皆从录”。由于录需要刀刻,后来便加上一个“金”字偏旁。录,从而由刻木之义,引申为记录、抄写和次第册籍等义。
目录学,“目”指的是书目分类的层次和结构,“录”指的是叙录,这些叙录包括:概述书本思想内容、著者事迹及写作、学术源流、品评版本等内容,后世简而言之为解题、提要等。
目录之学功用有三:
其一,有助于掌握历代文献的基本状况,了解历代文献学发展之大概。通过这些辑录而成的书目,可大致了解各时代文献的基本情况,略知一代文学的盛衰。如饶宗颐《潮州志·艺文志》,《汉志·诸子略》对“九流十家”的著作凡189家共4342篇的著录,从中想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散文发达之盛况,《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诗歌辞赋作品的著录共106家1318篇,据此可知西汉时期诗歌辞赋的蓬勃发展。
其二,利用目录及目录只是进行专题研究。
可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一书所列举的古人利用目录学考辨古籍的六项方法,此六种方法,对古籍的考辨、整理而言也是极其合适的。
其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示读书门径。考古发现,甲骨文书就有按类别存储的情况;孔子整理文献,将《诗经》分为风、雅、颂;孔子修《春秋》,删《诗》、《书》,订《礼》、《乐》,纂《易》;汉代刘歆撰《七略》,形成我国第一个完整分类体系,首创类目。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也曾言及目录学的分类及功用:
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三曰小序解题并无,祗著书名者。……综以上诸家之说观之,则其要义可得而言。属于第一类者,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属于第二类者,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属于第三类者,在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1]
张之洞之《书目答问》,其撰书目的非常明确。卷首之《书目答问略例》有言:“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絓漏,志趣学术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
可见,作者撰写《书目答问》,其目的即是为了指导后学,告诉学生们,该读何书,而书应该选择哪一个版本,如何做到事半功倍地读书学习。
余嘉锡先生曾言:“目录之学,实兼学术之史。”[3]古典目录学,不僅是一种读书治学的门径之学,而且是一门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特色的传统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因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作者的主观本意,是为了方便后生读书治学,实现了目录学的治学门径功能;而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客观体现了,清朝末年洋务派代表人物、一代名臣张之洞对中国学术源流的理解与阐释。
二.《书目答问》与其文学批评观念
文学批评反应了客观真实的文学史关于目录学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吴承学《〈郡斋读书志〉与文学批评》这一;篇文章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
“学人治书部的途径之一是学习古典目录,古典目录的学习也是一种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和学习的重要资源,古典目录的学习也就是历史的学习,这种学习从西汉时代刘向父子专门著的书,到后来西晋刘昫著述的《旧志》,目录学这一学科开始确立自己的地位,古典目录学显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这一学科又与其他学科存在密切联系,目录学和文学批评之间也是这种关系,“一方面,目录学著作会摘录文学批评典籍,同时设立对应的科目以表现目录学对文学批评发展的认识,另一方面,各种书籍中的序言和摘要都属于目录学批评的对象,目录学的文字批评功能开始显现,也正是这个原因,古典目录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4]
这段话充分说明了目录学之于文学批评的中重要意义。《书目答问》是清朝末年新旧文化交接碰撞之时的产物,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答问》的编排、类目的设置、序文和提要,无不反映着张之洞的文学批评观念。
《书目答问》体现的第一个文学批评观念,是尊经崇儒。
张之洞尊儒而斥诸子,而且他所尊宗的是纯正的孔儒之学,就连“八儒”之一的荀子,他都加以批评。他在《劝学篇·内篇·宗经》中说到:“《荀子》虽名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恶,法后王,杀〈诗〉、〈书〉,一传之后,即为道经籍之祸。”[5]
在《书目答问》中,选书目录最大的一门,是经学,包括了汉学和汉宋兼采两派的作家作品,数目达到了二百零二人。这二百零二人中,汉学家占据多数,达到了四分之三左右。由此也可看见,张之洞的“汉宋兼采”,其实仍然是以汉学为基本。朱维铮认为《书目答问》“述及清代初中叶的学术文化,更其是乾嘉汉学,则赞礼之情跃然纸上……且不说这般见解在根本上没有超越汉代就有的‘通经致用模式,即如说理习文从政都离不开经史考证,哪一项不是顾炎武、黄宗羲到戴震、阮元等人旧说的回声”。[6]在《书目答问》对儒家经学书籍的收录上的数量之多,可以看出张之洞的尊经崇儒思想;而在对儒家思想的解读上,采用了以汉学为主、宋学为辅、汉宋结合的学术思想。
《书目答问》表现出来的第二个文学批评观念,是浓厚的经世致用思想。
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开始,接着魏源提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以及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再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的内忧外患之际,经世致用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潮。中法战争之时,为抵御外族侵略张之洞起用冯子材,组织边防、购置武器、调拨物资,中法战争不断取得胜利,这就是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
从《书目答问》所收书目种类上看,有关于当时西方先进技术的新书品种的加入,对知识“实用”性的推崇,使得这本目录学著作有别于当时及之前的传统目录著作。
应该说,张之洞的经世致用思想,来源于其父亲张瑛及业师胡林翼。张瑛平素教子说:“汝辈当力学问、树功名,慎勿为田舍翁所为,予之所深恶也。”然而致力于“为学”只是一端,另一端则是以务实为主、不尚空谈的经世致用思想。
《答问》一书所录书目,都是以实用、真确为标准。《书目答问·略例》言及书目之五不录:
凡无用者、空疏者、偏僻者、驳杂者不录,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刻者不录,旧椠书钞,偶一有之,无以购求者不录。[7]
在诸多“不录”的书中,“无用”之书,是第一个剔除的。《书目答问》一书中,所呈现出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可以说是这本目录书籍的主线,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有社會责任感的士大夫对年轻学子提出的期盼和要求。
《书目答问》体现的第三个文学批评观念,是对乾嘉学派考据学的重视。如前文所述,张之洞主张“汉宋兼采”、“为学忌分门户”,然而在汉学和宋学之间,从收录汉学书目是宋学书目的三倍,可以看出他在汉学和宋学之间,是有所侧重的。
朱维铮在《近代学术导论》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张之洞虽然嘴上说着‘为学忌分门户,但是实际上张之洞十分欣赏汉学文化,比如说《书目答问》通篇都不提及邵氏,这就让人感觉非常奇怪,因为《礼经通论》曾经这么说到,体例不受刊书不能作为自己不著述的原因,文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数百人都在这个列举里面,但是举邵懿辰还是没有提及,这更加让人觉得奇怪,倘非显示张之洞本人的某种价值取向,便很难解释。”[8]
从《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学著作看:张之洞将“经部”分为“正经正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小学”三个部分,而在每个子目的安排上,《论语》、《孟子》、《尔雅》也都单独列出,而且收录的这类儒家经典的阐释著作,多数都是清代乾嘉考据学者的作品,充分突出了考据学在张之洞所倡导的学习体系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体现了清朝末年学术界的尊经崇儒思想,同时也在内忧外患的现实环境中,不断进取、吸收外来的知识文化。随着清帝国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与传统儒学相互交汇,迎来了新生的曙光。
参考文献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8页.
[2]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页.
[3]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页.
[4]吴承学,黄静:《郡斋读书志与文学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1期,第1页.
[5]张之洞:《劝学篇·輶轩语》;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14,第27页.
[6]朱维铮:《近代学术导论》;上海:中西书局,2013.第47页.
[7]张之洞:《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页.
[8]朱维铮:《近代学术导论》;上海:中西书局,2013.第44页.
(作者单位: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