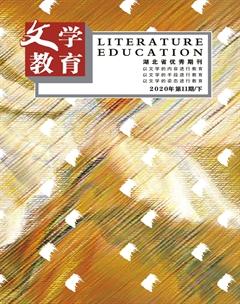相声的意义

2018年中秋节德云社在武汉的演出,我去看了。由于场馆选在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出地铁站几乎走了半小时。一路上一伙一伙的观众,以年轻人居多,大家神色安静矜持,但分明带着难抑的兴奋,许多小姑娘还抱着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小礼物。我的座位在剧场前面三分之一处,其实已经看不清台上的演员了。后面还有三分之二的观众,天知道能看见什么,一开场都因为听不清还骚动了一番。
十几年来,相声从落寞的传统艺术,又回到了大众娱乐的中心。和许多粉丝一样,相声成了我佐餐、催眠、散步的最佳选择。作为一个民间文化的研究者,我也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相声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相声的火热相比,关于知名相声团体如德云社争议也从没断过。尤其是关于“三俗”的控诉,更是悬在当代相声头上的一柄利刃。网络上的舆论也往往极端化,爱者爱死,恨者恨死。那么,相声到底有没有意义?不过在任何表态之前,你得先告诉我,什么叫意义。
一
《改行》是相声中的传统名段,充分发挥了这门艺术说学逗唱尤其是学唱(柳活)的魅力。而且,经过几代艺术家的打磨,它也成了最富有意味的名段之一。《改行》早期版本的故事背景是光绪皇帝驾崩,“国丧”百日,禁止了娱乐活动,一众戏曲和曲艺艺人被迫改行,所以闹出了许多笑话。比如人人都得挂孝,天下不许见红,卖红萝卜都得用蓝布套套起来,酒糟鼻子赤红脸出门也得染蓝了。生活无着,大鼓艺人刘宝全改行卖粥,拿粥锅当鼓,唱曲叫卖,失手打破了沙锅。唱花脸的艺人改行卖西瓜,手拿西瓜刀,使着花脸架子,反倒吓得众人不敢靠前。后来的版本还有以艺人得罪了袁世凯为背景的,新时期之后还出现了以文化革命为背景的。这其中最有趣的一段说,有个唱铁片大鼓的艺人,喜欢加虚字,这个那个之类,有一次红卫兵让他唱毛主席的《七律·解放军占领南京》,他给唱成了:钟山那个风雨起呀苍黄,百万那个雄师怎么能够过大江。
用作品里的话说,《改行》的原因是权力的“专制”,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教条主义。因为专制不一定会教条,会教条的也不一定是有权者。无论是谁,手伸得太长了,往往会教条,而一旦教条了,就一定会闹笑话——用电影《让子弹飞》里的台词,就是“步子迈得太大,会扯着蛋”。相声的基本机制,就利用了这个最朴素的道理: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度。不管多有意义的事情,也都有个度。在那个度内,事情就有意义;一旦过度,事情或者没意义,或者有害,大概率还可能很好笑。相声的基本手段是“包袱”,而包袱的最基本手法,就是找过了度的事情,找错位的情形。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错位也是最容易闹笑话的事。错位就是指不对,或者是不合常规,不正常。所以诸如纽扣系错,方音怪异(相声里所谓的怯口),挤眉弄眼,奇装异服,插科打诨,都会惹人发笑。总之,搞怪也往往搞笑,也就是相声演员常说的“理不歪,笑不来”。所以给姑娘起名叫铁锤、王钢蛋,聋子打岔,《白事会》里爹死了儿子还在剥蒜做炸酱面,这些种种不合情理,是构成笑料的基本手段。相声中有许多关于舞台事故的段子,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文昭关》里说伍子胥上场错带了刀,只能临时改词:“过了一朝又一朝,心中好似滚油熬,腰中空挂二尺刀,眼前的仇人杀不了”。《黄鹤楼》、《捉放曹》里外行冒充内行,频频出错,闹了不少笑话。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当然是《关公战秦琼》了,而《罗成戏貂蝉》、《张飞打严嵩》也是一个道理。错位是相声之为喜剧的基本逻辑,即使所谓“歌颂相声”,也是靠插科打诨支撑的,否则就与宣传、讲道没有区别。比如马季的《登山英雄赞》也得用珠穆朗玛峰上“吃冰棍不花钱”这样的梗。不过,单靠这点,相声不一定搞笑。
二
把唐代俳优李可及放到今天,绝对是一流的单口名家。古人记下了他表演一段杂戏“三教论衡”的内容。人问,释迦如来是什么人,李说,是个妇人。因为《金刚经》里说释迦如来“敷座而坐”,如果不是个妇人,怎么老让夫坐、儿坐呢?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说,也是妇人。因为《道德经》里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如果不是妇人,怎么会有身孕呢?又问,孔子是什么人,李说,还是个妇人,因为《论语》里记载,“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如果不是妇人,怎么会待嫁呢。
歪讲歪批是相声文哏类作品中的常用技法。比如研究孔子弟子有几多成年者,几多未成年者。答曰成年者四十二人,未成年者三十人,因为《论语》里说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加一块七十二人。但这个包袱远没有前面那个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后边只是一种“错”算,前一段还有更多的意味。相声利用错位,其实是把两件不同的事、两个不同的意思搁一块来说。而且,这两件事、两个意思之间还得有个高下之分,意义有别。两个意义间的差别越大,就越搞笑。《规矩论》就是利用了这个道理,把饭馆里的话搁到厕所里说,所以笑料很足。歪批类相声所以搞笑,就是利用了经典和日常之间的高下之分。李可及的段子之妙,正在于他将那个时代背景下最崇高的圣人和最卑微的女人搁一块来说了。其实这是喜剧艺术的通则,用电影导演王晶的话说,搞笑就是用最正经的话讲最不正经的事,或者反过来,用最不正经的话讲最正经的事。
因为屎尿屁和伦理哏的东西多了,相声(包括许多喜剧艺术)被某些人认为不正经、低俗,甚至于意图灭之而后快。不过有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正经,但不正常。如果屎尿屁能搞笑,那厕所估计就是人间天堂了。屎尿屁既不低俗也不搞笑,把它和另一些东西放一块,才可能有笑果。就像郭德纲的段子说,于谦一上台就把裤子脱了,不会有人买票来看。同样地,《金瓶梅》也不搞笑,只有说于谦的父亲出身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丰富,有各种版本的《金瓶梅》,这样才搞笑。因為相声不是单说一件事、一个意思,它把两件事、两个高下有别的意思搁到一块,才能制造笑果。而且,相声的艺术性还表现在,要在最出人意料处建立这种关联和对比。所以说,相声中荤口的趣味根本就不在色情,而是在最出其不意处建构色情。就像郭德纲的作品里说,于谦丢了烟卷,发一微博: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过来一分钟,嫂子发来短信:对不起!
三
那么,相声这样搞笑,到底有什么意义?估计正经人还是想不通。不过,相声专治正经人,尤其是正经到古板的人。回到前面那个意思,什么事情都有个度,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单拎出来说,每件事可能都有意义。吃饭这件事有它的意义,上厕所这件事也有它的意义;禁欲这件事有它的意义,男欢女爱这件事也有它的意义。最可怕、可笑的事,是把某一件事看得太重。相声和喜剧艺术的意义,就是用最搞笑的方式指认这个最严肃的道理。它在一件事过度的时候,用另一件事去挠痒痒,重新把快要混淆的界限厘清,为双方再次正名。侯宝林大师的《买佛龛》里说有个老太太迷信,买灶王爷都得说请,有人问,大娘,您多少钱请的?老太太说:“咳,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这老太太才是个健全的、通人性的人啊。
人分三六九等,肉有五花三层,事也有个轻重缓急。分开来看,事情都可能有它的意义,撞到一块,就必须得有个区分、抉择,这就是价值问题。相声专治各种拎不清轻重缓急的思维和做法。在这个意义上,相声是门讽刺艺术。传统作品《当行论》讽刺当铺先生的傲慢冷酷,《找堂会》讽刺艺人的虚荣与贪婪,单口《测字》讽刺江湖骗子的狡诈,《改行》、《关公战秦琼》讽刺当权者的蛮横无知,都令人印象深刻。八十年代《小偷公司》讽刺官僚主义,包括岳云鹏的歪唱《五环之歌》,都有所讥刺,而且是伤筋刻骨的讥刺。
但是,相声的讽刺,绝不是批判。批判就是一个对,一个错,对的表扬,错的处罚。相声的讽刺不是这样。它要区分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谁过分;谁的手神得过长,就打谁的手心。所以相声的讽刺针对的是教条,以及虚伪。教条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老子就是永恒、唯一的真理;虚伪则是明知道事情还有另一面,嘴上偏偏不承认,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著名相声作家何迟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名段《开会谜》里讲某干部,为剧团买俩脸盆的事,开个职工大会来民主决定,开头还要讲一段大好形势,这治的是教条病。郭德纲的段子说,有些人马路边上也是一说话一半儿中国话,一半儿英语。买个苹果也是“Hello,大爷。我look一look,你这apple是五块钱七斤吗”?这治的就是虚伪症。得前一种病的,是官人居多,得后一种病的,以文人居多。所以这两类人是相声中最大的笑料,也往往是这两类人,以相声为死敌。
四
人活着就得找出意义来。意义有高有下,有多有少,构成人生百态。但人生中有些事,它根本就找不出意义来。比如劳动这事有意义吧,当然是,人不能靠喝西北风活着,所以人必须劳动。但是,劳动一天,汗流浃背、腰酸背痛,它本身最终找不出任何意义。孝敬父母这事有意义吧,当然是,但是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事它也累啊!正因为累没什么意义,所以这些事才有意义;如果累本身有意义,这些事反倒没什么意义。所以人活着就是个大悖论。而且,这大悖论中最大的悖论,就是人还有死。而死,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意义的。如果说牺牲是最伟大最有意义的,那正是因为死是最没有意义的。幸亏,人生还有件事,是最没有意义又最有意义的,那便是男欢女爱。所以,性和死,成了相声(以及喜剧艺术)里最有力的题材。相声调戏死亡,它通过模拟死亡,驱散死亡无形的威胁;它模拟欢爱,给死亡和荒诞威胁的生存一个“底”。
讽刺仍然活动在意义的范围内,它针对的只是大意义和小意义,一种意义和另一种意义。但像死这种东西,直接掀开了人生意义的这层帷幔,透露出宇宙间无尽的空洞。讽刺对此是束手无策的,讽刺的笑驅散不了人生最终的空洞。它需要大笑,需要一种比无意义的空洞更无意义的大笑。那是对最没有意义的屎尿屁的沉溺,对最出其不意的欢爱的拥抱,对最阴郁的死亡的纵身一试。没有勇气直视人生之空洞者,也没有勇气承认这种笑。他们只敢匍匐在各种意义的包裹之中,受其枷锁桎梏,也不敢多越轨一步。
而敢于调笑是最勇敢者、最通达者的游戏,也是最伟岸者的游戏。只有伟大的勇士才能看破生死,笑对一切,牺牲者临死前的大笑,是比一切力量更伟大的力量。只有最懂得大义的人,才会不拘小节;而宵小虚伪之徒,才见不得一句脏话。所以,狠批三俗者,很可能毫无操守。而最伟大着,反倒不以相声为俗,且将这种曾被目之为下三滥的行当正名为“语言艺术家”。不过,很遗憾,这样的通达者并不常见,世间往往官人、文人横行,伪人、末人诺诺。尘世难逢开口笑。
五
因为权势者往往教条,高雅者易于虚伪,所以相声基本上还是弱者的艺术,穷人的艺术,被压迫者的艺术。相声是小人物们的艺术,是小人物的小思想。小人物许多时候没空想那么些宏达的主题,即使艳羡上等人的潇洒,往往没上等人的福份。相声于是专把高高在上的大人往下边拽。郭德纲的段子里,富人有钱了,早餐是卤煮,中午炖吊子,晚上大肠刺身。于谦有一段歪唱吕剧,也是异曲同工:“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剥大葱。”
小人物也艳羡英雄,又做不了英雄,受不了当英雄的罪,所以也怕英雄。相声也要把英雄拉下神坛。《卖马》里边是最落魄时候的秦琼。秦二爷交不起房钱,付不起酒钱,店家一要钱,还耍起了无赖,要不就是装睡。可是一听到包子,立马就醒了。同样,戏弄英雄,也不意味着否定英雄。还是那句话,相声不否定,它寻求平衡。
更何况,许多“意义”,其实是在上者发明出来,给自己挣面子、且驳下人的面子的。高雅、低俗就是这些雅人闲人的话术。比如喝咖啡高雅,吃大蒜低俗;喝蜗牛汤高雅,嘬螺蛳低俗。而相声偏偏专治高雅。据说八股文高雅,于是有了《文章会》;据说住大宅子的高雅,于是有了《夸住宅》;雅人自然多讲究,于是就有《夸讲究》。雅人一听吃牛舌就受不了,哎呀,牛嘴里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吃呢,给我来俩鸡蛋吧。
相声作为喜剧艺术,作为搞笑的艺术,其实也是分级的。就像相声里说到,笑也有规矩。最一般的笑,就是错位带来的笑,搞怪的笑;再有意义一点的笑,就是讽刺的笑;而最有意义的笑,就是最没有意义的笑,就是纯粹滑稽的笑。无论那种笑,都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任何意义,都是有限度的,过犹不及。这个道理,对相声本身也适用。如果某些调侃过了头,也会侵犯到某些彼时彼地应然的价值。近年来某些相声演员引起舆论非议,诚然不可卸责。
但是,无论如何,正如郭德纲所说,一个不会笑的民族是悲哀的。我想补充说,一个不会笑的民族,可能悲哀但算不上悲剧。因为悲剧告诉人们有些价值值得坚守,值得牺牲;喜剧(相声)则告诉我们,价值坚持得过了头,可能是个笑话。一个不懂得价值的界限的民族,很可能不是愚昧,而恰恰是因为虚伪横行,缺少对价值的坚守。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