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则贤:少年学得会“量子力学”吗?
向治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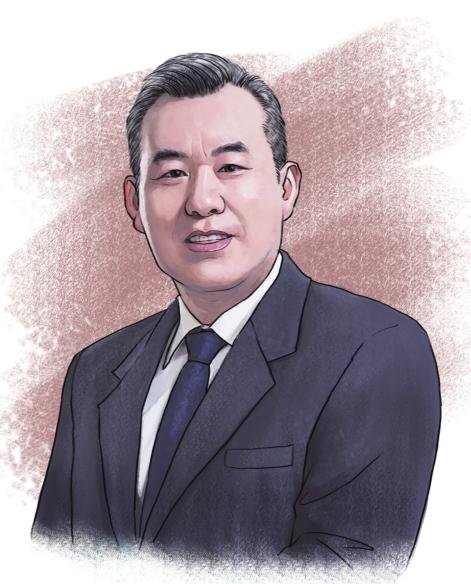
从19世纪以来,世界进入科技时代。无论喜欢与否,我们都不能否认,科技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用曹则贤的话说,“我们处在一个科技超越神话的时代”。
不过,科技不只是科技。比如在20世纪,核能源开发,送卫星上天……一系列科技成果,离不开政治的支持。这是因为,科技水平决定了国家强弱,那么,很显然,国家有必要主动参与技术的发展。
目前,“量子科技”就成为这样一座高峰。
国与国间的战略博弈已经开始。今年8月,美国政府公布提议,计划将人工智能(AI)和量子信息技术研发的预算增加约30%。美国一直在加码量子技术,这只是最近的一次。
中国方面,量子科技的重要性也被提出。10月 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举行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规格非同一般。
为什么在今年,量子科技被再次强调,而在此领域的角逐愈发明显?
为此,南风窗记者在北京专访了曹则贤。他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做科研的同时,曹则贤也出版了多本书籍,最近的有《相对论—少年版》和《量子力学—少年版)》。
为什么是“少年版”?曹则贤表示,少年版不代表“通俗易懂版”,而是说,这是少年就应该懂得的知识,这是人家的少年参与创造的历史。我们的对话就从两本书开始,谈到什么是“真知识”,而懂得“真知识”的少年,与国家量子科技的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一体性。
是“高阶”,还是“标配”?
南风窗: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给人的印象一直很高级、很难懂,到了大学专业课才会学的。你怎么想到写专门的“少年版”?
曹则贤:少年版有它存在的意义,分两方面吧。一方面是,人家在100多年前,创造量子力学学问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些少年。奠定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这两本书的关键思想的人,甚至有刚刚高中毕业的。
什么意思呢?量子力学也好,相对论也好,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要用群论的。奠定群论的人,也就是第一个把群论引入到数学里面的人,是法国人伽罗华,他1832年去世的时候,不到21岁。他给我们创造群论的时候,只有十八九岁。
第二,广义相对论的关键概念叫弯曲时空,那么弯曲时空就有一个到底怎么弯的问题,描述一个几何体怎么弯、弯的程度,那个概念叫曲率,而最先引入曲率这个概念、给出第一个曲率公式的人是法国人,叫克莱罗,人家给出这个曲率公式的时候是16岁。
还有很多例子,比方说,包括写相对论综述文章的人,在当时也是少年。我们知道,1916年3月份,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过了两三年的时间,要对整个相对论作一个总结,而总结的任务,落到了德国慕尼黑大学里面的大一新生,奥地利人泡利。
这是第一个方面,你就知道,学问的创造者,有些本身就是少年,而且还是100多年前的少年。
第二个方面,回到我们的21世纪,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始终认为,它已经是一个技术超越了神话的时代,我们现在玩的许多技术,比过去的神话,比方说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我们现在比那时候的神话已经高明多了,对吧?
那么在这个时代,知识已经发展到很高深的阶段。我们到了少年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大学之前,这些东西如果你没学过,或者还没有打下扎实功底,这个少年基本上是不可能到前沿去的,现在就是这个局面。
高深的知识太多了,上了大学,有的是更高深的内容要学,我想说的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我们的少年人,至少是一批优秀的少年人,他们应该学会。
南风窗:你的意思是说,在当下,少年们学会这两门课,对发展物理很有必要。但是,学不学得会又是一回事?
曹则贤:有的是少年能学会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主要在于教育,我们的教育水平太低了,我的说法是叫,“课程浅得让人想哭”。
当前,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提供课程的难易程度,远远赶不上欧洲100年前的难度,甚至也赶不上中国清朝末年洋务运动时候,中国学堂里的水平。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福建福州有一个马尾船政学堂。在那里,既有学堂,又有造船厂,还有设计局。当时那里面有牛人工作,同时开办了学堂,教育的孩子都是福建当地的孩子。
不存在有人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教会这种最深刻的学问,天底下没有这种便宜事。
我去看过,现在有个博物馆在那。清末的时候,十三四岁男孩读的数学物理,都是正经的法文、英文原版书,而且学的难度,可能比你读“985”的大学数学也要难一点。我看过一个21、22岁男孩学习过的书,一摞子书,比他人还高。
教育,是“死结”也是“钥匙”
南风窗:我看了一下《相对论—少年版)》,从十页往后,就出现了很多高数内容,不是轻松能读懂的。
曹则贤:这是我的一个理念问题,也是从自己的学习和教学过程当中,我得到的体会:不存在有人能够用轻松的方式,教会这种最深刻的学问,天底下没有这種便宜事。
这有一点像爬山。没有一个人能跟你说,不做专门的登山训练,不能够抗稀薄氧气,不能进入暴风雪,然后说,可以带你去看这个喜马拉雅山。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说到高数,我们还是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普及数学的思维。高等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难度、深度。但几何、代数、群论、拓扑、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微分方程理论,这些东西具体的没有学,却说学了高等代数,高等数学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没有给下定义。
这也是说,我们现在的常规教育,从过去那种扫盲班开始,就这种心态发展来的。它导致了我们的学生不知道,真正的学问有多深。也就是刚才说的,事实上,我们大学教育的内容,程度非常低。
南风窗:学生做题很厉害。
曹则贤:真题目他就不会了。什么是真题目呢?比如,氢原子四根谱线的波长数据,你能从中看出自然的奥秘吗?这就是好问题。算题不算本领。比方说一元二次方程,你会解。人家给你一个公式,有系数,你能找出两个根,对不对?但这不算什么水平。
真正的水平是,关于一元二次方程,你到底能看出它数学结构里头是什么东西?这些是学生们都没听过的,比方说有交替的问题,有循环群的问题,有用待求的根表示根的问题,有内积的问题,有判别式的问题……

只是对方程求解,那算什么本事啊?所以说,如果等到高中以后,习惯了这种认识:“给出公式、求解”。这就会导致,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学数学、研究数学的资格。
该怎么数学思考,该怎么看数学问题,这些训练如果没有,往后就来不及了。
南风窗:所以你面对的情况下,培养出一批懂“真问题”的学生,其实是很紧迫的?
曹则贤:对,学生再经过大学4年,本来4年也没上几天课,大四还马上去找工作,这时候没受到真正教育的人,从做研究的角度来看,就已经废了。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到研究生阶段,现在找优秀年轻人,但基础是那个样子,都来不及了。最怕的是,这一波人在将来成为老师的时候,就更要命了,他连眼界都没有,他没学过没听过。
少年的“可能性”
南风窗:你刚才说过,“年纪大了就来不及了”,这是“少年版”存在的意义之一。你以后还会写别的“少年版”嗎?
学问本身该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
曹则贤:我还有想写的,不一定要强调是“少年版”,但是我在写一些能鼓励少年的东西,比如说《一念非凡》和《经验一击》,都是介绍数学和物理里面重要的东西,都是能给年轻人讲懂的。
所以,虽然名字上没有少年版,但是我一再强调,这些都是少年要学会的东西。少年不是学不到这个层面,很多人只是不知道有这个层面。在今天的世界里面,想在数学和物理方面去做研究,这是必须的。因为这些东西,可能都是100年前人家少年做出来的。
再一个,其实我也不想用“少年版”的噱头, 有一些人,本来对这个说法就不太赞同,他们认为难了。可是,很多年前别人家的少年在大学里学的热力学、电动力学、经典力学这些东西,难度都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
所以在书里面,我都强调一个观点:限制这本书难度的唯一的因素,是作者本人的水平。你不能用你自己掌握的程度,来当成学问自身的程度。学问本身该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的。
其实出版社也对我说过,说我的书太难了,卖不出去多少。我会跟他说,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卖两本书挣钱,我要是为了挣钱,我为什么干这事?这能有几个钱?
南风窗:我发现,在你的写作里,“十几岁的少年”,始终是你想象中的读者。为什么“少年”对你是一个关键词。
曹则贤:知识在今天,发展到相当高深的程度。如果在少年时没达到一定层次,那么,他中老年做的那些东西,是很难有高度的。
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有钱做科研,其实很了不起,但其中多亏了一个人,就是李政道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他组织了一个叫CUSPEA的考试,把中国学物理的优秀少年们送到美国培养,总共选拔了913个少年,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物理的学生913人,其中中国科技大学是315人,我是属于考不上的。
这913位同学到美国去,因此培养出了一批人,使得华人在物理学界,多少有点声音了。再接下来,我们国家又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叫联合培养实验物理博士。第一批是7个人,我就是第一批的。差不多总共是组织了7届,前前后后40人左右。
我26岁去的,我就发现,已经是来不及了。像文小刚他们去到美国,差不多是20岁,然后他到美国以后,跟的是极优秀的物理学家,包括一些诺奖得主或者数学的菲尔兹奖得主。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成就的人了。
像我这样再去,26岁了,当然我自己底子也差,所以,论学问我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了。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这就让我在想,我们的少年培养,一定是要加速培养的。当年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确实培养出相当一批优秀的人。这个理念是对的。
科技追赶“路漫漫”
南风窗:现在不是上世纪80年代了,今天中国的科技和应用,已经追上来了,不是吗?
曹则贤:我们在技术领域方面有了相当多的创新,但是你同时也会注意到,我们所谓的卡脖子问题,什么叫卡脖子?人家会、你不会,而且那个东西是关键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光刻机,光刻机是一个技术问题,可是有这样技术的背后,是人家的积累。比方说,光刻机为什么产生在荷兰?它为什么只有荷兰有,它一定有它的必然性。
荷兰人对物理学的贡献,那是在根本上的。比方说,是荷兰的惠更斯,理解了光的波动性,他给人类做出了第一台钟表,有了钟表才有精确计时时间,才有物理学的发展。是荷兰人善于磨镜片,有一天,有个眼镜店的学徒工把两个镜片前后放的时候,才发明了望远镜。
光刻机是一个技术问题,可是有这样技术的背后,是人家的积累。比方说,光刻机为什么产生在荷兰?它为什么只有荷兰有,它一定有它的必然性。
技术的背后是科学,这是人家创造的。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光刻机在荷兰了。举个例子,固体刚体物理、流体物理、量子力学、相对论、规范场论,都产生于瑞士。你什么时候听说过,瑞士说谁卡它脖子?
南风窗:在新兴技术上,现在常说的“弯道超车”,你认为成立吗?
曹则贤:说个简单例子,比如谷歌公司。它有所谓的人工智能,对吧?那么,这个公司是怎么来的?它缘起一个数学算法,那个才是核心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的数学水平没上来,你最后的AI,一定是浅层次的AI,最新的最深刻的,永远是你不会的。你不能说拿别人的技术,或者说在这基础上有一点点创新,使得产量比别人多点,销售额比别人多点,这个就叫超车。这不成立。
南风窗:所以科技的追赶,并不像常人想象的简单。说回量子科技上,它很可能是下一个“科技革命”的主角,我们也能看到,它到现在受到的重视程度。从你的角度,如何评价?
曹则贤:其实,量子科技也不是现在才重要,只不过,“量子科技”这个叫法确实是在现在被提出来了,而且是专门提出来,说明国家更重视了。
我分析可能是有这么两点,一个是,到今天我们认识到,量子力学会带来更多的对技术的改造,对器件的运用,所以今天变得紧迫了。为什么?我在去年的量子力学跨年演讲里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是,光是我们和远方连接的唯一途径,另外一个,光也是我们能进入微观世界的唯一的工具。
另外一点就是说,紧迫性还在于,如果一类即将到来的新技术,关键是量子力学特征的东西,并且可能会有颠覆性意义的话,今天的中国希望开始就是个参与者,我觉得有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主角一直是电子和光子,而这,也是今天能够带来新技术的两个关键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当前社会,如果你要想创造出来新产业的东西,你是绕不过量子力学了。
在过去,热机时代、电气时代、半导体时代,我们都不是参与者,更不是创造者。国家对基于量子的技术的迫切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像跑步时,希望自己是第一梯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