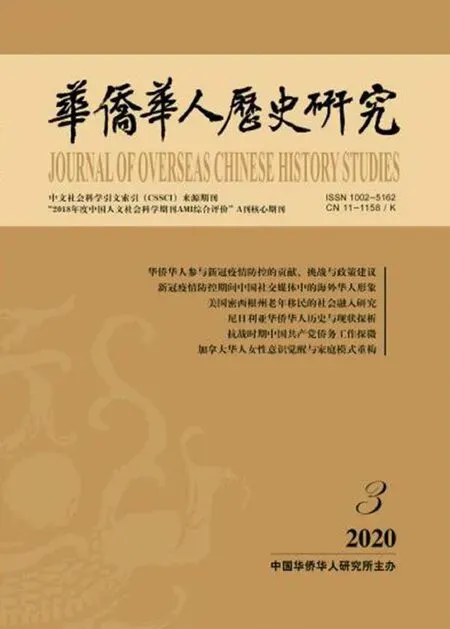晨曦微露:清政府对海外侨民身份认知的转型
——以新加坡为例
王学深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88)
19 世纪70 年代,清廷开始向海外派驻公使、领事。在此背景下,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 —1891)于光绪二年(1876)九月十七日在《出使英国酌带随员折》内建议,“南洋新加坡等地华民流寓数十万人,应设立领事”,[1]以管辖华民和保护华商,这一提议得到军机大臣“奉旨依奏” 的回复。次年,胡璇泽(胡亚基,1816 —1880)成为代表清廷驻新加坡的首任领事,同时新加坡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处设立领事官的海外驻地。光绪十六年(1890)十月初十日,薛福成(1838 —1894)又上奏折请求英属南洋各岛改设总领事官,经总理衙门大臣奕劻(1838 —1917)等会奏后,朝廷最终同意薛福成所请,新加坡改设总领事以管辖南洋各处华人商民,而具有出任旧金山领事经历的黄遵宪(1848 —1905)被清廷选任为首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自黄遵宪始,清廷共派驻新加坡总领事、署理总领事实际赴任者共9 人,依次为黄遵宪、张振勋、刘玉麟、罗忠尧、吴世奇、凤仪、孙士鼎、左秉隆和苏锐钊。
在清廷派使驻新加坡领事的34 年时间里(1877 —1911),新加坡的华人数量逐渐上升,从1860年的5 万人左右,上升至1911 年的219,577 人,增幅达338.8%。相应地,移居新加坡的华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也从62% 上升至72%,而其中80.2% 是在中国出生的。[2]虽然尚不清楚新加坡归化为英籍华人的准确比例,但根据埃迪所著《马来亚的华人》一文中所提出的28.2 万名华人中,归化英籍者占4.4 万人[3]的数据推测,新加坡一地华人归属英籍者之比例应该在15% 左右。换言之,在新加坡等地,华民尚未归化为他籍之人占据了更大比重。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晚清政府是如何看待这些移居南洋的华人的?对于大多未归化为外籍的华人群体,清政府是仍视这些移居南洋的华人为清朝子民,还是以外国子民视之?是将这些移居外洋的华人以偷渡者论罪,还是给予他们承认和保护?清政府为何转变对侨民属性的认知?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增进同在地侨民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追索,是推动本文写作的关键动力。
目前,学界对于清政府华侨政策转变之研究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积累,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关注晚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转变的总体性论述与分析方面;二是聚焦在清政府对海外华工的保护方面。①针对晚清政府与海外华工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颜清湟所著《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一书。该书讨论了晚清政府对于出国华工的态度转变,即从禁止苦力贸易向保护华工政策转变,并相应地努力保护海外侨民。参见[澳]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 年。这方面的著作还可参见赵巧萍:《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政府的华工出国政策》,《中国工运学院学报》1996 年第1 期;袁丁:《晚清对待华工出国中拐匪的态度及其演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庄国土:《清朝政府对待华工出国的政策》,《南洋问题研究》1985 年第3 期;李家驹:《清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态度与政策》,《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6 期;李家驹:《同治年间清政府对华工出洋的态度与政策》,《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3 期;等等。本文主要从晚清政府的角度讨论其对海外华侨认知的转变并聚焦于新加坡一地,属于上述研究的第一领域,故对这方面的学界成果集中做一个简短的学术回顾。
廖赤阳从“护侨” 政策出台的背景、护侨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清政府出台“保护章程”,设立“保商机构” 和兵舰护侨等具体措施。②廖赤阳:《晚清“护侨” 政策的实施及评价》,《华侨大学论丛》1984 年第1 期。刘世扬从政治、经济等角度讨论了晚清时期清政府开海禁、引利源的策略变化。③刘世扬:《清末华侨政策转变初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3 期。韩小林详细论述了清政府对海外侨民认知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变化不仅增强了海外华侨和祖国的联系,还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④韩小林:《论清代华侨政策的演变》,《嘉应大学学报》1995 年第3 期。黄小用不仅讨论了清政府对于“苦力贸易” 和对待海外华侨政策的转变,并着力研究了郭嵩焘、张之洞、黄遵宪、薛福成等人在“护侨” 方面的思想与行为。他通过开海禁、引侨资、建商会、兴教育四个方面论述了晚清政府对待海外侨民策略转变后的具体措施。⑤黄小用:《晚清华侨政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刘红艳、骆莉从清政府吸引华资、稳定统治秩序的需要和官员意识的转变等方面论述了晚清政府对华侨政策的转变,并提出清末期间驻外公使、领事的制度设立与派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当地华侨权益以及贯彻清政府侨务政策的作用”。⑥刘红艳、骆莉:《清末政府的侨务活动浅议》,《东南亚研究》2005 年第2 期。类似成果还有万晓宏⑦万晓宏:《浅论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之演变》,《八桂侨刊》2001 年第1 期。和李嘉川⑧李嘉川:《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华侨政策的变化研究》,《文史资料》2017 年第4 期。,均讨论了清政府对华侨政策变化的背景与具体措施。
在以上这些宏观的研究视角之外,学者也逐渐将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变化与具体地域相联系。以东南亚为例,冀满红就关注到清政府对东南亚华民的保护政策方面。他从清政府修例护侨、制定国籍法护侨、签订双边协定及设立保商局等机构护侨予以了具体的论述,并将国内形势变化与清政府对海外侨民政策变化相联系,认为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政策从“不闻不问” 向积极保护具有突破性进展。①冀满红:《论晚清政府对东南亚华侨的保护政策》,《东南亚研究》2006 年第2 期。近来,李章鹏更具体讨论了中荷在荷属东印度地区,针对设立领事和在地华侨国籍归属问题的谈判、交涉过程。作者提出虽然经过四年艰苦的谈判清政府被允许派驻领事,但却屈从于荷兰方面所坚持的在地华侨“属地” 原则,最终导致在地华侨全部被归入荷兰国籍。②李章鹏:《中荷设领谈判与华侨国籍问题交涉(1907 —1911)》,《近代史研究》2019 年第4 期。
通过以上学术回顾可见,学界对于晚清政府海外华侨政策转变的研究已有一定厚度,但更多是以宏观视角讨论清政府从禁海到开海禁的阶段性转变与时代背景,并选择清政府在修例、签订双边协议护侨等方面的努力,而作为华侨的因应互动,学者也更多选择了经济和教育领域展开论述,却忽视了清政府在观念转变后意图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行政手段,以图宣示“国家—侨民” 关系的努力。此外,虽然已有学者将东南亚作为研究的聚焦地区,但对于新加坡一地尚少关注。因此,本文试图以晚清政府的视角为基点,在“开海禁” 的大背景下,以清廷向新加坡颁发《时宪书》、《大清国籍条例》出台与新加坡户籍统计工作开展、派兵舰巡阅新加坡与南洋等地及新加坡在地华侨赈灾捐输与封赠的常规化等具体问题作为切入点,讨论在近代化大环境下清政府对于海外华侨认知的转变及其意图加强对海外侨民管控的努力。
一、从“偷渡正法” 到“我国侨民”:清代官方对子民出洋性质认知的转变
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初十日,作为二品顶戴出使大臣的薛福成以“时势互殊,例意已变”为由,上了一份《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折》的奏疏。这份长达千言的奏疏分为三个部分:回顾清代海禁历史,陈述南洋新加坡等地的移民现状,以及开海禁后所带来的益处。通过分析这份奏折,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18 —19 世纪世界大势的转型之际,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对18 世纪的禁海规定做出了修订。虽然在“近代化” 的外交领域内出使南洋新加坡的领事制度还有各种不完善之处,但对移居海外的华民身份认定却有了180 度的转变。
(一)薛福成关于开豁海禁背景的分析与论述
清初顺治、康熙年间,由于郑成功父子占据福建、台湾等地并不断袭扰浙、闽、粤等地,客观现实促使清政府出台“海禁条例”,规定“凡闽人在番托故不归,后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正法”。[4]虽然康熙五十六年(1717)对于南洋贸易案,康熙帝给予恩典,做出了“令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俱准回原籍” 的决定,但这并没有改变雍正和乾隆两帝延续清初海禁条例的做法与决心。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认为滞留外洋不归者“皆甘心异域”,并谕令“违禁偷往之人,不准回籍”,以防止这些久居外洋之人与番人勾结,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乾隆帝一以贯之,严查私自偷渡出海之人。乾隆十四年(1749),朝廷将私往噶罗巴充当甲必丹(Captian,船长之意)的陈怡老,给予“严加惩治,货物入官” 的惩罚。
通过这些官方条例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7、18 世纪清政府是严禁天朝子民私自出洋且滞留不归的,并将私自外出之人视为偷渡者,甚至是叛国行为。清政府认为对于私自出洋行为的管控“禁之则可以孤寇党、弭衅端,不禁则虑其泄事机、伤国体”,[5]所以这种从国家管控和安全出发的视角是贯穿于整个18 世纪的清政府政策中的。除此之外,对于劳动力流失与赋税减少的担忧,如“承平之世,地广而人不稠,人散则土益旷,深维至计,首悬厉禁”,[6]同样是清政府在这一时期禁止子民私自出洋的重要原因。
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迫使清政府对传统的朝贡体制做出调整,即“自道光庚子订约,始与敌体相等”,[7]更在“近代化” 的新型外交关系框架下,促使清政府和出洋大臣做出观念上的转变。在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旧禁以护商民折》的第二部分,他详细汇报了自光绪十七年(1891)以来对于南洋华人的观察状况。薛福成指出,南洋华人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比可达七成以上,而追寻这些华人的籍属又以“广、琼、惠、嘉各籍,约居七之二;粤之潮州,闽之漳、泉,乃占七之五”。[8]
作为南洋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些自中国移居新加坡等地的华民,并没有改变他们作为中华子民的风俗习惯,而这一点也是薛福成主张清朝政府仍将允许这些侨居在新加坡和南洋各地的华人回归清朝,并予以保护的有力依据。薛福成指出,这些华人“虽居外洋已百余年,正朔服色,仍守华风;婚丧宾祭,亦沿旧俗。近年各省筹赈筹防,多捐巨款,竞邀封衔翎顶以志荣幸。观其拳拳本国之心,知圣泽之浃洽者深矣”。[9]
除了在实际生活中的服饰与风俗坚守之外,身处南洋的华人对于故国的捐款和仍以获得清朝封赠为荣的态度,构成了他们回归清朝的内心认同。然而,移居的华民尚未回归清朝的原因,在薛福成看来就是因为清朝“海禁条例” 尚没有被废除,担心朝廷仍旧以“逋盗者”“通番者”“接济海盗者” 等罪名将他们惩处,从而招致“官长之查究,胥吏之侵扰,宗党邻里之讹索” 等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薛福成认为要招徕海外华人回归故国必须从国家层面转变,并对出洋者身份性质的界定,以“大张晓谕,申明旧例既停,新章早定”,怀着开放的态度接纳这些久居新加坡等处的海外华人。实际上,在薛福成奏折的第二部分,他已经明确提出了清政府应该转变陈旧的禁止国民私自出洋的陈腐章程。在这些南洋华人风俗、衣着未变的大前提下,将他们从传统负面性质界定下的“偷渡者”身份中解放出来,这是其“时势互殊,例意已变” 的重要注脚。
在薛福成奏折的第三部分主要谈及了开豁“禁海令” 对于清朝的益处。他提出转变对于海外华人的身份界定,“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10]薛福成对于开放海禁和招徕南洋华人的主要目的,还是希望本着经世致用的原则,“凝聚人心”,“提振国力” 以更好地应对19 世纪末的危机与新格局。
(二)清政府允准薛福成奏请并正式开豁海禁
在薛福成的这份奏折上达朝廷后不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经过商议后,认为应该允准薛福成的提议,并提出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予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并得到朱批“依议,钦此”[11]的肯定回复。至光绪十九年(1893)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以字寄的形式抄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刑部,确认了薛福成和总理衙门申请豁除海禁的两份奏折,并令各有关衙门和沿海督抚遵照办理。兹录全文如下:
军机大臣字寄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刑部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奉
上谕刑部奏遵议出使大臣薛福成奏请《申明新章,豁除海禁》一折。据称内地人民流寓各国,其有确守华风,情愿旋归乡里者,应由各出使大臣颁给护照,任其回国,并由沿海各督抚督饬地方官严禁胥吏人等侵扰、诈索。至私出外境各条,薛福成所请酌量删改之处,拟待纂修则列时,奏明办理等语,著依议行,即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行沿海各督抚及出使大臣一体遵照。刑部折著抄给总理各国事衙门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2]
至此,清初为防止东南沿海袭扰的“海禁条例” 在清末最终被废除。该谕旨颁发后不久,“豁除海禁” 的消息传到新加坡等南洋各地。在1894 年1 月31 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新晚报》和《海峡时报》上对该诏谕做了转述,并言及“一切出洋的守法中国人仍然是帝国的子孙”。[13]实际上,在这份诏谕传到新加坡后不久,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就开始推进华人返乡颁给护照的具体步骤,并以在地的福建商家作为传播和推行这一新条例的代理人。虽然英人提出“中国领事若是误以为他可对华人所感兴趣的本地事务进行干预,那将是错误的”[14]的指责,但从黄遵宪在接到诏谕后招徕在地华人返乡的积极性来看,他无疑对薛福成和朝廷开豁海禁的做法表示赞同,也表达了他对国家管控属民的认知。①“天到珠崖尽,波涛势欲奔。地犹中国海,人唤九边门。南北天难限,东西帝并尊。万山排戟险,嗟尔故雄藩。” 此诗是在黄遵宪任新加坡总领事期间所留存的一组杂诗中的第一首,不仅表达了新加坡所处的地理位置,即“珠崖尽”,且以“中国海” 和“九门边” 暗指清朝和英帝国,表明虽然新加坡还地处中国海范畴之内,但却已为英所属。不过作者话锋一转,强调尽管清朝与新加坡虽分处南北,远隔万里,但是却保持着联系,以致天险难以限制。特别是后半句,黄遵宪更以战国中期,秦昭襄王与齐闵王并称“东西二帝” 为例,比喻自清政府设立新加坡总领事后,清朝总领事与英帝国新加坡总督共同治理此地。在一定程度上,此诗表达了黄遵宪清晰的近代化“国家” 模式下的外交思想,并暗喻了对当地华民治理的“国—民” 关系模式。
(三)清政府对于海外华民身份属性认知的转变
清政府对于新加坡在地华民身份属性从“偷渡者” 向“我国侨民” 的转变,更加清晰地体现在朝廷为两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1850 —1924)和苏锐钊(1863 —?)所颁发的敕谕中。在给左秉隆的敕谕中,朝廷提出左秉隆作为新加坡总领事,对于侨寓华民负有“稽查保护责任”,即“照料所有华商即内地人民”[15]的责任,从而使得在地华民各安生业。而在给苏锐钊的敕谕中,更是明确了清朝作为国家和驻外华民的关系,以“侨民” 身份正式定性了这些出洋谋生寓居之人的性质。谕旨中言及“新加坡一埠为南洋各岛商业之总枢,我国寓居侨民日益众多,商务殷繁,保护稽查在在均关紧要”。[16]同时对驻新加坡总领事提出了保护在地华民的职责要求,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政府以“我国” 定义自己的政权,而将出洋寓居之人称为“侨民”。这些词汇的使用,不仅让人明确感受到一种近代外交观念和模式的形成,同时更加清晰地界定了清朝政府和这些出洋华民的关系。
从清初以来所规定的海禁政策并以“偷渡者”“通番者” 甚至“海盗” 等形象界定出洋谋生的中国人,到1893 年朝廷谕旨正式豁免海禁,给予出洋华民合法身份,最终到“我国侨民” 概念的使用,这一转变历经了近250 年的时间,这种近代外交观念的形成是清朝政府面对“千年变局” 的时势所做出的一种因应调整。实际上,这种转变也被视为光绪帝在位期间的一项重要惠政。在光绪帝的奉安表文之中,言及“(其)他如豁除海禁、侨民内渡、遇险外夷亦蒙矜恤。万方赤子,一视同仁”。[17]笔者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通过清政府向新加坡华民颁布《大清时宪书》和户籍统计工作展现这种新型“国家—侨民” 关系的确立。
二、“得奉正朔”:时宪书的颁发与户籍统计对新加坡华侨身份属性的认定
时宪历在帝制中国有着昭示天下一统的寓意,任何个人不可私刻,否则政府将处以严厉的刑罚。乾隆元年(1736),为了避讳乾隆帝弘历之讳,钦天监将时宪历改为时宪书,并作为清政府唯一授权的机构,继续掌管时宪书颁行天下事宜。嘉庆年间,就曾发生过坊间小贩私刻时宪书被给予严惩的事例,涉事的官员们也都受到朝廷的处分,以致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强调“时宪书颁行天下,以便民用。若不遵钦天监推算,自行私造,干支错误,自应从重治罪”。[18]由此可见,颁授时宪书实际上暗示着清政府对臣民的一种统治权。
(一)向新加坡华民颁发时宪书
随着清朝政府“海禁条例” 的豁除,以及对移居外洋侨民认知态度的转变,意味着那些移居外洋但尚未加入其他国籍的华民,仍旧被视为清朝子民。在这种新确立的“国家—侨民” 关系下,清朝政府开始考虑向移居外洋的华侨同样颁授时宪书,以昭示清朝政府依旧是这些域外华民的正朔。
正是在清政府承认华侨身份属性,并希图加强管控域外子民的动因之下,民政部于宣统元年(1909)正月二十二日请旨上奏,希望朝廷允准给出洋华侨颁发时宪书以资利用,并得到“依议,钦此” 的肯定回复。在奏折中,清政府明确提及了令钦天监向海外侨民颁发时宪书的目的,即“华民世居外洋,沿用西历,不知本国之纪年,即应早为颁给时宪书以资遵守”,[19]从而使得海外侨民可以“心怀祖国”,“内感殊诚”,最终达到奉“王之正朔” 的目的。
因此,民政部、度支部通力配合,并拨款钦天监,迅速印刷3000 册小本时宪书,以颁发给出使大臣和所管辖的华侨。在钦天监赶印时宪书后,四月由时任署理新加坡总领事左秉隆接收时宪书200本,并向当地华侨发放。根据左秉隆回奏,清政府的这一做法使得新加坡华侨“得奉正朔,莫不鼓舞欢欣,同深感戴”。[20]虽然笔者并不清楚颁发时宪书对当地华民自我认同的影响,但从清政府的角度看,颁发时宪书这一行为本身无疑已经清晰地昭示着“国家—侨民” 关系的确立与巩固。
(二)《大清国籍条例》的颁行与影响
随着清政府对域外华侨身份的界定和时宪书的颁授,进一步表明了意图管控出洋华民的态度,而对于新加坡在地华侨人口的统计则可以视为清政府这种意图下的具体步骤。宣统二年(1910)四月十四日,民政部致电新加坡总领事,要求详细调查尚未归化他籍的新加坡华民人口(包括华侨户口、姓名、籍贯、住址、营业等项目),并提出应按照“本部奏订章程第三十九条内载,凡旅居外洋无论留学、经商、作工人等,应由出使大臣督率各该领事照本章程另订细则,分别调查,一律按期汇报民政部”。[21]
这次调查移居新加坡华人户籍的做法,实际上是对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在对“宪政” 背景下出台的《大清国籍条例》的进一步深化。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出洋大臣刘式训(1869 —1929)在《奏为妥定华侨出入国籍条例事折》中提出,自古以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道同风,罔有歧视”。[22]然而,刘式训认为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原来所定籍贯之例,只是为区别人口出生地和区域所定,而对于出洋域外的侨民没有规定,因此旧有章程规定已经无法适应新的世界形势。刘式训在“国家—侨民” 这一框架下,基于以下四点原因提出应该出台国籍条例,并加强对海外侨民的管理:第一,区别是否为清朝国籍,以确定领事保护与否,防止外交纷争;第二,防止华人侨民在移民地注册他籍后,却仍习华俗与平民无异,往内地置产设肆,以致地方官难以察觉、禁阻;第三,西洋有属地原则,即出生于某地即为某国籍的条例,而清朝应以何为依据,应以明确规定;第四,若侨民国籍管理清晰,行宪政选举之时,侨民虽远居他国也同样可以行使选举权利,尽国民义务。[23]
在奏疏上达朝廷后,经过中枢讨论并确定后,决定颁布《大清国籍条例》。清政府强调“血统原则”,在“固有籍” 条目下提出如果父为中国籍,子女无论出生何地均为中国籍民。[24]实际上,英政府对于清朝所出台这一界定中国人国籍的标准也给予了默认。根据宋旺相(1871 —1941)的记载,“当时(指1844 年左右)我们政府(英国)不承认中国政府当局对他们自己的那些自行移居出来的国民具有管辖权利,如今,如果他们的父亲是在中国本土出生的,我们的政府就勉强地发给在海峡出生的华人一种护照给他们回中国去”。[25]因此,正是在《大清国籍条例》出台的背景下,民政部对于新加坡领事官员统计在地华民户籍的催促,无疑是清政府对新加坡海外侨民国籍身份的正式认同,以及加强对海外华侨管理的具体办法,再一次证明了“豁除海禁” 条例后,近代化“国家—侨民” 关系的确立。
(三)民政部推动对新加坡在地华民的户籍调查
根据民政部要求,驻新加坡总领事尽快将华侨人口调查清楚,以便于区分清楚国民与已归化他籍者,并将其上升到影响国体的高度。民政部认为对于新加坡等域外华民户籍的调查与预备立宪的关系极为重要,统计人口的蓝书“一日不出则华侨民数永无当行调查之日,于宪政前途大有妨碍”。[26]因此,民政部要求总领事迅速调查,以重宪政,不可拖延办事。以致在左秉隆的电文中,也有“嗣奉部文严催,仍照定章办理”[27]之语。
然而,当民政部要求调查新加坡在地华民户籍电文下达后,驻新总领事及属下官员却有着不小的畏难情绪。虽然他们承认“泰西各国多事立宪之国,亦知调查户口极关紧要”,但是作为驻外领事,在新加坡总督管辖下开展人口调查实乃力所不逮,而且新加坡华侨人口众多,若要将20 余万华人户口、姓名、籍贯、营业等一一统计清楚,实在是颇有困难。更有妨碍的是驻新加坡总领事及其属员门认为,当时正是革命党和保皇党在新加坡煽动人心之时,“于国家一切行政肆多反对,恒生阻力”。[28]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此时派人四出稽查户口必定会造成人心浮动,导致英国官员干涉,旁生枝节。
虽然清政府要求派出驻新加坡调查当地华侨人口一事,随着不久后清朝的覆亡戛然而止,但是依旧可以看到清政府试图将海外华侨人口户籍调查清楚,并直接纳入天朝统治的努力。为弄清楚驻新加坡华侨人口情况,清政府曾有意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协同调查,甚至有计划仿照荷兰稽查局,在中国沿海口岸稽查出洋与归国之人信息,并形成和出洋所在地领事馆的互动。这些做法,实际上已经初步具有现代海关出入境管理的性质,是在“国家—侨民” 这一大概念下国家对属民管理的进一步深化。
三、“俾旅居者增气以自壮”:晚清政府派兵船巡洋新加坡
随着清政府对海外侨民身份属性的认知转变后,也开始探索和效仿他国经验保护侨民,其中包括派军舰巡阅与保护驻地华侨等众多具体措施。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十一日,张之洞(1837 —1909)就曾以《为劝令华商捐款造船巡历南洋保护侨民片》上奏,希望能够通过在地商民捐款的形式,派驻兵船保护华民,以达到“皇威远播” 的目的。事后,虽然朝廷有旨军机处会奏,以南洋吕宋、苏禄、新加坡等处为兵船巡洋之始,但并没有实际派出舰船巡阅。
(一)薛福成奏请军舰巡阅新加坡等地的尝试
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十一日,薛福成在上奏《奏请豁除海禁以保护商民折》当日,再上奏《附陈派拨兵船保护商民片》请求清政府再次讨论派兵巡洋以保护侨民。在这份奏疏中,薛福成认为流寓外洋的华民因为没有背后国家的庇护以致势单力孤,常常被他人所轻视,甚至羞辱,而西方国家“莫不派拨兵船保护商民”,从而使得其子民“俾旅居者增气以自壮”。[29]他认为应该将兵船巡洋保护侨民的方式常规化,并让当地华民感受到背后有来自“国家” 的支持。
在这份奏疏中,薛福成提及“中国海军各舰亦尝历新嘉坡,诸坡华民喜色相庆,以手加额,谓为从前未有之光宠”。[30]通过奏疏中的言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海军巡洋新加坡,给当地华民带来的归属感与光荣感。①实际上,北洋水师曾三次到访新加坡。首次时间为光绪十三年九月,“致远”“靖远”“经远”“来远” 四艘巡洋舰到访新加坡;第二次时间为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定远”“镇远”“济远”“致远”“来远” 五舰到访新加坡;第三次时间为光绪二十年,“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 六舰到访新加坡。在薛福成这份请旨巡航新加坡奏折前,北洋水师已有两次巡访新加坡、宣慰侨民的历史,故在奏折中薛福成提到“中国海军各舰亦尝历新嘉坡” 之语。北洋水师三次到访新加坡的历史,参见柯木林:《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的历史反思——兼谈甲午海战时期的北洋舰队》,《南洋学报》第65 卷,2011 年8 月,第17~61 页。实际上,作为英属殖民地上客居的普通华民,如果其身后能有清朝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对于他们的侨居生活大有益处。恰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和颜清湟(Ching-Hwang Yen)所提出的观点,“一个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似乎有可能成为保护和提升他们(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地位的依靠”,[31]并给予海外华人以“自豪感和尊严”。[32]
薛福成认为军舰巡阅一事,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能够相机利导,提出以闽商作为资助兵船巡视南洋新加坡等地的支柱,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国家—侨民” 理念的相互依托感。一方面以巡视增强清政府对于海外侨民的管辖与保护,在形式上实现国家“近代化” 的风貌;另一方面也通过巡洋的模式,切实保护新加坡在地华民,以保护华商营业。最后,薛福成提出“盖华商有力者之在外埠,商务之旺衰系之,军实之强弱系之,即西人亦视之颇重也”[33]的论断,明确指出了国家兵力强盛与在地华商民众营业兴旺与否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国家—侨民” 互为依托的认知在晚清民族主义的情绪下被进一步渲染。
薛福成这份奏疏没有像他的“豁除海禁折” 一样立刻得到朝廷的允许。虽然以奕劻为代表的总理衙门大臣认同侨民“羁栖异国冀借声威亦人之常情”,[34]但由于中国兵舰数量较少无力分拨巡视,希望日后再行办理。在甲午战后,北洋水师的战败更使得海军派舰巡阅新加坡之事不得不暂时搁置。不过随着清末“新政” 的开展,海军常规化巡航新加坡也再次成为了可能。
(二)袁世凯奏请军舰巡阅新加坡等地的施行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十六日,北洋大臣袁世凯(1859 —1916)再次奏请派兵舰巡阅新加坡等处,奏疏上达后获得朝廷允准,获准派兵船两艘前往新加坡。[35]经过筹备,海军部奉旨派出“海筹”“海容” 两艘快舰出洋巡阅。当两艘兵船行驶至法属西贡一带时,当地华侨“遥望龙旗,欢声雷动,中外观者如堵,咸称为中国自开海禁以来难得之盛事”。[36]这两艘兵舰的巡阅,激发了当地华侨极大的热情,以致“侨民欣感交集”。实际上,兵舰巡阅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清朝的“国威” 和影响力,也增强了出洋华侨的向心力。所以,在官员的奏折中,也提及侨民“莫不额手称庆,同呼万岁”,“乡、国情殷,忠爱之色露于言表”。[37]不过这两艘驶往新加坡的巡阅军舰因遭遇东南亚的海上飓风,不得不暂回上海修整。
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十八日,经过修整后的两艘军舰“海圻”“海容” 号终于抵达新加坡,当地华侨同样给予了热情的迎接。在经过5 天的巡阅后,两艘军舰离开新加坡赴南洋他埠继续巡访。这种军舰巡阅行为实际上强化了“国家—侨民” 的关系,清政府也试图将这种巡访常规化。在宣统三年(1911)六月,海军部再次筹划派出“海琛” 号兵舰巡视新加坡等地,但是由于在不久后清朝即宣告覆亡,相应地也就永远失去了常规化派军舰巡阅南洋等地的机会。
四、“一如内地”:新加坡华侨的捐款赈灾与清政府的封赠赏赐
晚清政府除了开豁海禁、颁发时宪书与统计户籍,以及派兵舰巡阅新加坡等举措外,在“国家—侨民” 关系下,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还发挥着其他重要职能,如保护侨民、开展捐输、考察当地商业与商会管理。①清政府不仅经常性地考察新加坡当地华侨的商业情形,还会经当地商会奏请像管理内地商会一样为新加坡商会注册并加以管理。例如,在《商部奏新加坡创设中华商务总会予以立案奏立折》中就提及“援请按照内地商会办理成案,颁给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关房一颗……所举会员一体给予委任”。这种提及对商会组织的管理,有助于将来内地农、工、路、矿各项目“召集华侨资本,次第兴办”。参见《秦报》1907 年第十期第一册,第21~22 页。作为近代外交体系下的清朝驻新加坡总领事,对在地的华民,甚至南洋各地仍属于清朝的子民都负有领事保护之责。例如,新加坡总领事发现荷属东印度华民劳工遭到虐待时,就向朝廷代为奏陈并照会荷兰以解救荷属华民劳工一事,[38]即为典型代表。甚至,新加坡总领事还曾奏报华民被拐卖到荷属文岛的惨酷情形,并用钱款赎回贵州廪生金一清,广西附生朱叡文、董林浩,湖南廪生谭书麟、附生梁槐,广东文童欧月秋、李星暨及李及卿等8 人。[39]对于这些具有功名侨民的解救,不仅体现了清朝对所属子民保护的职责所在,同时也为清朝自身找回了“天朝的颜面”。
(一)新加坡华侨对内地的赈济与捐输
19 世纪70 年代以后,在清政府财政日益艰难的情况下,面对各种自然灾害所需赈济时,获得海外侨民捐款成为了一种解决之道。在处理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陕西灾荒时,署理新加坡总领事刘玉麟(1863—1942)就奏报当地侨民“羁身海外,眷念宗邦,或劝募多金,或慨输巨款”,[40]并为陕西省募集洋银22,166 元。作为回报,朝廷予以新加坡当地华侨各种封赠的荣誉头衔。当泉州府属晋江、南安、安溪三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发生水患时,新加坡当地侨民捐款1 万元以赈家乡,而当地潮州侨民在六年前同样也曾捐银助赈山东有功。作为回报,福州将军崇善奏请御书匾额悬挂于新嘉坡天后庙,[41]匾曰“曙海祥云”。[42]诸如此类新加坡当地华民捐款救助内地水、旱灾等记录,屡见于薛福成、黄遵宪等人的奏疏中。[43]新加坡和南洋华侨除了对于内地灾害的捐款解囊外,对于晚清近代化建设的捐资成为保障内地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这也成为推动清政府试图积极联络、认同和管控海外侨民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转变也可视为清政府经济现代化和扩展外交网络的努力。[44]例如,当四川办理矿务需要投资时,曾到新加坡等地劝捐投资。[45]薛福成在他的奏疏中也认为流寓南洋的数百万华民是朝廷重要的“利源” 所在。
(二)清政府对于新加坡华侨的封赠赏赐
当新加坡华侨向清政府捐资赈济灾害和投资后,作为相应的回报,清政府常规化地授予出资为巨者封赠的荣誉。这种荣誉不仅是朝廷的一种恩典,更重要的是在形式上的一种对当地华侨基于“国家—侨民” 身份关系的认同的体现,更是与英殖民政府在新加坡当地展开的对华民“属权” 的较量。例如,在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为新加坡华侨精英章桂苑(1841 —1892)所写的《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盐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中得以佐证。[46]章桂苑因捐输有功,获得从三品盐运使的职衔。又如新加坡华侨吴进卿以捐输有功被陈金钟保奏由朝廷赏给二品封典,戴花翎,并赐匾额。[47]类似记载不胜枚举。在时人李钟珏(1853 —1927)所著的《新加坡风土记》中就有对这种情况的观察,其载“年来赈捐防捐,富商乐输巨款,核奖得虚衔封典者比比,其门前榜大夫第、中宪第、朝议第,一如内地”。[48]这种荣誉的封典对新加坡等地土生华人显然有着“拉拢” 作用,与英政府所颁授“太平局绅” 等荣誉形成竞争关系,使得清政府和新加坡华民精英增进互动,增强了在地华人对于清政府的认同。白伟权曾就以新山“皇清” 墓文作为切入视角,展现出新山一地华人墓碑抬头使用“皇清” 字样,并指出“基本上还是能够表现承认清朝在一般移民社会中所具备的正统性、代表性和权威性”。[49]这种互动无疑增进了清政府和域外所属华民的联系,也增强了当地侨民对清政府的向心力。
五、结语
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并卷入世界格局之中。作为对这种新格局的应对,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以新型和“近代化” 的外交体制应对同各国的关系。而在这种转型之下,清政府重新思考如何看待与界定19 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出洋华民。以薛福成为代表的出洋大臣和官员,根据实际形势提出“豁除海禁”“户籍统计”“派兵巡阅” 等建议并得到清政府的认可。这一认可本身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清末政府的近代化思维与追求,而清政府也从募集新加坡等处侨民捐输与投资中获得了回报,形成双向的互动与关系网络。此外,虽然如宣统三年(1911)内阁中书陈震福提出针对清朝政府南洋华人教育和商业的六条建议①陈振幅六条建议中,有关教育者三条,商业者三条。其中有关教育的三条建议为:一恭绎列朝掌故,以彰圣德;二请设立中国官报,以正民听;三请添置侨籍学额,以示一体。有关商业的三条建议为:一合办商业银行;二组织邮船公司;三推广华商联合会。六条对于南洋华人的建议不仅明显具有国家官方主导的性质,而且延续了南洋作为清朝海外“利源” 的功能。参见《宣统政纪》卷五十七,宣统三年闰六月辛酉。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不了了之,但朝廷内外已经在新形势下,逐渐转变了传统的海禁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的“国家—侨民” 思维模式。
本文以新加坡作为考察点,展现出清廷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为“近代化” 转型所做出的努力。正是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 的历史大背景下,清政府在被动中接受新的观念,豁除了海禁并给予海外侨民以合法保护。对待出洋华民身份属性观念由“偷渡者” 向“我国侨民” 转变后,在“国家—侨民” 这一概念下,加强了国家与域外侨民的互动,也展现出清末中国外交领域近代化的曙光。①例如,学者李文杰认为,近代外交制度建立起了一个大体完善、不依附于科举制度的外交官培养制度,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外交官。与此同时,外交人事结构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清末外交改革并非一步到位,却已走出最重要的步伐。参见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 —1911)》,三联书店,2017 年,第535~536 页。这种晚清外交制度领域内的变革努力,虽然囿于时代局限向现代化的转型无法一蹴而就,但这种尝试在笔者看来仍可视为外交领域近代化的曙光。虽然风雨飘摇之中清王朝最终快速走向了覆亡,但是作为近代化模式下“国家—侨民” 观念和驻外领事制度却并未因帝制的终结而走向终点。相反,这“一缕晨曦”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逐步焕发出光芒。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第1~3 页。
[2]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年,第19 页。
[3]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第283 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1 页。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2 页。
[7] 赵尔巽等纂:《清史稿·交聘年表》第29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8781 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2 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3 页。
[10][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4 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十九年上谕档》第19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313 页。
[13][14]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年,第233 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十九年上谕档》第19 册,第145 页。
[16]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奏折件》,《恭拟驻扎英属新加坡总领事官苏锐钊委任敕谕》,文献编号:188940,宣统02 年06 月23 日。
[17]《清德宗实录》卷五百九十七,宣统元年十一月戊辰。
[18]《清仁宗实录》卷之三百二十四,嘉庆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军机处奏折件》,《遵旨核议钦天监匠役私将时宪书稿本卖给民人预先翻刻一案》,文献编号:049325,嘉庆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551 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466 页。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481 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193 页。
[2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193~194 页。
[24]《大清国籍条例》,第一条,固有籍。
[25] 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第58 页。
[2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481 页。
[27][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480 页。
[29][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1 页。
[31] 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李明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287 页。
[32] Ching-Hwang Yen,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2008, p.339.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91 页。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189 页。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385 页。
[36][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396 页。
[38] 对于荷属殖民地虐待华民劳工一事,可参见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第118~120 页。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377 页。
[40]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奏折档》,录副奏折,升允奏报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官刘玉麟等募集洋银救济陜省灾民并请奖叙(折片),文献编号:146014。
[41]《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24 册,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1975 年,第330 页。
[42]《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四十三,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丙午。
[43]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下,第1~8 页,光绪甲午孟东开雕版。
[44] 有关清政府经济和外交现代化的论点,参见Godley M., “The late Ch’ing courtship of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1, 34(2), pp.361-385; Ching-Hwang Yen,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Beyond: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p.344。
[4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245 页。
[46] 黄遵宪:《皇清特授荣禄大夫盐运使衔候选道章公墓志铭》,收录于《黄遵宪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631~632 页。黄遵宪所写这篇墓志铭提及章桂苑“拳拳一心,眷恋宗国。为郑弦高,为汉卜式”,表达出作者对章公认同清朝的赞赏。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1 册,第223 页。
[48]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收录于王云五主编:《海录·新嘉坡风土记·日本考略·西方要纪》,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初版,第1~15 页。
[49] 白伟权:《从政治标示到族群边界: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绵裕亭[氵月]与[皇清]墓的个案研究》,《南洋学报》第68 卷,2014 年12 月,第85~118 页。
——以美国、爱尔兰和印度为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