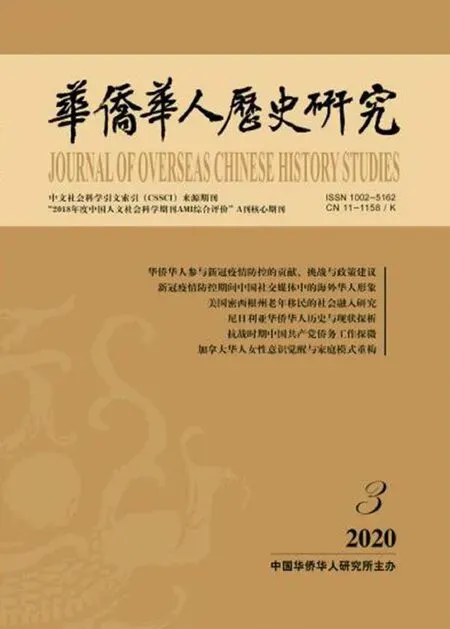20 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华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家庭模式的重构*
——以加拿大华裔作家郑霭龄《妾的儿女》为中心
蔡晓惠
(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中国人最早移民加拿大始于19 世纪中后期,是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的推力与加拿大社会建设发展的拉力之双重作用下而产生的移民现象。当时的移民多为广东沿海地区的农民。尽管他们移民的初衷是受北美淘金热的吸引,但是很多华工也参与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建设。上述两种华工占了全部华工的约一半左右,另外一半则进入采矿业、渔业、农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1]因此,加拿大早期华人移民大多从事繁杂的体力劳动。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加拿大华工以男性为主。另外,由于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向来安土重迁,华工不愿携带妻小漂洋过海,而后来加拿大社会“人头税”(head tax)①1885 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以后,加拿大国会首次通过“人头税案”,向入境华人征收50 加元的人头税。之后,在1900 年和1903 年,人头税分别涨至100 加元和500 加元。和排华政策的制定,又极大地限制了家眷到加拿大与华工团聚的可能性,导致加拿大华人社区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单身汉社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加拿大华人社区没有女性。据记载,早在1860 年,加拿大就出现了第一位女性华人。②根据《巾帼:加拿大华裔女性的声音》,1860 年3 月1 日,“李邝太太” 以商人妻子的身份从美国旧金山来到加拿大维多利亚,成为第一位来加的华裔女性。参见: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 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18。后来,以华工或华商妻子、母亲、女儿或纸新娘③在加拿大禁止华人入境期间,有些华工通过中间机构购买假的移民身份(即“移民纸”),设法让远在中国家乡的女性赴加与之结婚。通过这种方式入境的新娘被称为“纸新娘”。身份入境的华人女性不绝如缕。但是,这些华人女性的生存境遇在官方历史和文献中并未得到相应的表现和记载。20 世纪90 年代,先后有三部颇有影响力的作品在加拿大文坛问世:《残月楼》(Disappearing Moon Café, 1990)、《巾帼:加拿大华裔女性的声音》(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 1992,以下简称《巾帼》)和《妾的儿女:一个分居家庭的画像》(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 1994)。它们分别以小说(《残月楼》)、家族传记(《妾的儿女》)和口述实录(《巾帼》)的方式聚焦于加拿大华裔女性这一特殊群体,打破了华裔女性在加拿大社会中长期的沉默失语和无名状态。本文以《妾的儿女》为中心,辅以《残月楼》和《巾帼》的文本资讯,探讨在20 世纪上半期(即加拿大社会排华时代)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群体的历史境遇、生存形态以及由此给家庭模式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关于加拿大华人的研究,国外主要有三本著作:魏安国(Edgar Wickberg)等人编著的《从中国到加拿大:加拿大华裔社区历史》(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 1982),该著作追溯了从1858 年直至1980 年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历史;安东尼·陈(Anthony B. Chan)的《金山:新世界的华人》(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 1983)关注了美国华人和加拿大华人在北美社会的历史境遇;李胜生(Peter Lee)的《加拿大华人》(The Chinese in Canada, 1988)侧重的是加拿大华人自移民之日起在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这三部著作关注的都是华人社区整体的历史,而1992 年出版的《巾帼》则把重点聚焦在加拿大华裔女性群体,以访谈的形式生动记录了诸多华裔女性在加拿大的个人经历以及家庭状况,因此成为本文重要的参考文献。国内的加拿大华人研究较早的著作为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1990 年),后来还有黄昆章、吴金平的《加拿大华侨华人史》(2001 年);黎全恩等著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 —1966)》(2013)是这方面较新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关注的基本都是加拿大华人的总体状况和社区历史,对于加拿大华裔女性和华裔家庭状况仅偶尔提及,也很粗略。知网上这方面的研究也寥寥无几。因此,本文以《妾的儿女》为主探讨加拿大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家庭模式的转变,无论在加拿大华人研究领域还是相关文学研究领域都有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和研究意义。其创新之处体现在:一是本文将文学文本研究与历史资料相结合,把研究视角集中在长期被忽略的加拿大华裔女性群体上,关注她们在加拿大的生存状态,并与同期国内女性群体的命运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尚属首次。二是本文还关注了华裔女性群体的生存形态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婚姻模式的影响,为加拿大华人整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蓄妾制在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延续与变异
《妾的儿女》为出生于加拿大的第三代华裔郑霭龄(Denise Chong,1953 —)的处女作和成名作。作者在经过实地考察和缜密研究之后,以自传体的方式讲述了家族三代人在加拿大的多舛命运和艰辛历程。通过作者身为小妾的外祖母梅英及其儿女跌宕起伏的人生,此书折射出以作者家族为代表的早期加拿大华人在异国环境中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妾的儿女》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家族史,更为研究早期华人移民生态提供了生动的资料,又因其独特的女性视角,成为研究文学、历史、女性的重要资料和教材。该书赢得了温哥华图书奖、加拿大纪实文学奖、女性文学奖等多项荣誉,并被翻译成十几国文字。
《妾的儿女》虽然形式上是自传体,但实际上主要围绕作者外公陈山和外婆梅英展开。陈山是陈家第一代移民,他于1913 年抵达加拿大,成为最早落户温哥华的“金山客” 之一。在此之前,陈山在国内已经娶妻,在第一任妻子死后又续娶了第二任妻子黄波。十年以后,为缓解独处异乡的孤独、绵延子嗣,陈山托人为自己纳妾,即后来他通过“纸新娘” 方式从国内购买的小妾梅英。
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蓄妾制是否合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古已有之,且一直延续到20 世纪50 年代才告废止。[2]在陈山纳妾的民国时期,无论是立法还是舆情,对于废除蓄妾制的态度都相当暧昧。[3]事实上,纳妾习俗在社会高层和普通民众间,还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行为。晚清时期移民北美的华人在惯性上和事实上都承继了这一风俗,“对于漂泊海外的已婚男子来说,要求娶个小妾并不稀奇。留在家里的老婆,就是父母选定的老婆,是‘留守老婆’。从中国娶来的小妾,漂洋过海与男人结合,像夫妻一样在国外生活。”[4]从表面看,海外华人的纳妾行为与国内并无二致,但当这种根植于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家庭伦理嫁接到北美土壤之后,在新的律法和伦理环境中却无可避免地发生变异,甚至渐趋瓦解。
(一)“妾” 成为华人家庭的顶梁柱
20 世纪上半期,大部分华工在加拿大社会都是“廉价劳工” 的角色,收入微薄,很多人还要寄钱给中国老家。而从中国买妾的费用不仅包括逐年增长的“人头税”,还包括为妾侍购买加拿大出生证明的钱,支付给温哥华、香港和国内中间人的钱和小妾赴加的旅费。大部分华工根本无力支付这笔高昂的费用。因此,华工的妻、妾或其他亲属即使勉强来到加拿大,也难逃辛苦劳作的命运。在《妾的儿女》中,陈山从中国购买小妾梅英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案例。
梅英刚下船,还陶醉在陈山请吃点心的喜悦之中时,陈山便把茶楼老板介绍给她:“这是你的新老板。”[5]原来,陈山已将梅英作为契约劳工典当给这座叫做“北京茶楼” 的老板,直至付清梅英来加拿大的所有费用为止。在此期间,梅英需要一周工作六七天,每月工资被老板扣留,所得小费交给陈山。在加拿大的唐人街,由于女性极度缺乏,并且法律禁止华人雇佣白人女性,因此女服务员待遇优厚,薪资远远高于男性华工。1924 年,在加拿大唐人街,“女服务员每周工资可达25 加元,而男性华工最多15 加元,通常只有7 加元。”[6]所以,梅英实际上成为这个家庭经济的顶梁柱。在与陈山维持夫妻关系的十几年里,作为妾的梅英不仅供养着陈山老家的“大婆” 和寄养在大婆身边的儿女,还成为陈山在老家所盖的大房子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陈山和梅英的关系与国内的夫妾关系已经迥然有别:两人之间并非仅仅是性关系,还存在金钱上的绑定关系——不是侍妾依赖夫主的恩赐,而是恰恰相反。
(二)“妾” 在加拿大社会的非法性与夫妾关系的不稳定性
加拿大华人社区蓄妾制与国内的另一个差别是:加拿大的律法环境并不承认一夫多妻制。中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一夫多妻制的传统,即使民国时期立法有意要废除蓄妾制,在民间实践和公众意识中,蓄妾制的维持依然有着强大的基础。但是,包括加拿大在内的西方社会从来没有一夫多妻制传统。所以,加拿大华工和妾之间的事实婚姻关系并不受加拿大法律的保护。除了从中国社会所继承下来的伦理束缚,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将丈夫和妾永久绑定。这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妾的儿女》中提到,“那些想遵从西方风俗的人会领取结婚证,使自己跟小妾的婚姻合法化。但是,没有多少人觉得有此必要,因为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留守老婆’才是正牌老婆”。[7]基于这样的观念,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很多华工和其妾之间实际上只是“非法同居” 的关系。在中国蓄妾制传统中,妾处于完全的依附地位,要仰赖丈夫的喜好决定自身命运。但是,在加拿大华人社区中,由于经济独立而自我意识增强的华人女性便有了自主决定命运的可能。《妾的儿女》中的小妾梅英便是如此。由于生活习惯和观念等各方面的分歧,梅英对陈山日渐不满,最终离家出走,两人开始分居生活。而标志着中国传统蓄妾制彻底失势则是在梅香与情人周光同居之后。陈山和梅英分居以后,拥有众多追求者的梅英,选择了一个叫周光的男人为情人。陈山知道后,按照中国蓄妾制传统,去向周光索取买妾之资,梅英对此反唇相讥:“我不是用来买卖的!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怎么可以这样?!他不会付给你钱的。我想怎样就怎样。”[8]陈山没有拿到一分钱,悻悻而归。中国传统父权制在北美经济社会环境下早已失去往日雄风,旧世界男尊女卑、侍妾从夫的伦理秩序已然悄悄发生逆转。
(三)蓄妾制在加拿大社会发生变异的原因
由上可见,在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蓄妾制传统在加拿大华人社区有其延续的一面,但在加拿大特殊的历史语境和生存环境下,也表现出极大的变异,尤其是妾侍主体意识的提高和父权制对于妾侍的控制无能。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华人在加拿大社会谋生的艰难。在淘金潮和修铁路结束之后,因为语言和技能上的先天不足,加之加拿大白人社会对于华人的排斥和仇视,华人无法与白人劳工竞争,被排挤出大部分行业,只能从事工资低、劳动强度大的体力工作。这使得中国社会传统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生存模式无以为继,女性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必须参加工作。这种家庭经济格局的改变必然影响传统的家庭秩序和家庭观念。二是加拿大实施了一系列不利于华人入境的政策,从最初征收高额“人头税”,到1923 年禁止华人入境,使得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1921 年加拿大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为15∶1,到1941 年为8∶1。[9]女性的极端匮乏使得唐人街的女性格外珍稀,这不仅给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上的优势,也给予她们婚恋关系上极大的选择权和自由度。
二、加拿大华人女性意识的增强及其与国内“女性的发现” 之差异
(一)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与逐渐强大的女性形象
在20 世纪上半期的加拿大华人社区,从中国移植过来的父权制和封建伦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但由于北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势,又不得不做出妥协和改变,“因为有偿劳动而强大”[10]的华裔女性对强加于自身的父权制枷锁做出了反抗,与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相比,她们有了鲜明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展现出“华裔加拿大女性的觉醒”[11]。《妾的儿女》中的梅英、《残月楼》中的芳梅以及《巾帼》中的一系列女性,都突破了旧世界儒家伦理对于女性的约束,表现出反传统的面向。
《妾的儿女》中的梅英,在1935 年—1936 年陈山回国盖房子期间之所以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经济援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延长丈夫不在身边的自由”[12]。为此,梅英不惜欠债和赌博,甚至走上很多唐人街女服务员的老路——以肉体交易来获得金钱。在陈山从中国返回温哥华唐人街后,梅英的独立意识和自主精神由于对陈山的不满和经济窘困而日益滋长。在大萧条席卷北美的20 世纪30 年代,华人“像石子一样沉入雇佣大军的最底层”[13],陈山数月找不到工作,两个人的关系因相互指责降至冰点。此时,梅英上演了一出北美版的“娜拉出走”——抛下陈山和三个月大的女儿阿杏,独自去了纳奈莫的唐人街。但是,与鲁迅所预测的中国社会语境内“娜拉要么堕落,要么回来”的结局不同,做出妥协的是陈山——他抱着孩子亲往纳奈莫,好声相求才缓解了两人的矛盾。此外。梅英从穿着打扮、生活习惯、思想意识等各方面都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的约束。像华裔评论家赵廉所说的,“把女性从父权制的欺压中解放出来”[14]:她改穿男士西服、戴帽子打领带;她像男人一样出入赌场豪赌滥饮;最后甚至突破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束缚公然与情人周光同居。这些似乎都是梅英的女性宣言:“她要向世人宣告,自己在男人的世界中享有一席之地,是一个自力更生、不依靠男人的女人,应当获得其他人的尊重。”[15]可以看出,身处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小妾梅英已经完全摆脱了旧世界加诸女性和侍妾身份的伦理枷锁,从“命运无法自主的男性附属物” 转变成“拥有个人尊严和自由的准女性主义者”。
李群英的小说《残月楼》中也刻画了一系列强大起来的华人女性形象,而其中,女性自主意识的增强是伴随着家族内部经济权和话语权的强势拥有而实现的。《残月楼》的故事讲述通过黄家第四代女性凯英的视角,重点围绕黄家第一、二代女性李美兰与儿媳芳梅及其后代子女展开。其中,中国父权制传统中的男性权威走向衰落,代之以强势的母亲和妻子形象,家族掌控权也在强势的女性成员之间流动。李美兰是1911 年以唐人街富商黄贵昌妻子身份移民加拿大的第一代华人女性。在打理家族餐馆生意的过程中,李美兰自我认同感增强,在处理家族事务的时候对家长黄贵昌阳奉阴违、独断专行,成为黄家实际的掌权者。儿媳芳梅1919 年以“纸新娘” 的方式入境,虽然开始因未能为黄家传宗接代备受婆婆欺凌,但是在产下儿女后,逐渐获得经济自主权和家族掌控权,不仅通过地下私情背叛了男权伦理,还对软弱无能的丈夫冷嘲热讽、颐指气使。通过刻画几代“血管里流淌着激情和强势”[16]的女性形象,《残月楼》也间接展现出加拿大华人社区封建男权文化的式微及女权意识的崛起。正如华裔评论家班尼特·李(Bennett Lee)所言,“《残月楼》中的男性经常是一副可怜和无助的样子,而女性则充满激情、怒火中烧、诡计多端、生机勃勃、强大有力,成为家族母系纽带通过高超手段对社区施加影响的活生生的范例。”[17]
(二)加拿大与中国女性意识之差异
这样的一种趋势与同时期中国社会“个性解放” 和“女性的发现” 似乎不谋而合。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风气,以其激烈的颠覆封建礼教性别规范的锋芒鼓舞诸多新女性走出家庭、追寻个人独立和自由,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遂成为“浮出历史地表” 的“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诞生期”[18]。一时间,从北欧引进的文学形象——娜拉成为引导中国女性的一面精神旗帜,此时,无论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都涌现出不少“娜拉” 式女性——从胡适《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到北京师范学校的李超,都表现出追寻婚恋自由、反抗封建伦理的新女性立场。
但是,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同时期中国社会新文化运动后“女性的发现” 在几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对于“女性的发现” 是近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整体学习西方、试图解救民族危机的文化思潮中出现的副产品。它由知识分子阶层率先发起、并在知识女性之间得到强烈呼应。因此,它的主要受力区域和受影响人群大多为民国教育制度下的现代学校和在校女大学生。这项运动对于革新数千年来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性别伦理和观念、提高女性的性别认同和自我意识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但是当五四新女性将这些先进思想转化为争取婚恋自由、寻求个人独立的行动时,却经常会遭遇从经济现实到伦理道德的诸多困境,因而往往以失败或悲剧而收场。1923 年,鲁迅在北京女高师文艺会所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娜拉出走之后“从事理上推算起来,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9]——这正是看到了当时中国社会语境下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因而所有对“自由”“爱情” 的追寻只能沦为乌托邦式的空想。
1. 女性觉醒主体阶层的差异
加拿大华人社区与中国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女性之差别首先在于女性主体的阶层——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女性基本上都是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底层女性。她们不仅从未有机会接受中国新文化运动思想的洗礼,也并没有因为身处西方社会而充分接触和吸收西方女性的家庭观念或者平权意识。这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20 世纪上半期及以前的加拿大唐人街基本上是被隔离于主流社会的“贫民窟”(ghetto),这大大减少了华人社区女性与主流社会互动的机会和可能;而且因为早期华人女性不会英语,受语言能力的限制,活动空间也大多局限在唐人街范围内。二是加拿大排华法案自1923 年生效,直到1947 年才废除。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西方社会对华人存在根深蒂固的歧视和偏见,华人深受其害,这导致华人社区对白人社会及其风俗也往往持拒斥的态度。这在20 世纪上半期第一代华人中尤为普遍。所以,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女性群体并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作指导,其对自我尊严的追求和自主意识的增强主要出于反抗华人社区父权制压迫的原始本能,带有很强的原初和蒙昧色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因此,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虽有追寻独立自主的意识,却又常常表现出对封建性别伦理的无意识遵从和妥协。就像《巾帼》所看到的,“20 世纪上半期,华裔加拿大女性的生活既受传统束缚又打破了传统”。[20]
以《妾的儿女》中的小妾梅英为例。她1924 年入境加拿大,但直到1940 年才产生摆脱陈山独立生活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在此十多年间,她一直忍受着丈夫陈山的种种管教并且承受着他对自己劳动的残酷剥削(陈山每月定时到梅英工作的餐馆将其工资领走)。而在梅英入境之初的加拿大华人社区,实际上已经为包括梅英在内的华人女性提供了追求独立的土壤:华人女性获得了工作机会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加拿大律法并不为中国的蓄妾提供法律保障等等。梅英等早期华人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现实环境,主要在于从旧世界承继下来的儒家伦理观念已经深入其集体无意识并且自觉转化为指导其行为的规范。比如,梅英最开始对自己的侍妾身份毫不质疑:她把自己看作夫家的一员,将挣得的血汗钱悉数交给陈山;内心深深惧怕被丈夫休掉,认为这是女人最大的耻辱;她认为,只有生下男孩才能为陈家延续香火,并确保自己的家庭地位。这些都表明,梅英等华人劳动女性尽管身在北美,却依然是旧中国封建伦理的产物,她们要摆脱身上的伦理枷锁追求独立自主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对自身现实的清醒认知。
《残月楼》中的芳梅也是如此。中国传统父权制伦理历来重视父系血缘传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便是这一观念的集中展现。当芳梅结婚五年一无所出时,作为封建伦理代表的婆婆便以休妻相威胁迫使儿媳芳梅接受自己炮制的“借腹生子” 计划。如果芳梅对于加拿大社会的法律和社会文化足够谙熟,原本可以以此为武器据理力争。但是入境五年的芳梅,当时却并未充分领会加拿大社会赋予女性的自由和权利,反而在与姐姐的通信中不断接受旧式家庭伦理的洗礼。虽然身处北美,芳梅却仍然深受封建礼教和传统价值体系的影响。尽管她对婆婆的刁钻霸道深恶痛绝,但在潜意识的伦理观念中,她是认可婆婆“男尊女卑、传宗接代” 的一套说辞的。因此,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人女性芳梅并未像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新女性一样对抗婆家和父性权威,而是通过与他人偷情生子的不正当方式获得家族中的地位。直到多年以后,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的芳梅在子女发生乱伦惨剧后才不无懊悔地反思:“我本来可以跟任何一个孤独的金山客私奔,都不会有婆婆的压迫。这是一片可以随时重新开始的土地……如果男人让我不开心,那我完全可以放下他们往前走!……如果我当时拒绝为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生孩子该有多好?!”[21]
这种反思是很多加拿大华人社区第一代华人女性所共有的。《巾帼》里的玛格丽特·陈(Margaret Chan)也在采访中提到:“那时候我很蠢。我不应该为他(玛格丽特的丈夫)生孩子——我当时应该早点离开他。还有其他跟我一样的人,但是我却走了一条狭窄的直接的道路,我想表现得规矩一些。”[22]这些反思其实也充分表明了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意识觉醒的滞后性和局限性。
2. 女性觉醒经济基础的差异
20 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意识觉醒与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内女权运动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其经济基础的差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lf)曾经说过,女性“需要一年有500 块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带锁的房间才可以写小说或诗歌”。[23]这实际上是告诉女性,如果想追求性别平等和一份职业,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后盾,否则,便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而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女性大多为在校女大学生,她们的经济来源多为其想挣脱的父母和家庭。因此,其追寻婚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愿望往往因为其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而不得善终。而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底层劳动女性却恰恰相反,说她们的女性意识觉醒是由“经济驱动” 的也不为过。因为正是其自身持有工作的现实以及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和满足感,才真正促使她们摆脱封建男权伦理的束缚、争取自己的独立个性和尊严。
在《妾的儿女》中,梅英的精明能干和巧嘴使她成为所在餐馆的模范员工,甚至成为广东茶楼“最珍贵的资产”。不仅如此,在与陈山共同经营麻将馆生意时,她的聪明机智不仅使她成为麻将桌上的好手,还能妥善处理顾客纠纷,成为比陈山更受欢迎的好掌柜。正是在工作中所获得的对自身能力的自信,赋予她足够的勇气,才使她在丈夫陈山对她辱骂和管教时能够“不管是家事还是生意对他的固执提出抗议,而不是忍气吞声”[24]。而在加拿大社会大萧条时期,梅英更成为“家里唯一挣钱的人,是财源”[25]。在陈山返回广东老家盖房子的两三年间,梅英通过不断给老家提供经济援助换取了丈夫不在身边、摆脱父权制绑缚的自由,也更加滋养了梅英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为她最终摆脱自己的妾侍身份、成为一个“拥有自我意志的、解放了的前女权主义者(self-determined liberated pre-feminist)”[26]做好了准备。而当梅英最终与陈山彻底分手以后,也正是这种独立生活的能力使她能够一手带大女儿阿杏。虽然梅英离开陈山后的生活一直贫困潦倒,但是那是因为她沾染了酗酒和赌博的恶习,而非像中国新女性一样失去了经济来源。因此,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迫于生存不得不参加工作的现实对于其摆脱父权制枷锁、争取独立和自由反而是因祸得福。
《残月楼》中的芳梅嫁入的是温哥华唐人街有名的富商大户黄家,但是由于人手缺乏同样需要参与经营家族生意。她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学会了记账、管理仓库和与白人用英语打交道。黄廷安更是称赞她“是那种特别有决心的人,很乐于学习,从来不会忘记被教过的东西”。[27]为黄家生下子孙后,她更一步步获得了生意的管理权和股份,“先是学会了开车,后来又在家族生意中拿到了股份,并把它转变成最盈利的产业——房地产。”[28]正是由于对经济的把控权和对自己能力的自信,让芳梅有底气去对抗霸道的婆婆和软弱的丈夫,不仅在家族事务中说一不二,而且在整个唐人街都颇有影响力,甚至白人警察都尊称她一声“黄太太”。
《巾帼》中的诸多女性也有与梅英和芳梅类似的经历。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女性通过辛勤劳动不仅养活了自己,更为自己赢得尊严和自信、换来自由和独立。《巾帼》里对加拿大华裔女性的评价非常中肯:她们“并非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的被动牺牲品,也非超级女英雄”。[29]加拿大华人社区女性意识的觉醒固然有其局限和落后的方面,但是,由于她们脚踏实地、更接地气,反而更能持久、更成功。
三、加拿大华人社区家庭模式的转变
正像《巾帼》里所提到的,“很多中国传统家庭生活无法移植到海外社区”[30],不仅蓄妾制传统在加拿大华人社区内产生了巨大的变异,很多其他中国传统家庭秩序也无法维持其原来的样貌。
(一)大量临时家庭和第二家庭的出现
1923 年6 月,加拿大国会通过新的《华人移民法》(即“排华法案”),其中包含歧视华人的43项条款。根据《华人移民法》,加拿大公民的华人妻子,如果从未登陆过加拿大的话,也不能入境加拿大。这样便彻底断绝了华工妻子来加与丈夫团聚的可能性。这使得原本就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加拿大华人社区因为没有华裔女性的输入更陷入女性匮乏的境地。数据显示,1941 年,全加拿大15 岁以上华人男性共有29,033 人,女性只有2,337 人。[31]其中,虽然显示已婚男性为23,556 人,[32]但实际上,因为妻子远在中国老家,他们过的仍是单身汉的生活。根据《巾帼》中让·朗布(Jean Lumb)的口述,1935 年,多伦多唐人街只有大约12~14 户完整华人家庭,其余的2000 多华人大多为单身男性。[33]但是,这些加拿大华人社区的男性无论是出于缓解异乡孤独的情感需求还是解决生理需求,都渴望异性的抚慰。于是,便催生了一批“临时家庭” 和“第二家庭”。
所谓“临时家庭” 是指华人男性和女性搭伙过日子,却并不履行婚姻手续。这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华人男性在老家已有妻室。《妾的儿女》中,梅英和情人周光便组成了这样的临时家庭。周光是唐人街的职业赌客,受过教育,像唐人街上的大部分单身汉一样,他在中国老家已经结婚并且有两个儿子。但是老家妻子无法来加拿大,他被漂亮的女服务员梅英吸引并展开追求,之后与梅英组成临时家庭并维持了数年。这样的非婚关系并非梅英和周光一例个案,而且被排华时代的加拿大华人社区广为接受。就像《妾的儿女》所说,“中国的婚姻风俗在新世界已经失去了意义……老一辈华人对非婚的男女关系宽容了很多。像梅英跟周光这样,一个女人跟老婆留在中国的男人在一起,在唐人街是可以容忍甚至宽恕的”。[34]如果这些男性选择将临时家庭的同居关系合法化,那么便构成了“第二家庭”。在《巾帼》中有不少华裔女性在采访中都提到,自己的父亲在老家还有一个家。[35]
因为唐人街华人女性的匮乏,这样的临时家庭有时候甚至是跨种族的。《残月楼》中的黄贵昌曾在拾骨重捡途中被印第安女子凯罗拉搭救,之后,维持了三年的同居关系并育有一子。但是这样的异族关系通常不会走入正式婚姻。因为尽管华人在北美族裔等级制度中是处于底层且被歧视的族群,但华人族群对于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其他族裔同样抱有偏见,与这些人的婚姻关系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黄贵昌后来又返回中国老家娶了个“真真正正的华人女子” 为妻。在《巾帼》中,也记录了不少华人男性与法裔加拿大白人女子同居的情形。[36]
(二)收养子女和契纸儿女的普遍存在
加拿大华人社区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不仅改变了华人传统的婚姻模式,也对华人子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以单身汉为主的唐人街,完整的华人家庭很少,婴儿出生率极低:1931 —1941 年这十年间,温哥华唐人街人口出生率仅为9‰。[37]这使得儿童在唐人街显得格外珍贵。《残月楼》和《妾的儿女》中都提到了这一点:“男孩女孩都很稀罕,因为没有多少女人可以生育。”[38]中国传统历来重视血缘传承,没有子女的家庭或个人往往通过“过继” 的方式从亲戚那里收养孩子。但是在加拿大华人社区,人们没有多少这样的家族亲戚可以依赖。因此,买卖和收养孩子便成为加拿大唐人街的一种常见做法。《妾的儿女》中,梅英因担心老无所养,便从一个叫叶内莉的女人那里买了一个男孩。但是,不同于西方人的做法,中国人在收养关系中,养父母往往不会告知养子女实情。这会使收养的子女在成年以后可能产生身份困惑和认同危机。著名华裔加拿大作家崔维新就在其作品中曾经提到:在自己的母亲死去18 年后,有人打电话声称,“我上周见到了你的母亲”。[39]由此,他在自传体小说《纸影:唐人街的童年》中开启了身份追寻之旅。在20 世纪上半期的加拿大华人社区,非血缘的亲子关系成为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加拿大华人社区的临时家庭也导致了不少非婚生子女的出现,这不仅使得某些华人家庭关系复杂,也给后代带来很多困扰。《残月楼》中的黄廷安本来是黄贵昌和印第安女子的亲生儿子。但是碍于他的私生子身份,黄贵昌虽然将他收养,并将其培养成家族生意的得力干将,却始终不敢将其身份曝光。这成为黄家后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乱伦悲剧的原因之一。《巾帼》中的华裔女性费尔·胡姆(Fern Hum)在采访中提到,“我父亲在跟别人的同居关系中生有一个女儿,我母亲在来加拿大之前对此一无所知”。[40]因此,费尔·胡姆的母亲一直无法接受这个继女,迫使她在一个个收养家庭间辗转。
另一个在加拿大华人社区非常突出的现象是契纸子女现象。根据1923 年《华人移民法》,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儿童是有资格入境加拿大的少数几种人之一。因此,买卖子女出生证明在加拿大华人社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并且常见的做法。《妾的儿女》中,当陈山在得知在老家由大婆抚养长大的两个女儿来加无望后,便将其在加拿大的出生证明高价卖出,以此支付了三女儿阿杏买房的首付。
20 世纪上半期,加拿大华人社区的家庭模式和家庭关系颇为复杂,这无不根植于北美社会排华时代的特殊历史语境。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20 世纪初期连年上涨的“人头税” 以及后来的《排华法案》,这导致加拿大华人社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婴儿出生率下降。无论是临时家庭、非婚子女还是收养关系和契纸子女,都是华人为适应当时的加拿大社会而不得不进行自我调整以应对恶意环境的产物。
四、结语
20 世纪上半期正是北美地区排华政策和种族歧视猖獗的时代。此时的加拿大华人社区处于女性匮乏的“单身汉社会”:《残月楼》《妾的儿女》和《巾帼》这三部作品分别以不同的文体和方式聚焦于这一时期加拿大华人社区的生存状况,尤其关注了其中华裔女性的生存形态和历史境遇以及华人社区婚姻关系和家庭模式的改变。加拿大华裔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华人社区家庭模式的改变既植根于加拿大华人社区对传统中国伦理和中国习俗的无意识坚守,又与异域生存的现实息息相关,是中国传统嫁接于异域土壤的特殊产物,也是加拿大华人在当地环境中不得不做出妥协、适应和改变的生存策略。这些改变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与当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也会随着这一历史阶段的结束和所在国政策的改变而渐趋消亡。但是这一阶段对加拿大华人社区和后代所产生的影响却仍然以种种可见和不可见的方式持续存在着。
[注释]
[1] 黄昆章、吴金平:《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56 页。
[2] 程郁:《清至民国蓄妾习俗之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233 页。
[3] 程郁:《清至民国蓄妾习俗之变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206~214 页。
[4]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22.
[5]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25.
[6]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29.
[7]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22.
[8]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125.
[9] 黎全恩等:《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 —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65 页。
[10] Lindsay Diehl, “Disrupting the National Frame: A Postcolonial, Diasporic(Re)reading of SKY Lee’sDisappearing Moon Caféand Denise Chong’sThe Concubine’s Children”,ESC,42.3-4(September/December 2016).
[11] Lien Chao,Beyond Silence: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oronto: TSAR, 1997, p.114.
[12]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84.
[13]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49.
[14] Lien Chao,Beyond Silence: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oronto: TSAR, 1997, p.105.
[15]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123.
[16] Sky Lee,Disappearing Moon Café,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Ltd., 1990, p. 196.
[17] Bennett Lee, “Introduction”, Lee, Bennett and Jim Wong-Chu, eds.,Many-Mouthed Birds: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Chinese Canadians. Vancouver: Douglas & Mc Intyre, 1991, p.6.
[18]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29 页。
[19] 鲁迅:《鲁迅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30 页。
[20]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21.
[21] Sky Lee,Disappearing Moon Café,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Ltd., 1990, pp.253-254.
[22]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p.29-30.
[23] Virginia Wolf,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121.
[24]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37.
[25]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89.
[26] Lindsay Diehl, “Disrupting the National Frame: A Postcolonial, Diasporic (Re) Reading of SKY Lee’sDisappearing Moon Caféand Denise Chong’sThe Concubine’s Children”,ESC,42.3-4 (September/December 2016).
[27] Sky Lee,Disappearing Moon Café,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Ltd., 1990, p.70.
[28] Sky Lee,Disappearing Moon Café,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Ltd., 1990, p.182.
[29]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23.
[30]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19.
[31] 黎全恩等:《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 —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65~366 页。
[32] 黎全恩等:《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 —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66 页。
[33]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50.
[34]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124.
[35]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 Toronto:Women’s Press, 1992, pp.105, 118, 122.
[36]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 Toronto:Women’s Press, 1992, pp.51, 125.
[37] 黎全恩等:《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 —1966)》,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81 页。
[38] Denis Chong,The Concubine’s Children: Portrait of a Family Divided,Toronto: Penguin, 1994, pp.115-116.
[39] Wayson Choy,Paper Shadows: A Memoir of a Past Lost and Found,New York: Picador USA, 1999, p.3.
[40] Women’s Book Committee, Chinese Canadian National Council,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Toronto: Women’s Press, 1992, 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