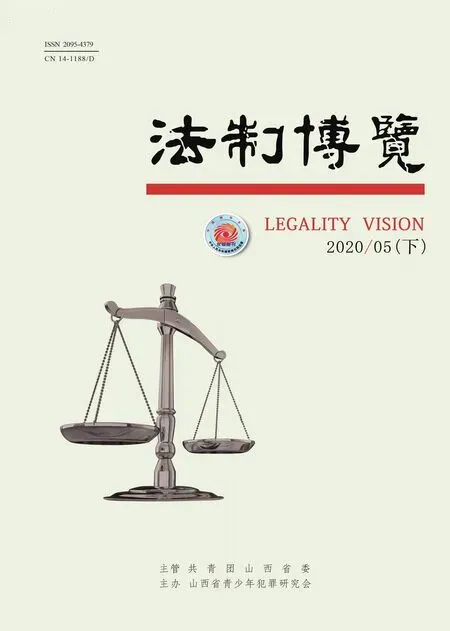干扰婚姻关系的第三者侵权责任浅析
章欣贝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 201206
一、问题的引出
案例:甲与乙系夫妻,婚内女方生育一子,后双方离婚孩子同乙共同生活,甲支付抚养费。后甲得知孩子系乙与第三者丙所生,故甲向法院起诉乙、丙要求支付其经济损失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甲错误抚养非亲生子受到较大精神损害,以《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为依据,支持甲精神损害抚慰金及部分经济损失的主张。①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离婚纠纷仅限于夫妻双方之间,若受害配偶因婚姻关系被干扰、被侵害而遭受财产、精神之损害,可否就此向干扰婚姻关系之第三人请求赔偿?此类案例层出不穷,实践中多以侵权相关规定予以解决。
二、干扰婚姻关系的定义
干扰婚姻关系即侵害合法存续的婚姻。因婚姻关系兼具财产及人身属性,单纯地将夫妻一方作为另一方之权利客体显然不可,故,将夫妻之间互相忠实、彼此尊重从而维系夫妻共同生活,这一互相关系具有重大利益,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予以权利化。[1]尽管学术界对于配偶权的涵义有不同争议,有身份说、陪伴说、利益说、法定说等。[2]但笔者认为,因此,干扰婚姻关系行为实际即为侵害“配偶权”。而就其行为方式,又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通奸
配偶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内,与非配偶的第三者,并未长期共同公开生活,但隐蔽地、持续地发生性关系,可谓之通奸。因该行为的隐蔽性,诸多学者均认为该行为不应由法律介入认定为侵权行为,而因将其归于道德范畴,仅受道德伦理之审判。由此,除特殊的破坏军婚行为之外,现行法律制度也未将一般通奸行为列为违法,乃至现行婚姻法中,也未明确该行为属于可得损害赔偿的导致离婚之“过错”②。但是,该行为对受害配偶一方以及对婚姻的伤害亦是显而易见的。
(二)重婚
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重婚的定义应以主体不同分为两种:1.有配偶而与第三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2.第三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者与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刑法对重婚行为明确入罪,故对该行为,无论是配偶一方还是第三人,均可因其行为侵害一夫一妻制、侵害配偶权而得到惩戒。
(三)同居
同居,顾名思义,即双方共同生活、居住,在本文主旨范畴下,可定义为第三人明知他人有配偶,仍与其长期共同生活、居住,且发生有通奸行为。同居行为一般介于通奸行为与重婚行为之间。
三、被干扰婚姻的受害配偶之救济途径
司法实践中,对上述所论干扰婚姻关系之行为,可得援引的法律条款一般为《婚姻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民法总则》,而受害配偶一方若欲行使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在选择起诉其配偶时案由一般为离婚、离婚后损害赔偿、婚姻家庭等,在选择起诉第三人时案由则一般为人格权纠纷。
(一)向第三者主张损害赔偿之法律依据
1.《侵权责任法》第22条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认定过错配偶及第三方的通奸行为系侵犯无过错配偶人格权的,以侵权责任形式要求第三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民法总则》第112条“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该条款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婚姻关系”的权利化,给予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案例适用该条款的可能性。
但纵观相关案例可知,司法实践中通常以是否存在“较严重损害后果”等进行法益衡量。若“出轨生子”“错误扶养非婚生子”“重婚被定刑”等可直接得以证实的事实存在,则受害人之请求一般能得到支持,而若仅以“同居”“通奸”予以主张,一方面,受害人对于该主张之举证较难,另一方面,为避免突破现有法律规定过度干预道德范畴,个案法官亦困于认定这一步,就更难提支持请求了。
(二)要求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之形式
第三者侵害无过错方的配偶权给无过错方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侵权责任法》第20条的规定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责任。给无过错方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精神损害赔偿也应当由第三者和过错方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应注意对无过错方的精神损害承担应当达到“严重”的程度,此种应当结合《婚姻法》相关司法解释以及《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这一标准。虽然解释中没有提及是否可以向第三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是,笔者认为受害配偶可以向第三者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因在于,第三者和过错方实施的是一个共同侵权行为,两者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所以,对过错方的标准的判断也应当适用于第三者。此外,赔礼道歉也应当成为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3]
四、第三者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认定构想
对构建第三者干扰婚姻关系致使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制度,笔者有如下构想。
(一)责任主体及客体之立法明确
根据《民法总则》第112条及《民法典草案》第1001条规定:“对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法总编、婚姻家庭编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4]。若该民法典正式施行该条款,“婚姻关系所产生之身份权利”即为法律明文保护之客体,以法律规定为道德伦理约束加码,将社会价值取向导向忠实婚姻、恪守承诺,也为受害人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提供明确法律依据。但纵观草案至婚姻家庭编及侵权责任编,却未提及侵权主体、侵权行为方式、侵权责任范围等,而人格权编中亦未提及具体,故笔者认为不妨再进一步明确对婚姻关系产生的人身权利之范围,并将侵权责任之主体由此限定将违反忠实义务的配偶及干扰婚姻关系的第三者,作为侵害配偶权的共同侵权人。因两者行为结合才导致侵害行为及损害后果,两者应承担连带责任,而非割裂的,由配偶承担离婚过错责任、第三者承担侵权责任。由此,也能一定程度的避免夫妻合意,利用该制度反而侵害第三者权益的情形出现。
(二)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之举证倾斜
精神损害事实之存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从损害后果去倒推,以较为严重的后果例如“错误抚养非亲生子”等才予以认定,而判例之间亦有衡量的不同,若司法解释能将“损害事实”认定进行不完全例举,更利于法律对婚姻关系的保护。此外,司法实践中受害人往往难以举出完整、明晰之证据证明损害事实及因果关系,且一般提交的更多是电子证据(例如聊天记录、音频视频、照片)及证人证言,也常有受害人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证据,但因其配偶及第三者拒绝配合而难以成行。故笔者认为应拓宽电子证据之采用标准、举证责任负担比例之衡量,将法律已经明文禁止的“重婚”“与他人配偶同居”等情形,以要求侵害配偶及第三者必须配合法院调查举证,由第三者自证其不属于“故意”侵害,更利于法律事实的查明也更利于对各人权利的保护。
(三)侵权责任、损害赔偿之司法裁量
在赔偿金额上,司法实践中在未涉及人伤,仅以精神受创、财产受损主张,受害配偶能获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金额几乎都难以达到对其“失爱”“失婚”之痛苦弥补,亦难有对侵害人之惩戒震慑之效果。故笔者认为应更多引入“公开道歉”之形式,毕竟,在婚姻关系所致人身权利被侵害前提下,受害配偶因此被“讥笑、嘲讽戴绿帽子”等,也仿佛导致其社会评价之降低,一定程度上也类似于名誉权受损,此时,在追求金钱弥补之外,将“公开道歉”作为此类侵权责任承担形式,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受害人内心之苦痛,许有更好社会效果。
注释:
①详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454号民事判决书.
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文义来看,“过错”似乎已被完全例举,也就是该四项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