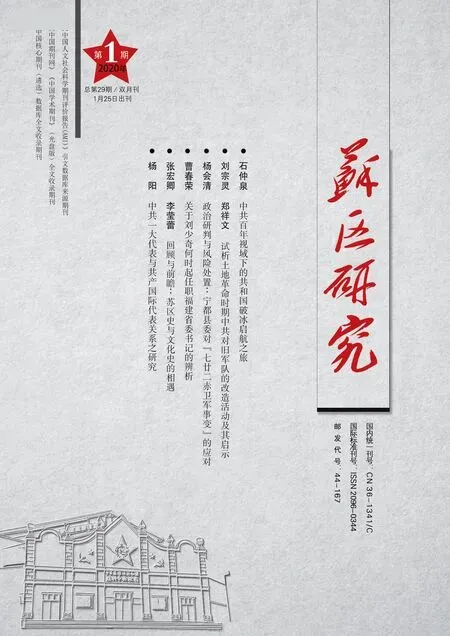回顾与前瞻:苏区史与文化史的相遇
提要:新文化史在内在理路上与革命史、苏区史有不解之缘。新文化史研究理路介入苏区史之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和进展,主要体现在关注革命年代人的内在感受与体验、研究视野的拉伸与微观史学的并存、革命史解释方式的变化与史料的拓展等方面。但在两者的交融过程中,亦存在史料欠缺与过度阐释、微观化与碎片化趋势、选题笼统与研究泛化等诸多不足。展望未来,苏区史研究者既要借鉴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实现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也要在关注人性与主体这一永恒主题的同时,探索苏区史研究的回归与融合之道。
引言
文化史记录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和表达模式,与政治史、经济史或环境史相比,文化史更加注重个人对历史的能动作用。人类掌控人情世故的能力虽然有限,但他们通常可将自己对亲历的事件和过程的反应表达出来。在一定意义上,作为一种范式的历史解释的文化转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情感因素、个性化特质与不确定性也正是研究者的魅力所在。苏区史作为中共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真正达到党史、革命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效,文化史侧重于人性、个性化的倾向值得苏区(革命)史研习者借鉴。时至今日,笔者认为,“革命史”与“新文化史”在内在理路上具有不解之缘。一是研究内容的相同之处。不管人们如何定义“文化”的概念,“作为符号世界”的文化——是新文化史的最大特点,而革命年代,“革命”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种“生存哲学”,从这一层面来说,作为“象征”、“仪式”、“意义”与“符号”等概念同样是“革命史”研究不可替代的议题。二是研究方法的相通之处。“新社会史”的主要特点是“眼光向下”,“新文化史”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关注象征概念群、思想心态与意义阐释,而这些研究方法,在党史、苏区史研究中同样是需要的。那么,对于从事苏区史、党史研究的学人,新文化史与苏区(革命)史“相遇”之后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又有什么不足之处与未来走向呢?围绕着这三个方面,笔者作一个简略的梳理。
一、成就与进展:苏区史的“文化转向”
(一)关注革命年代人的内在感受与体验
苏区史或党史,由于其较为特殊的学科背景、时政纠葛、资料局限等因素,框架较为单一,叙事也显简略,为了突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难逃挂一漏万之弊,一般民众的个性化感受与体验付之阙如。相对于传统的党史、革命史研究,当史学研究者开始了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转向之际,其研究成果不仅有清晰的、内在性的、主体性的逻辑解释构架,还有更为复杂的人的体验与活动,党史、革命史的叙事更为有血有肉、更为丰满。这一突破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中共革命精神史研究资料收集与整理中的“口述”与“访谈”。2012年6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2013年6月,教育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决定联合设立8个“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纳入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这两大举措无论是从财力上还是从人力上都较以前大大地推动了苏区(革命)史的研究,一批批中共精神史研究系列丛书(在江西如《苏区精神》《八一精神》《方志敏精神》)先后面世。在这一批研究成果中颇有史料价值与社会文化意蕴的是其中的“口述”与自传类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如《井冈山斗争口述史》(1)黄仲芳、罗庆宏:《井冈山斗争口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就记录了140多位当年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及相关人员的口述与回忆资料,多维视角地“再现”了当年的革命图景。
二是革命大潮中历史人物的多维“面相”与革命动员中底层群体的主体呈现。领袖、精英、伟人等重要历史人物,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历来颇受研究者的青睐,但不少也难免落入脸谱化、政治化的俗套,如果有了对史料的全面关注、人的全面了解与人性的共情解读,多维面相的历史人物呈现就成为可能。如杨天石先生用时十个半月,读完蒋介石自1918年至1972年长达53年的全部日记,通过这些“比较真实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内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难知的政坛内幕”的日记,写成《找寻真实的蒋介石》(2)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受“眼光向下”社会史的影响,不少苏区史研习者将其目光转向了革命中的下层民众。如黄琨博士在其论文中涉及到农民就有这样的表述:“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自身的生存性感受,即:只有当革命组织能为他们提供所必需的安全感时,农民才会不断汇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来”(3)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同样,苏区史研习者张宏卿博士也认为:“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革命,可以走进历史的深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特殊性质。也许是另一种真实与别致。”(4)张宏卿:《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一般老百姓在革命年代的主体性呈现,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民间文艺(如戏曲、歌谣等),如陈杰认为:“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的创作和广泛传播,旨在对苏区民众中的不同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形塑,通过革命化改编的歌词对苏区民众进行现代民主、自由、平等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5)陈杰:《歌谣与政治:鄂豫皖苏区革命歌谣研究》,郑州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三是具有整体观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共革命的多维视角。党史学者何友良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中提出“借鉴社会学方法,把这场改革社会、改变人的苏维埃运动,放到近代中国波澜迭兴的社会流变中进行考察”(6)田居俭:《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序》,《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第79-81页。之际,就是在探索一条苏区史(党史)与社会史的融合之道。黄道炫先生在强调“无论是历史具体情境下的革命实践,还是整体范围内的革命运动,终究还是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制约”(7)黄道炫:《革命的张力与历史的弹性:苏区史研究的再解读》,《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24-26页。的时候,则是尝试着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这场近代革命置于整体历史发展脉络之中。
(二)研究视野的拉伸与微观史学的并存
从审美层面来说,距离产生美;而从历史研究来说,也许是距离产生“真”。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也许只有打破中共政权中的1949年界线,对一些史实和历史事件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共党人的组织框架、动员模式抑或是民众的思维方式、行动模式都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点,况且较长时段地聚集某一区域或某一相似的历史事件,学者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其运动轨迹与时代特点,而且还能弥补革命史研究中的较短时间内同质事件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如许金华就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赣南苏区革命背景拉伸到了晚清以来的乡土窥社会变迁,认为清末民初“制度缺失、政府式微的社会是没有应对动荡与危机的机制与可能……,力行转型的必然后果往往是革命的悄然发生,现代化与革命化构成了其当然的一体两面。”(8)许金华:《社会变迁与乡村革命(1860~1928):赣南农民暴动的源起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0页。
这种“长时段”理念不仅体现在具体的选题或行文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作者的思维模式或写作背景,海外一些研究者在这一层面较为擅长,如美国学者凯末尔·希尔在其《中国的农民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方志敏与信江区域的农民运动起源》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冲击之后的赣东北乡土社会,指出民国以来的经济变化而导致的内部凝聚性的流失为1920-1930年代革命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土壤。(9)Kamal Sheel.Peasant Sox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 Movement in the Xinjiang Reg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12.
此外,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中不乏小人物与小故事。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同时关注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这种历史叙事的手法加上文学的审美与散文的情趣,给党史国史一种崭新的视角,给人一种全新的别致甚至惊叹“原来历史可以如此书写!”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10)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一书就有如此之效,体现了强烈的“在场”精神和散文的审美性。她从个体的经验出发,抵达的是家族的命运沧桑、国家与民族的大命题,是对于故土和大地的深情感念,也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度探测。在这部内敛、朴素而沉静的作品中,社会与人生,现实与历史,记忆与遗忘,生活细节与时代风云,经由她简洁而舒徐的叙述,以及悲欣交集的断片人生的组构,呈现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独特面貌。
(三)革命史解释方式的变化与史料的拓展
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应该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1)[英]爱德华·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风俗发展之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国内学者俞思念则指出“文化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留存下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是经过积淀而相对固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现象。”(12)俞思念:《文化与宽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循着这一理路,苏区史革命史对社会文化史的吸纳、借鉴与运用是自然而然之事。只是在解释理路上稍有出入,新文化史所追求的是意义的阐释与因果的分析并存。传统的苏区史、革命史研究中很注重的是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在力求学术性与政治性统一的同时,着重追求的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当新文化史介入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或者说当中共党史出现了“社会文化”的转向之时,革命史、党史研究范式则出现新解释理路。另外,当新文化史作为一个方法论上的意义时,苏区史选题与史料都有很大的拓展。作为符号、话语、象征、仪式等研究对象,极大地扩展了苏区史与革命史的议题,而在成文的过程中,由于解释理路的不同,很多在正统史学研究中很少出现的边缘史料(如图像、音像、习俗、空间、记忆等)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如对苏区年代的美术、漫画、节日、民谣、戏剧等的研究。刘文辉认为,中央苏区红色演剧形象直观地虚拟出军民一体的激情浪漫的“节庆生活”与“狂欢仪式”,把戏剧舞台扩展为孕育和激发苏区军民革命信仰的“政治剧场”。(13)刘文辉:《革命剧场、仪式与生活空间:中央苏区红色戏剧舞台的文化透视》,《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42-47页。耿殿龙则把其兴趣点投向了中央苏区的新诗阅读与政治空间的再造,认为中央苏区新诗营造的这种精神与意象加强了无产阶级政治空间的革命色彩,让苏区空间带有鲜明的中共和苏联的意识形态特点。(14)耿殿龙:《中央苏区新诗与意象性政治空间的构造(1931-1933)》,《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第93-106页。总的说来,苏区史、革命史的“文化转向”大大地拓展了党史研习者的视野、党史资料的范围,同时丰富了中共党史的解释力与吸引力。
二、不足之处:文化的“泛化”与史学的“碎化”
(一)史料不足与过度阐释问题
毋庸讳言,新文化史研究理路的介入对中共党史研习在资料运用上打开了另一扇窗,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的不足,而且新文化史最大的特点与优点之一也是其与传统史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能够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的相关理论对一些历史事件作一个梳理和逻辑的顺延与细腻解读。文化史的魅力所在也是能够“打通”一些隐匿的历史细节,“勾连”出一些看似中断的链节,“还原”一个有趣而有张力的历史场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罗伯特·达恩顿在解读法国文化时走的是“通往历史地图上尚未明确标识的一片精神高地”,旨在展示的是“以人类学家研究异质文化的同一方式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是民族志观察入微时所看到的历史”(15)《拉伯雷笑声中的〈屠猫记〉》,段炼:《读史早知今日事》,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屠猫记》(16)[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吕健忠译:《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所具人类学、民族学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思路正是优秀的党史研习者需要养成和具备的素质。孔飞力的《叫魂》(17)[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则是强劲地体现出了文化史的“勾连”与“解读”,能在一个看似无关宏旨的却又被民众所奉守的民间信仰之处探讨了中国官僚制度如何运作的问题,这就是社会文化史的魅力所在。
但是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相对于传统的“史料即史学”、“七分史料三分表达”的观点,新文化史最受诟病之处也就是其史料的欠缺与过度的解释。求真,是史学的生命力,在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同时我们应该慎重,尽量不要去做一个“当‘证据’不足时也不惧去推测的历史学家。”(18)Daniel Snowman,Natalie Zemon Davis:Danie Snowman Meet the Historian of ‘Martin Grerre’-Today’s History-Interview.History Today,Vol.52,Issue 10(Oct.2002),p18.具体而言,新文化史学者转向研究中共革命史或者是党史革命史学人借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之际,面对“七分史料,三分表达”的传统之际,要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话,史料收集与整理的一定量累积,问题阐释度的一定收缩是其必须注意之处。
(二)微观史学与碎片化问题
一般来说,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但是如果微观史学缺乏了整体视角与意义关照,就很容易流于“碎片化”。于是有人如此形容新文化史的题材:“一些诸如气味、想象、死亡、空间、梦、……等过去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在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家的关注对象。”(19)于沛:《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时至今日,社会文化导向下的史学研究的确有走向“碎片化”的趋势,但其根源就在于史家治史观念的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时代需求与心理导向——从原来希求探讨、解释历史演化到纯粹描述历史事件或人物行为。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微观史学是革命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向运动,也是一定时期内“水到渠成”的学术走向。而从另一层面来言,作为整体叙事、承有教育功效的苏区史、革命史,“碎片化”问题,毫无疑义是其必须直面的。
(三)选题的丰富、有趣与研究的泛化
事实上,新文化史已经大大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实践以及人们关于历史的思维方式,在此情况下,文化史几乎成为新文化史的简称,大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风俗宗祠、空间记忆、节日仪式,从有形到无形,从城市到乡村,从一般老百姓的风俗礼仪到官方政权的政治仪式,基本上无所不包地纳入了新文化史的行文之中。从选题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转向”最容易陷入笼统。
但是苏区史、党史的研究,其中的政治意义、整体与主流等是学者无法绕开的话题。从学术研究特性来说,做党史、革命史研究的既要对总体的框架与脉络有个了解,更要从事一定的调查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工作,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入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各项专门史的建构,有一定的积累之后,自然而然地做一个综合性的研究。从学科的社会功效来看,作为党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苏区史,“选题的现实关照”、“用学术讲政治”、“宜粗不宜细”是其必须考虑与遵守的。
三、走向未来:人性的关注与“政治史”的回归
新文化史研究理路介入苏区史之后,对其产生较大的推动与冲击,新文化史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把所有的人类活动轨迹都纳入其研究对象,而苏区史的“正统性”、“规律性”、“宏大性”的研究则受到其挑战而必须作出应有的回应,而不是简单的拒绝与回避。总的来说,当苏区史与新文化史“相遇”,苏区史或者说中国革命史研究者应该理性地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一)人性与主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永恒主题
在革命年代,我们可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构架与运作模式,某一区域内的社会变迁,参与革命的农民精神状态与日常生活;自然而然也可以研究重要的领袖人物、政治精英与上层路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再也不是简单地叙述领袖人物天才式的文韬武略、政治精英气势磅礴的“左”“右”之争、已有上层路线的进废,而是更为关注个人情感、人际往来以及个体念憬与现实之间的纠葛,以探究大人物在大时代之中的平凡与非凡。回顾历史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并不简单是寻求真相,而是要给后人以反思、启迪与感悟,从而达到趋利避害,总结经验,完善人性。
在“人性”、“个体”、“主体性”等概念层面,新文化史有着传统史学无法企及的深度与“亲度”,而且新文化史学者解释史实的方式是旨在强调人的行为之后的思维逻辑与文化密码,而在党史、革命史的研究中,单一地依靠框架式的“规律化解读”很难达到,在一定程度上也必须借鉴这一理路,才能让革命史、党史的总体进程中涉及到动机、心态、意义等层面的解读更为丰满。
(二)回归与融合——苏区史研究的正道
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时至今天,一定程度的“回归”也成为必然。党史实践的“现场”(这里所指的“现场”具有跨越时空的意蕴,既包括历史情景也直指当下情势)回归,新文化史“碎片化”现象的再反向,传统党史的“整体史观”,这一切使得当今党史界一定程度的“回归”成为必然。中共党史作为一部政党的历史,它既是一部政党的组织行为史,“组织”、“精英人物”的集中呈现是其较为重要的一部分。不过,研究方法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较少独立性的要素,它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而与史家的价值取向、史学观念和题材选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向新文化史取法时,千万不可把方法从一整套复杂的研究范式中分离出来。说到底,新文化史在研究理路上与“新史学”是十分相似的:重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中共党史或者说中国革命史有其一定的独特性,“眼光向下”、“关注底层”与“精英历史”、“上层路线的升废”同样具有其局限性,一定程度的“回归”与“融合”才是正道。
在此,笔者必须要说明的是,“回归”绝对不等于简单地“重新捡起”,“融合”也不是一味地所谓的“平分秋色”,关键还是要看具体的选题、研究现状与学人自身的史学关怀。以苏区史(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政治路线、政党建设相关研究为例,研习者把握主流、看清本质,紧绷用“学术讲政治”这根弦的同时,应该好好思考苏区史(党史)学者的入世情怀与学术追求之间的张力。
(三)助力与提升——作为苏区史研究方法论的“新文化史”
作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启示与意义,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能在以下三个层面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是语言的张力——虚实融通的笔法。文艺作品的合理运用与人事情节的贯通,不但充分地拓展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而且把史学之“实”与文学之“虚”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87岁的资中筠先生2017年7月8日在其音乐小传《有琴一张》(20)资中筠:《有琴一张》,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我经历了很多时代的起伏波动,回顾某一个方面经历的人和事,总也还有‘从一滴水看大海’的意义;我们现在讲历史,总是先想到朝代、政府的更迭等等,但是还有一种历史的角度是‘生活史’。所以我想我学琴生涯中跟音乐有关的人和事也是一个时期的生活史。”
二是文学性格的书写——细腻的史学叙事技巧。凭借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的一些概念,史学分析路径与故事性的叙事技巧让人耳目一新。如与文化学、人类学与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在党史、革命史研究中的运用,格尔茨对于“文化”一词是这样解读的:“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也就是说,深的——描述。”(2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借鉴格尔茨的这种“深描”,史学的叙事更为细腻而有趣,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近代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有了另一种更为“有料而又有趣”的解读。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22)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以民国初年北方某村为背景,充分展示出的“洗练幽默的语言,神韵无穷的人物故事”,也很值得史学研习者学习与借鉴。
三是史学的“温度”——关注重心的下移与个性化史料的运用。日常生活场景的叙事、弱势与下层群体的关注,这一切不但与传统党史研究路径相互补充,而且让研究者与读者有一定的“代入感”与“参与性”。苏区革命年代,曾经留下了大量的回忆录、自述、日记等当事人的文字记录,建国初期也做了一些访谈,这些资料都是较为宝贵的个性化史料,但是要多方印证并与相关的文献相互配合,才可以运用。这些史料的运用,不但大大地拓展了革命史料的解读,而且让革命史的写作与阅读都具有一定的趣味与愉悦。
结语
在苏区史或革命史的研究中大力借鉴新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实现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新文化史表现出的以人为研究中心、对研究对象和读者都体现出一种更加平等的精神,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的方法论意义,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寻求各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的研究方法,等等,这些都值得苏区史、党史研究者的学习与借鉴,从而大力提升党史、苏区史研究成果的热度与亲和力,提升苏区史的学术认同度,达到其“资政育人”之功效。但是,另一方面,新文化史研究内容多样性、零散性和非系统性的特征,以及史料与解读的匹配度问题,也是我们必须注意之处。而对于苏区史的研习者来说,需要具备的是一种追求历史真相的韧性与操守、相互尊重与开放包容的学人品性以及与时俱进的入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