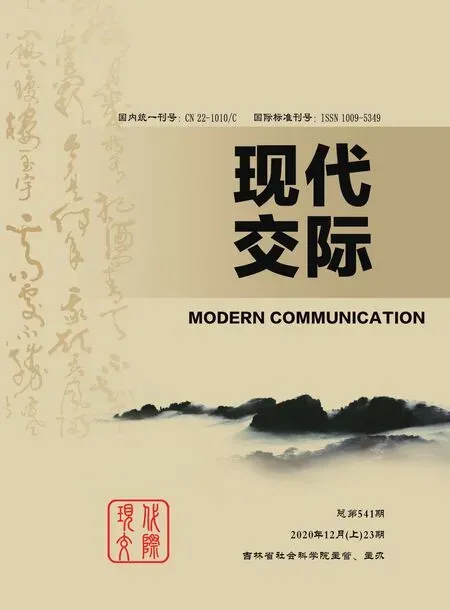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向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于苏格拉底推动了古希腊哲学发生转向,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人本身和社会,开创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1]。就苏格拉底哲学思想转变来看,它并非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有深厚的理论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由于苏格拉底自身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因而本文只得通过对其弟子的记录资料及其他相关著作的分析方式,探讨其哲学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不同时期的苏格拉底哲学思想
苏格拉底被称为政治哲学的创立者,他的哲学思想转变同时推动了古希腊哲学发生转向,即从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2]。探究苏格拉底哲学转向的原因,我们首先要对苏格拉底的前后期思想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苏格拉底所必不可少的考察材料,按时间顺序是: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柏拉图的对话;色诺芬的著作。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上演时苏格拉底45岁,可知阿里斯托芬描述的主要是苏格拉底早期的情况。而柏拉图的对话作品中特别是《理想国》中描述的苏格拉底是不同于阿里斯托芬的。两者对于苏格拉底人物的刻画存在较大差别,但除了个人带有的主观立场外,更多的其实是人物的变化,换句话说,柏拉图和阿里斯托芬分别描述的是不同时期的苏格拉底。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向,阿里斯托芬笔下的是前期研究自然哲学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是转向研究政治哲学的苏格拉底。因而本文从这两类材料出发对比分析,探究苏格拉底哲学转向。
首先我们来分析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是最早记述与苏格拉底言行有关的史料。阿里斯托芬所描述的苏格拉底不关心现实中的人、不关心政治事务,是一个仰望云端,深究宇宙天体的自然哲学家。因而在《云》中描述苏格拉底经常是将自己悬挂在半空中来思考高深的哲学问题,这其实是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嘲弄[3]。他把苏格拉底刻画成一个“探索天上地下一切事物,并使弱的论证变强”的人。他的这一描述指出,当时的苏格拉底研究自然,特别是天空,目光只集中在自然事物、自然规律,以理性追求事物的本质和起源,崇尚绝对的自由,并将人等同于和物质一样的自然物,只遵循自然法则,而不再拥有人类所特有的人性法则。虽然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本身的刻画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和偏颇,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前苏格拉底的哲学研究状态。而且事实上,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自然科学非常原始、朴素。那个时候还没有后来自然科学的实验和理论的工具,他们的研究观察常常带有很大的想象甚至是幻想成分,因而他们的某些具体学说,常常不需要很多学习时间就可以被那些哲学家、科学家等人怀疑、甚至被推翻,对于经常看见的自然现象,还可能被普通的人怀疑,所以多数自然哲学家对“天体”这个遥远的领域抱有很大的兴趣,其原因就如同中国俗话说的“画鬼容易画人难”那样,这个领域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不容易进行实践的检验的,从而可以较长时间保持自己的学说。同时,从《云》中描述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于人的称呼是“朝生暮死的人”,从侧面反映了以前苏格拉底为代表的自然哲学认为人是短暂的、变化的,并不是自然哲学所追求的永恒的东西,因而并不在意对于人、人类社会的研究。而与之相对应的天空、宇宙,始终不变的运转,这一特性让自然哲学认为对宇宙研究才能接近永恒。这也是为什么前苏格拉底所代表的自然哲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天上的原因,同时也揭示自然哲学作为导向将人们的眼光引向集中于自然,而忽略了自我。
柏拉图的《斐多篇》中描述,苏格拉底在临终的那一天说到,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曾非常热衷于研究天体和自然的奥秘,想知道每件事的产生、继续和消亡的原因。苏格拉底原以为自己认识得清清楚楚了,但他却开始怀疑起来,特别是关于人的成长的原因更是如此。苏格拉底还尝试着去学习阿那克萨哥拉的书,想要找到作为万物本原的因果性知识,但最终他的希望落空,作为万物原因的仍然是气、以太、水以及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这里也反映出早期自然哲学的特点是探索宇宙的具体本原。早期自然哲学对于宇宙本原的探索主要以“观察”为手段,带有想象、幻想的成分。当科学式的逻辑推演方式出现,带有幻想成分的本原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就发生了矛盾。苏格拉底按照早期自然哲学的路线探求自然的因果关系,他无法得到令他满意的答案,也因而引起了苏格拉底思想的转变。因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政治有所研究。《理想国》中描述的苏格拉底虽然关注政治生活,研究城邦、伦理等问题,但却不实际参与政治生活。原因可能在于对哲学家而言“过哲学生活是第一等善,过政治生活是第二等善”,研究的转向并不影响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对自然哲学的追求。因而我们能更加深入地理解《理想国》第七卷的洞穴喻,哲人王离开洞穴后,见到了真实世界,他为什么还愿意回到洞穴。哲人王明白他无法将所有人带出洞穴,洞穴的存在始终是自然的一部分,研究自然哲学必然不能少了这一部分。站在政治哲学的角度,人作为研究对象,洞穴外没有人,哲人王也必然是要回到洞穴的[4]。
二、苏格拉底哲学转向的原因
从与苏格拉底相关的材料分析得出,苏格拉底对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断然转变研究方向,必定不会是对原有研究的放弃。经联系相关材料可以得出,苏格拉底的转向一是将政治哲学作为一条研究自然哲学的新路径,从整体退到部分,再从部分重新出发去观察研究整体;二是对自然哲学和政治的冲突关系的思考。
1.将政治哲学作为研究自然哲学的新路径
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是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自然哲学是人类思考与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界而形成的哲学思想,虽然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但自然哲学关注研究的是人的自然属性,自然机能,忽视了人作为人其本身最大的特性——社会性。自然哲学的这一导向,就使得哲学研究与现实间产生诸多疑问无法解决,或者哲学给出的答案之间相互矛盾,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人开始思考自然哲学研究的片面性[5]。人的社会性交往产生城邦国家,产生规则,亦即产生政治生活。因而苏格拉底转向研究政治哲学,是以其作为一种研究自然哲学的新路径。
苏格拉底对人间事物的研究,就在于对那些事物提出“是什么”的问题,比如“正义是什么?”或者“城邦是什么?”“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还提出人间事物本身是什么或者说有关人间事务的理论是什么的问题[6]。然而,研究问题需要运用方法论,典型的对比分析条件表明,不能够把握人间事物与自然事物的实质差别,也就无法认识到人间事物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要对自然事物有深刻的理解认识。因此可以说,苏格拉底前期对于自然事物完备的研究,为其转向人间事物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浅显粗略阅读《理想国》的人的大多观点看来,苏格拉底对自然不以为意,因而从自然的研究中抽转身来,把他的研究集中于人事。但实际与表面现象相反,苏格拉底的转向是苏格拉底尝试了解宇宙一切事物的新路径,并非是苏格拉底漠视自然事物。而且,鼓励研究人间事物本就该是新路径的应有之意。
苏格拉底带来的转变,用我们今天通俗的话叫作回到“常识”或回到“常识世界”。苏格拉底的“是什么”的问题所指向的是一物的形状、形式、颜色等,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可以被称之为“表面”的东西。《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将世界分成了可见世界和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在可见世界之上的,可见世界是基础。可见世界中的东西有些是不需要求助于理性思考的,因为感官就能胜任判断[7]。所以对于可见世界的认识,人凭借基本感官,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便可进行。当然还是有一些是需要求助于理性的,因为感官对它们不能做出可靠的判断。但我们都知道研究一个事物的过程是由浅到深、由低到高,苏格拉底在哲学转向后首先将研究对准可见世界,这是符合逻辑,也是必然的。正如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所说:“苏格拉底的出发点,不是在其本身为最初或就其本性为第一位的东西,而是对我们来说最初的东西,进入我们视野的最初的东西,也即现象。”[8]然而,我们对于事物外在的认识、它们的特征,最初的呈现并非我们所看到的表象,而是从人们社会交往中所接收到的关于它们的言说或者有关它们的意见中得到的。于是,苏格拉底通过人们对于事物的评价意见来认识事物的本性。苏格拉底表达出来的是,每一个意见都是每个人对于某一事物的某种感知,一个个的意见的堆砌构成对宇宙的意见,然而无视这些意见,无异于是舍弃掉对未知宇宙探索为之重要的渠道,或者是舍弃掉了我们力所能及的最为重要的真理的足迹。
2.自然哲学和政治的冲突关系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整体观念及时代的发展看来,自然哲学的研究对于政治、国家更多的是有利,而非有害。但在苏格拉底时代,究其本质追求来看,自然哲学的研究对政治具有有害性。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政治和自然哲学冲突的展现[9]。哲学在本质上是爱智之学,因而哲学展现出对智慧的狂热的、无法无天的追求,这就必须求自身有绝对的自由,要求不受任何法律宗教、道德习俗的束缚。自然哲学追求本质、追求自然法则,用理性来看待万事万物;而政治社会本身却要求遵循传统,但很多法则确是与理性相悖的,以此看来,自然哲学与政治社会是不相容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力求达到认识真理,自然哲学力求在社会中实现“真理”取代“意见”,以遵循宇宙本身的自然法则,但这些“意见”也即所谓的法律宗教、道德习俗正是政治社会存在的表现、产物;如果这些“意见”被“真理”所取代,就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的瓦解。政治社会同时又反作用于自然哲学的研究,政治社会瓦解自然不利于自然哲学的发展,甚至会让自然哲学走上绝路。因而自然哲学在探究真理之际,一定不能忘记自己的政治基础。哲学和政治的完全分离对于两者而言都是危险的。政治脱离哲学就会陷入非理性的狂热和愚昧中,一切政治选择和决断都将丧失理性的标准和尺度。另一方面哲学脱离政治则容易陷入玄学形而上学[10]。苏格拉底之所以转向研究政治哲学,就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到自然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冲突关系。苏格拉底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的转向,是将目光从“天上”转向了“地面”,也即是自然哲学下降到政治哲学,其必要性就在于防止自然哲学的走火入魔[11]。苏格拉底将自然哲学转向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改变了自然哲学的性质,而是改变了自然哲学的表达方式。
三、结语
苏格拉底哲学具有伟大的哲学变革意义和广泛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促使古希腊哲学、科学和文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深刻影响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和文明,而且在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还将继续着它的影响,因而对其的思辨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具意义的。同时我们应当清晰认识到哲学的政治转向不是要终结哲学,而是要摆正哲学的位置,从而使哲学更好地成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