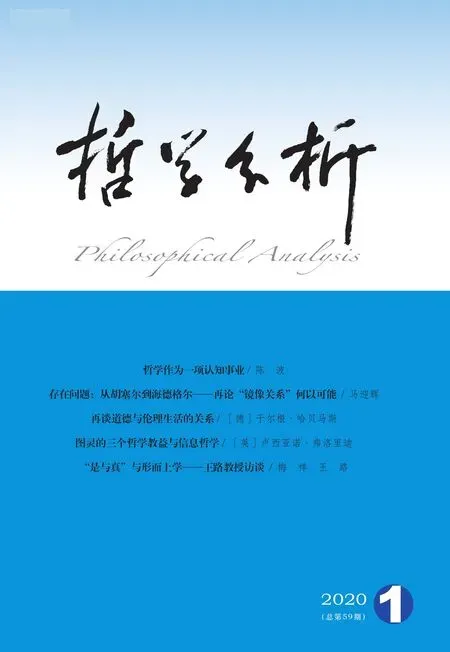图灵的三个哲学教益与信息哲学①
[英]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文
姜晨程/译
一、引 言
当一个人研究图灵的哲学遗产时,可能存在两种危险。一种危险是将其归纳为他最著名的测试②A. M.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Vol. 59, 1950, pp. 433—460.,这样做的好处是清晰。任何人都能在讨论中将它辨识出来,并找到它在相关争论或人工智能哲学中的位置。另一种危险是将其削弱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叙事,将图灵的观点视为我们今天所做和所知的任何事物的来源。这样做的好处是承认了这个天才的伟 大。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将不太可能识别出,图灵的哪些概念贡献已经在我们当代的哲学讨论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哪些又会指导它们的未来发展。为了避免这两种风险,在下文中我会专注于三个特定的哲学教益,考虑到信息哲学的出现和其后续的发展,这三个教益看来是特别重要的。我将提供的不是一种文献学或博学(scholarly)的分析,而是一种极简主义的、解释学的实践。图灵非凡天才的一部分,就是不同的解释者会从他的智识遗产(intellectual legacy)中得到更多的和不同的教 益。
我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三个哲学教益是:图灵有关抽象层次的方法(levels of abstraction,LoA)的工作,是如何教导我们合适地提出一个哲学问题的;作为对图灵工作的推论,什么哲学问题在今天是最紧迫的;以及,图灵对塑造我们的新的哲学人类学的影响,我将这种新的哲学人类学称为第四次革命;最后,我会将这些教益联系到信息哲学的发展 中。
二、教益一:锚定(fixing)抽象层次/如何问哲学问题
想象如下场景。你询问一个物品的价格,如一辆二手车,然后收到如下回复:5000。这个问题牵涉一个变量,即这辆车的价格x,但当你收到了一个精确的数值x时,这里仍然漏掉了一些东西。你仍然不知道价格,因为你不知道变量x的类型——它是英镑、美元、欧元或是别的什么?当然,语境通常有所帮助。如果你在英国问一个汽车商,那么你的问题就应该被理解为按英镑计算的价格,回复也是如此。你可能认为这不过是鸡毛蒜皮,格赖斯①即保罗·格赖斯(Herbert Paul Grice),英国著名语言哲学家。——译者的会话规则(conversational rules)显然适用。这确实是鸡毛蒜皮,那些规则也的确适用。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容易被遗忘的重要假设。在1999年11月,NASA损失了价值1.25亿美元的火星气候轨道探测器(Mars Climate Orbiter, MCO),只是因为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工程团队使用了英国测量单位,而其代理商的团队却在宇宙飞船的一个关键操作上使用了米制计量法。从而导致MCO在火星坠毁了。②《火星气候轨道探测器事故调查委员会第一阶段报告(新闻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参见ftp://ftp.hq.nasa.gov/pub/pao/reports/1999/MCO_report.pdf。总是假设语境能消除你所使用的变量类型的歧义,无异于为昂贵的错误铺路。不过这一切和图灵有什么关系呢?事实证明:有,而且很大。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介绍一个略微抽象些的模型。③对 此 的一个简 介,参见L. Floridi, Inform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一个完整的哲学分析,参见L.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我们可以将这类事实信息视为问题+回答的复合(compound),它由上述二手车价格的例子所描述。如果允许一些理论上的简化,问题可以被简化为布尔型(Boolean)的,即由“是”或“否”来回答。于是在最初版本的例子中,二手车的价格变成了:这辆车的价格是5000吗?回复:是的。你能立即看到出错的不是回答,而是问题:它不包含对目前处理的变量类型的指示。正确的信息当然应该是:这辆车的价格是5000£吗?回复:是的。这里刚刚介绍了一种正确的抽象层次,或者说LoA,它由英镑的符号£而不是由欧元的符号€所表征。而图灵是第一个理解这一做法的至关重要性的人,即表达出一个合理问题(sensible questions)所在的LoA。它可能看上去令人惊讶地明显,但上述第二个关于MCO的例子,展示了忘记隐含的LoA是多么的容易和危险。清楚自己的抽象层次的重要性就像地球是圆的一样明显,而美洲正是由于后者才被发现。现在,我们用了图灵的天才智慧才将它揭示出来。当然,图灵的贡献不是介绍了“有类型的变量”(typed variables)这个概念,也不是确立了对参照系的需要。这些观念在他的时代就早已很常见了。他的教益是第一次澄清了哲学的和概念的问题只能在锚定的LoA中才能得到有意义的回答。这是他那个著名测试的最伟大和持久的贡献之一。远比那些对“机器什么时候会通过这个测试”,还有“如果机器的确通过它了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的错误预言重要。①L. Floridi, M. Taddeo & M. Turilli, “Turing’s Imitation Game: Still a Challenge for Any Machine and Some Judges”, Minds, Mach. 19, 2009, pp. 145—150.有一件事时常会被遗忘,即图灵拒绝哪怕是尝试性地给“机器能思考吗?”(can a machine think?)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回答,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过于无意义以致不值得被讨论”。用我们的简单例子,它就像完全在数字上问这辆二手车的价格,并坚持不用任何货币来表征它。这毫无意义。同样,图灵反对包含了诸如“机器”和“思考”这样的模糊概念的问题。换句话说,它缺乏一个清晰的抽象层次。因此他建议将其替换成模拟游戏(the Imitation Game),后者是更易管理的和更少苛求的,因为它锚定了一个基于规则的,易于执行和控制的情境。②J. Moor, The Turing Test: The Elusive Standar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通过这样做,他制订了一个LoA——他为这个游戏选择的“货币”是人类智能,但这也可以是别的,如从动物智能到人类创造性,就像许多其他版本的图灵模拟游戏的所展示的那样——并且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被概括为:“在由模拟游戏所表征的抽象层次上,一个人可以断定一个机器正在思考吗?”经过了半个世纪,哲学依然在学习如此重要的一课。③关于抽象层次的方法的使用,参见L.Floridi, Informatio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和L. Floridi, “The Method of Levels of Abstraction”, Minds, Mach 18, 2008, pp. 303—329。关于图灵在这个方法的发展上的关键性角色,参见L. Floridi, “Turing Test and the Method of Levels of Abstraction”, in Alan Turing: His Work and Impact, S. B. Cooper & J. van Leeuwen eds,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Elsevier (in press)。第二个教益将会需要一个更长的前提。
三、教益二:专注于最重要的问题/问哪个哲学问题
在2010年4月23日,比尔·盖茨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麻省理工学院作了一个演讲,其中他问道:“最聪明的头脑们在致力于最重要的问题吗?”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指的是“改善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提升教育、健康、营养”。不过,这个清单可能还应该包括促进和平互动,人权、环境、生活标准,等等,并且这些仅仅只是开始。①L. Floridi, “Information Ethics”, in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Ethics, L. Floridi(ed.), Ch. 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无疑,最聪明的哲学头脑们不应成为例外,而是应该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到这些紧迫的挑战上去。当然,有的人可能会停止哲学思索,并开始为这个混乱的世界做些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关闭我们的哲学系,绝不用哲学来腐化我们最聪明的年轻人们。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案有点自我挫败(self-defeat)的意味。它就像因为热气球下降得太快了,而决定烧掉我们在其中旅行的柳条筐。哲学是那种你会在一个好的世界中想要保留下来的东西,而不是你会在一个坏的世界中想要摆脱的东西。有苏格拉底的雅典是一个更好的雅典。因此这里必须有一条不同的前进道路。事实上哲学可以变得极为有帮助,因为正是被理解为概念之设计的哲学,锻造出了新的概念、理论、观点以及更一般的智识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这种智识框架可以被用于理解和处理那些对我们最具紧迫性和挑战性的根本问题。在最聪明的头脑们的团队合作中,哲学工作者可以贡献洞察和远见、分析和综合、启发式思路和解决方案,它们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处理“最重要的问题”。每一个小的努力都能够在对抗愚蠢、蒙昧主义、褊狭、狂热和所有类型的原教旨主义、盲从、偏见和纯粹的无知的更大战场上帮助我们。如果这听起来像是自利的(self-serving),那就想想向前跳跃的距离越长,助跑的距离也就相应越长。或者,用一个不同的比喻,哲学照顾根部,以便植物的其他部分可以更为健康地成长。假如我们接受了所有这些作为一个合理的预设,那么哪些概念、理论、观点以及更一般的智识框架是哲学家们应该在现在或在可见的将来进行设计,以便能够及时而有益地作出他们的贡献?哪些哲学问题又是他们应该处理的?如果这个回答中缺少了图灵的遗产,那将会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它所位于的概念路线穿过了如此多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全球性的信息社会,事实上我们面临的任何重要挑战都与信息和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相关,并由原因、结果、解决方案、科学研究、真实的改进等术语所描述,因此概念资源对于理解这些挑战是必要的,甚或是处理它们所必需的资产,就像比尔·盖茨的例子所清晰的展示的那样。显然,信息资源、技术以及科学并不是万能药,但它们在我们与这么多困难的战斗中是一种重要而强大的武器。因而,从图灵那里获得的第二个教益是关于最聪明的哲学头脑们应该处理的问题的类型。我们生活在每个最重要的问题背后都躺着一台图灵机的信息圈(infosphere)。这是一个我们开始重新概念化人类自身的新世界,这也是我们从图灵那里获得的第三个教益,我将在第四节中讨论 它。
四、教益三:发展一种新的哲学人类学/从哪个视角来切入哲学问题
极度简化地说,科学有两个改变我们的理解的基础方式。一个可以被称为外向的(extrovert),或者说关于世界的,而另一个可以被称为内向的(introvert),或者关于我们自身的。三次科学革命已经同时通过外向和内向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改变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与其互动的方式的过程中,它们也修改了我们关于我们是谁和希望成为谁的概念。在哥白尼之后,日心宇宙学取代了地心说,也因此将人类从宇宙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达尔文展示了所有的生命都源于共同的祖先,并通过自然选择随着时间进化,因而将人类从生物王国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接着是弗洛伊德,我们今天已经承认了心智也包含潜意识,并且受制于对压抑的防御机制,并因此也将人类从纯粹理性的中心的位置上拉了下来,这个位置至少从笛卡尔开始就被假定为是无可争议的。即使像波普尔和我这样的,会对遵循弗洛伊德并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像天文学或进化论一样严格的科学事业表现出不情愿的读者,现在也会愿意承认当代神经科学是对这一革命性角色的很有希望的候选者。不管怎样,结果就是现今我们承认我们不再是固定的位于宇宙的中心(哥白尼革命),我们不再是不自然地与动物王国里的其他生命不同的(达尔文革命),而且我们也远不是那种对自己完全透明的笛卡尔式的心智(弗洛伊德或神经科学革 命)。
对于这个经典图景,人们往往会质疑它是否有存在价值。毕竟,弗洛伊德①S. Freud, A Difficulty in the Path of Psycho-analysis, in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he Standard Edition, Vol. XVII, J. Strachey (ed.), London, UK: Hogarth Press,1917, pp. 135—144.自己就是第一个将这三次革命解释为重新评估人类本质这一单一过程的一部分的人。②F. Weinert, Copernicus, Darwin, and Freud: Revolution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Oxford, UK:Blackwell, 2009.他的解释学策略被公认是自利的,但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观点。在计算机革命之后,当我们现在感知到一些非常重要和意义深远的事已经发生于人类生活之中,我将要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论证我们的直觉又一次是敏锐的,因为在对人类的本质及其在宇宙中的角色进行脱位(dislocation)和重新评估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革命。这个进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持续进行着,而图灵无疑是这次革命的代表性人物。计算机科学及其不断发行的技术应用已经在其内部和外部都产生了影响。它们不仅提供了对自然以及人工实体的史无前例的认知以及工程力量,还已经通过这一过程使我们对“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相互联系”以及从而“我们如何理解我们自身”有了新的认识。今天,我们正慢慢接受我们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一观念,我们更像是以信息方式具身的有机体(informationally embodied organisms,简称infrogs,即信息体),在一个信息化环境(也就是信息圈)中相互连接和嵌入,我们跟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相似的自然以及人工能动者(agent)共享这个信息圈。图灵已经像哥白尼、达尔文以及弗洛伊德一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哲学人类学。这已经对在图灵之后做哲学意味着什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上就是我想引起读者关注的最后一个教 益。
五、教益的总结:建立一种新的信息哲学/如何理解当今世界
什么能赋予人类理解、尊重并且负责任地改善当代世界的能力,并从而在解决“最重要的问题”上有所助益?答案看起来很简单——一种新的信息哲学。在我们日常的和技术的概念中,信息是当前最重要的、被广泛地使用的却最少被理解的概念之一。最聪明的哲学头脑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它,以便设计我们时代的,并为这个时代而合适地概念化了的哲学。不过,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在哲学史上非常必要的发展来介绍也只是一个粗糙的权宜之计。现在,让我来概述一个将其与图灵相联系的更久远的脉络。
的确,将一种新的信息哲学的基础甚或其创建归因于图灵,似乎延伸得太过分了。毕竟图灵从未专注于信息这个概念本身,也从未专注于被理解为信息流动或传输的通讯问题(尽管他和香农事实上了解彼此的工作)。因此图灵的《图灵精义:计算、逻辑、哲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的重要著作,以及恩尼格玛的秘密》①A. M. Turing, The Essential Turing: Seminal Writings in Computing, Logic, Philosoph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rtificial Life, Plus the Secrets of Enigma,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2004.甚至没有包含“信息”这个条目,而龙贝格②D. G. Luenberger, Information Sc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写的另一本类似的书也仅仅在说到布莱切利园③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位于英国,它曾经是二战期间英国政府进行密码解读的主要场所,轴心国的密码与密码文件,如恩尼格玛密码机等,一般都会送到那里进行解码。——译者时提到了图灵一次。然而,我将论证,没有图灵和他在信息处理上的开创性的工作及其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影响,以及上面已经勾勒出的三条教益的轮廓,当代对信息哲学的关心将会难以解释。图灵、香农和维纳共享了唤起我们对信息世界及其动力学的哲学关注的功绩。没有他的三个教益,就没有信息哲学。今天我们更倾向于把电脑作为通讯机而不是强大的计算机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了图灵的工作对我们的世界造成了多么深的影 响。
六、结 论
新的哲学观念的发展和经济创新有相似之处。因为,当熊彼得用“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来说明经济创新,他也许同样在说智识的发展。哲学是通过持续地重建自身来获得繁荣的。现在,它的创新引力(pulling force)是由信息、计算和通讯现象——以及相应的科学、技术、新环境、社会生活,包括它们带来的关于存在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教育的问题——的世界所表征的。这是一个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图灵的工作和智识遗产的新情境。在前文中,我已经概括了我们应该从图灵那里获得的三个哲学教益。我认为信息哲学——在它实现图灵遗产的范围内——可以将自身呈现为一个创新范式,这个范式打开了一个非常丰富、有助益并且适时的概念研究领域。从学术上说,信息哲学是一个哲学领域,它涉及对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则的批判性调查,这包括它的动力学、利用以及科学,还包括对信息理论和计算方法论在哲学问题上的详细阐释和应用。更具体地说,信息哲学致力于给出一个明确的、清晰的、精密的对于经典的“是什么”(ti esti)问题,即“信息是什么?”的阐释,而这个问题是一个新领域的最清晰的标志。但和其他领域问题(field-question)一样,这也仅能供一个研究领域的划界之用,而不能详细确定它的特定问题的位置。信息哲学力求通过提供创新的方法论来处理在当代视角下最重要的那些问题,扩展我们哲学理解的边界。它依赖于图灵的这一直觉——以抽象方法来确保问题在正确的层次上被处理,是至关重要 的。
科学革命使得十七世纪的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可知对象的本性上(因此也从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上)转移到了它和认识主体之间的认识关系中。信息社会的后续发展和信息圈——也就是如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在其中度过他们的生活的环境——的出现,已经将当代哲学的批判性反思优先引向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由组织知识的记忆和语言,以及信息圈赖以管理的工具——哲学也因此从认识论转到语言哲学和逻辑学——所表征,同时也优先引向了它们所特有的结构和实在的本质,还有信息本身以及它的动力学、通讯、流动和处理。信息因此成为了一个和存在(Being)、知识、生活、智能、意义、善和恶——还有所有与它们相互依赖的关键概念——一样重要而根本的概念,而且同等地值得自发的研究。但这也是一个相较更为贫乏的概念,因为其他概念在没被明确定义时,也能被表达和相互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信息哲学可以解释和指导对我们的智识环境的有目的的建设,并为当代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处理方案。信息哲学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与图灵的智识遗产、与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以及与经典哲学问题打交道。对此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要感谢图灵的是,理解和处理宇宙的基本知识的培根—伽利略工程已经开始在计算机的和信息的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实现方法,它对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对我们概念化实在的方式,和在对其中的我们自身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信息的叙述拥有一种本体上的力量,而不是一些迷人的闲谈、神学的逻各斯(logos)或者神秘的规则,而是内在的,就像可以描述、修改和实现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建筑工具。从这个角度,信息哲学可以被表征为对信息活动——自然的和人工的,物理的和人类学的——的研究,这些活动使对实在的建设、概念化、语义化和道德上的管理成为可能。信息哲学使人类能够理解世界,并且负责任地建设它。它有望成为最令人兴奋和最有益于我们时代的哲学研究领域。它的发展将会成为在哲学中继承图灵的工作和尊敬他的遗产的合适方 法。